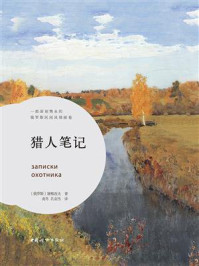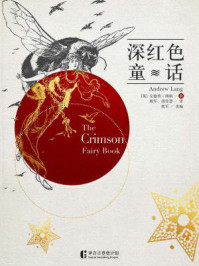深挚的情感犹如伟大的作品,总比有意表达出来的蕴含更多。心灵的某种活动或者反感所具有的恒定性,也在所为或所思的习惯中再现,还延续到心灵本主都不知晓的后果中。伟大的情感游荡时,总携带着自己的宇宙,不管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宇宙。伟大的情感以其激情,照亮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并在其中重获自己的氛围。无论嫉妒、野心、自私还是慷慨,都有自己的一洞天地。所谓一洞天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和一种精神姿态。已经专一化了的情感,既然有真实的流露,那么初发的激情就会流露出更多的真实:初发的激情宛若美感或荒诞引起我们的反应,都同样未确定,都同样模糊而又同样真切,都同样遥远而又同样“近眼前”。
无论哪个人,走到哪条街的拐角,荒诞感都会扑面而来。原本原样,赤裸裸地实在败兴,倒是明亮,却没有光芒,又难以捕捉。然而,这种难题本身就发人深思。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情况大概确实如此:他身上总有什么我们把握不住的东西。然而,通常我认识这些人,我通过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行为总和,通过他们所经之处给生活留下的后果,就能认出他们来。同样,所有这些非理性的情感,想分析都无从下手,我却通常能够确定,通常也能品评,也就是说,将这些情感的全部后果归拢到智力范畴,抓住并记录其各种各样的面孔,再勾画出情感的天地来。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即使我看了他上百场演出,也未必更好地了解他本人。然而,如果我把他扮演过的人物归拢起来,如果清点到一百个人物时,我说少许了解他了,大家就会感到我这话有几分道理。只因这种表面上不合理的事物,也是一种简单的寓言,有一定的教益,能让人了解,既可以通过他演的戏,也可以通过他的真情冲动来界定一个人。同样道理,一种低调、一些心中难容的情感,也会因其激发起来的行为,因其假定的精神姿态,总能部分地暴露出来。大家会明显感到,我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不过,大家也会同样感到,这是分析方法,而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也包含着形而上学,会不知不觉暴露出有时坚称还不甚了了的结论。一本书也如此,结果在开篇就有所表露——这种盘根错节无法避免。这里界定的方法宣扬这种感觉,不可能完全认识真相。唯有表象可以量化,氛围可以感知。
这种难以捕捉的荒诞感,我们也许能在迥异的但是友爱的世界中不期而遇,那便是智力的、生活艺术的,或者纯艺术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有了荒诞的氛围结局,就是荒诞世界和这种精神姿态,须知精神姿态是用自己特有的光照亮世界,并且能从自身认出这张得天独厚的冷酷面孔,以便使之大放光彩。
但凡伟大的行动,但凡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者一家餐馆的小门厅。荒诞也如此。荒诞世界还甚于别的事物,更能从这种卑微的出身赢得高贵的身份。在某些场合,一个人用“没什么”回答关于他的思想本质的提问,也许就是一种敷衍。被对方爱的人都心知肚明。话又说回来,假如这一回答是真诚的,反映出这种特殊的心态,即空虚富有深意,日常行为的链条断了,心灵无奈地寻找重新接起来的一环,那么,这种回答就可视为荒诞的第一个征象了。
有时候,布景会坍塌。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干四小时,吃饭,乘电车,再干四小时,吃饭,睡觉,而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全是同样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里,这条路走得相当顺畅。不过有一天,突然萌生“为什么”的疑问,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开始了”,这很关键。一种机械生活的行止,到头来就是厌倦,但是厌倦也同时开启了意识的活动。厌倦唤醒了意识,并且挑起了一系列状况。一系列状况,就是不自觉地回顾生活链条,换言之,这是最终的觉醒。随着时间的推移,觉醒到一定程度,便有了后果:自杀或者复萌故态。厌倦本身,有其令人作呕的成分。可是在这里,我应得出结论:厌倦是有益的。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只有通过意识才有价值。这些见解毫不独特,但是显而易见:用在一时就足够了,正好可以粗略地辨识荒诞的根源。简单的“思虑”是一切的初始。
同样,日复一日,生活毫无光彩,同时裹挟着我们。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刻,应当裹挟时间了。我们生活在未来:“明天”,“以后”,“等你混出个样儿来”,“等你长大就会明白”,这些不着调的话令人赞叹,因为最终,就关系到死亡了。总归有那么一天,人觉察到,或者,说他已三十岁了。他这样也是强调年轻,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根据时间给自己定位了。他在时间里就位了。他承认自己处于人生弧线的某一时间点上,从而表明他应当走完全部路程。他从属于时间了,不免心生恐惧,确认了时间是他的死敌。明天,他盼望明天,而他全身心本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
 。
。
再低一个层次,就是陌生性了:发现世界“厚实”,看出一块石头陌生到何等程度,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大自然显示何等强度,一处风景就可以否定我们。自然美的深处,无不潜伏着非人的东西:就说这些山峦、天空的晴和,这些树木曼妙的图景,转瞬间就丧失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的意义,从此就跟失去的天堂一样遥不可及了。世界原初的敌意,穿越了数千年,又追上我们了。这个世界,一时间我们看不懂了,只因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非是我们事先赋予它的各种形象和图景,只因从此以后,我们再无余力使用这种伎俩了。世界又恢复原样,也就脱离我们的掌握了。这些由习惯遮饰的布景,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离我们远去了。同样,本来一位女子熟悉的面孔,已经爱了数月或数年的一位女子,有些日子忽然觉得是个陌生人了,甚至可以说,我们也许渴望使我们突然如此孤独的东西。不过,时间还没有到。唯一可以肯定的事:世界的这种厚实和这种陌生性,正是荒诞。
人也同样分泌出非人性的东西。在清醒的某些时刻,他们行为机械的样子,毫无意义的忸怩作态,能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至极。一个男人在玻璃电话亭里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却看得见他那毫无意义的手势,让人不由得发出疑问,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产生的这种嫌恶,面对我们本身形象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还有,如同一位作者所称我们时代的这种“恶心”
 ,这些也都是荒诞。同样,在某些瞬间,陌生人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再熟悉不过的兄弟,却又令人不安,在我们的相册里重新见面,这还是荒诞。终于该谈谈死亡了,谈谈我们对死亡的感受。这个话题已经说尽,谨防再唠叨些悲天悯人的话。人人都活在世上,却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对此世人怎么表示惊讶也不过分。还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死亡的经验。就本义而言,只有生活过来的,并且意识到了,才算是经验过了。这里,仅仅探讨一下,是否可能谈谈别人死亡的经验
,这些也都是荒诞。同样,在某些瞬间,陌生人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再熟悉不过的兄弟,却又令人不安,在我们的相册里重新见面,这还是荒诞。终于该谈谈死亡了,谈谈我们对死亡的感受。这个话题已经说尽,谨防再唠叨些悲天悯人的话。人人都活在世上,却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对此世人怎么表示惊讶也不过分。还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死亡的经验。就本义而言,只有生活过来的,并且意识到了,才算是经验过了。这里,仅仅探讨一下,是否可能谈谈别人死亡的经验
 。 这是一种代用品,精神上的一种看法,我们自己也从来不会特别信服。这种约定俗成的伤悲,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其实,恐惧来自死亡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畏惧,那是因为时间进行了演示,随后才是答案。关于灵魂的所有漂亮的演说,在这里,至少此刻要接受其相反观点的粗略验算。灵魂从这打耳光再也留不下痕迹的僵体中消失了。这种偶发事件最终的基本面,就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在这种命运的死亡的光照下,百般无用显现了。任何道德,任何成果,面对支配我们生活状况的血腥的数学,都不能先验地得到证实。
。 这是一种代用品,精神上的一种看法,我们自己也从来不会特别信服。这种约定俗成的伤悲,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其实,恐惧来自死亡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畏惧,那是因为时间进行了演示,随后才是答案。关于灵魂的所有漂亮的演说,在这里,至少此刻要接受其相反观点的粗略验算。灵魂从这打耳光再也留不下痕迹的僵体中消失了。这种偶发事件最终的基本面,就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在这种命运的死亡的光照下,百般无用显现了。任何道德,任何成果,面对支配我们生活状况的血腥的数学,都不能先验地得到证实。
重复一遍,这一切都已经一说再说了。我在这里只是简括地归类,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在所有文学作品和所有哲学作品之中,也充斥于每日的谈话,没有必要再重新制造出来。但是,必须首先确认这些明显的见解,才可能接着探讨首要的问题。我所感兴趣的,再重复一遍,主要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发现荒诞的后果。如果确认了这些事实,那么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什么也不避讳能走到什么地步呢?就该情愿一死,还是不顾一切抱着希望不放呢?在心智的层面上,也必须预先同样快速地清点一下。
思想头一个活动,就是辨识真伪。然而,思想一旦反思,那么首先发现的却是一种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极力说服人是徒劳的。多少世纪以来,论述这个问题,谁也比不上亚里士多德这么明晰,这么精彩:
这些观点,后果备受嘲笑,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肯定一切皆真,我们就肯定了对立观点肯定的真理,从而也就肯定我们自己论点的谬误(因为对立观点的认证不容许我们的论点是真的)。如果说一切皆伪,这种论断同样是谬误。如果声称,只有同我们对立的论断是错的,或是唯独我们的论断不是错的,那么就不得不接受无限数量或真或伪的判断了。因为,一个人提出一个正确的论断,那么同时也就宣称这个论断是真理,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这仅仅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个,进行反思的思想深陷其中,迷失在令人眩晕的旋涡里。这些悖论简单明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管搞什么文字游戏、逻辑杂耍,理解——首先就是整合。精神深层次的渴望,即便在演化最快的活动中,也要会合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就是要求认同,渴求明确。对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压缩为人性,打上人的烙印。猫的世界就不是食蚁兽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同样,精神力图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压缩成为思想术语时,才能心满意足。如果能看出世界也同样,会爱和感到痛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如果思想在外界现象的哈哈镜里,发现了永恒关系,既能把现象概括起来,自身又能概括为唯一的原则,那就可以侈谈精神的幸福了,而这些幸福者的神话,也不过是一件可笑的赝品。这种对一体化的眷恋,这种对绝对的渴求,标明了人类悲剧的基本演变。即使这种眷恋成为事实,也并不意味它必然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如果我们跨越了横亘在渴望与获取之间的深渊,同巴门尼德
这仅仅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个,进行反思的思想深陷其中,迷失在令人眩晕的旋涡里。这些悖论简单明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管搞什么文字游戏、逻辑杂耍,理解——首先就是整合。精神深层次的渴望,即便在演化最快的活动中,也要会合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就是要求认同,渴求明确。对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压缩为人性,打上人的烙印。猫的世界就不是食蚁兽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同样,精神力图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压缩成为思想术语时,才能心满意足。如果能看出世界也同样,会爱和感到痛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如果思想在外界现象的哈哈镜里,发现了永恒关系,既能把现象概括起来,自身又能概括为唯一的原则,那就可以侈谈精神的幸福了,而这些幸福者的神话,也不过是一件可笑的赝品。这种对一体化的眷恋,这种对绝对的渴求,标明了人类悲剧的基本演变。即使这种眷恋成为事实,也并不意味它必然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如果我们跨越了横亘在渴望与获取之间的深渊,同巴门尼德
 一起肯定单一为现实(不管哪种单一),那么我们就跌进精神的可笑矛盾中:这种精神肯定完全的一致,并以其肯定本身来证明它自己与众不同,证明它声称解决的分歧。这是另一种恶性循环,足能扼杀我们的希望。
一起肯定单一为现实(不管哪种单一),那么我们就跌进精神的可笑矛盾中:这种精神肯定完全的一致,并以其肯定本身来证明它自己与众不同,证明它声称解决的分歧。这是另一种恶性循环,足能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些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再次重复,它们的趣味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可能引出的后果中。我了解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它告诉我人必有一死。可以历数从中得出极端结论的那些智者。要知道,我们想象中了解的和实际了解之间的恒定差距,实际的认同和假装的无知之间的恒定差距,在本论著中必须视为永久的参照。至于假装的无知,正是让我们抱着一些观念活在世上,而这些观念,我们真若亲身体验一番,那就势必打乱我们的全部生活。面对精神的这种纠缠不清的矛盾,我们恰恰可以完全把握一点:将我们同我们的创造物拆开的分离。思想只要在它希望的静止世界中缄默,就会在它眷恋的一体中井井有条。然而,思想只要动一动,这个世界就会断裂并倒塌;无穷数的闪光碎片蜂拥呈现在认识的面前。根本无望了,再难重建能给我们心灵宁静的那种亲切而平静的表层。探索了多少世纪之后,多少思想家前仆后继,我们十分清楚,对我们的全部认识,这是千真万确的。除开职业的唯理论者,如今对真正的认识都不抱希望了。如果只能写一部人类思想有深意的历史,那么就应该写成人不断懊悔而又无能为力的历史。
的确如此,提起谁,提起什么,我能说:“这我知道!”胸膛里这颗心,我能感受到,能判断它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到,也能判断它存在。我的全部学识到此为止,其余的就是构筑了。因为,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抓住,如果我试图确定下来并加以概括,那么“我”就会完全化作水,从我的手指缝儿流走了。我可以一一画出“我”所能呈现的各种面孔,也能一一画出别人赋予“我”的各种面孔,表现这种教育、这种出身、这股热情或者这样缄默、这样高尚或者这样卑劣。可是,人们并不能把这种面孔加起来。甚至我这颗心,我也永远确定不了。我确信自己的存在,我还力图给这种确信提供内容,但这两者之间的沟壑却永远也填不平。我对我本人,始终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上犹如在逻辑学上,有一些真理,又根本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这句“认识你自己”,和我们忏悔中说的这句“要有德行”,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两句话同时透露出眷恋和无知。这是在重大题材上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游戏,这些游戏只要靠点谱就算不错了。
再比如这些树木,我知道树皮粗糙,里面有水分,也闻到了树香。夜间,花草和星辰的芬芳,在心情轻松的夜晚,我怎么能否认我感到其强势和力量的世界呢?然而,大地的全部知识,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东西让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向我描述这个世界,教我如何分门别类。你们向我列举了它的法则,而我求知若渴,也就同意这些法则真实可靠。你们还剖析世界的机制,我的希望也随之增加。到了最后阶段,你们又告诉我,这个五彩缤纷的奇妙宇宙,最终分解为原子,而原子又分解为电子。这一切看来不错,我等待你们继续下去。可是,你们却对我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星体系统,许多电子围绕着一个核运转。你们用一种形象给我解释这个世界。于是我承认,你们到了诗的境界:那是我永远也不能了解的。我还来得及表示气愤吗?你们又改换了理论。这门本来应当让我认识一切的科学,就这样在假想中结束了。这种明晰沉没在隐喻中,这种不确定性化为艺术作品。何必让我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呢?这些山峦柔美的线条、抚摸这颗慌乱的心的夜晚之手,能告诉我更多的东西。但我又回到自己的起点。我算明白了,如果说,我能通过科学掌握自然现象,并且一一列举出来,我却不能相应地理解这个世界。纵然我用手指顺着起伏的地势摸遍了世界,我也不见得了解更多。你们要我选择:要么是一种确切的描写,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要么是种种假想,声称能教导我,可又一点也不确切。对于我本人和这个世界,我都是陌生者,唯一可以求救的就是一种意念,而这种意念一旦要肯定什么,就自我否定了。我这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中啊?我要想得到安宁,就只能放弃认知和生存,想进取的渴求处处碰壁,遇到坚不可摧的壁垒!一有意愿,就要引起混乱。一切都排列有序,从而诞生一种毒化的安宁,始作俑者,就是这种无忧无虑、心灵的这种睡眠状态,以及坐以待毙的放弃。
智慧也以其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智慧的反面,即盲目的理性,怎么断言一切都明白无误也是枉然,我还等待拿出证据,但愿理性言之有理。不过,尽管多少世纪都那么自以为是,更有那么多令人信服的雄辩家,但我知道这是虚假的。至少在这方面,绝没有什么幸运者为我所不知。这种无论实践的还是精神的普遍理性,这种决定论、这些解释一切各种范畴,说到底,无不有令正派的人发笑的成分。这些理性的东西,跟精神根本搭不上边,而是否认受束缚的思想乃真知灼见。在这个有限的而又看不透的世界里,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意义。一大批非理性的人群起而攻之,直到最近这种意义才寿终正寝。这些非理性的人又恢复了明智,现在更同心协办,荒诞感就渐趋明朗,越发真切了。我前面说过世界是荒诞的,未免操之过急。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可理喻,眼下也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其实,所谓荒诞,就是这种非理性同执意弄明白这种渴望的冲突,须知人的内心深处,总回荡着弄清世界的呼吁。荒诞既取决于人,也同样取决于世界。荒诞在目前,是人与世界的唯一纽带。荒诞将人与世界捆绑在一起,正如仇恨,唯有仇恨能把世人联系起来。我在这个无可比拟的世界中探险,所能辨别清楚的,也只有上述这一点。就此打住吧。支配我同生活关系的这种荒诞,如果说我当真的话,面对世界的景观震慑我的这种荒诞感,以及探索一门科学强加给我的明智,如果说我坚信的话,那么我就应该为这类坚信牺牲一切,我就应该完全正视,以便牢牢地把握住。我尤其应该在坚信中调整我的行为,不管产生什么后果都要坚持到底。我这样讲是真心诚意的。不过,我事先还是想了解,在这大片沙漠中,思想能否存活。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进入了这片沙漠,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面包,还在沙漠中醒悟了,尽管先前一直以幻影为食。思想趁机提出了几个最紧迫的主题,以供人类思索。
荒诞被承认之时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肝裂胆的激情。但是,问题全在于要了解,人能否与荒诞的激情共生存,能否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同时焚毁被它激发起来的人心。这倒也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这一法则处于这场探索的中心。到时候回头还要再谈。我们先得承认,这些主题和冲动产生于荒漠。只要列举出来就够了。这些也同样,已经尽人皆知了。始终有人站出来,捍卫非理性的权利。有一种可以称为受屈辱的思想,其传统从来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未免太多,不必再做了。然而,我们的时代却重又出现这些荒谬的体系,千方百计地让理性蹒跚而行,就好像理性真的在一直往前走似的。不过,这也证明不了理性多么有效力,更证明不了理性的希望有多么强烈。看看历史,这两种态度始终并存,表明人的主要激情:一面激情呼唤向往一统,另一面又明白看到高墙壁垒的包围,人实在进退维谷。
不过看起来,对理性的攻击,也许任何时代也不如现时代来得猛烈。前有查拉图斯特拉
 大声疾呼:“也是天缘凑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肯高踞于世间万物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头衔还给了世间万物。”后有患了不治之症的克尔恺郭尔:“这病症导致死亡,人一去世万事皆空。”荒诞思想富有深意又百般扭曲的主题层出不穷。至少可以说(而这种差异至关重要),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主题就是如此。从雅斯贝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舍斯托夫
大声疾呼:“也是天缘凑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肯高踞于世间万物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头衔还给了世间万物。”后有患了不治之症的克尔恺郭尔:“这病症导致死亡,人一去世万事皆空。”荒诞思想富有深意又百般扭曲的主题层出不穷。至少可以说(而这种差异至关重要),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主题就是如此。从雅斯贝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舍斯托夫
 ,从现象学者到谢勒
,从现象学者到谢勒
 ,思想上全是一家人,由他们的眷恋结成亲族,活跃在逻辑和道德领域,以不同的方法,或者抱着不同的目的,不遗余力地阻挡理性的阳关大道,要重新找到直通真理的路径。我在此假设,这些思想为人了解并体验过。这些先贤时俊,不管他们先前或现在有什么雄心大志,他们全从这样一个世界出发:这个世界难以描摹,由矛盾、二律背反、惶恐或无能为力统治着。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所揭示的这些主题。关于他们,也同样必须说,尤其看重的,就是他们从这些发现中所得出的结论。这十分重要,值得单独进行研究。眼下只谈谈他们的发现,以及他们最初的体验,只谈谈已证实的他们的不谋而合。如果说想要谈论他们的哲学,有点不自量力的话,那么不管怎样,让人感受一下他们的共同氛围还是可能的,这也就足够了。
,思想上全是一家人,由他们的眷恋结成亲族,活跃在逻辑和道德领域,以不同的方法,或者抱着不同的目的,不遗余力地阻挡理性的阳关大道,要重新找到直通真理的路径。我在此假设,这些思想为人了解并体验过。这些先贤时俊,不管他们先前或现在有什么雄心大志,他们全从这样一个世界出发:这个世界难以描摹,由矛盾、二律背反、惶恐或无能为力统治着。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所揭示的这些主题。关于他们,也同样必须说,尤其看重的,就是他们从这些发现中所得出的结论。这十分重要,值得单独进行研究。眼下只谈谈他们的发现,以及他们最初的体验,只谈谈已证实的他们的不谋而合。如果说想要谈论他们的哲学,有点不自量力的话,那么不管怎样,让人感受一下他们的共同氛围还是可能的,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眼审视人类生活状况,宣称这种生存是一种侮辱。唯一的现实,就是人在各个阶段的“思虑”。对于迷失在世界和自身迁徙的人来说,这种思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忧虑。不过,这种忧虑一旦意识到了,就会转化为惶恐,清醒者永久的氛围,“生存重又陷入其中”。这位哲学教授拿笔的手丝毫也不发抖,用最抽象的语言写道:“人生存的有限性与限定性,比人本身还重要得多。”他对康德感兴趣,只是看出康德的“纯理性”的局限性,也是为他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再也不能向惶恐的人提供什么了。”在他看来,这种思虑事实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因而他一心只想着这种思虑,只谈这种思虑了。他列举了思虑的种种面孔:烦恼的面孔,当凡夫俗子力图将思虑同自身挂钩,并力图使之减缓的时候;恐惧的面孔,当智者贤达直面死亡的时候。意识到死亡,这便是思虑的呼唤,“于是,生存通过意识,也向自己发出呼唤”。死亡的意识正是惶恐的声音,要求生存“主动从毁灭返回芸芸众生”。他也不例外,不能睡大觉,必须日夜警醒,一直守到生命耗尽。他在这荒诞的世界中坚守,又强调荒诞世界的可毁性。他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路。
雅斯贝斯对整个本体论大失所望,因为他断言我们丧失了“天真”。他知道我们必然一无所成,不能让表象的乏味游戏升华。他也知道,精神的归宿就是失败。他久久徘徊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冒险之路上,无情地揭示了每种体系的缺陷,识破了拯救一切的幻想、毫无掩饰的说教。在这荒废的世界,已然证明了根本不可能认识,虚无仿佛是唯一的现实,无可补救的绝望,唯一的姿态,因此,他试图重新找到阿里阿德涅的小线团,沿导线通往秘密的神界。
舍斯托夫另有建树,通过一部单调得叹为观止的著作,反复不断地进取同样的真理,持续不断地指出,最缜密的体系,最广泛的理性主义,最终总要绊倒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任何具有讽刺意味明显的道理、任何贬损理性的可笑的矛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引起他兴趣的事,那就是例外,无论属于心灵史还是属于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体验,通过尼采式的狂放的精神冒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诅咒,或者易卜生式的苦涩的贵族生活,他不断发现,指明并赞扬人对无可补救的世界的反抗。他拒绝将自己的道理归附理性,而且直到这片没有色彩、一切确定的东西全变为石头的荒漠深处,他才颇为坚定地开始大踏步前进。
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吸引人的也许还是克尔恺郭尔,至少他那人生的一部分是如此,他远比发现荒诞胜过一筹,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三缄其口,而是开口说话。”
 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让本身都不成立的存在令人满意。这个洞达事理的唐璜
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让本身都不成立的存在令人满意。这个洞达事理的唐璜
 ,不断变换笔名发表文章,频繁地制造矛盾,他写了《布道词》,同时又炮制出《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慰、道德,也拒绝一切令人安心的原则。这根刺,他感到扎在心上
,不断变换笔名发表文章,频繁地制造矛盾,他写了《布道词》,同时又炮制出《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慰、道德,也拒绝一切令人安心的原则。这根刺,他感到扎在心上
 ,但绝不会试图减轻痛苦,他反而唤起痛苦,乐在绝望中,像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有一种求苦受罪的满足感,清醒、拒绝、戏谑,他一点一点塑造一类魔鬼附身者。这张既温和又讪笑的面孔,这种伴随着从灵魂深处发出喊叫的旋转,正是荒诞精神在同超越它的现实进行拼搏。精神的冒险,将克尔恺郭尔引向他那些宝贵的轰动效果,而冒险本身也是在混乱中开始的,进行一场丧失其背景、回归原初缺乏条理的体验。
,但绝不会试图减轻痛苦,他反而唤起痛苦,乐在绝望中,像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有一种求苦受罪的满足感,清醒、拒绝、戏谑,他一点一点塑造一类魔鬼附身者。这张既温和又讪笑的面孔,这种伴随着从灵魂深处发出喊叫的旋转,正是荒诞精神在同超越它的现实进行拼搏。精神的冒险,将克尔恺郭尔引向他那些宝贵的轰动效果,而冒险本身也是在混乱中开始的,进行一场丧失其背景、回归原初缺乏条理的体验。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其他现象学派哲学家们,同样以夸张的手法,重建了多样性的世界,否定了理性超验的能力。精神世界同他们一起,无法估量地丰富充实起来。玫瑰花瓣、公路的里程碑,或者人手,比起爱、欲望,或者万有引力来,都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不再一统天下了,不再是使表象以大原则的面目变得为人熟知了。思想,就是重新学会观察世界,学会集中注意力,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将每种意念、每个形象,都转化为一块福地。一切都成为优选了,也实在反常了。能为思想说得通的,就是思想的极端自觉性。胡塞尔虽然显得比克尔恺郭尔,或者比舍斯托夫更为实证,可是当初,他却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打破希望,敞开直觉和心灵的门,迎入庞杂的现象,而那些纷繁的现象则有些非人性的东西。他走过的一条条路,通向一切科学,抑或通不到任何科学。这就是说,方法在他这里,比结果更为重要。仅仅重在“认识事物的一种姿态”,而非寻求安慰。再说一遍,至少当初是如此。
这些聪慧的人深层的亲缘关系,怎么能感觉不到呢?他们聚集在优选之地,痛苦丛生而再无希望,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要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否则免开尊口。面对这种心声,理性就无能为力。被这种要求唤醒来的精神,不断探索,也只是发现矛盾和非理性。我不懂的东西,就没有道理。世界充斥着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单说这个世界,我不懂得它单一的含义,那它就是个非理性的大千世界。哪管能讲上一次:“这明明白白”,那么一切都会得救。谁知,这些人却抱着宣布:什么也不明确,一切都混乱不堪,人仅仅保留了自己的明确,以及对围墙的真切认识。
所有这些体验不仅协调一致,而且相辅相成。精神探到边缘,就应当作出判断,选择其结论。这便是自杀和答案的所在之地。不过,我要将探索的顺序颠倒一下,从精神探险出发,再回到日常的行为中。前面提到的体验是在荒漠中,还绝不能离开。至少应当了解,体验达到了什么地步。这样努力的结果,人就迎面撞上非理性,内心不由得感到渴望幸福和理性。一边是人的呼唤,另一边是世界毫无理性的沉默,这两者对峙便产生了荒诞。这一点不应当忘记,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因为从而就可能产生人生的全部后果。非理性、人的怀旧眷恋,以及由这两者冲撞而产生的荒诞,这就是人生悲剧的三个特点,而人生悲剧,势必同一种生存成为可能的全部逻辑一起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