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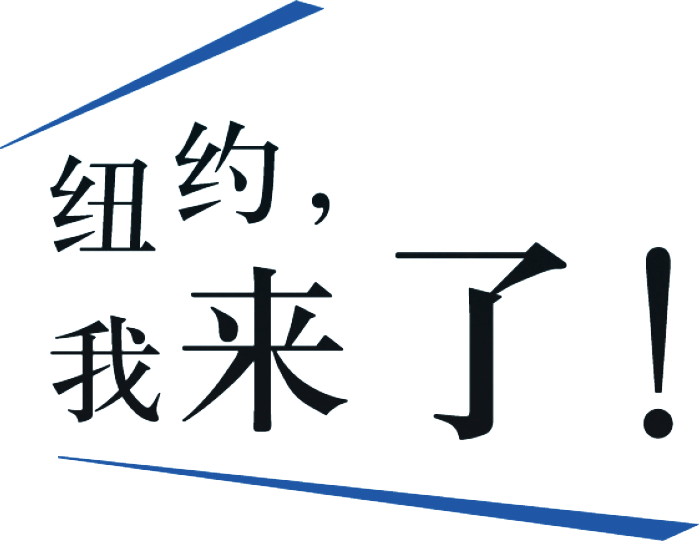
埃迪·吉利根和他弟弟乔伊一起在十九层上班。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重大聚会、客房会议、舞厅宴会和婚礼作准备。乔伊没多大用处,因为他的手和手指像机器人一样笨拙。他一只手握着把长柄扫帚,另一只手夹着根香烟,四处溜达,假装很忙碌的样子,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厕所里,或者和地毯工迪格·姆恩一起抽烟。迪格·姆恩声称自己是黑脚族印第安人,铺地毯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快,都牢固,除非心情不好。那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他不会忘记族人的苦难。说起族人的苦难,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就是乔伊·吉利根,因为乔伊正遭受着关节炎的折磨。迪格说乔伊能理解他。当关节炎带来巨大的痛苦,让你几乎不能擦屁股时,你就会理解各种苦难了。迪格就是这么说的。不用一层一层铺地毯或者撤地毯时,他就盘腿坐在地毯间的地上,和乔伊一起受苦。一个忍受过去的苦难,另一个忍受关节炎之苦。没有人会打搅迪格和乔伊,巴尔的摩酒店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痛苦。白天,他们可以待在地毯间里或者到街对面的麦克安酒吧放松一下。凯里先生的胃不好。上午和下午巡视时,他得忍受妻子做的早饭和午饭的折磨。他对埃迪说他妻子是个漂亮女人,是自己唯一爱着的女人,但她正在慢慢地谋害他。她的腿因为风湿而肿胀,身材也不好了。埃迪对凯里先生说,他自己的妻子在四次流产后身材也不好了,现在还患上了让医生担忧的血液感染。我们为“美国-爱尔兰历史协会”年会作准备的那个早上,埃迪和凯里先生站在十九层舞厅的入口。埃迪抽着烟。凯里先生穿着双排扣西服,褶裥打得很巧妙,让人以为他没什么肚子。他拍打着肚子以减轻痛苦。埃迪对凯里先生说,他从来都不抽烟,直到在奥马哈海滩
 挨了一枪。一些可恶的家伙,对不起,凯里先生,说脏话了,趁他躺在那儿等急救员的时候往他嘴里塞了根烟。他抽了一口,这大大减轻了肠子流到奥马哈海滩上的痛苦,从那以后,他就抽上了烟,再也无法戒掉。试过,上帝知道,但是戒不掉。这时,迪格·姆恩肩膀上扛了块巨大的地毯溜达过来,对埃迪说该对他的弟弟乔伊做些什么了。那个狗娘养的可怜家伙受的难比七个印第安部落受的还多。在该死的太平洋当步兵期间,迪格被日本佬扔的各种东西(疟疾等等)击中。自那以后,他就对苦难有所了解了。埃迪说:是的,是的,他了解乔伊。他很抱歉,乔伊毕竟是他弟弟,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妻子、她的流产和血液感染,还有他自己因为没放回原位而变得一团糟的肠子。乔伊将酒和各种止痛片混在一起喝的做法,很让他担心。凯里先生打了个嗝,哼了一声。迪格说:你还在吃屎哪?迪格不怕凯里先生,也不怕其他人。当你是个伟大的地毯工时,事情就是这样了。可以和任何人说想说的话,如果他们把你解雇,康莫德酒店、罗斯福酒店,上帝,是的,甚至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总有份工作等着你。这些酒店一直想将迪格挖走。有些日子,他受不了族人遭受的苦难,拒绝铺任何地毯。而凯里先生没有解雇他,他说:好吧,没了我们印第安人,白人就没法过日子。白人需要易洛魁人
挨了一枪。一些可恶的家伙,对不起,凯里先生,说脏话了,趁他躺在那儿等急救员的时候往他嘴里塞了根烟。他抽了一口,这大大减轻了肠子流到奥马哈海滩上的痛苦,从那以后,他就抽上了烟,再也无法戒掉。试过,上帝知道,但是戒不掉。这时,迪格·姆恩肩膀上扛了块巨大的地毯溜达过来,对埃迪说该对他的弟弟乔伊做些什么了。那个狗娘养的可怜家伙受的难比七个印第安部落受的还多。在该死的太平洋当步兵期间,迪格被日本佬扔的各种东西(疟疾等等)击中。自那以后,他就对苦难有所了解了。埃迪说:是的,是的,他了解乔伊。他很抱歉,乔伊毕竟是他弟弟,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妻子、她的流产和血液感染,还有他自己因为没放回原位而变得一团糟的肠子。乔伊将酒和各种止痛片混在一起喝的做法,很让他担心。凯里先生打了个嗝,哼了一声。迪格说:你还在吃屎哪?迪格不怕凯里先生,也不怕其他人。当你是个伟大的地毯工时,事情就是这样了。可以和任何人说想说的话,如果他们把你解雇,康莫德酒店、罗斯福酒店,上帝,是的,甚至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总有份工作等着你。这些酒店一直想将迪格挖走。有些日子,他受不了族人遭受的苦难,拒绝铺任何地毯。而凯里先生没有解雇他,他说:好吧,没了我们印第安人,白人就没法过日子。白人需要易洛魁人
 在摩天大楼的六十层上沿着钢梁跳舞。白人需要黑脚族人铺好地毯。每次迪格听到凯里先生打嗝,就叫他不要吃屎了,好好地喝顿啤酒,因为啤酒从来不会让人伤脑筋。是凯里夫人的三明治让凯里先生难受的。迪格对凯里先生说,他有一套关于女人的理论,她们就像交配后咬掉雄蜘蛛该死的脑袋的黑寡妇蜘蛛。女人不关心男人,一旦她们过了生育年龄,男人就一无是处了,除非她们骑在马上攻击另一个部落。埃迪·吉利根说,你骑着马沿麦迪逊大道攻击另一个部落,看上去真他妈的傻。迪格说他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在脸上涂上颜料、骑马、投梭镖、杀死另一个部落的人。埃迪说:呀,胡说。迪格说:呀,胡说,信你才怪呢,你在干吗,埃迪?一辈子在这里准备晚饭和婚礼吗?这是男人的生存方式吗?埃迪耸了耸肩,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迪格突然转身走开,撞到地毯边上的埃迪和凯里先生,将他俩撞出五英尺远,撞到了舞厅。
在摩天大楼的六十层上沿着钢梁跳舞。白人需要黑脚族人铺好地毯。每次迪格听到凯里先生打嗝,就叫他不要吃屎了,好好地喝顿啤酒,因为啤酒从来不会让人伤脑筋。是凯里夫人的三明治让凯里先生难受的。迪格对凯里先生说,他有一套关于女人的理论,她们就像交配后咬掉雄蜘蛛该死的脑袋的黑寡妇蜘蛛。女人不关心男人,一旦她们过了生育年龄,男人就一无是处了,除非她们骑在马上攻击另一个部落。埃迪·吉利根说,你骑着马沿麦迪逊大道攻击另一个部落,看上去真他妈的傻。迪格说他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在脸上涂上颜料、骑马、投梭镖、杀死另一个部落的人。埃迪说:呀,胡说。迪格说:呀,胡说,信你才怪呢,你在干吗,埃迪?一辈子在这里准备晚饭和婚礼吗?这是男人的生存方式吗?埃迪耸了耸肩,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迪格突然转身走开,撞到地毯边上的埃迪和凯里先生,将他俩撞出五英尺远,撞到了舞厅。
这是个意外,没有人说什么,但我还是很钦佩迪格的处世方式,像我在利默里克的帕特舅舅一样,对什么都不在乎,仅仅因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铺地毯。我希望自己能像迪格那样,但不是铺地毯。我痛恨地毯。
我要是有钱,就会买个手电筒,看书看到天亮。在美国,手电筒不叫torch而叫flashlight;饼干不叫biscuit,而叫cookie;小圆面包不叫bun,而叫roll;甜食不叫confectionery,而叫pastry;肉末不叫minced meat,而叫ground;男人穿的裤子叫pants,而不是trousers。他们甚至说这条裤腿要比另一条裤腿短,这太傻了。当我听到他们说“裤腿”的时候,感觉呼吸在加快。电梯叫elevator,而不是lift。如果想上厕所,不说WC或者lavatory,得说bathroom,即便那儿没有浴室的标记。在美国,没有人死亡,他们去世或者过世。死了以后,称为遗骸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而人们只是站在四周看着遗体,没有人唱歌或讲故事或喝酒,然后遗体被装进棺材运走下葬。他们不喜欢称棺材为coffin,而叫casket;也不喜欢将下葬说成buried,而用inferred这个词。他们说墓地不用graveyard,cemetery听上去就好多了。
我要是有钱,就会买顶帽子再出门。我不能光着脑袋在曼哈顿大街上溜达,人们可能会以为是一副骨瘦如柴的肩膀顶着一个雪球。一星期后,当头发染黑头皮,我就能再次出门了。对此,奥斯丁夫人也无能为力。躺在床上想着那些没人能干涉的事儿,我很是开心。这就是奥哈洛伦校长曾在利默里克的学校对我们讲过的:大脑是你们的宝库,世界上没有人能干涉得了它。
纽约是我梦想的城市,但是现在我身在纽约,梦想却已消失,这根本就不是我期望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酒店大堂里跟在人们后面打扫卫生,在厕所里刷马桶。我怎么能写信告诉母亲或利默里克的任何人,我在这个富裕国度的生活方式呢?两美元过一个星期,光头,眼睛疼,还有一个不让我开灯的女房东。我怎么能告诉他们,酒店担心波多黎各人可能感染上我的新几内亚病而不让我靠近厨房拿残羹剩饭,我不得不每天吃香蕉这种世界上最便宜的食物呢?他们不会相信我,会说别傻了,会大笑,因为他们只会看看电影,了解美国人如何富裕:美国人会胡乱扒拉食物,盘子上还剩些东西就推到一边。他们甚至很难为电影《愤怒的葡萄》里贫穷的美国人感到难过,所有的庄稼都旱死了,他们不得不搬到加州去,可至少他们是干爽温暖的。我姨父帕·基廷曾经说过:如果爱尔兰有个加州,全国的人都会蜂拥而去。他们吃掉很多橘子,还整天游泳。在爱尔兰,很难相信美国有穷人,因为人们见过爱尔兰人从美国回来时的样子。他们被称为归国的美国佬,穿着紧绷绷的裤子,裤子的颜色是你在爱尔兰从未见过的:蓝色、粉色、浅绿色,甚至是暗红色。他们肥肥的屁股在奥康纳大街上来回晃动,你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发现。他们显出很有钱的样子,带着鼻音谈论他们的冰箱和汽车。如果走进酒馆,他们就会点没人听说过的美国酒——鸡尾酒,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要在利默里克的酒馆点这个,酒保就会煞煞他的气焰,提醒他是怎么光着屁股到美国去的。别在这儿摆架子,爱尔兰人,在你的鼻涕挂到膝盖上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人们也总能发现真正的美国佬:身穿浅色衣服,大屁股;微笑着观光游览,还给衣衫褴褛的孩子几个便士。真正的美国佬不摆架子,他们来自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国家,用不着摆架子。
即使奥斯丁夫人不让开灯,我依旧可以坐在床上或者躺下,也可以决定待在屋里还是出去。今晚,因为光头,我不会出去。我也不介意在屋子里待着,我可以待在这儿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一部关于利默里克的电影。这是我躺在屋子里的伟大发现:如果因为眼睛或者奥斯丁夫人抱怨开灯而无法看书,我可以在脑海里放映各种电影。如果这里是午夜,利默里克就是早上五点。我可以想象母亲和弟弟们还在睡觉,那条叫幸运的狗正冲着世界狂吠,我舅舅帕特·西恩头天晚上喝了酒,在床上打呼噜,因为吃了太多的鱼和薯片在不停地放屁。
我可以在利默里克城中到处游荡,看着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去参加首个周日弥撒。我可以进出教堂、商店、酒馆、墓地,看着人们入睡或在城市之家的医院里痛苦呻吟。在脑海中回到利默里克是件奇妙的事儿,尽管这让我泪流满面。经过贫民区的小巷,查看他们的屋子,听到婴儿啼哭,看到女人们试图生火用水壶烧水、准备早饭的茶和面包,这叫人难以忍受。孩子们不得不起床上学或参加弥撒时浑身颤抖的样子,让人不忍心看下去。屋子里没有暖气,不像我们在纽约,早上六点暖气管就哗哗作响。我想把利默里克的街巷搬空,把所有的穷人都带到美国,安置到有暖气的屋子里,给他们保暖的衣服和鞋子,用粥和香肠把他们的肚子塞饱。总有一天,我会挣到上百万美元,我会把穷人带到美国,再把屁股肥肥的他们送回利默里克,让他们穿着浅色衣服在奥康纳大街上来回晃荡。
我可以在床上做任何我喜欢的事情,任何事情。我可以梦到利默里克或者手淫,即使是罪孽,奥斯丁夫人也绝不会知道。没有人会知道,除非我自己坦白,那样的话,我就死定了。
头上还有头发但身上却没钱的晚上,我可以在曼哈顿四处走走。这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街道和第六十八大街剧场里的任何一部电影一样精彩。总是有消防车、救护车或者警车尖叫着拐过街角。有时候它们一块儿呼啸而来,你就知道发生火灾了。人们总是看着消防车放慢车速,告诉你它们要去哪个街区,上哪儿寻找烟雾和火焰。如果有人站在窗口准备往下跳,就更刺激了。救护车会闪着灯等待,警察会让所有人都退后。这是纽约警察的主要工作:叫所有人都退后。他们拿枪持棒,很强大,但真正的英雄是消防员,尤其是他们爬上梯子从窗户救出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救出一个拄着拐杖、只穿了一件睡衣的老人,但如果救出的是一个吮着大拇指、将长着鬈发的头靠在消防员宽阔肩膀上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就会欢呼,相互望望,知道我们在为同一件事高兴。
就是这件事促使我们第二天翻看《每日新闻》,看看自己是否有机会和那勇敢的消防员,以及鬈发的孩子一起出现在照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