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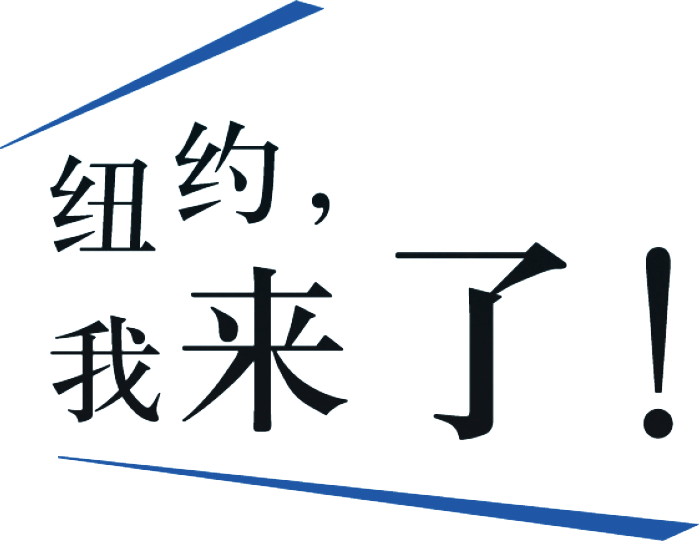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月,“爱尔兰橡树”号内燃机船驶离科克港,本应在一星期后到达纽约市。然而出海刚两天,我们就被告知船正驶向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对大副说我只有五十美元,爱尔兰船运公司能替我支付从蒙特利尔到纽约的火车票钱吗?他说:不,公司对此不负责。他说货船是公海上的妓女,可以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你可以说货船就像墨菲的灵魂狗,会陪任何一个流浪汉走上一段路。
两天后,爱尔兰船运公司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驶往纽约市。但是又过了两天,船长被告知:驶往奥尔巴尼。
大副跟我说奥尔巴尼是哈德逊河上游的一座城市,是纽约州的首府。他说奥尔巴尼拥有利默里克的所有魅力,哈哈,那是个养老的好去处,却不是结婚养孩子的地方。他是都柏林人,知道我从利默里克来。当他嘲讽利默里克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用机敏的话语击败他,可我照镜子看了看自己的模样:长满丘疹的脸、疼痛的双眼,还有糟糕的牙齿。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勇敢地面对任何人,特别是一个穿着制服、将来会拥有自己的轮船的大副。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谈论利默里克呢?在那儿,我拥有的只是痛苦。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奇怪的事。十月美丽的阳光下,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努力幻想着纽约的样子,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四周。我要去看看第五大道或者中央公园或者格林威治村,在那儿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明星,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但是利默里克将我推回到过去。我没有在第五大道和深褐色皮肤、闪亮牙齿们闲庭信步,而是回到了利默里克的街巷:女人将披巾裹到肩上,站在门旁闲聊天;孩子们玩耍、嬉笑,哭着找妈妈,脏兮兮的脸上沾满面包屑和果酱。我看到人们参加周日上午的弥撒,当某个饿得全身疲软的人从长椅上倒下,不得不被教堂后面的男人们抬出去时,窃窃私语声就会传遍整个教堂。那些男人对众人说:让开,让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难道没看见她喘不过气来了吗?我想成为那么一个叫大家让开的人,因为那样就有权待在教堂外面,直到弥撒结束,然后还可以到小酒馆去,而这就是要和男人们站在后面的原因。不喝酒的男人总是笔直地跪在圣坛边,显示他们是多么好,又是多么不在意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酒馆是否关闭。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弥撒的应答。他们祝福自己,一会儿站一会儿跪,在祈祷时不停地叹息,好像比其他教徒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痛苦。有些人彻底戒了酒,可他们是最坏的,总是宣讲酒的害处,瞧不起那些依赖于酒精的人,好像他们走在通往天堂的正道上。每个人都知道讲坛上的神甫很少谴责酒或喝酒者,而他们的行为却好像上帝会抛弃喝酒者似的。想喝酒的男人们待在教堂后部,一听到神甫说“礼毕,会众散去,走吧,解散了”,他们就作好溜出门的准备。他们待在后面是因为口干舌燥,而且觉得自己太卑微了,不能和那些严肃的人在一起。我待在门边,可以听到他们小声议论那乏味的弥撒,但如果你不去,就是道德犯罪,尽管你不清楚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说“这个神甫不快点你就会当场渴死”是不是更严重的道德犯罪。如果怀特神甫出来布道,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呻吟:世界上最乏味的布道。而怀特神甫双眼转向天堂,宣布我们都在劫难逃,除非改正错误,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圣母马利亚。我的姨父帕·基廷会说:
如果圣母马利亚给我一杯可爱的奶油黑啤酒,我就会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她。他的话让男人们发出阵阵窃笑。我想和已经长大成人、穿着长裤的帕·基廷姨父一起,和那些口干舌燥的男人站在一起窃笑。
我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骑车沿着利默里克市到乡村送电报的情形。我看见自己一大早骑行在乡村公路上。雾气从田野里升起,奶牛时不时冲我哞哞几声,狗朝我跑来,我用石头将它们赶跑。我听见农舍里婴儿哭着叫妈妈,农夫们挤完奶后将奶牛赶回田里。
躺在甲板躺椅上,湛蓝色的大西洋环绕着我。前面就是纽约,我梦想的城市,我可以拥有深褐色皮肤、令人目眩的洁白牙齿的地方。可是我开始暗自落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竟然会怀念利默里克,那座有着灰色记忆的城市,那座我梦想着要逃离的城市。我听到了母亲的警告:你熟悉的魔鬼比你不熟悉的魔鬼强。
船上原定有十四名乘客,但有一人取消了行程,因此我们只好带着不吉利的数字出发。出海的第一个晚上,船长在晚餐时起立欢迎我们。他笑着说,虽然他对乘客的数字并不迷信,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有一位神甫,如果尊敬的阁下能祈祷我们免遭危难,那就再好不过了。神甫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儿男人,出生在爱尔兰,但在洛杉矶堂区待得太久了,没有一点爱尔兰口音。他站起来祈神保佑时,有四名乘客将手放在大腿上。那动作告诉我,他们是新教徒。我母亲曾经说过:新教徒矜持的样子,让你可以在一英里之外就发现他们。神甫请上帝用怜悯和爱俯视我们;在风暴频仍的海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准备好永远投入他神圣的怀抱。一名上了年纪的新教徒伸出手,想要握住妻子的手。她笑了笑,冲他摇了摇头。他也笑了笑,好像在说:别担心。
晚餐时,神甫坐在我旁边。他小声说那两个上了年纪的新教徒在肯塔基州饲养纯种赛马,很有钱。如果我还有点常识,就该对他们表示友善。世事难料。
我想问对饲养赛马的有钱的新教徒表示友善的好方法是什么,但是我不能问,因为担心神甫会认为我是个傻瓜。我听到新教徒们说爱尔兰人是那么迷人,他们的孩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你几乎注意不到他们是多么贫穷。我知道,如果想和有钱的新教徒交谈,就得微笑,就得露出我那糟糕的牙齿,那就完了。等我在美国赚到钱,一定冲到牙医那儿将我的微笑修缮一番。你可以从杂志和电影上见到微笑是怎样攻城略地,让女孩发狂的。如果没有那种微笑,我还不如回到利默里克,找一份在邮局的黑暗后屋里分拣信件的工作。在那儿,他们不关心你是否有牙齿。
睡觉前,服务员在娱乐室提供茶水和饼干。神甫说:我要杯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忘了茶吧,迈克尔,威士忌有助我入睡。他喝着威士忌,又小声问我:你和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过了吗?
没有。
该死!你怎么搞的?你不想在世上取得成功吗?
想。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呢?他们也许会喜欢你,给你一份马夫之类的活儿。你的地位会得到提升,而不用去纽约。那里是犯罪的发源地,邪恶的渊薮,天主教徒得日夜抗争才能保持信仰。所以,为什么你不跟那有钱的肯塔基人谈谈,让自己有所成就呢?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到有钱的肯塔基人,他总是会窃窃私语,而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弟弟马拉奇在,他就会径直走到那有钱人跟前,让他们着迷。他们也许会收养他,留给他上百万美元,还有马厩、赛马、一幢大房子和打扫房子的女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和有钱人说过话,除了说过:夫人,电报。而后我会被告知绕到佣人专用门:这里是前门,你不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跟神甫说的话,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对神甫所有的认识就是他们用拉丁语讲弥撒和其他事情。他们听我用英语忏悔我的罪孽,代表我们的主,就是上帝,用拉丁语宽恕我。当神甫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知道自己有权根据心情决定是否宽恕别人。当你懂得拉丁语并能宽恕罪孽时,你就很有权,而人们也就难以和你交谈,因为你知道世上黑暗的秘密。和神甫交谈就像和上帝本人交谈一样。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死定了。
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怎样和有钱的新教徒,以及要求严格的神甫交谈。我姨父帕·基廷能告诉我,可他远在利默里克。在那儿,他把任何事情都搅得一团糟。如果在这儿,他一定会拒绝和有钱人谈话,还会叫神甫去亲吻他那高贵的爱尔兰屁股。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样,但是当你的牙齿和眼睛都被毁了,你永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了。
船上的图书室有一本《罪与罚》。我想这也许是本很好的推理小说,尽管里面全是些让人看不懂的俄国名字。我坐在躺椅上翻看,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讲的是一位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俄国学生杀死了一名放债的老妇人,然后努力让自己相信,他有权拥有老妇人的钱,因为她对世界无益,而她的钱可以支付他上大学的费用,这样他就能成为一名律师,替像他这样为钱杀死老妇人的人辩护。这故事让我感到很奇怪,在利默里克,我曾经有过一份为有钱的放债老妇人菲奴肯太太写威胁信的活儿。当她坐在椅子上死去后,我拿了她的一些钱,用来支付到美国的费用。我没有杀死菲奴肯太太,但是拿了她的钱,这让我觉得自己几乎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坏。如果我现在死去,他一定会是我在地狱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可以向神甫忏悔,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神甫一旦宽恕了你,就应该忘掉你的罪孽,即使他会因此而控制我,会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让我去诱哄那有钱的肯塔基人。
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名水手叫醒了我:先生,你的书被雨淋湿了。
先生。我来自利默里克的街巷,可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人却称呼我为先生,尽管按照规定他不应该和我说话。大副告诉过我,水手除了说声“你好”或“晚安”以外,绝不允许和乘客说话。他说这名满头灰发的特殊水手曾经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船长,但是被发现和一名头等舱的乘客待在她的船舱里,所以被解雇了。他们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忏悔。这个人名叫欧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上,显得与众不同。当船靠岸,他会带着一本书上岸,在咖啡馆里阅读,而其他船员则喝得酩酊大醉,得由出租车拖回船上。我们的船长对欧文很敬重,甚至把欧文叫到他的船舱里一起喝茶,谈论在英国驱逐舰上共同服役的日子。那艘驱逐舰被鱼雷击中,他们俩抓着救生筏在大西洋上漂浮,浑身发冷地谈论着回到爱尔兰后的日子。他们要好好地喝上一顿,要吃山一样多的熏肉和卷心菜。
第二天,欧文和我交谈。他说知道自己没有遵守规定,但还是忍不住要和这艘船上任何一位读《罪与罚》的人说话。船员中无疑有些名副其实的读者,但他们读的不外乎埃德加·华莱士
 或者赞恩·格雷
或者赞恩·格雷
 。若能和人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想知道我是否看过《群魔》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我说从来没听说过的时候,他显得很伤心,建议我一到纽约就冲到书店买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那样就不会再孤独了。他说不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一本书,他都会给你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便宜货了。这就是欧文跟我说的话,尽管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若能和人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想知道我是否看过《群魔》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我说从来没听说过的时候,他显得很伤心,建议我一到纽约就冲到书店买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那样就不会再孤独了。他说不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一本书,他都会给你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便宜货了。这就是欧文跟我说的话,尽管我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神甫来到甲板上,欧文走开了。神甫说:你在跟那人说话吗?我知道你在和他说话。嗯,我跟你说,他不是个好伙伴。你明白,是吧?我听说了他所有的事。他顶着一头灰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在擦洗甲板。很奇怪,你竟然会和一个毫无道德的普通水手说话,可是我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新教徒说话,你却连一分钟时间也没有。
我们只是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的,那会给你在纽约带来很多好处。你看不到多少需要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招聘广告。没办法让你和有钱的肯塔基人交谈,你却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水手们废话连篇。离老水手远点,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跟那些对你有用的人交谈吧。看看圣徒的人生故事吧。
沿哈德逊河靠新泽西州的这一侧,上百艘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一起。水手欧文说,那都是战时和战后给欧洲运送给养的自由轮。想到它们总有一天会被拖到造船厂拆解,真是让人感到伤心。但世界就是这样,他说,轮船的寿命比妓女的呻吟还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