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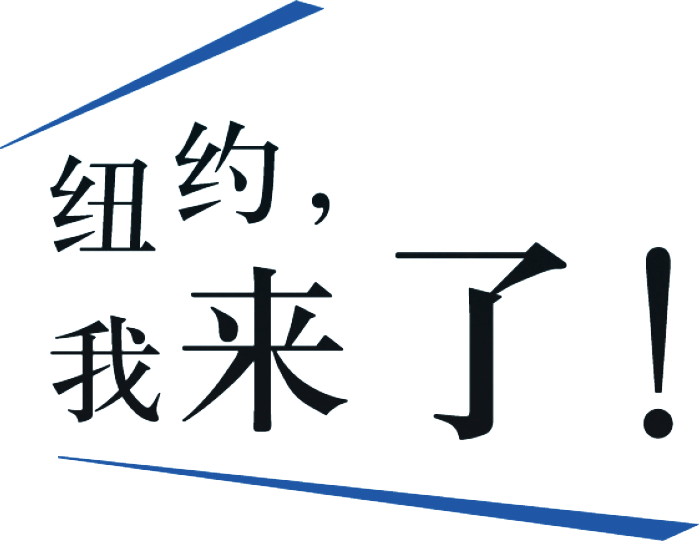
去拿三天休假证的那个星期五,我和等着拿普通周末休假证的人一起列队站在连队办公室外。一名训导下士斯尼德(他的真名是一个谁也不会念的波兰名字)对我说:嗨,士兵,把那烟头捡起来。
哦,但是我不抽烟,下士。
我没有问你他妈的是不是抽烟。捡起烟头。
豪伊·阿布拉莫维茨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小声说:别犯傻了,捡起那该死的烟头。
斯尼德把手叉在腰上。嗯?
我没有扔烟头,下士,我不抽烟。
好吧,士兵,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连队办公室。他拿起我的休假证。现在,他说,我们到你的营房去,换上劳动服。
但是,下士,我有三天的休假证。我是上校的通信员。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擦过上校的屁股呢。穿上你的劳动服,快点!带上你的铁锹。
明天是我的生日,下士。
快点,士兵,要不然我就关你他妈的禁闭。
他让我正步走过站成一排的人们,冲他们挥了挥我的休假证,让他们对它说再见。他们笑着挥手,因为他们只能这样,不想惹麻烦。只有豪伊·阿布拉莫维茨摇了摇头,好像说他对这一切表示遗憾。
斯尼德让我正步走过阅兵场,再走到阅兵场后面树林的空地上。好了,笨蛋,挖。
挖?
对,给我好好挖一个三英尺深、两英尺宽的坑。干得越快,对你就越好。
那一定意味着我越快挖完,就能越早拿到休假证,然后离开。还有什么呢?连里的人都知道斯尼德很刻薄,因为他是巴克内尔大学的橄榄球大明星,想到费城鹰队打球,只是鹰队不要他。现在,他四处闲逛,让人挖坑。这不公平。我知道大家都是被逼着挖坑,把自己的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把它们挖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得干这个。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如果这是个普通的周末休假证,我不介意,但是这是个三天的休假证,而且明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我得干这个?但是对此,我无能为力,最好尽快挖好坑,将休假证埋起来,然后再将它挖出来。
我一边挖坑,一边想着:我要抓起小铁锹敲斯尼德的脑袋,敲得他头破血流。我一点也不介意替这个肥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挖个坑。这就是我想做的。
他递给我休假证,叫我埋起来。铲完泥土,他叫我用铁锹将泥土拍实。干得漂亮点,他说。
我不知道一分钟之后就要将休假证挖出来,他为什么要叫我干得漂亮点。但是现在,他对我说:转过身,向前走。他叫我沿来时的路正步走回去,经过连队办公室。那些等着拿休假证的人都走了。我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满意了,那样他就可以到办公室为我换张休假证。但是,不,他叫我向右转,来到食堂。他对那儿的军士说,我是帮厨的候选人,需要在服从命令方面接受点小教训。他们大笑了一番。军士说他们什么时候一定要一起喝一杯,谈谈费城鹰队,那真是个该死的球队。军士冲着远处一个叫亨德森的人喊,让他给我介绍工作——任何一个食堂里最糟糕的活儿:刷锅洗碗。
亨德森叫我擦洗那些大家伙,擦得它们闪闪发亮,因为经常会有检查。任何餐具上的一点油渍都会让我再干一小时的帮厨。照这个速度,我会一直待在这儿,而朝鲜人和中国人早就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现在是晚饭时间。锅碗瓢盆在水池边堆得老高。垃圾桶在我身后靠墙排着。新泽西州的苍蝇正在那儿大快朵颐。蚊子从开着的窗户嗡嗡地飞进来,在我身上就餐。到处都是煤气灶和烤箱,还有四处横流的热水释放出来的水蒸气和烟雾。很快,我就满头大汗,浑身油渍了。下士和军士们从旁边走过,摸摸那些锅碗瓢盆,叫我重来一遍。我知道这是因为斯尼德正在外面的食堂讲橄榄球的故事,叫他们如何和那个刷锅洗碗的新兵开个小玩笑。
食堂安静一些、活儿少了一些的时候,军士跟我说,晚上可以不用干了,但是明天早上我得到这儿报到。星期六早上六点。他是说早上六点。我想对他说作为上校的通信员,我应该享受三天的休假;明天是我的生日;纽约有个女孩在等我。但我知道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说,因为每次我一开口说话,事情就变得更糟。我知道军队意味着什么: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
埃默在电话里哭着说:噢,弗兰克,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军服社。
什么是军服社?
军人服务社。我们买东西和打电话的地方。
为什么你不来这儿?我们有小蛋糕什么的。
我在帮厨,刷锅洗碗,今晚,明天,也许星期天。
什么呀?你在说些什么呀?你没事吧?
挖坑和洗碗把我累坏了。
为什么?
我没有捡烟头。
为什么你不捡烟头?
因为我不抽烟,你知道我不抽烟。
但是为什么你得捡烟头呢?
因为一个该死的下士,对不起,一个被费城鹰队拒绝的训导下士叫我捡烟头,但我对他说我不抽烟。这就是为什么我应该在我该死的——对不起——生日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却待在这儿。
弗兰克,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喝酒吗?
没有,我没喝酒。我怎么可能同时喝酒、挖坑又帮厨呢?
但是你为什么要挖坑呢?
因为他们叫我把休假证埋了。
哦,弗兰克,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我不知道。也许你见不到我了。他们说盘子上留下的一个油渍就会让我再帮厨一个小时。我会一直在这儿刷锅洗碗直到退役。
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去见见神甫祭司什么的?
我不想去见神甫。他们比下士还要糟,他们那……
他们那什么?
哦,没事了。
哦,弗兰克。
哦,埃默。
星期六的晚饭是冷切肉和土豆色拉,厨师用的锅碗瓢盆不多。六点时,军士对我说我的活儿干完了,星期天早上可以不用来了。不应该说这个的,他说,但那个斯尼德是个没人喜欢的讨厌的波兰鬼。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费城鹰队不要他。军士说他很抱歉,但既然我抗拒了一个直接的命令,除了让我帮厨,他什么也做不了。是的,他知道我是上校的通信员,但这是军队。对于我这样的新兵,最好的策略就是闭上嘴巴。除了你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外,什么也别说。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闭上嘴巴,尤其是如果你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如果你照办,就会完好无损地去见女朋友。
谢谢你,军士。
不客气,孩子。
除了连队办公室和被关在营房里的人外,整个连队驻地空无一人。
迪·安杰洛躺在床上。他被关在营房里,是因为在他们放完电影后,他说了句中国人是那么穷,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可以救中国。放电影的中尉说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迪·安杰洛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反美的。他怎么也不会给主义两分钱,因为信仰主义的人给世界带来麻烦。你可能注意到了,民主是没有主义的。中尉说,他说错话了。迪·安杰洛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结果他被关在营房里,三个星期不准休周末。
他在床上看邓菲下士借给我的那本《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看见我就说是从我衣柜上面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是谁把我扔到油沟里的,他说,有个周末他也那样帮过厨。邓菲告诉他如何将劳动服上的油渍弄掉。我现在应该穿着劳动服站到尽可能热的热水喷头下,只要我能承受就行,用板刷和一块他们用来洗厕所的酚皂将油渍刷掉。
当我站在喷头下擦洗的时候,邓菲探进脑袋,想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对他说了原委,他说他以前也这么干过,只不过把来复枪也带了进来,同时做所有的事。他刚参军时还是个孩子,拥有连里最干净的劳动服和来复枪。如果不是那该死的酒,他现在就是军士长,准备退休了。说到酒,他要到军人服务社喝杯啤酒,问我脱下满是肥皂泡的劳动服后,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然了。
我想邀请迪·安杰洛一起去,但他因为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而被关在营房里。当我换上卡其布军装时,我跟他说我是多么感谢毛泽东出兵朝鲜,将我从巴尔的摩酒店棕榈庭解放出来。他说我最好留神,要不然结局就会像他一样,被关在营房里。
邓菲在营房的一头叫我:快点,孩子,快点,我要去喝啤酒了。我想留下来和迪·安杰洛说话,他是那么温和。但邓菲曾帮我成为上校的通信员,这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他也许需要人陪。如果我是个正规军下士,我就不会星期六晚上在基地闲逛。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像邓菲这样喝酒、没有人陪、无家可归。现在,他在喝酒,速度快得我跟都跟不上。如果我试着跟上,就会吐。他喝酒抽烟,一直用右手的中指指着天空,跟我说,军队的生活很棒,尤其在和平时期。永远不会感到孤独,除非你像斯尼德,那个该死的橄榄球运动员,那样的浑蛋。如果你结婚,有了孩子,军队会料理一切。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作好打仗的准备。是的,是的,他说,他知道自己没有保持身体健康。但他的身体里存了那么多德国佬的弹片,都可以当作废金属卖掉了。喝酒是他唯一的乐趣。他有妻子,两个孩子,但是她们都走了,去了印第安纳州,回到了岳父岳母身边。鬼才会去印第安纳州呢。他从钱包里掏出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举起来让我看。我正要说她们是多么可爱啊,他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又咳嗽起来。我只好拍拍他的后背,防止他呛着。好了,他说,好了,该死的。每次我看她们的照片都会哭。瞧,我失态了,孩子。我原可以让她们在迪克斯要塞附近的小屋里等我的,我原可以回家的:莫妮卡做饭,我跷着双腿,穿着军士长的制服打个小盹儿。好了,孩子,我们走吧,离开这儿,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东西清理掉,然后去印第安纳州。
离营房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他变卦了,又回去喝啤酒。从这件事上看,我知道他是永远不会去印第安纳州了。他和我的父亲一样。当我躺在床铺上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否记得他大儿子二十一岁的生日,是否会在考文垂的酒馆里向我举杯。
我怀疑。父亲就像那个永远也见不到印第安纳州的邓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