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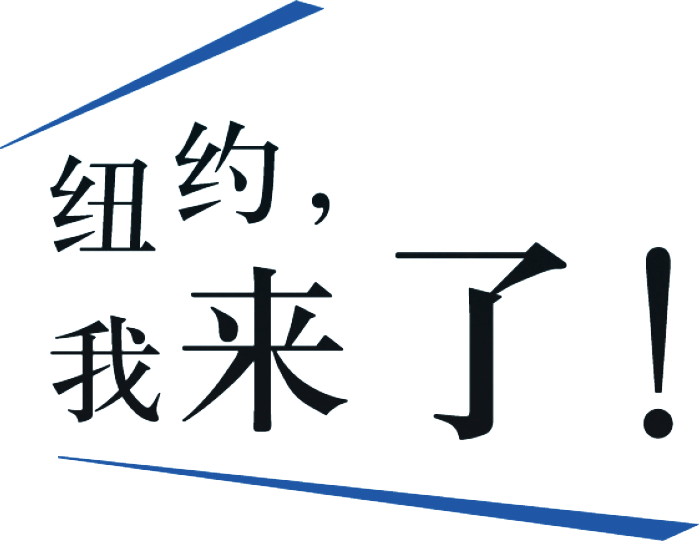
汤姆在无尾礼服舞厅和一个叫埃默的女孩跳舞。埃默是和哥哥利亚姆一起来的舞厅,利亚姆和汤姆去喝酒的时候,她就和我跳舞,尽管我不知道该怎么跳。我喜欢她,因为即使我踩到她的脚,避免撞到来自凯里郡、科克郡、梅欧郡和其他郡的男男女女而被她推着胳膊或后背往正确方向转,她都很宽容。我喜欢她,因为她很容易就笑,尽管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嘲笑我笨拙的舞步。我二十岁了,这辈子从来没有带过女孩去跳舞、看电影,甚至没有请女孩喝过茶。现在,我得学着怎么做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孩交谈,因为家里除了母亲就没有一个女孩了。我在利默里克长大,星期日听神甫们大声斥责,反对跳舞,反对和女孩逛马路。我什么也不知道。
音乐结束了。汤姆和利亚姆在吧台那边不知为什么放声大笑。我不知道该和埃默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对她怎么办。是站在舞厅中央等着下一首舞曲呢,还是应该带她到汤姆和利亚姆那儿去?如果站在这儿,就得和她说话,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果领她到汤姆和利亚姆那儿去,她就会认为我不想和她在一起,这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我很紧张,心脏跳得像机关枪,几乎无法呼吸。希望汤姆能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和利亚姆一起笑;但又不想让汤姆来打断,因为我想和埃默在一起,可汤姆并不想。就在这时,音乐再次响起,是吉特巴之类的舞蹈,男人们把女孩在空中抛来抛去,让人做梦都不敢想。我很笨,不能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可现在,我得把手放在埃默身体的某个部位,跳吉特巴。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她拿起我的手,领我来到汤姆和利亚姆大笑的地方。利亚姆说如果我在无尾礼服舞厅多待几个晚上,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弗雷德·阿斯泰尔
 。他们都笑了,知道那永远都不可能。我脸红了,因为埃默看着我的样子表明她知道的要比利亚姆说的多,也许甚至知道我的心跳得很厉害,知道我呼吸急促。
。他们都笑了,知道那永远都不可能。我脸红了,因为埃默看着我的样子表明她知道的要比利亚姆说的多,也许甚至知道我的心跳得很厉害,知道我呼吸急促。
没有高中文凭,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一天天地过着日子,不知道该如何脱身,直到朝鲜爆发了一场小战争。我被告知,如果战争扩大,就得应征入伍。埃迪·吉利根说:不会有机会的。陆军一见你那长疮的眼睛就会把你送回家交给你妈妈。
但是中国人参战了。政府来了封信,说:祝贺你。我得到白厅街报到,看是否适合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作战。汤姆·克利福德说,如果要去,我该用盐把眼睛揉疼。医生检查眼睛时,我应该呻吟。埃迪·吉利根说,我应该抱怨头疼,眼睛疼。如果他们让我读表,就给他们读错。他说我不应该当个傻瓜。可以待在巴尔的摩酒店获得提升,为什么要让一群朝鲜人把我的屁股打飞?我可以去上夜校,看看眼睛,补补牙齿,长点肉。用不了几年,我就会像凯里先生那样,身穿双排扣西服,打扮光鲜。
我不能对埃迪或汤姆或其他任何人说,我是多么想双膝跪地,感谢毛泽东派他的军队到了朝鲜,将我从巴尔的摩酒店解放出来。
白厅街的军医根本就没看我的眼睛。他们叫我读墙上的图表,说:好了。他们看了看我的耳朵,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声音。你听得见吗?很好。他们看了看我的嘴巴。上帝呀,他们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牙医。从来没有人因为牙齿而被拒绝入伍。这是件好事,因为大多数到这儿来的人牙齿都像垃圾场一样。
他们让我们在屋子里排成队。一名军士和一名内科医生走了进来,对我们说:好了,小伙子们,脱下裤子,现在开始手淫。医生挨个检查我们的阴茎中是否有分泌物排出。军士冲着一个人吼道:你!你叫什么名字?
马尔多纳多,军士。
我看见的是硬起来的吗,马尔多纳多?
噢,不是,军士。我……啊……我……啊……
你兴奋吗,马尔多纳多?
我想看看马尔多纳多。但是如果不冲正前方看,军士就会冲你吼:你到底往哪儿看哪?谁让你看的?你们这帮该死的同性恋。后来,他对我们说:转身,弯腰,把它们露出来,我是说把你们的屁股露出来。医生坐在椅子上,而我们不得不弯腰露出屁股让医生检查。
我们排队站在精神科医生的小房间外。他问我是不是喜欢女孩。我脸红了,那是个愚蠢的问题。我说:是的,先生。
那你为什么脸红呢?
我不知道,先生。
但是比起男孩,你还是更喜欢女孩吧?
是的,先生。
好了,走吧。
我们被送到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地参加迎新情况介绍,熟悉军事知识、制服和装备,还被剃光了头。他们说我们是群没用的废物,是这个营地迎来的最烂的新兵,是山姆大叔的耻辱,只能当刺刀靶子和炮灰。时刻牢记这些,你们这群拖着屁股中途退学的懒鬼。站直身子,听好了:抬头,挺胸,肩膀向后,吸起那肚子。妈的,小子。这是部队,不是他妈的美容院。噢,妞儿,你真美,周六晚上你做什么呀?
我被派到新泽西州迪克斯要塞,接受为期十六周的步兵基本训练。我们再次被告知:我们是废物,每天得嗨嗬嗨嗬嗨嗨嗨嗬地训练。到那儿站好队,士兵们。妈的,叫你们士兵真是要了我的命。你们这群军队屁股上该死的脓疱。站好队,要不然你们的肥屁股就会挨下士的靴子。嗨嗬,嗨嗬,快点,快点,齐步走,大声唱:
我在泽西城有个妞儿
她的乳头上有梅毒瘤
齐步走,数节拍
齐步走,数节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是你的来复枪。你听我说,是你的来复枪,不是他妈的卡宾枪。这个叫卡宾枪。我会拿它塞你的屁股。你的来复枪,士兵,你的枪,明白吗?这是你的来复枪,你的M1,你的枪,你军旅生涯的女朋友。这是你睡觉带着的东西,你抱着这该死的枪就像抱着女人那样,不,像紧搂着女人那样。丢了这东西,你的屁股就要挨枪子儿。丢了这东西,你就会进该死的禁闭室。一支弄丢了的来复枪是一支能发出巨响、打烂别人屁股的来复枪。真有那样的事,妞儿,你就死了,你就他妈的死了。
训练我们的人也是刚入伍的新兵,只不过比我们早几个月而已,被称为训导教官。我们得叫他们下士,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列兵。他们冲我们大喊大叫,好像对我们有深仇大恨似的。如果还嘴,你就有麻烦了。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屁股就要挨枪子儿了,士兵。
在我那个排,有些人的父亲和兄弟参加过二战,对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说在军队摧毁并重塑你之前,你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士兵的。你们带着各种鬼主意来到军队,认为自己了不起,但军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从裘力斯·他妈的恺撒时起就有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对付有个性的新兵蛋子。即使很积极地进来,军队也会将你们的积极性踢掉。积极或消极,对军队来说都不算什么,它会告诉你该想些什么,该感受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拉屎、撒尿、放屁、挤你那些该死的小脓疱。如果你不喜欢,去给国会议员写信呀。写呀。一旦让我们知道,就会踢你的小白屁股,把你从迪克斯要塞的这一边踢到他妈的那一边去,而你就会哭着去找妈妈,找姐姐,找女朋友,还有隔壁街道的妓女。
熄灯之前,我躺在床铺上,听他们谈论姑娘,家人,妈妈做的饭,爸爸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每个人都喝醉了的高中班级舞会,离开该死的军队后打算做些什么,如何迫不及待地来到戴比或苏或凯西的身边,如何上床做爱。妈的,我不要一个月都穿这该死的衣服。我要和我的妞儿、我哥哥的妞儿、任何妞儿上那该死的床,不会喘口气的。退伍的时候,给我份工作。我会开始做买卖,搬到长岛去住,每天晚上回家跟妻子说:宝贝,脱了短衬裤吧,我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有孩子,耶!
好了,小伙子们,闭上你们肮脏的屁股。熄灯了,不要发出该死的声音,要不然我就立马罚你去帮厨。
下士走了以后,聊天又开始了。哦,五周基本训练之后的第一个周末,进城,找戴比、苏、凯西、任何人。
我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例如我要在第一个周末到纽约喝个酩酊大醉。我希望自己能说些东西让大家笑笑,即使只是点点头表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好。但我知道,如果我开口说话,他们就会说:好,听听这个爱尔兰人讲讲妞儿吧。要不然,他们中的一个人——汤普森会开始唱“当爱尔兰人的眼睛微笑时”,而他们就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眼睛。
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介意这些,因为我可以在晚上洗完澡后浑身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躺在床铺上。背着六十磅的背包,下士说那比法国雇佣军的背包还要重,跑步操练了一整天,我已经很累了。一天的武器使用训练,拆卸、组装、靶场射击;在铁丝网下爬行,机枪在头顶噼啪作响;爬绳、爬树、爬墙;冲着布袋子练刺杀,喊着“他妈的朝鲜人”(下士叫我们这么做的);和戴着蓝色头盔代表敌军的其他连队在树林里摔跤;肩扛点五〇口径机枪跑上山;在泥地里爬行;背着六十磅的背包游泳;枕着背包、蚊子叮在脸上,躺在树林里睡上一个晚上。
没有野外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屋子里听讲座。讲座都是关于朝鲜人(北朝鲜人)如何危险,如何鬼鬼祟祟,而中国人甚至更坏。如果这个连有个中国人,那就不走运了。我父亲是德国人,伙计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酸白菜”变成了“自由白菜”,他不得不忍受很多的脏话。这就是战争,伙计们,可见到你们这些人,一想到美国的未来,我的心都凉了。
有一些关于美国陆军光荣历史的电影,讲述这支军队抗击英国人、法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日本佬,而且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争,从来没有。记住这些,伙计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该死的战争。
有一些电影是关于武器、战术和梅毒的。一部关于梅毒的影片叫《银色子弹》,讲述那些失去声音、奄奄一息的人们,告诉世人他们是多么的悲伤,和那些染病的外国女人约会是多么的愚蠢。现在,他们的阴茎就要掉了,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乞求上帝的宽恕,乞求家人宽恕他们、让他们回家。爸爸和妈妈在阳台上抿着柠檬水,妹妹在后院秋千上笑着,查克,那个从大学回家的四分卫在帮着推秋千。
我们排的人躺在床铺上谈论《银色子弹》。汤普森说那他妈是部愚蠢的电影。你得是个真正的马屁股才能像那样染上梅毒。我们那些避孕套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吧?迪·安杰洛,你上过大学吗?
迪·安杰洛说:你可得当心点。
汤普森说:你到底知道些啥呀,你这个该死的吃意大利面的意大利人!
迪·安杰洛说:再说一遍,汤普森,看我不把你扔出去。
汤普森笑笑:好吧,好吧。
接着说,汤普森,再说一遍。
不,你没准儿带着刀。你们意大利人都有刀。
没有刀,汤普森,只有我自己。
我不相信你,迪·安杰洛。
没有刀,汤普森。
好了。
整个排的人都很安静。我不知道为什么汤普森那种人可以那样和别人说话。那表明在这个国家,你总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美国人。
有一位正规军老下士叫邓菲,负责武器的分发和维修,浑身总是一股威士忌味道。大家都知道他早就应该被踢出军队了,但军士长托尔罩着他。托尔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肚子大得要用两根腰带才能围上,胖得到哪儿都得坐吉普车。他老是冲着我们吼叫,说受不了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我们是他不幸见到的最懒的傻大个。他对我们及全团人说,如果有人找邓菲下士麻烦,他就会赤手打断那个人的背。在我们刚开始手淫时,邓菲下士就已经在卡西诺山
 打德国佬了。
打德国佬了。
一天晚上,邓菲下士看见我用一根清洁棒上下捅来复枪的枪膛。他从我手里夺过来复枪,叫我跟他到厕所去。他把来复枪拆开,将枪管浸到热肥皂水里。我想对他说,所有训导教官都警告过我们,绝不能让枪沾上水,得用亚麻籽油,水会让枪生锈,接下来枪就会在你手里腐烂卡壳。你又怎么能保护自己不受从山那边蜂拥而至的百万敌人的攻击呢?
邓菲下士说:胡扯。然后他用清洁棒一头的布条擦干枪管,顺着枪管看了看自己的大拇指指甲,将枪管递给我。我很惊讶地发现枪管里面亮闪闪的。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我。我只能说:谢谢,军士。他对我说,我是个不错的孩子,还让我看他喜欢的书。
那是詹姆斯·T·法雷尔
 的《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本快要散架的简装书。邓菲下士要我用生命去保卫这本书。他一直在看这本书,詹姆斯·T·法雷尔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新英格兰那些胡说八道的艺术家们不同。他是一位了解你和我的作家,孩子,他说。在完成基本训练之前,我可以留着这本书。但之后,我就得自己买一本了。
的《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一本快要散架的简装书。邓菲下士要我用生命去保卫这本书。他一直在看这本书,詹姆斯·T·法雷尔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和新英格兰那些胡说八道的艺术家们不同。他是一位了解你和我的作家,孩子,他说。在完成基本训练之前,我可以留着这本书。但之后,我就得自己买一本了。
第二天,上校要来检查。吃过饭后,我们就被关在营房里洗枪、擦枪、将枪擦亮。熄灯之前,我们得站在床铺前,接受托尔军士长和两名正规军军士更为仔细的检查。他们什么事都要管,如果发现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得做五十个俯卧撑,而托尔还要把脚踩在我们背上,嘴里哼着“轻轻摇荡,心爱的马车,来把我带回家乡”。
上校没有检查每一支来复枪,但看了看我的枪管后,他后退一步,对托尔军士长说:这来复枪真干净,军士。然后他问我: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是谁,士兵?
阿尔本·巴克利,长官。
很好。说说被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的城市。
长崎,长官。
不错,军士,这是我们的人了。这来复枪真干净,士兵。
编队之后,一名军士告诉我,明天我就会成为上校的通信员,可以整天和司机一起坐他的车,为他开车门,敬礼,关车门,等待,敬礼,再开车门,敬礼,关车门。
如果我是个不错的通信员,不吊儿郎当,第二个星期就会有三天休假,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晚上。我就可以到纽约,喝个酩酊大醉。这名军士说在迪克斯要塞,没人不愿花五十美元成为上校的通信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可以仅凭一根干净的来复枪枪管得到这个职位。我究竟是从哪儿学会那样清洗来复枪的?
上校早上有两个长会。除了和司机韦德·汉森下士坐在一起,听他说话,抱怨梵蒂冈统治整个世界外,我无所事事。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出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他就移民到芬兰,芬兰限定天主教徒的活动范围。他来自缅因州,是个公理会信徒,并为此感到骄傲,不能容忍其他宗教。他的第二个表妹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不得不离开缅因州,搬到波士顿。那儿到处都是将钱财交给喜欢小男孩的教皇和主教们的天主教徒。
这一天和上校一起待的时间不长,因为他午饭时喝醉了,把我们打发走了。汉森开车把他送到住处,然后叫我下车,不希望他的车里有个鱼头。他是个下士,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但即便他是个列兵,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人们那样说话时,要理解是很困难的。
现在只有两点钟,到五点开饭之前,我没什么事,可以到军人服务社看杂志,听自动唱机里的托尼·贝内特唱“因为你,我的心里有首歌”。我梦想着那三天的休假,梦想着见到纽约的女孩埃默。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或许到一个爱尔兰舞厅,她在那儿教我舞步。那是个美梦,因为这个周末就是我的生日。我就要二十一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