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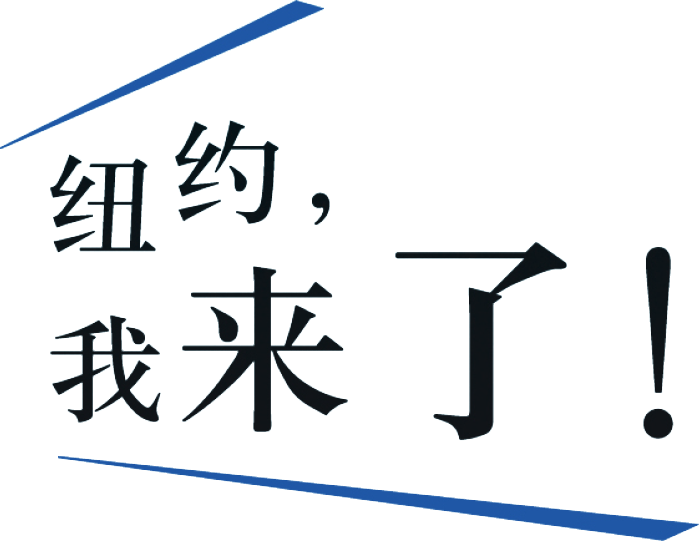
奥斯丁夫人告诉我,她那位嫁给爱尔兰人的妹妹汉娜将在圣诞节期间来,之后她们前往她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家。汉娜想见见我。我们一起吃三明治,喝圣诞酒。那样汉娜会暂时忘掉她和那位疯狂的爱尔兰人之间的烦恼。奥斯丁夫人也搞不懂汉娜为什么想跟我这样又一个爱尔兰人一起度过平安夜,但她一直有点古怪。或许她终究还是喜欢爱尔兰人的。你相信吗,二十年前在瑞典,她们的母亲就警告过她们,离爱尔兰人和犹太人远点儿,和本民族的人结婚。奥斯丁夫人不介意告诉我,她丈夫尤金有一半瑞典血统和一半匈牙利血统。尽管他好吃,但终生滴酒不沾,而这却最终要了他的命,去世时人胖得像座房子。她不做饭时,他就洗劫冰箱。他们买了台电视机后,他的末日就到了。他坐在电视机前吃呀喝呀,极为关心世界局势,以至于心脏停止了跳动。她想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特别是他们又没有孩子,这对她来说真是太难了。她妹妹汉娜有五个孩子,因为那个爱尔兰人从来不让她一个人待着。一两杯酒下肚,他就跳到她身上,典型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做派。尤金可不那样,他尊重她。无论如何,奥斯丁夫人都希望在平安夜下班后见到我。
那一天,凯里先生邀请酒店勤杂工和四个女服务生主管到他的办公室喝点圣诞酒。办公室有一瓶帕蒂牌爱尔兰威士忌和一瓶迪格·姆恩碰都不碰的四玫瑰酒。他搞不懂为什么明明可以喝爱尔兰出产的最棒的威士忌,还会有人愿意喝四玫瑰酒这种尿一样的东西。凯里先生顺着双排扣西服拍拍肚子说,对他来说,这都一样。他什么也不能喝,那会要他的命。但为了祝福圣诞快乐,他还是会喝一点的。谁能知道明年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乔伊·吉利根一整天拿着屁股口袋里那个不知道装着什么的瓶子喝,这时正咧着嘴笑呢。因为关节炎,他走起路来时不时会趔趄,这让他不能总是笑。凯里先生对他说:到这儿来,乔伊,坐到我的位子上。乔伊试着坐下时,大声呻吟了一声,脸上还挂着泪珠。女服务生主管海因斯夫人走到他跟前,将他的头搂到自己胸前,拍拍他,轻轻摇着说:哦,可怜的乔伊,可怜的乔伊。你在战时为美国付出了那么多,我不明白仁慈的上帝怎么会把你的骨头给扭伤了呢?迪格·姆恩说:该死的太平洋,那个让乔伊得关节炎的地方。人类已知的该死的疾病,那儿都有。记住,乔伊,是该死的日本佬让你得了关节炎,就像他们让我得疟疾一样。从那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乔伊,你和我。
凯里先生说:不要生气,注意点言辞,这儿还有女士在呢。迪格说:好吧,凯里先生。为此,我敬重你。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没关系。海因斯夫人说:这就对了。今天是圣诞节,必须彼此相爱,宽恕我们的敌人。迪格说:宽恕个屁。我不宽恕白人,不宽恕日本佬,但我宽恕你,乔伊。你得了那该死的关节炎,比十个印第安部落受的苦还要多。当他抓住乔伊的手要握一握时,乔伊疼得直叫。凯里先生说:迪格,迪格。海因斯夫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尊重一下乔伊的关节炎吗?迪格说:对不起,夫人,我最尊重乔伊的关节炎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起一大杯帕蒂牌威士忌送到乔伊的嘴边。
埃迪手里拿着杯子站在角落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全世界都担心他弟弟时,他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有自己的烦恼——妻子的血液感染,但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和弟弟站得近一点。
杰里·克里斯克小声说:我们得离这群疯子远点,去喝啤酒吧。因为母亲身处困境,我不想到酒吧乱花钱,但今天是圣诞节。刚才喝了点威士忌,让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感觉良好。为什么我不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像个男人一样喝威士忌。既然和杰里一起到了酒吧,我可以说说话,不用担心眼睛或别的事。现在,我就可以问问杰里为什么埃迪·吉利根对他弟弟那么冷淡。
女人,杰里说。埃迪应征入伍时和一个女孩订了婚,但在他走后,她和乔伊恋爱了。她把订婚戒指还给埃迪的时候,他都疯了,说一见到乔伊就杀了他。但是埃迪被派到了欧洲,乔伊被派到了太平洋,忙于杀其他人。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乔伊的妻子,也就是埃迪要娶的那个女人开始酗酒,使得乔伊的生活像地狱般糟糕。埃迪说这是对那个狗娘养的偷他老婆的家伙的惩罚。他自己在部队里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意大利女孩,一个陆军妇女队队员,但有血液感染。你也许会认为整个吉利根家族都遭到了诅咒。
杰里说,他认为爱尔兰母亲都是对的。应该和自己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结婚。这样就可以保证她们既不是酒鬼,也不是有血液感染病的意大利人。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笑,但满脸严肃。我什么也没说,因为知道自己不想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结婚,不想后半生拖着孩子去忏悔和领圣餐,不想在每一次见到神甫时说:是的,神甫,哦,的确是,神甫。
杰里想在酒吧再喝些啤酒。我告诉他,我得去看望奥斯丁夫人和她妹妹汉娜,他变得怒气冲冲——可以在爱尔兰三十二郡酒吧跟来自梅欧郡和凯里郡的女孩一起共度美好时光,你为什么愿意和两个至少四十岁的瑞典老女人一起过平安夜?为什么?
我没法回答他,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就是你到美国后要面临的,一个决定接着另一个决定。在利默里克,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但这是我在纽约度过的第一个平安夜。一边是杰里·克里斯克、爱尔兰三十二郡酒吧、和梅欧郡凯里郡女孩共度的美好时光;另一边是两个瑞典老女人,一个总呆呆地凝视窗外,以防我偷带食物或饮料,另一个对爱尔兰丈夫不满意,谁知道她跳起来会是什么样。我夹在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去奥斯丁夫人那儿,她可能会对我大发雷霆,叫我滚蛋。那样我就得在平安夜,拎着棕色小提箱,怀揣着在寄钱回家、付完房租、现在又不分青红皂白买啤酒后仅剩的几美元露宿街头。这样,我就没有能力支付爱尔兰女人整晚的啤酒钱。这些杰里能理解,也让他不再生气。他知道钱是得寄回家的。他说,圣诞快乐,然后笑了笑:我知道你今晚会和那两个瑞典老女孩玩得很开心。酒保竖着耳朵在听,他说:参加瑞典人的聚会,你得小心点。他们会让你喝本族酒,格拉格甜酒。你要是喝了,就分不清平安夜和圣母无沾成胎节了。那东西又黑又稠,得身强力壮才能喝。他们让你就着它吃各种各样的鱼:生鱼、咸鱼、熏鱼,任何你不会拿来喂猫的鱼,瑞典人喝格拉格甜酒。那种酒让他们变得很疯狂,还以为自己成了北欧海盗呢。
杰里说,他不知道瑞典人是北欧海盗,丹麦人才是。
才不是呢,酒保说,所有北方人都是北欧海盗。只要能见到冰的地方,就能见到北欧海盗。
杰里说,可真是见识不凡啊。酒保说,我可以给你讲一两个故事。
杰里又要了杯啤酒为我送行。我喝了,尽管不知道在凯里先生的办公室喝了两大杯威士忌,现在又和杰里喝了四杯啤酒后,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酒保的预言是对的,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充满格拉格甜酒和各种鱼的夜晚。
我们沿第三大道向北,唱着“不要搪塞我”,人们从身旁匆匆而过,为圣诞节而疯狂,狠狠地瞪我们。到处都是跳动着的圣诞节彩灯,可布鲁明黛尔百货公司外的彩灯闪得太厉害了,我不得不抓住一根第三大道高架铁的柱墩,吐了起来。杰里用拳头顶住我的肚子。都吐出来,他说,你得有肚子喝格拉格甜酒。明天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他说着“格拉格甜酒,格拉格甜酒,格拉格甜酒”,然后笑了,笑得那么厉害,几乎被汽车撞到。一个警察让我们走开,说作为尊重救世主生日的爱尔兰孩子,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该死的。
第六十七大街有个小饭馆。杰里说,在见瑞典人之前,我应该喝杯咖啡清醒一下。他付钱。我们在柜台前坐下。他告诉我,他不打算下半辈子像奴隶一样在巴尔的摩酒店干活,也不打算落得为美国而战的吉利根兄弟那样的结局。他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呢?关节炎、血液感染和酗酒的妻子,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噢,不,杰里要在阵亡将士纪念日
 那天前往卡茨基尔山
那天前往卡茨基尔山
 ,五月末,爱尔兰的阿尔卑斯山
,五月末,爱尔兰的阿尔卑斯山
 。那儿会有很多活儿:为就餐的顾客服务,打扫卫生,各种活儿都有,而且小费也不错。那儿也有犹太人,但他们给小费不是很积极,因为他们提前将所有的钱付清了,不需要带现金。爱尔兰人喝酒,钱掉在桌子或地板上,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你的了。有时候,他们会回来抗议,但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雇主付钱只是要你打扫卫生。当然,他们不相信你,会说你撒谎,骂你,但他们也只能再到别的地方花钱。卡茨基尔山上有很多女孩。有些地方有露天舞会,你只需要领着你的玛丽跳华尔兹,一直跳到树林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爱尔兰女孩到卡茨基尔山后就迷上了这种舞会。她们在施拉夫餐厅那种高级场所穿着黑色小裙系着白色小围裙干活:噢,是的,夫人;噢,的确是,夫人;土豆泥有点结块吗,夫人?她们在城市里一点希望也没有,但被带上山后,就像猫一样,有了,怀孕了。在她们明白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之前,一打又一打的肖恩和凯文就在神甫的怒视下和女孩哥哥们的威胁声中拖着屁股来到了教堂。
。那儿会有很多活儿:为就餐的顾客服务,打扫卫生,各种活儿都有,而且小费也不错。那儿也有犹太人,但他们给小费不是很积极,因为他们提前将所有的钱付清了,不需要带现金。爱尔兰人喝酒,钱掉在桌子或地板上,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你的了。有时候,他们会回来抗议,但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雇主付钱只是要你打扫卫生。当然,他们不相信你,会说你撒谎,骂你,但他们也只能再到别的地方花钱。卡茨基尔山上有很多女孩。有些地方有露天舞会,你只需要领着你的玛丽跳华尔兹,一直跳到树林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你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爱尔兰女孩到卡茨基尔山后就迷上了这种舞会。她们在施拉夫餐厅那种高级场所穿着黑色小裙系着白色小围裙干活:噢,是的,夫人;噢,的确是,夫人;土豆泥有点结块吗,夫人?她们在城市里一点希望也没有,但被带上山后,就像猫一样,有了,怀孕了。在她们明白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之前,一打又一打的肖恩和凯文就在神甫的怒视下和女孩哥哥们的威胁声中拖着屁股来到了教堂。
我很想整晚坐在那个小饭馆里,听杰里讲卡茨基尔山上的女孩,但老板说今天是平安夜,出于对基督教顾客的尊重,要打烊了,尽管他是希腊人,这真的不是他的圣诞节。杰里想知道这怎么就不是他的圣诞节了,只要往窗外看看就能明白。但希腊人说:我们不一样。
对于从来不为这类事争辩的杰里来说,这就够了。再来一杯啤酒,梦想着在卡茨基尔山的美好时光,不去和希腊人争辩圣诞节的事,这种看待生活的方式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希望能像他那样,但脑海深处总是有块乌云:等着和我一起喝格拉格甜酒的瑞典女人,或者母亲对几美元表示感谢的信。迈克尔和阿非会有鞋子了。在上帝和圣母马利亚的帮助下,我们在圣诞节会有一只不错的鹅。她从来不说自己需要鞋。我一想到这个,脑海深处就出现一块乌云。我希望能有个小隔间,可以让我溜进去释放这些乌云,但是没有。我不得不另想个办法,或者停止收集乌云。
希腊人说:晚安,先生们。我们能带些甜甜圈吗?带吧,他说,要不我就扔了。杰里说要吃个甜甜圈,好有力气走到爱尔兰三十二郡酒吧,再吃顿咸牛肉加卷心菜和粉白土豆。希腊人往袋子里装甜甜圈和甜食,对我说,我看上去像是个能体面用餐的人,所以拿着袋子。
杰里在第六十八大街对我说晚安,我希望能和他一起走。这一整天搞得我晕头转向,可还没完,瑞典人搅着格拉格甜酒,切着生鱼片,还在那儿等着呢。这么一想,我又在街上吐了起来。那些为圣诞节疯狂的行人发出厌恶的声音,从我身边走开,告诉小孩子:不要看那个恶心的家伙,他喝醉了。我想对他们说:请不要教唆小孩子厌恶我,这不是我的习惯。我的脑海深处有很多乌云,我的母亲至少有只鹅,但她需要鞋子。
但是,和那些手里牵着孩子、拿着大包小包、满脑子响着圣诞颂歌的人说这些,一点用也没有,因为他们要回家,回到明亮的公寓里。他们知道神在天堂司宇宙,世上一切皆太平,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奥斯丁夫人打开门:噢,看哪,汉娜,迈考特先生为我们买了一整袋甜甜圈和甜食。汉娜在沙发上微微挥了挥手,说:好极了,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一袋甜甜圈。我一直以为爱尔兰人会带瓶酒来,但你不一样。给这男孩来杯酒,斯蒂芬妮。
奥斯丁夫人打开门:噢,看哪,汉娜,迈考特先生为我们买了一整袋甜甜圈和甜食。汉娜在沙发上微微挥了挥手,说:好极了,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一袋甜甜圈。我一直以为爱尔兰人会带瓶酒来,但你不一样。给这男孩来杯酒,斯蒂芬妮。
汉娜在喝红酒,可奥斯丁夫人冲着桌子上的一只碗走去,用勺子舀了些黑东西倒到杯子里。格拉格甜酒。我的胃又开始翻腾,不得不强忍着。
坐下,汉娜说,我跟你说点事,爱尔兰男孩。我一点都不在乎你们爱尔兰人。你也许不错,我姐姐说你不错,你带来不错的甜甜圈,但是在骨子里,你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好了,汉娜,奥斯丁夫人说。
好了,汉娜,好了才怪呢。除了喝酒,你们这些人对世界都做了什么?斯蒂芬妮,给他些鱼,不错的瑞典食品。圆脸蛋的爱尔兰人,让我恶心,你这个小爱尔兰人。哈,哈,你听说过那里的诗吗?
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的诗。我一只手拿着格拉格甜酒,奥斯丁夫人往我的另一只手里塞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奥斯丁夫人也在喝格拉格甜酒,晃晃悠悠地从我身边走过,走到碗那儿,又走到汉娜坐的沙发。汉娜递过她的杯子又来了点红酒,咕噜一口喝了,瞪着我说:我嫁给那个爱尔兰人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十九岁。多少年前来着?上帝呀,二十二年。你呢,斯蒂芬妮?四十多年?将我的生命浪费在那个爱尔兰人身上。你在这儿干什么?谁让你来的?
奥斯丁夫人。
奥斯丁夫人。奥斯丁夫人。大点声,你这个小蠢货。喝了你的格拉格甜酒,大点声。
奥斯丁夫人拿着装着格拉格甜酒的杯子晃到我跟前。来吧,尤金,我们上床吧。
噢,我不是尤金,奥斯丁夫人。
噢。
她转过身子,摇晃着进了另一个房间。汉娜又开始喋喋不休:看吧,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是个寡妇。真希望我也是个该死的寡妇。
喝下去的格拉格甜酒让我的胃不舒服。我想冲到街上去,但门上有三道锁,还没等跑出去,我就在地下室的门厅里吐了。汉娜摇摇晃晃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叫我到厨房拿拖把和肥皂,把这该死的脏东西清理掉。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不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你就是这样对待你那仁慈的主人吗?
我拿着滴水的拖把走到门口,擦地,拧干,到厨房的水池冲洗,然后再来一遍。汉娜拍拍我的肩膀,亲吻我的耳朵,对我说我不是个太糟糕的爱尔兰人。从清理脏东西的样子可以看出,我的教养不错。她叫我不要客气,格拉格甜酒,鱼,甚至是我自己的甜甜圈,随便吃。但我把拖把放回原处,从汉娜身边走过,脑子里想着:打扫干净,就不用再听她或像她那样的人说话了。她冲我喊:你到哪儿去?你到底想到哪儿去?但我已经上了楼梯,走向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我可以躺在那儿听收音机里的圣诞颂歌。世界在周围旋转,我幻想着今后在美国的生活。如果给利默里克的任何一个人写信,告诉他们我在纽约度过的平安夜,他们一定会说是我编的,纽约一定是个疯人院。
早上,有人敲门,是戴着墨镜的奥斯丁夫人。汉娜站在楼梯下,也戴着墨镜。奥斯丁夫人说,听说我在她的公寓里发生了意外,但是没有人能责怪她或者她妹妹,因为她们提供了最好的瑞典式待客方式。如果我参加她们在某个州的小型聚会,就不会责怪她们了。真是糟透了,她们只是想要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平安夜,只是想告诉你:迈考特先生,我们一点也不欣赏你的行为。是不是,汉娜?
汉娜咳嗽着抽烟,发出一阵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她们下楼回去。我想叫住奥斯丁夫人,看她可不可以从希腊人的袋子里给我留一个甜甜圈,昨晚吐完以后我饿坏了,但她们已经出门了。透过窗户,我看到她们将圣诞包裹装进汽车,然后驾车离开。
我可以一整天站在窗前,看着幸福的人们牵着孩子到教堂去。正如他们所说,在美国就是这样。或者坐在床上看《罪与罚》,看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的结局,但这会激起各种罪恶,而我没有力气去应对。不管怎样,这不是适合圣诞节看的书。我想上街到圣文森特·费勒大教堂参加圣餐仪式,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忏悔了。我的灵魂就像奥斯丁夫人的格拉格甜酒那样黑。手牵孩子的幸福教徒一定会去圣文森特·费勒大教堂。如果跟着他们,一定能感受到圣诞节的氛围。
走进圣文森特·费勒大教堂是件高兴的事,那儿的弥撒跟利默里克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没什么两样。在萨摩亚群岛或喀布尔举行的弥撒也一样。即便在利默里克他们不让我当辅祭,我还是会说父亲教我的拉丁语,不论走到何处,我都能和神甫应答。没人能挖空我头脑里的东西:烂熟于心的所有圣徒节日、做弥撒时讲的拉丁语、爱尔兰三十二个郡的主要城镇和物产、关于爱尔兰苦难的无数歌曲,还有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
 那首可爱的诗——《荒村》。他们可以将我投入监狱并扔掉钥匙,但绝不能阻止我梦想自己环绕利默里克、沿着香农河两岸闲逛的情景,也不能阻止我思考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他的苦恼。
那首可爱的诗——《荒村》。他们可以将我投入监狱并扔掉钥匙,但绝不能阻止我梦想自己环绕利默里克、沿着香农河两岸闲逛的情景,也不能阻止我思考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他的苦恼。
去圣文森特·费勒大教堂的人很像那些去第六十八大街看《哈姆雷特》的人,会用拉丁语应答,就像了解那部戏剧一样。他们共享祈祷书,一起唱圣歌,互相笑笑,因为知道女佣布丽吉特已经回到中央大道的厨房,为他们看着火鸡。他们的儿子和女儿看上去刚从学校回来,朝长椅上也是从学校回来的人笑笑。他们有实力笑,因为有着闪闪发亮的牙齿,如果牙齿掉到雪里,就永远找不着了。
教堂很拥挤,有人站在后面。可我一直没吃东西,平安夜又喝了威士忌和格拉格甜酒,后来都吐了,身体很虚弱,我想找个座位。中间过道尽头的长椅边上有个空位。可我刚悄悄坐下,一个人就冲我扑过来。穿得一本正经,条纹裤子燕尾服,但眉头紧锁,低声说:你必须马上离开,这是常客的位置。快点,快点。我觉得自己脸红了,而那意味着眼睛更红。沿过道离开时,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这个偷偷溜到幸福家庭坐的长椅上的人。他们的孩子刚从学校回来。
即便站在教堂后面也没有什么用。他们彼此相识,会给我脸色看,所以最好离开,累累罪孽上再添一项“圣诞节不参加弥撒”这不可饶恕的大罪。至少,上帝知道我试过了。不小心坐到中央大道的幸福家庭坐的长椅上,不是我的错。
现在我肚子空空如也,很饿,想放纵一下自己,到霍恩和哈达特自动售货餐厅好好撮一顿,但又不想在那儿被人看见,人们可能认为我就像那些一杯咖啡、一张旧报纸就一坐大半天的无家可归者。几个街区外有一家Chock Full o'Nuts咖啡店。在那儿,我要了一杯豌豆汤、一个带果仁奶酪的葡萄干面包、一杯咖啡、一个带白糖的甜甜圈,还看了份别人留下的《美国人》杂志。
现在只是下午两点。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门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手里牵着孩子的过往行人可能以为我无家可归,所以我昂着头,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好像急着赶火鸡宴似的。我希望能推开某一扇门,听到人们说:嘿,你好,弗兰克,你真准时。纽约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带着礼物,收到礼物,享受圣诞节大餐,绝不会知道有人在这个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普通的纽约人:晚饭吃得饱饱的,伴着收音机里的圣诞颂歌和家人交谈。我不介意回到利默里克,和母亲、弟弟们,还有那只不错的鹅在一起,但是现在我在这个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纽约。沿着这些连一只鸟也看不见的街道走了那么久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
我无所事事,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听收音机,看《罪与罚》,搞不懂为什么俄国人办事拖沓,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纽约侦探会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那样除了谋杀老妇人之外什么都谈的人一起四处闲逛。纽约侦探会抓住他,控告他,接下来就是辛辛监狱的电椅了。美国人都很忙碌,侦探没时间和那些他们认为犯了谋杀罪的人闲聊。
有人敲门,是奥斯丁夫人。迈考特先生,她说,你能下楼一会儿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她妹妹昨晚那样说我,她今天早上那样奚落我之后,我想叫她亲我的屁股,但还是跟她下了楼。楼下的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她说这都是她从妹妹家带来的,还说她们担心我可能在这个美丽的日子里没地方可去或没东西可吃。她对今天早上对我说话的态度表示歉意,希望我能有个宽容的心态。
桌上有火鸡、馅料和各种土豆,白的、黄的,配上让所有东西都变得甜甜的越橘酱。这让我有了个宽容的心态。她给我倒了点格拉格甜酒,但她妹妹把它倒了。这样最好,那东西让所有人不舒服。
吃完后,她邀请我坐下看她新买的电视机。电视里放着关于基督的节目,内容是那么神圣,我都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她家壁炉上的钟正指向凌晨四点二十分。奥斯丁夫人在另一个房间里小声地哭泣:尤金,尤金。那证明你要是有个妹妹,就可以到她家吃圣诞晚餐,但如果没有了你的尤金,就和坐在自动售货餐厅里的人一样孤独。知道在利默里克的母亲和弟弟们有只鹅,这让我感到宽慰。明年,被提升为巴尔的摩酒店餐厅勤杂工时,我会给他们寄钱,让他们在利默里克溜达,用新鞋叫众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