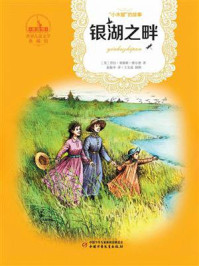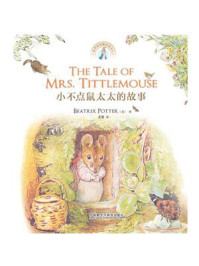日子还是一天天地继续着,冬天依然没有过去。姥姥每天夜里都会虔诚地祷告,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她向上帝祈求赐福与帮助。
姥姥会把家里的事一点儿不落地告诉上帝。她祈求上帝开导执拗的姥爷,祈求上帝让我的母亲快乐一些,祈求上帝别忘了格里高里……她几乎向上帝倾诉一切,就好像上帝是她可亲的邻居一样。有时候,她祈祷的时间很长,我在被窝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一天,姥姥正跪着虔诚地祷告,姥爷突然闯了进来,吼道:“上帝来了!老婆子,着火了!”
“你说什么?啊——”姥姥腾地一下从地板上跳起来,飞奔着跑了出去。很快,外面就传来了她着急的指挥声:“叶芙格妮娅,把圣像取下来!娜塔莉娅,快给孩子们穿衣服!”姥爷明显被吓坏了,他在院子里大声地哀号着。
我跑进厨房。厨房地板上是闪烁着的红光,整个屋子被火焰照得红红的。 染坊的房顶上,火舌舒卷着,舔着门和窗。 外面一片混乱,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和姥爷、舅舅们、格里高里的叫喊声响成一片。
这里运用了拟物的修辞手法,将火比喻成舌头,生动地描绘出火势之大。
“混蛋们,硫酸盐要爆炸了!”姥爷高喊着。人群中的姥姥突然大叫一声,然后顶着一个空口袋,身披一条湿被子,飞也似的冲进了火海。
“啊,格里高里,快拉住她!快!唉,这下她算完啦……”姥爷狂叫着,但谁也没能拦住姥姥。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我才看见姥姥钻了出来,她两手端着一大盆硫酸盐,浑身上下都在冒烟。
“还不快给我脱下来!我都快烧着了!”姥姥哑着嗓子叫喊着。姥爷赶忙跑上去,急匆匆地将地上的雪往姥姥身上撒。
染坊的房顶塌了,从几根梁柱上蹿起来的烟直冲上天空。染坊里噼啪乱响,火苗乱蹿。大火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突然,一个人骑着马闯进了院子。他戴着铜盔,高举着鞭子,喊道:“快闪开!”
警察来了,火势被压了下去,最后火终于被扑灭了。
天黑了,姥姥走进厨房,坐在我身旁。一切好像又跟以前一样了。
姥爷走进来,点上蜡烛,挨着姥姥坐了下来。
“你去洗洗吧!”姥姥对姥爷说——其实她的脸上也满是灰尘。
姥爷叹了一口气,说:“上帝大发慈悲,赐给了你智慧,否则……”姥爷还没把话说完,门外就传来了雅科夫舅舅的哭声。姥姥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和姥爷并排坐着,沉默着。过了半天,姥爷也没有看我,只是轻声地说:“你姥姥怎么样?她岁数大了,一辈子受苦,又有病,可她还是很能干!唉,你们这些人啊……”
【 姥爷没有接着往下说,转而催促我去睡觉。可是我刚躺到炕上,一阵号叫声又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我跑到厨房里,看到姥爷和舅舅们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着,姥姥吆喝着他们,让他们闪开。
格里高里把柴火填进火炉,又往铁罐里倒上水。他晃着大脑袋来回走着,就像一只大骆驼。
“先把火生起来!”姥姥指挥着。
格里高里赶紧去找松明,却一下子摸到了我的脚。他吓了一跳,喊道:“啊,是谁啊?吓死我啦,你这个小鬼!”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我问。
“你的娜塔莉娅舅妈在生孩子!”格里高里面无表情地回答。所有人都忙乱着,听从姥姥的指挥。我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 】
【姥爷没有……打起了瞌睡。】
拿姥爷和舅舅们的惊慌失措与姥姥的沉着冷静作对比,鲜明地刻画出姥姥坚韧、果敢的性格特点,强调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主心骨地位。
嘈杂的人声、关门声、喝醉了的米哈伊尔舅舅的叫喊声不断把我吵醒。我从炕上跳下来,火炕烧得实在是太热了。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抓住我的脚踝,一使劲,我就仰面倒了下去,脑袋砸在了地板上。
“混蛋!”我大骂道。
米哈伊尔舅舅跳起来,把我抓起来又摔在地上,“摔死你这个王八蛋……”
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姥爷的膝盖上。他仰着头,摇晃着我,念叨着:“我们都是上帝的不肖子孙,谁也得不到宽恕,谁也得不到……”
我往周围看去,一切都显得很奇怪:大厅里的椅子上坐满了陌生人,有神父,有穿军装的老头子,还有些说不上是干什么的人。
我又被打发去睡觉了。雅科夫舅舅把我送到姥姥的房间时,低声对我说:“你的娜塔莉娅舅妈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因为娜塔莉娅舅妈已经很长时间没露面了,她既不去餐厅吃饭,也不出门。但是我很害怕,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后来,门开了,姥姥几乎是爬着进来的。她对着长明灯伸出两只手,孩子般地哀叫着:“疼啊,我的手!”
连续经历了大火和儿媳难产而死这两件事之后,姥姥已经筋疲力尽了,“孩子般地哀叫着”表明了姥姥深深的无助感。
冬去春来,姥爷和舅舅们分家了。雅科夫舅舅分在了城里,米哈伊尔舅舅分到了河对岸。
姥爷在波列沃伊大街上买了一座很有意思的大宅子:楼下是酒馆,楼上还有阁楼,后花园外是一座山谷,到处都种着柳树。这座宅子里住满了房客,姥爷只在楼上给自己留了一间房,姥姥和我则住在顶楼。
每天一大早,姥爷就到两个舅舅的染坊里去转转,给他们帮帮忙。晚上回来时,他总是一副又累又生气的样子。姥姥在家做饭、缝衣服,在后花园里种地,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每天 从早到晚 ,院子里都有房客 来来往往 ,邻居家的女人们也经常跑过来说这说那。 有时,还会有人来向姥姥求助,这时候,姥姥就会教给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
每天”、“从早到晚”、“来来往往”充分体现了姥姥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性格特点。
我就像姥姥的尾巴一样,整天跟在她后面,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还跟着她串门。有时候她在别人家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喝茶,一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喜欢听姥姥讲故事。有一回,她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我母亲很穷,右手也摔残了,所以地主赶走了她。就这样,她不得不到处流浪,乞讨为生。每年一到秋天,我和母亲就留在城里要饭或织花边卖。等到冬天过去,我们就继续向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也不管那是什么地方。
“后来,我母亲的右手萎缩了。对一个靠卖花边维持生计的女人来说,这可是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到处流浪、乞讨。那时候,人们比现在富有,木匠和织花边的人们都很善良。 流浪的生活虽然很穷苦,但也很好玩儿。 可是我逐渐长大,母亲觉得再领着我到处要饭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每天她都到街上去挨家挨户地乞讨,每逢节日,就到教堂门口去等待人们的施舍。
流浪、乞讨的生活对一般人来说是穷苦而窘迫的,而姥姥却能苦中作乐,觉得“很好玩儿”,体现了她积极乐观的心态。
“我呢,就坐在家里学习织花边。我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全学会了,而且手艺在城里还小有名气,人们来找我做手工时,都会说:‘喂,阿库莉娜,给我织一件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像过节似的!
“我说:‘妈妈,你不用再去要饭了,我可以养活你啦!’她说:‘你给我闭嘴!你要知道,这些钱是攒给你买嫁妆的!’后来你姥爷出现了,他是个出众的小伙子,才22岁就当上了一艘大船的工长!”
说到这里,姥姥笑了起来,鼻子微微地颤动着,眼睛闪闪发光。这时候的姥姥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我还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傍晚,我和姥姥在姥爷的屋子里喝茶。
姥爷身体不好,斜坐在床上。他没穿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手巾,隔一会儿就擦一次汗。我靠窗坐着,仰头望着天空的晚霞——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误,所以姥爷禁止我到屋外去玩。
【 花园里,甲壳虫围着白桦树嗡嗡地飞着。隔壁院子里,木匠正在工作,不时传来敲打物体的当当声,还有霍霍的磨刀声。花园外的山谷里,孩子们在灌木丛中乱跑乱跳,吵闹声不断地传过来。 】
【花园里……传过来。】
环境描写,展现了屋外一派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景象,暗示了“我”对外面的美好事物的向往。
一股黄昏的惆怅涌上心头,我非常想到外面去玩。
突然,姥爷拍了我一下,兴致勃勃地要教我认字。他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新书,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
“来来来,小鬼,你这个高颧骨的家伙,看看这是什么字?”
我回答了。
“啊,对了!那这个呢?”
我又回答了。
“不对,混蛋!”姥爷骂了我一句。
姥姥插嘴道:“老头子,你就老老实实地躺一会儿吧。”
“你别管我!我得教他认字才觉着舒服,否则老是胡思乱想!好了,往下念,阿列克塞!”姥爷用一只滚烫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把书摆在我的面前,另一只胳膊则越过我的肩膀,用手指头点着字母。
他把字母表颠来倒去地念,顺着问、倒着问、打乱了顺序问。
我也来了劲,头上冒着汗,扯着嗓子喊。
姥爷可能觉得这很好笑,拍着胸脯咳嗽着。他揉皱了书,哑着嗓子说:“老太婆,听听这小子的嗓门有多大!喂,喂,你这个小家伙,你喊什么?嗯?喊什么?”

“不是您先喊的嘛……”
姥爷拍着胸脯咳嗽着,哑着嗓子说:“我喊是因为我身体不好。你呢?你是为什么?”
姥爷没有等我回答,就摇着头对姥姥说:“死了的娜塔莉娅说这小子的记性不好,这可没说准! 你看看,他的记性像马记得走过的路一样好! 好啦,小翘鼻子,继续念!”
有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出自《韩非子·说林上》,意思是老马认识曾经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比较熟悉。
我高声地念下去。最后,姥爷笑着把我从床上推了下去,说:“好,把这本书拿走吧!明天,你必须把所有的字母念给我听,如果都念对了,我就给你五个戈比作奖励!”
我认字认得很快,姥爷对我也越来越关心,很少再打我了。不久我就能念诗了,在喝过晚茶以后,我还会给大家读圣歌。
我一边用字棒指着书,一边念着,觉得很乏味。
“姥爷!”我叫了一声。
“啊?”
“讲个故事吧!”
“懒鬼,你继续念吧!”姥爷揉了揉眼睛,好像刚刚醒过来似的。
我不停地恳求,姥爷终于让步了。
“好吧好吧! 诗篇永远都在心里,我快要去上帝那儿接受审判了…… ”说着,他往那把椅子的镶花靠背上一仰,望着天花板,讲起了陈年旧事。
姥爷将自己的故事比喻成诗,说明对姥爷来说这些故事是美好的、刻骨铭心的。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住的地方来了一伙土匪。我爷爷的爸爸去报警,土匪追上他,用马刀把他砍死了,扔在大钟下面。那时候,我还很小。
“我记得在1812年,当时我刚12岁。巴拉赫纳来了三十多个法国俘虏。后来,大家和这些法国人混得很熟。他们都是些快乐的人,经常唱歌。”
沉默了一会儿,姥爷用手摸了一下头,继续追忆逝去的岁月,“冬天,暴风雪横扫了整座城市,天气冷极了,简直要冻死人!很多法国人不习惯这么冷的天气,被冻死了。我们的菜园里有间浴室,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军官奇瘦无比,皮包着骨头,穿一件只到膝盖的女式外套。他为人很和气,可嗜酒如命。
“我妈妈偷偷地酿啤酒卖,那个军官总是买回去喝,喝完了就唱歌。勤务兵米郎特别喜欢马,经常去别人家的院子里,比划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他是个红头发、大鼻子的家伙,嘴唇特别厚。养马是他的拿手活儿,他给马治病的技术也是一绝。后来,他在尼日尼做了马医,但是不久就疯了,被活活打死了。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尼古拉纪念日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坐在窗前,后来把头伸到窗户外面,就这样死了。
“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那个军官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
天完全黑了下来。黑暗中,姥爷的身体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像猫眼一样闪着亮亮的光。他语气激烈、表情狂热,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我们谈话的时候,姥姥走了进来。她坐在角落里,很久也不吭一声。偶尔她会温柔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的事?多好啊!那是哪一年来着?”
姥爷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那是在霍乱大流行之前,在树林里捉奥郎涅茨人的那一年吧?”
“是的,是的!”
姥姥又说:“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姥爷很严肃地问:“哪一次大火?”
于是他们开始一起回忆过去,把我给忘了。
【 他们用不高的声音一句一句地回忆着, 好像在唱歌 ,但都是些不怎么快乐的歌:疾病、暴亡、失火、打架、乞丐、老爷…… 】
【他们用……老爷……】
这里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姥姥和姥爷回忆过去时一问一答的情形比喻成唱歌,体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与温情。
慢慢地,他们谈到了我的母亲瓦尔瓦拉,谈到了两个舅舅。姥爷的情绪突然变得特别差,他有些不能自控地乱喊乱叫起来,骂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
“都是你!是你把他们惯坏了,臭老婆子!”姥爷向姥姥挥舞着瘦小的拳头。如果和往常一样,我和姥姥一起回顶楼去睡觉也就没事了,可这次姥姥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
姥爷却猛地一翻身,抡起拳头,啪的一声打在了姥姥的脸上。
姥姥被打得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了。她的嘴唇被打破了,出了血。 她用手按住嘴唇上流血的伤口,低声说:“ 你这个小傻瓜 !”然后不慌不忙地向门口走去。
这句简单的话虽然是姥姥对姥爷的嗔怪,但更刻画出姥姥对姥爷的无限宽容。
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让我难以置信,这是姥爷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姥姥,我觉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过了许久,姥爷才痛苦地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屋子中间,跪下往前一趴,又直起上身,捶胸喊道:“上帝啊,上帝啊……”
我跑到姥姥身边,姥姥还在顶楼上漱口。
“他为什么这样?”我问姥姥。
姥姥看了看窗外,说:“你姥爷总是感到事事不如意,所以老发脾气……你快睡吧,别想这些了……”
姥姥在窗边坐下,吸溜着嘴唇,不断往手绢里吐着带血的唾沫。
我上了床,一边脱衣服,一边看着姥姥。 她头顶上方青色的窗户外,星光闪闪。
“一边……一边……”这一并列关联词的使用,表明“我”对姥姥的关心。
街上很静,屋子里很黑。
姥姥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睡吧。我去看看你姥爷……你不要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错……睡吧!”她亲了亲我就走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清冷的街道发起呆来。
有一天晚上,喝过茶以后,姥爷和我坐着念诗,姥姥在洗盘子和碗,突然,雅科夫舅舅闯了进来,满头的乱发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雅科夫舅舅不问好,也不看谁,把帽子一扔,挥着两手叨叨起来:“爸爸,米希加疯了!他在我那儿吃晚饭,可能是多喝了两杯,结果又砸桌子又砸碗,把一件染好的毛料撕成了一条一条的,把窗户也给砸坏了。他还没完没了地欺负我和格里高里!现在他正往这儿来,说要杀了您!您可要小心啊……”
【 姥爷用手把身体慢慢地撑起来,脸皱成了一把斧头,眼珠几乎瞪了出来,说:“听见没有,老太婆?好啊,杀他爹来了,亲生儿子啊……” 】
【姥爷用手……亲生儿子啊……”】
这里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姥爷的脸比作一把斧头,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姥爷极度愤怒的神态。
姥爷端着肩膀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突然伸手把门关上了,并带上了沉重的门钩。他转身问雅科夫舅舅:“是不是不把瓦尔瓦拉的嫁妆拿到手你就不甘心?是不是?”
雅科夫舅舅作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爸爸,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关不关你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什么东西!”
“我是来保护您的……”
“好啊,保护我!好极了,老太婆,快给这只狐狸一件武器,雅科夫·华西里耶维奇,你哥哥一冲进来,你就对准他的脑袋打!我知道,是你灌醉了他,是你让他这么干的!”姥爷怒吼道。
姥姥悄悄对我说:“快,去上面的小窗户那儿,你的米哈伊尔舅舅一露面,你就下来告诉我们!”
我跑上楼,从小窗户往外认真地注视着街道。秋雨冲洗过的矮矮的屋顶又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挤挤挨挨的,就像教堂门口的叫花子。所有窗户都瞪着眼睛,它们大概和我一样,在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 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心沉了下来。墙壁在推我,而我的身体里好像也有东西在向外撑,像是要挣断我的肋骨,撑破我的胸膛。 】
【我感到了……我的胸膛。】
这里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手法,将静止的“墙壁”比作动作发出者,进一步强调了“我”极度压抑的情绪。
是他,米哈伊尔舅舅!他东张西望地出现在了街口,我看见他蹑手蹑脚地朝酒馆走来。哗啦,是他在开酒馆的门。
我飞也似的跑下楼去,敲响了姥爷的门。
“谁?”
“我!”
“他进了酒馆?好吧,你去楼上待着!”
我只好又上楼去了,趴在窗户上。
天黑了,远处的窗户睁开了淡黄色的眼睛,不知道是谁在弹琴,悠扬而忧郁的琴声一阵阵地从远处传来。我就像在做梦一样,感到非常疲惫。我希望有个人能够陪在我身边,最好是姥姥,姥爷也行!
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姥爷和舅舅们那么不喜欢他?为什么姥姥、格里高里和叶芙格妮娅谈起他来却那么怀念?母亲又去哪儿了呢?
我越来越多地想起母亲,逐渐把她当作姥姥所讲的童话中的主人公。母亲的离家出走使我觉得她更富有传奇色彩了。我觉得她现在已经成了绿林好汉,住在路旁的森林里,杀富济贫。
突然,楼下的吼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
我赶紧往窗下一看,只见姥爷、雅科夫舅舅和酒馆的伙计麦瑞昂正把米哈伊尔舅舅往外拉。
米哈伊尔舅舅抓住门框,硬是不走。他们打他、踢他、砸他,最后把他扔到了街道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虽然我们在这座宅子里总共也就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从第一个春天到第二个春天,可是我们的名声传得很远,每周都会有一群孩子跑到门口,欢呼着:“卡什林家又打架了!”
天一黑,米哈伊尔舅舅就会来到宅子附近,等待时机下手,搞得大家都提心吊胆的。他有时候还会找几个帮凶,这些人不是醉鬼就是小流氓。他们拔掉了花园里的花草树木,捣毁了浴室,把蒸汽浴的架子、长凳、锅全都砸了,甚至连门也没放过。
姥爷站在窗前,脸色阴沉地听任别人破坏他的财产。
有一回,也是这么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姥爷病了。他躺在床上,头上包着手巾,在床上痛苦地翻来覆去。他大叫着:“辛苦一生,攒钱攒了一辈子,结果落得这么个下场!如果不是害臊,我早把警察叫来了!唉,丢人现眼啊!叫警察来管自己的孩子,无能的父母啊!”
说着说着,姥爷突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窗前。 他像拿着一把枪一样端着烛台,冲着窗口大吼道:“米希加,小偷!癞皮狗!”
这里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将烛台比喻成枪,表达了姥爷对儿子的强烈愤怒。
话音未落,一块砖头哗的一声破窗而入!
“没打着!”姥爷哈哈大笑,这笑声却像在哭。姥姥一把将他拖回床上,就像拖着我似的。
我抓起那块砖头,向窗口冲去。姥姥一把抓住我,喊道:“浑小子,干什么?”
有一次,米哈伊尔舅舅拿着一根大木棒撞门。
姥爷、两个房客和高个子酒馆老板的妻子都在屋子里,大家拿着武器,只等着他冲进来。
姥姥哀求道:“让我出去见见他,跟他谈谈……”姥爷不出声,却固执地用身体将姥姥往身后推。
门旁边的墙上有一扇小窗户,窗户上的玻璃已经被米哈伊尔舅舅打碎了,看起来就像一只被挖掉了眼珠的眼睛。
姥姥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伸出一只胳膊,向外面摆着手,大叫道:“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走吧!他们要把你打残啊!你快跑!”
米哈伊尔舅舅在外面,照着姥姥的胳膊就是一棍子。姥姥倒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米……沙……快……跑……”
门一下子被撞开了,米哈伊尔舅舅冲了进来。屋里的几个人一齐动手,一下子就把他扔了出去。
酒馆老板的妻子把姥姥搀回姥爷的屋子里。姥姥开始痛苦地呻吟,她的手臂骨折了。
姥爷他们把米哈伊尔舅舅捆了起来,然后给姥姥找了正骨婆。我再一次被赶到楼上去了。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姥爷有一个上帝,姥姥的上帝则是另一个。 每天,姥姥都能找到新的词句来赞美圣母,而我也每次都会全神贯注地听她祈祷。
姥爷和姥姥信奉的上帝各有不同,象征了姥爷和姥姥迥异的性格特点。
姥姥祈祷时,含笑的双眼炯炯有神,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她抬起沉重的手,在胸前缓缓地画着十字。在早晨,姥姥祈祷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因为她要烧茶。如果到了喝茶的时间她还没把茶备好,姥爷就会大骂不止。
有时候,姥爷比姥姥起得早,他来到顶楼,如果碰上姥姥在祈祷,就会轻蔑地撇一撇嘴。等到喝茶时,他就会说:“我教过你多少次了? 你这个 榆木脑袋 ,老是按你自己那一套来,简直是个异教徒,上帝能容忍你吗? ”
“榆木脑袋——不开窍”是一句歇后语,比喻思想顽固,不会变通。
“他理解我,不论我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会懂的。”姥姥回答道。
姥姥的上帝永远与她相随,她甚至会跟牲畜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蜜蜂、草木,都会听从姥姥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同样的慈祥、同样的亲切。
我觉得姥姥的上帝很好理解,也不可怕,但是在他面前你一点儿谎也不能说,因为你不好意思那么干。上帝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廉耻,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对姥姥说半句谎话。
有一次,酒馆老板的妻子跟姥爷吵架,连姥姥也一起骂上了,还向姥姥扔胡萝卜。
姥姥没有生气,只是安详地说:“你可真糊涂!”我却气坏了,发誓要报复那个胖女人。
一天,酒馆女主人下了地窖。我看准机会,合上地窖的盖子,并上了锁。在上面跳了一通复仇者之舞后,我把钥匙扔到了屋顶,然后一溜烟跑回厨房去了。
姥姥正在做饭。一开始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可等问清楚之后,她就生气了。她朝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命令我立刻把钥匙找回来。
酒馆女主人出来后,姥姥和她友善地谈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大笑起来。
没过多久,姥姥就把我揪回厨房里,开始盘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谁让她拿胡萝卜打你……”我回答道。
“哦,原来是为了我!”
姥姥一整天没理我。做晚祷之前,她坐在我身边,说了几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她说:“亲爱的,你要记住,不要介入大人的事情!大人正在接受上帝的考验,因为他们都学坏了,而你没有,你应该按一个孩子的方式去生活。至于谁犯了什么错,这可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有时候上帝也不清楚。”
姥爷也说过,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见,不论什么事他都会给人们善意的帮助。
可是,姥爷的祈祷和姥姥截然不同。每天早晨,他总是洗干净脸,穿上整洁的衣服,梳理好棕色的头发,理理胡子,照照镜子,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走到圣像前。
姥爷总是在那块有马眼似的大木疤的地板上站定,不吭声地站一会儿,低着头,像个士兵似的。然后,他会庄严地开口:“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审判者必将到来,每个人的行为都必有应得……” 屋子里一下子就 肃穆 起来,连苍蝇都 飞得小心翼翼的 。姥爷在给我讲上帝的无限力量时,总是强调这种力量的残酷。他说:“人如果犯了罪,就会被淹死或者被烧死,而且他们的城市要被毁灭。上帝用饥荒和瘟疫惩罚人类,用宝剑和皮鞭统治世界。”
这里运用了拟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用“飞得小心翼翼的”来形容苍蝇,进一步强化和渲染了屋子里异常“肃穆”的氛围。
姥爷的圣人都是受难者,因为他们踢倒了神像,反对罗马教皇,所以他们受刑,被剥了皮烧死了。
姥爷经常领我到教堂去,每周六去做晚祷,假期则去做晚弥撒。
在教堂,我也把人们对上帝的祈祷加以区别:神父和助祭所念的一切是在向姥爷的上帝祈祷,而唱诗班所赞颂的则是姥姥的上帝。
姥爷的上帝让我恐惧,并对他产生敌意,因为他谁也不爱,永远严厉地注视着一切,一刻不停地寻找人类罪恶的一面。而姥姥的上帝则热爱一切生灵,我沉浸在他爱的光辉之中。
在那段时间,上帝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我的头脑中如果说还有任何别的印象的话,也都是生活中那些残暴污浊的、丑陋的东西。
我”在精神上对上帝极为依赖,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残暴污浊的、丑陋的东西”对“我”的冲击之大,让“我”除了信仰上帝,无所寄托。
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姥爷就看不见那个慈祥的上帝呢?
家里的人从不让我上街去玩,他们说街上太污浊了。我的生活因此变得沉闷,一种喝醉了酒般的感觉让我整天心情沉重。
我没有什么朋友,街上的孩子们都仇视我;我越不喜欢他们叫我卡什林,他们就越起劲地故意这么叫。
我非常生气,冲上去和他们打架。论岁数,我并不比他们小,力气也还可以,可他们几乎是整条街上所有的孩子啊。每次我都寡不敌众,回家的时候总是鼻青脸肿的。
姥姥见我这样,惊骇而又怜悯地叫道:“哎呀,怎么啦,小萝卜头?打架啦?瞧瞧你这个惨样……”
姥姥给我洗脸,然后在青肿的地方贴上湿海绵,还劝我说:“不要老打架了!你在家挺老实的,怎么到了街上就不一样了呢?我要是告诉你姥爷,他非把你关起来不可……”
但姥爷看见鼻青脸肿的我从来不骂,只是说:“又带上奖章了?你这个阿尼克武士,不许你再上街了,听见了没有?”
我对静悄悄的大街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孩子们在外面一闹,我就抑制不住地想要跑出去。
最让人难过的是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他瞎了,靠沿街乞讨生活。 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牵着他的手,他木然地迈着步子,高大的身体挺得笔直,一声不吭。
格里高里虽然处境艰难,却依然保持着尊严,始终不卑不亢。
那个老太婆领着他,走到别人家的门口或窗前说:“行行好吧,可怜可怜这个瞎子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经常见到这幅惨景,可从来没听格里高里说过一句话。我感到胸口压抑得难受!
每次遇见他,我都远远地躲开,并跑回家去告诉姥姥:“格里高里在街上要饭呢!”
“啊!”姥姥惊叫一声。
“拿着,快给他送去!”姥姥递给我一些东西,吩咐道。
我断然拒绝了,于是,姥姥便亲自走到街上,和格里高里交谈。
格里高里总是面带微笑,像个散步的老人一样捻着胡须。他即使开口也不过是三言两语,没有太多的话。
有时候,姥姥会把他领到家里来吃些东西。
有一次,姥姥把他送走以后,慢慢地走回来,低着头哭泣。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她看了看我说:“他是个好人,很喜欢你,你为什么躲着他?”
“姥爷为什么把他赶出去?”我反问道。
“哦,你姥爷……”姥姥停住了脚步,搂住我,几乎是耳语似的说,“记住我的话,上帝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一定会惩罚……”
果然,十年以后,惩罚终于到了,那时姥姥已经永远地安息了。 姥爷疯疯癫癫地沿街乞讨,低声哀告着:“给口吃的吧,行行好吧!给口吃的吧!唉,你们这些人啊……”
这里运用了跳叙的写作手法,将时间跨越到“十年以后”,叙述了姥爷沿街乞讨的悲惨境地,是对“惩罚”一词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