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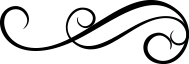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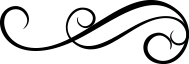
她磨了一个表姐过来给她做头发,单纯为了好玩,前刘海用火钳烫作卷发,堆砌成云笼雾罩的一大蓬。辫子没动,只拿粉色丝带紧紧绕了两寸长短。毛糙的巨型波浪烘托出脸庞与两根乌油油的辫子。她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去帅府,有个姨太太生日。听说老帅父子俩正在奉天,今年也许不摆酒了。她一夜伏着桌子睡觉,脸埋在肘弯里,头发微微烧焦的气味使她兴奋。
他在家。但是在陈家的这些热闹中常常会有这么一刻,盛大的日子在她身边荡荡流过,平滑中略有起伏,仿佛一条太阳晒暖的大河,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辜负这样的时光。那些戏她全都看过了,最好的男旦压轴才上场。那丑角挥着黑扇子念出一段快板献寿,谁也不去听他。她跟着另外几个女孩子瞎逛。洛阳牡丹盆栽——据说是用牛奶浇灌的——叠成的一座假山,披挂着一串串五彩电灯泡,中间摆得下一张饭桌。今天变魔术的是个日本女人,才在上海表演过的,想必精彩。她们在少帅书房里议论戏码单,他好奇地瞥了她两眼,然后几乎再不看她。是头发的缘故。她顶着那个热腾腾的云海,沁出汗珠来。几个月不见,她现在大了,他不再逗她了。朱家姊妹不在,其他女孩子也都没什么话说。他把别人从杭州捎给他的小玩意分赠她们。
“咱们走吧,魔术师该上场了。”一个女孩子说。
她正要跟着出去,他说:“这柄扇子是给你的。”
她展开那把檀香扇,端详着。
“现在是大姑娘了,不再搭理人了。”
“啊?”
“而且这么时髦。要定亲了。”
“哪儿来的这些昏话?”她不禁红了脸。他以前从来不和她开这种玩笑,老太太们才喜欢这样说。
“你不肯说。喜酒也不请我吃啰?”
“别胡说。”听上去不像是戏言了。临头灾祸陡然举起她,放到成年人中间。
“唔?那我等着吃喜酒了。”
“呸!”她作势一啐,转身要走,“你今天怎么了?”
“好好,对不起,是我多管闲事。”
“这些话都是打哪儿来的?”
“你真没听说?”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有焦急的神色,一闪而过。
“没有的事儿。”
“唐家人正在给你说媒。”
“没这事儿。反正我不会答应的。”
他笑了,“你不答应有什么用?”
“杀了我也不答应。”机会来了,为他而死并表明心迹。
“不如告诉他们说五老姨太认了你做女儿,你的终身有她来安排。”
“我永远不结婚。”
“为什么?”
“不想。”
“那你一辈子做老姑娘是要干什么呢?上大学?出洋?做我的秘书陪我一道出洋,好不好?你在看什么?”他凑近看看折扇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她着迷。
“我在数数儿。”
“数什么?”
“美人儿。”
他逐一点算花园中亭子里的彩绘人物,“十。”“十一。”
“应该是十二。通常有十二个。”
“窗子里的这个我数漏了。正好是十二。”
“这个我数过。这儿,树后面还有一个。”
“一、二、三、四……”她数出十个。
靠得这样近,两人都有些恍惚,每次得到的数目都不同。他终于一把捉住她,轻轻窘笑了一声,“这儿还有另一个。”
“让我数完。”
“这儿的一个呢?一丁点儿大,刚才都没看见。”
他不放开她的手腕,牵起来细看,“怎么这么瘦?你从前不是这样的。”
她立即羞愧自己始终没长到别人期望的那么美,只好咕哝一句:“只不过是最近。”
“最近不舒服吗?”
“不,只是没胃口。”
“为什么?”
她不答。
“为什么?”
她越是低着头,越是觉得沉重得无法抬起头来。
“不是因为我吧?”
他撩起她的前刘海,看她脸上被掩映的部分。她一动不动,迎风光裸着。他的手臂虚虚地笼着她,仿佛一层粉膜。她惘然抵抗着。他一定也知道是徒然。由于他们年岁的差别,他很早以前就娶了亲,犹如两人生在不同朝代。她可以自由爱恋他,仿佛他是书里的人。不然她怎会这样不害臊?她忽然苦恼:如果他不懂,她不知道如何才说得明白。他又怎能猜到?跑开只会显得是假装羞涩。她跑了,听见那扇子在脚下嘎吱一响。
出了那房间,她很快便放慢脚步,免得被人瞧见。他没有追随她。她既如释重负又异常快乐。他爱她。随他们说媒去,发生什么她都无所谓了。他爱她,永远不会改变。居然还是下午,真叫人惊异。舞台上的锣声隐隐传来。她寂寞得很,只能去触摸游廊上的每一根柱子每一道栏杆。又拐了个弯,确信他不会看见之后,她的步子跳跃起来,只为了感受两根辫子熟悉的拍打落在肩膀上,不知为何,却像那鸣锣一样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