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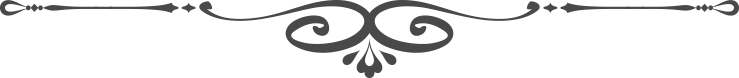
夜里两点钟是最坏的时辰,这时候你又困又冷。假如还不能上床睡觉,心情会很恶劣,各种坏想法也会油然而生。有一回夜里两点钟我坐在厨房里,听见有人在捅楼下的门。我认为这是个贼,当然,也可能是有人回来晚了,找不着钥匙,在那里瞎捅。不管是哪种情形,我都该下楼去看看。但我懒得动弹:我想,住在这房子里的人,总不能指望夜里两点钟归来时,还会有人给他开门。假如要是贼,那就更好了。我就坐在这里等他。等他撬开了门,走进二楼的厨房时,我会告诉他,他走错门了,这座破楼里住了七个穷学生。他马上会明白,这房子里没什么可偷的。也许他会说:sorry,撬坏了你的门。也许什么都不说——失望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教养。门坏了我不心疼:它是房东的,但我喜欢看到别人有教养。不说sorry我就骂他……当然,是用中文骂,让他听不懂。他身上没准还带着枪哪,听懂了就该拿枪打我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有天夜里睡不着,在厨房里看书,情形就是这样的。那座房子是座摇摇晃晃的木板楼,板缝里满是蟑螂,杀不净打不光。那间厨房点着一盏惨白的灯,冷冷清清,有个庞大的电冰箱,不时发出嗡嗡的声响。说句实在话,我的脑袋也在嗡嗡地响,声音好像比冰箱还大。响了半天以后,门开了,是用钥匙打开的。有人上了楼梯,一步三蹬地走上楼来。在一团漆黑之中又轻又稳地走上一道摇摇晃晃的木楼梯,说明此人有一双很强壮的腿。此人必是住在三楼的小宋。这孩子高考时一下考中了两所大学:一所是成都体院,另一所是东北工学院。后一所不说明什么,前一所则说明他能把百米跑到十一秒多,而且一气能做一百多个俯卧撑。最后他上了后一所大学,毕业后到这里来留学。我朝书本俯下身来:叫他看见我的正脸不好。小宋和我不坏,我没有汽车时,常搭他的便车去买东西,他还带我去考过驾照……算是个朋友吧,虽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情。我觉得他该去当贼,因为他走路这么轻。再说,他跑得很快,别人也逮不住他。他念了工科——这也不坏,而且他还要读博士,这样就加入了我们这一群。假如你还年轻,请听我的劝告:首先,你别去念文科和理科,最好去念点别的。其次,千万别读博士。博士是穷鬼的代名词。小宋现在已经是博士了,我猜他正在做博士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学问大了不好找事做: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那天夜里的事:脚步声经过我的门口停住了,等了一会儿还没有动静。我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果然是小宋。我真不愿意看到他——我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夜里两点钟不睡,坐在厨房里,这不是什么好景象。他戴着白边眼镜,镜片上反着白光,表情呆滞——这也不足为怪,夜里两三点钟,谁不困。他先是呆呆地看着我,然后小声说道:嗨。我也说:嗨。夜里两点钟,打过这样的招呼就够了。但他悄悄地走了进来,在我对面坐下,看看我的样子,说道:明天考试吗?我说:不,我老婆明天要答辩论文。如果他再问,我就告诉他:我老婆每隔半分钟就要翻一次身,差不多是在床上打滚。天一黑她就睡下了,一直滚到了现在。每隔十分钟她都要问一句:现在几点了,听声音毫无睡意。所以我才到厨房里来熬夜。告诉他好一些,免得他以为我们两口子打架了。但小宋没有再问。他拿起那本霍夫曼看了看,说道:这本书现在在你这儿了……
有关这本霍夫曼,有个典故。谁要是上了数学系的代数课,谁就需要这本书,因为它是课本。有两个途径可以得到它:其一是到书店去买一本。这本书着实不便宜,要花掉半个月的饭钱。另一个途径是到图书馆借。图书馆只有这么一本,谁先借到谁就能把它霸住。先借到的人有资格续借,没借到的人只好去买了。我很不愿意回想起这件事:我三十六岁时还在学校里念书——这个年龄比尔·盖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所用的教科书还是借的。小宋拿着这本书,看了一会儿(我觉得他很怪:这又不是金庸、古龙的小说,是本教科书,有这么拿着看的吗?),又把它小心地放在桌面上,小声问道:有喝的吗?我朝冰箱努了努嘴。于是他找出了那瓶可乐,一口就喝掉了半升——喝别人的饮料就是这么过瘾。我猜他是在系里带实验课,有学生实验做不完,他只好陪着,一直陪到了后半夜——这份助教的钱挣得真是不容易。他又何必读博士呢?读个硕士就去找工作,比受这份罪不强得多——话又说回来,我又何必要念这本霍夫曼。假如他对学生说,别做了,早点去睡吧,学生必然不乐意:工科的学生实验要算分的,没做出结果就是零分。这个毛头小子必然答道:我交了学费了!美国人在这方面很庸俗,什么事都要扯到钱上去——既然交了学费,就有权利使用试验室。他才不管你困不困。假如你说:我教给你怎么做;或者干脆说:拿过来吧,我给你做!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还要说:不,谢谢你。我要自己做出来。于是你只好眼睁睁地看这个手比脚笨的家伙在实验台上乱捅。在十二点之前,你恨不得拿刀子宰了他。到了十二点以后,你就没这份心了。你会找个东西靠着,睁着眼睛打盹。说起来也怪,我这颗脑袋困得像电冰箱一样嗡嗡响,冒出来的念头还真不少。喝完了可乐,他在我对面坐下了。看来他是想找我聊天。好啊,聊吧。夜里两点,真是聊天的好时候。但他又不说话,只管傻愣愣地看着我。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有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自己是个忠厚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满脑子都是些尖酸刻薄的话。这要怪这个时辰:夜里两点钟好人都睡了,醒着的必是坏人。平常天一黑,我就睡得像个死人。可那天晚上睡不着,因为我老婆在身边打着滚。开头我劝她吃片安眠药,她不肯吃,说是怕第二天没精神。后来我叫她数绵羊:一只羊、两只羊,最后数出一大群来。想到自己有这么多羊,就会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她说她一直在数,不管用。再后来我说:咱们俩干好事,干完就能睡了。她说:别扯淡了。最后她朝我大吼一声:你这么胡扯八道,我怎么睡啊!我看帮不上什么忙,就到厨房里来看书了。然后每隔一个钟头,她又到厨房里来看我,问我怎么不睡觉。我说我也睡不着——其实这是假话,我困死了,觉得书上的字都是绿的。我觉得我老婆那晚上的态度十足可恶。小宋看了看我的脸色说:你困不困?我说不困,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老婆好久没动静,大概睡着了;这样我也可以回去睡了;所以我们的谈话要简短些才好……
小宋的脸色不好:也可能是灯色的缘故,他脸色发灰。我觉得他心里有鬼。他摇头晃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两天我去看亲戚了。我说:噢。过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怪不得这两天都没看见你。说来不好意思,小宋两天不在,我都没发现。不过这也不能怪我:这两天我都在围着老婆转。小宋说:这两天都没课,然后又犹犹豫豫地不往下说了。忽然之间,我心里起了一阵狐疑:他会不会看完了亲戚回来,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然后他把死人装在行李箱里带了回来。现在他想叫我陪他去埋死人……如果他要和我说这件事,我就要劝他去投案自首。我倒不是胆小怕事,主要是因为把人撞死已经很不对,再把他偷偷一埋,那就太缺德了。小宋又接着说下去:我这个亲戚住在Youngstown,那地方你也去过——顺着七十六号公路开出去,大概走一个钟头,那儿有个大立交桥……
小宋说的不错:那地方我果然是去过。那座立交桥通到一个集市,那里的东西很便宜。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搭小宋的车。从桥上往下看,下面是一条土路,两边都是森林。路边有个很大的汽车旅馆,门窗都用木板钉住。那地方荒得很,根本就没有人。他大概就在那里撞死了人……我看着灯泡发愣,影影绰绰听小宋说那个没人的立交桥下——现在那里有人了,因为正在修新的公路。汽车旅馆里住满了工人。他那个亲戚正在经营那家旅馆。这叫胡扯些什么?他这个亲戚到我们这里来过,尖嘴猴腮一个南方人。说是给人当大厨的,还给我们露了一手,炒了几个菜,都很难吃——牛肉老得像鞋底,油菜被他一炒就只剩些丝——这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火候。难怪老板要把他炒掉。当时他在到处找工作,这只是三个月前的事。怎么这么快就开起旅馆了?那家旅馆有四五排房子,占地快有一百亩了。我说:那旅馆还不得有一百多间房子?他说:足有。按月出租,一人单住一间,一月四五百块钱,两人合住另加钱,每月总有近十万的收入。我想了想说:你的亲戚一定是中了六合彩,买这么大一片房子。小宋笑了起来说:哪是买的,我这个亲戚连彩票都买不起。我说:噢。原来是租的。他说:也不是。这就怪了,难道是捡的不成。小宋说:这回你说得差不多。这就怪了,哪有捡旅馆的?我怎么没捡着?
小宋这位亲戚有四十多岁了,既没有签证,也没有护照,更不是美国公民,我也不知他怎么来的。他不但没手艺,人也够懒,哪个老板都看不中他。所以开着一辆破车,出来找工作——我猜他也没有驾驶执照。这种人什么都敢干,现在居然开起旅馆来了。你知道这事情怎么发生的吗?他走到这立交桥下,在这个没人的旅馆里打尖,忽然来了几个筑路工人,见他待在里面,问他认不认识老板——这几个人要找住的地方。此人灵机一动,说道:我就是老板。你们要住房,就帮我把封窗的木板拆下来。美国工人帮他把房子打开,还修理了房子,不但没要工钱,还倒给他一笔房钱。此后一传十十传百,工地上的人都到他这里来住,把房子都住满了。这是包租房子,和开旅馆不同,不管床单被褥,没有房间服务,只是白拿房钱。还有一件妙事:那旅馆里有水有电,就是没人来收水电钱。小宋问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想了想答道:没什么看法。现在是夜里两点,我整个脑子像一块木瓜。想要有看法,得等到明天了。但我觉得美国的有钱人似乎太多了一点。到处都有没人的房子,把门窗一封,主人不知干啥去了。小宋听了点点头,说道:这不也是一种看法吗?我又补上一句说:亲戚毕竟是亲戚嘛。他听了点点头,说:你说得对。然后就不说话了。
现在我又想起了小宋的那个亲戚,此人和从温州到北京来练摊的大叔们样子差不多。这些大叔卖的全是假货,在地铁站上买票从不排队,还随地吐痰。此人可能还在七十六号公路上开旅馆——一年挣三十万,这么多年就是三四百万了,一有这么多钱可真让人羡慕啊。那家旅馆空着的时候,我老从它门前过。我怎么就没想过闯进去。说句实在话,美国没人的房子实在是太多了。
夜里两点钟我和小宋聊天,忽然想起了去年冬天,我们两口子到佛罗里达去玩,遇上了一条垃圾虫。和我们一道的还有我哥哥。家兄在国内是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也出来念博士。放假时他闲着没事,我接他出来散散心。一散散到了Key West,这地方是美国最南端的一个群岛,是旅游胜地,岛上寸土寸金。别的不要说,连宿营地里的帐篷位都贵,在那儿露营一天,换个地方能住很好的房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空房子也很多,我们在闲逛时闯进了一座没人的别墅,在房门前休息,忽然冒出个人来,问我们认不认得此地的业主。那个人留一撮山羊胡子,大约有三十来岁,穿一身油脂麻花的工作服。这就是那条垃圾虫了。他开着一辆很少见的中型卡车——我四五岁时在北京见过这种车,好像是叫万国牌。此人修理汽车的本领肯定很不错。
该垃圾虫说,看到海边有几条破船,假如业主不要了,他想把它们搬走。我们当然不认识业主——说完了这几句话,他没马上走开,和我们聊了起来——就和现在一样。但当时可不是夜里两点钟。你猜猜聊什么?哲学。此人自称是老子的信徒,他说,根据老子的学说,应该物尽其用,不可以暴殄天物;美国人太浪费了,老把挺好的东西扔掉。他自己虽是美国人,也看不惯这种作风。所以别人扔的他都要捡起来,修好,再卖钱——我一点都不记得老子有这种主张。我只觉得他是在顺嘴胡扯,掩饰自己捡垃圾的行径,但家兄以为他说得有理论依据。不唯如此,他们聊得还甚为投机。眼见得话题与魏晋秦汉无缘,直奔先秦而去,听着听着我就听不懂了。这个老美还冒出些中文来,怪腔怪调,半可解半不可解。说来也怪,这家伙不会讲中国话,但能念出不少原文——据说是按拼音背的。我哥哥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公孙龙和惠施,还能和他扯一气。要是换了我,早就傻了。就是这条垃圾虫说:美国的有钱人太多,就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岛(我记得是叫马拉松岛)上,还有无数的房子成年空着。在厨房里,我和小宋谈起这件事。小宋打断我说:这件事你讲过,我知道。你哥哥还说,这个垃圾虫是他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人。别人听过的故事,再给他讲一遍,是有点尴尬。我摇摇头不说话了。
有关这条垃圾虫的事,小宋听过,你未必听过。那人长了一嘴黄胡子,头发很脏,身上很破,看上去和个流浪汉没两样——要是在中国,就该说他活像是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但我哥哥对他的学养甚为佩服。和他分手之后,家兄开始闷闷不乐。开车走到半路上,只听他在后座上长叹一声:学哲学的怎么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哥哥拿到了学位,没有去做学问,改行做生意去了。我没有去做生意,但我怎么也看不惯富人的作风。每天早上去上学,都要经过一个富人的庭院:那地方真大,占了整整一个街区,荒草离离的院子中央,有座三层的石头楼房。已经三年了,我天天从那里过,就是没见过里面有人,这种事叫人看了真是有气……我哥哥和收垃圾的谈了半天,对他的见解很佩服,就说:你可以出本书,谈谈这些事情。那人顺嘴带出一句“他妈的”来,说道:Mr.王,出书是要贴钱的呀。看来收垃圾的收入有限,不足以贴补出书。后来他面带微笑地说:咱们这么聊聊,不也是挺好的吗——这种微笑里带着点苦味了。现在这位老子的信徒大概还在海天一色的马拉松岛上收着垃圾,遇上中国来的高明之士,就和他谈谈哲学——与俗世无争。这种生活方式大有犬儒的遗风。但我不信他真有这么达观,因为一说到出书,他嘴里就带“他妈的”。尽管是老子的信徒,钱对他还是挺有用处。我现在也想说句“他妈的”,我有好几部书稿在出版社里压着呢,一压就是几年,社里的人总在嘀咕着销路。要是我有钱,就可以说,老子自费出书,你们给我先印出来再说——拿最好的纸,用最好的装帧,我可不要那些上小摊的破烂。有件事大家都知道:一本书要是顾及销路的话,作者的尊严就保不住了。
现在又是夜里两点钟。我睡不着觉,在电脑上乱写一通。我住在北大的五十一公寓,一间一套的房子,这回没有蟑螂了,但却在六楼顶上,头顶和蓝天之间只有一层预制板,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凭我还要不来这间房子——多亏了我老婆是博士。要不然还得住在筒子楼里。现在她又出国做访问学者去了,每月领二百八十镑的生活费。这笔钱可实在不多,看来她得靠方便面为生了。但不能说给的钱太少:国家也很困难。和别人比起来,我们俩的情形还好。我老婆是博士,搞着专业,我是硕士,就不搞专业,写点稿子挣些零花钱。要是两口子都是博士,我们的情形就会相当难堪。不管怎么说吧,我不想抱怨什么。没什么可抱怨的。
小宋问我:你看,该给我亲戚什么样的劝告?我脱口说道:这还用想吗?劝他见好就收。把本月的房钱收齐了,赶紧走人,哪儿远往哪儿跑,别让人找着。小宋听了显出一点高兴的样子:你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就放心了。我说:光放心有什么用,你得劝他呀!他听了这话又不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没劝?不劝还好,一劝他倒老大不高兴,差点和我翻了脸。人家说,他已经住进来了,这地方是他的,干吗要跑。我说噢,他不知道这地方不是他的。那你告诉他好了。小宋说:我告诉他了,但人家不信。我说:啊呀,那怎么办。小宋愣愣地看着我——我能看出来,他也很困——看了一会儿,忽然一笑说:我现在正问你该怎么办。我想了一会儿,看看手表说:不知道。我们应该去睡觉。他说我说得对,于是我们就往各自的房间里走……
*载于1997年第1期《北京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