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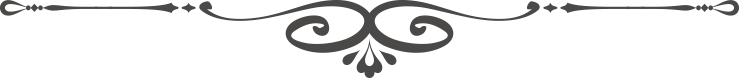
我待在一个游艇里。这条船好像是在岸上,架在一个木架上修理。有关这条船,可以补充说,它是用层压板做成的,因为船壁上剥落了几处,薄薄的木片披挂下来。这让我想起了好几件往事:一件是我小时候到胡同口的肉铺去买肉馅,店员把肉馅裹在桦木膜里递给我;另一件是我上大学时,在礼堂里听大课,椅子上的书写板就是层压板的。看到这条船是层压板做的,我就暗自庆幸道,幸亏我没有驾着它出海。这条船实在是太小了,在里面连身都转不过来,驾着它出海一定要晕船(我既晕飞机,又晕小车,坐在这么一个小船里到了大海上,一定要把胆汁都吐出来),更何况它是木头片儿做的,肯定不太结实。可是船舱里有一面很大的舷窗,我从窗口往外看,看到远处有一个灯火通明的码头,但近处是一团漆黑,可是在一团漆黑中,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我俯下身去,想要看清楚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朝舷窗开了一枪——这就是说,舷窗上出现了一个星形的洞,而舱里的壁板“乒”的一声碎了一块。这一枪着实让我惭愧,因为假如我告诉别人说,有人朝我开了一枪,他们一定会以为我在编故事。那一枪打来时,我影影绰绰想到了它的缘由,头天晚上在海上,我看到两条渔船在交接东西。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在海边住过,所以对这一片蓝色的流体抱有最热烈的好感。现在我就想到了在电视上看到的加勒比海,是从飞机上拍摄的,海底清晰可见,仿佛隔了一层蓝色的薄膜看到一片浅山。如果能够在加勒比海边上建起一个别墅,拥有这样一片大海的话,死有何憾。这件事实现起来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非几百万不行——这几百万还得是美元。因为这个缘故,人家打我这一枪不可能是在加勒比海边上。那一枪打得我心惊胆战,躲在墙角,手里拿了一根铁棍,等着打了我一枪的人进来。现在我讲到这些事,毫不脸红,因为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我亲身所历。本来我该站在门后,但是那条船太小了,门后根本就站不了人。后来,那扇门开了,进来一个头上戴了黑油布帽子的矮胖子。假如这条船是架在空中,他就是爬梯子上来的。本来我该给他一铁棍,但是他把手指放在嘴上,这就使我犹豫了。事后回忆起来,我没有马上朝那个矮胖子扑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我身材魁梧,手里又拿了一根铁棍,没有理由怕别人;二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条船里,人家为什么要打我一枪等等,我都不大明白,所以就犹犹豫豫的。不管怎么说吧,我对这个矮胖子保持了警觉,他进了门之后,就把门关上了,走到窗前往外看。然后他走到那破壁板前面,用手指一抠,就把那颗子弹抠了出来扔给我。然后我手里掂着那颗子弹,发现它是尖头的——据我所知,手枪子弹是钝头的,所以人家是用一条步枪来打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动作博得了我的好感,我相信他是来帮助我的。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到舱上面去,我就放下了那条平端的铁棍,从他身边走过——就在这时,我一跤栽倒了;有只手从身体下端伸上来,经过了大腿、肚子、胸口,一把捏住了我的脖子。此时,我气愤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自己这么容易就上了别人的当,被人用一片刀片就划开了脖子;同时也不无欣慰地想到,这个梦就要醒了。
每天早上我从梦里醒来时,都会立刻从床上爬下来,在筒子楼狭窄的楼道里摇晃着身躯去上厕所。这时我根本就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在这里根本就用不着眼睛,有鼻子就够用了。除此之外,睁开眼睛来看,所见到的景色也远不是赏心悦目。总而言之,我闭着眼睛上过了厕所,又闭着眼睛回到床上。此时我还想回到这个梦里,但已经回不去了。
那个困在船舱里的梦,我希望它是这么结束的:那个矮胖子捉住了我之后,并没有割断我的喉咙,他把我放开了。这就是说,他是善意的。他抓住我,只是警告我不要这样轻信。然后他就打开船舱的门,离去了。当然,这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结果,那就是我被割断了喉咙,浸在血水里招苍蝇。换言之,我在梦里死掉了。因为是在梦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做梦,在我看来,梦就像天上的云。假如一片天空总是没有云,那也够乏味的了。这个看法不是人人都同意,所以才有了“无梦睡眠器”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铁片,带有一条松紧带,上面焊了很多散热的铁片,把它戴在额头上,感觉凉飕飕的,据说戴着它睡觉就可以不做梦,但我不大相信。不管是真是假,梦这种东西,还是留下的好。
大家肯定都知道,格调不高的梦是万恶之源——从前,有位中学生,本来品学兼优,忽然做起了格调不高的梦,就此走向了堕落的道路;还有一位家庭主妇,本来是贤妻良母,做了几个格调不高的梦,就搞起婚外恋来——像这样的事例大家知道得都不少。本来大家最好只做高格调的梦,但是做梦这件事又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就说今早我做的梦,格调高不高就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没问题,也可能有问题,总得上级分析了才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会自找麻烦,把它说出去。人家问我做了什么梦,我就说,一个大南瓜、一块大豆腐。你听了信不信,我就不管了。
每天早上我上班,在办公桌后坐定。有人走过来,问道:老王,梦?我就把手一挥,说:南瓜豆腐!这场面像一位熟客在餐馆里点菜,其实不是的。如前所述,大家睡着了就要做梦,这已经成了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如下:上班之前由一个专人把大家的梦记录下来,整理备案。这样你想到了自己的坏想法已被记录在案,就不大敢去做案,做了案也有线索可查。我认为,这是个了不得的好主意。眼前的这位女同事就是来记录梦的。我对她说,南瓜豆腐。就是说,我梦到了一个南瓜、一块豆腐。身边的人一齐笑了起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不像一个梦。其实这的确是一个梦,只不过是多年以前做的。她记了下来,并且说:该换换样了。老是南瓜豆腐。这就是说,嫌我的梦太过单调。我说:你要是嫌它不好,写成西瓜奶酪也行。别人又哄笑了一阵。然后,别人轮流讲到自己那些梦;所有的梦都似曾相识……
有的人的梦是丰富多彩的,说起来就没个完,逗得小姑娘格格笑个不停。有时候,他中断了叙述,用雄浑有力的男低音说:记下来,以下略去一百字,整个办公室里的人就一齐狂笑起来。但我一声都不吭。这个小子在讲《金瓶梅》。他是新来的,他一定干不长。他现在用老板的时间在说他的梦,这些梦又要用老板的纸记下来,何况这样胡梦乱梦,会给老板招麻烦——而老板正从小办公室里往外看。顺便说一句,谁也不能说这位老板小气,因为他提供厕所里的卫生纸。但是谁也不能说这个老板大方,因为不管谁从卫生间出来,他马上就要进去丈量卫生纸。我说出的梦很短,而且总出去上公共厕所,但也不能因此就说我是个好雇员,因为我一坐下,马上又打起瞌睡来了。而我打瞌睡的原因,是《金瓶梅》我看过了。假如不瞌睡,待会儿就要听到一些无聊的电视剧。这是因为有些人懒得从书上找梦,只能从电视上看。从这些事实我推测大家早就不会做梦了,说出来的梦都是编出来的。但我为什么还会做梦,实在很有趣。
有一件事你想必已经知道,但我还要提一提: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梦档案,存在区梦办。在理论上档案是保密的,但实际上完全公开。你可以看到任何人的档案,只要编个借口,比方说,表妹快结婚了,受大姨之托来看看这个人的梦档案。因为电视、报刊不好看,好多人都转这种念头,档案馆里人很多。我也到那里看过梦,但是梦也不好看。如前所述,某些人会梦到《金瓶梅》《肉蒲团》,但那些梦因为格调不高,内部掌握不外借。外借的和电视、报刊完全一样。顺便说一句,现在写小说写剧本的人也不会做梦,所以就互相抄,全都无味之极……有一天我到那里去调查未来的“表妹夫”,忽然灵机一动,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众所周知,人不能和自己的表妹结婚,因为会生下低智儿。但我的例子特殊,我没有表妹,姑表姨表全没有,所以很安全。就算有了也不怕,可以采取措施,不要孩子——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个表妹要嫁我,我还巴不得。至于为什么想看自己的梦,我也说不清。借梦的小姑娘对我嫣然一笑说:就借这本罢,这本最好看。应该承认,这话说得我也二二忽忽,不知道自己梦到了些什么……
有关我们的生活,可以补充说,它乏善可陈,就如我早上上班时看到的那样,灰色的煤烟、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雾。在我桌子上放了一个白瓷缸子,它总是这样。我看惯了这些景象,就急于沉入梦乡。
我年轻时摔断过右腿,等到老了以后,这条腿就很不中用地拖在了身后。晚上我出门散步,走在一条用石块铺成的街道上。我记得南方有些小城镇里有这样的街道,但是这里不是中国的南方;我还记得欧洲有些城市里有这样的路,但是这里也不是欧洲。这条街上空无一人。一个老人,身上又有残障,孤身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实在让人担心。但是我不为我自己担心,因为我有反抢劫的方案。我的右手拄了一根手杖,手杖的下部有铁护套,里面还灌了铅。假如我看到了可疑分子,就紧赶几步,扑向一根路灯杆。等到左手攀住了东西,就可以不受病腿的拖累。这时我再把手杖挥舞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坏蛋能经得起这根手杖的重击。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个可疑的家伙。如果浙江人不介意,我要说,他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同乡;如果他们介意,我就要说,他长得哪里的人都不像。小小的个子,整齐的牙齿露在外面,对我说道:大伯,换外汇吗?我赶紧说:什么都不换。同时加快了脚步。这家伙刺溜一下跟了过来;但不是扑到我的右面,而是扑到了我的左面,搀住了我的左肘。这一搀就把我的好腿控制住了。更糟的是,我右手上拿的手杖打不着他。于是我身不由己地跟他走进了一条小巷。这条巷子里黑咕隆咚,两面的房子好像都被废弃了,呼救也没有用。巷子尽头,有一间临街的地下室亮着灯。那个窗口好像一张黄色的纸板。
有人在我头上敲了一下,我醒过来,看到老板正从我身边气呼呼地走开。他走了几步,猛一转身,朝我挥了一下拳头说:醒醒啊——上着班哪!然后,整整一上午,我都听见他对别人说:上我的班老睡觉——还当是吃大锅饭哪,我也不能白给他薪水。我听了着实上火——你知道,我们到哪里都会碰上像他那种头发花白或者头顶光秃秃的家伙,要学问没学问,要德行没德行,就会烦人。我环顾四周,看到同事们都板着脸,只有一个人脸上通红通红,他就是那个要从梦里略去一百字的人。看来他也挨了一顿训。小潘(她就是我们公司的记录员)走到我面前来,问道:又梦到什么了?等到大家笑过了之后,她把我名下的记录翻给我看,上面写着:南瓜豆腐——南瓜豆腐——南瓜豆腐——南豆——南。她说,以后你再梦到南瓜豆腐,我连南字也不写,给你画一杠,你同意吗?我对此没有不同意见。这姑娘很漂亮,就是太年轻。我让她走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假装在写什么。假如老板正在一边偷看我,就让他以为我在拟销售计划好了。其实他让我销的东西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计划,或者说这个计划我已经有了,那就是不给他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顺便说一句:他让我卖的就是那个无梦睡眠器。现在市场上这种东西多得要了命,什么无梦手表、无梦眼镜、无梦手镯、无梦袜子等等。凭良心说,我们这种无梦睡眠器并不坏,即便起不了好作用,也起不了坏作用。时常有人投诉说,戴无梦眼镜戴成了三角眼,穿无梦袜穿出了鸡眼,我们这种东西不会有这种副作用。唯一的坏处是假如屋里冷,戴它睡觉会感冒。但是我就是不给他推销——现在电视不好看,报刊上全是广告,再不让人做做梦,那就太霸道了……
有关我的梦,需要补充说,它就是南瓜和豆腐,即便在梦办的档案上也是这样。只是“南瓜豆腐”这四个字,刚出现时是楷体,后来变了宋体。再后来成了隶字,再后来金石甲骨就纷纷出现。可以想见,这是抄录员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南瓜豆腐”的必然反应。后来,南瓜豆腐就成了画面,有水彩、蜡笔、铅笔、钢笔,各种各样的画,五彩缤纷。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南瓜豆腐菜谱,什么南瓜排、南瓜饼,大豆腐、小豆腐。从菜谱上看,小豆腐不属豆腐之列,它只是野菜和豆面。作为南瓜豆腐的创始人,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忽然之间,变成了“南瓜豆腐,我爱你”。此后她(我希望是她)又恢复了一丝不苟的字体,写下了“南瓜豆腐,I love you”。当然,她也可以推托说,“I love you”不是她写的,是别人注上的。此后南瓜豆腐还是那么一丝不苟,“I love you”就越来越花,出现了意大利斜体、德国花体等等,“love”也变成了红唇印,“you”也向人脸的样子变迁,看上去还挺像我的。凭良心说,从楷到宋,从蔬菜到爱人,我都承受得住,受不了的是别人在档案本上乱批乱注。那些话极是不堪,在此不能列举。这本账在我这里很清楚,我说的只是南瓜豆腐,后来有人爱我,再后来就有人乱起哄。但我恐怕别人就不这么清楚,把这些乱七八糟全算在我的账上,因为卷宗上写着我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铁板钉钉一样。现在我走在街上,常有人在后面窃窃私语:知道他是谁吗——谁——南瓜豆腐!然后就有人往我前面挤,想方设法看我的脸。好在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变态的性行为没有兴趣(我档案里连篇累牍全是这种东西),而且我也不叫南瓜豆腐。
中午,该给大家订午饭的时候,老板从小办公室里冲出来说:别给我和老王订,今儿中午我请他吃饭。众所周知,老板不经常请雇员吃饭,所以这意味着我会有麻烦。但这不能使我着急——这世界上没有几件能使我着急的事。再说,俗话说得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憋住。这个民谣还有另一个版本,后两句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军会要我的,我是弹不虚发的神枪手,又有文化,只是年龄大了点……老板点菜时,我一声不吭。凉菜端上来,我还是一声不吭。他给我斟上了啤酒,斜眼看了我半天,忽然用拳头一敲桌子说,老王,你也太不像话了!这句话使我松懈了下来,因为不是要炒我鱿鱼的口气。我猜他也不敢炒我的鱿鱼。这倒不是舍不得我,而是舍不得我的客户。他多次想让我把客户名单交给他,但是威胁也好,利诱也好,对我都不起作用。后来他就说:看不出老王迷迷糊糊一个人,还这么有心眼。此言大谬!我认为老板让我们交客户是不正派的,所以才不交。这是原则问题。
说到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也是一种奇遇——我绝不会有这种心眼,去结识一大批商业部门的人,以备推销伪劣商品之用。前几年我在函院教书(说是函院,实际主管一切成人教育),学生年龄都比较大,念起书来比较迟钝,但也比较尊重老师。这是文凭热时的事,现在你再到函院教书,就会一无所获。我承认自己的关系多,但我从不用它来干坏事情。老板给我的货太烂,我就不给他推销。我不能害自己的学生。老板假装恨我打瞌睡,其实是恨我的原则性。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说道:我都不知怎么说你。这就对了。我没什么不对的,为什么要说。
老板请我吃火锅,点菜时我没有注意,他要的全是古怪东西,什么兔子耳朵、绵羊尾巴之类。这些东西我都不吃。我正在用目光寻找小姐,要添点东西,老板又向我开炮道:老王啊,不能这样迷糊了,就算不为我也为你自己呀……睁开眼睛看看,大家都在捞钱哪!这些话里满是铜臭,我勉强忍受着。他又用拳头敲着桌子,说道:钱在哗哗地流,伸手就能捞到……这简直是屁话:谁的钱在流?你怎么捞到它?为了礼貌,我勉强答道:我知道了。然后他又说:还有一件事,以后你别老梦见南瓜豆腐。我很强硬地答道:可以,只要你能证明南瓜豆腐有什么不好。这一下把他顶回去了。
我能够证明坐在我对面的这个花白头发的家伙是个卑鄙之徒,没有资格说我,甚至没有资格和我同桌吃饭。他进了几千打无梦睡眠器,让我给他推出去。这东西肯定是卖不掉的,我也不想给他推,他提出可以给一大笔回扣,由我支配。不管你给多少,我有我的原则:梦是好的,不能把它摧残掉。所以我要另外想办法。以下是曾经想到的一个办法:说这东西不是无梦睡眠器,而是一种壮阳的设备,放到药房里卖,连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销魂一刻,当头一镇,果然不同!”
在小报上一登,肯定好卖。唯一的问题在于,我没有把握是不是真的不同。从理论上说,脑袋上放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应该有区别,但我没试过,因为我至今是光棍一条。假如我知道真有区别,不管是好区别还是坏区别,就可以这么干——我的原则是不能骗人。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假如有人无聊到需要壮阳的器械,骗他点钱也属应该,因为想必他的钱也不是好来的。它的不足之处是必须等到我婚后加以试验才能实行。我今年三十九岁了,还是童男子。但我一直在找老婆,还上过电视。我把这些对他汇报过,他问我还有没有正经的。正经的有,但我不能说出来,那就是把那些铁丝笼子当废铁卖掉。那东西戴上去照样做梦,只不过梦到的都是不戴帽子到北极探险——我试验过的。——这一点更不能说,因为众所周知,我梦到的只是南瓜和豆腐——这种狗屁东西只有报废的资格,但是他老逼我把它卖掉;你说他是不是个卑鄙的家伙?他还说:你得干活,不能再泡了——否则另寻高就。听到这里,我决定告辞,否则就没有原则了。当然,告辞也有艺术,不能和他搞翻。我说:我吃好了。其实我还饿着。他说,哎呀,剩了这么多,浪费了不好。我要尽力再吃吃。我说:那我失陪。就这样走掉了。
这种无梦睡眠器其实不难卖掉,只要找个区教育局的人,让他和下属的学校说一声,就能把这种铁丝筐戴到中小学生头上。但我不想把它戴到入睡的孩子头上,只想把它戴到做爱的秃头男子额上,这就是我的原则。因此,我从饭店里往外走时,心里很不愉快,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牺牲原则:我懒得另外找事干。后来我又变得愉快了:一出了饭店的门,就听见有个女声说道:往后看。于是就见到原来同过事的小朱站在门旁边,原来她在公司时是记录员。那时候她老劝我说,你梦点别的罢,我替你编。有人还给我们撮合过,不过最后没成。她结过婚,有个孩子,这种情况俗称拖油瓶。这一点我是不在乎的,只要人漂亮就成。遗憾的是,这位小朱虽然脸像天使,腿可是有点粗。另外,当时我的情况比现在好,所以有点挑花了眼的感觉——现在不这样了,最近几个月觉得头顶上有点凉快,很快就会需要一个头套。现在我不觉得她腿粗,也许是因为天凉了她没有穿裙子。
她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我别声张,然后让我和她走。到了没人的地方她说:看见你们俩在里面就没进去。我猜你马上就会出来。她猜对了。她又猜我没吃饱,又猜对了。于是她请我吃饭,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到了饭桌上,她又猜我和老板搞得不顺心。我说,你怎么都知道?她就哈哈笑着说:这些事我都经历过。原来老板也请她吃过饭,在餐桌上说,自己夫妇感情不好,feel lonely。她听了马上就告辞,老板也说,要了这么多东西扔了可惜,要留下吃一吃。事实证明,这个老板是色鬼、小气鬼、卑鄙的东西,还feel lonely 哩,亏他讲得出口来。给这种人当雇员是耻辱,应该马上辞职。她就是这样做的。她做得对。但他没对我说过feel lonely。所以我还要忍受这个坏蛋。我就这样告诉小朱,并且愁眉苦脸,好像我正盼着老板来冒犯我,以便和他闹翻,其实远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老板告诉我他feel lonely,我也不会立即辞职,而是说:对不起,你搞错了,我不是同性恋。我只会逆来顺受,像一匹骟过的马一样。
吃完了饭,我们来到大街上,这是一条尘土飞扬的街,所有的房子全都一样。我在梦里见过无数条街,没有一条是这样的……小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忽然搀住我的手臂说:走,到你那里去看看。其实我那里她去过了,不过是筒子楼里一个小小的房间,楼道里充满了氨味。不过,她要去就去吧。
有关这位小朱,我需要补充说,她穿了一件绿色的薄毛衣,并且把前面的刘海烫得弯弯曲曲的。看上去不仅是像天使,而且像圣母——假如信教的朋友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她在我那间房子里坐了很久,谈到她那次失败的婚姻——她前夫有外遇——然后说,你们男人一个好的都没有。这样就把我、她前夫,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板归入了一类。这使我感到沮丧,不过我承认她说得有道理。就拿我来说,坐在她对面聊着天,心里想的全是推销伪劣产品的主意:劝诱她和我共享销魂一刻,然后把那个劳什子戴到额头上。等到知道了果然不同,就在报上登广告,把这种鬼东西卖出去。在这个弯弯绕的古怪主意里,有几分是要推销产品,几分是要推销我自己,纯属可疑。这无非是要找个干坏事的借口罢了。当然,小朱也同样的古怪。假如她以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那么坏,何必要跑到其中之一的房子里来。这都是因为我们感到需要异性,然后就想出些古怪的话来……
等到天快黑时,她起身要走,我起身送她,还没走出房门,她就一把抱住我。因此我们就没有出门,回到屋里那张破沙发上坐下了。她自己说,好久没有个好男人抱住我了——但是她自己刚刚说过,男人里一个好的都没有,这是个悖论。这张破沙发在公共厨房里摆了很久,现在是本屋除床外唯一的家具,油脂麻花的,除了蟑螂,没有谁喜欢它。在两个人的重压之下,它吱吱地响着,好像马上就要散架。于是我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床上,又过了一会儿,就开始互相脱衣裳了。
这是我的一次浪漫爱情,我记述它,统共用了一千三百个字,连标点符号全在内。说起来我们俩还都是知识分子,填起履历来,用着一种近似黑话的写法——硕研——大家都懂这是什么。根据金西的调查,知识分子在性爱方面行为很是复杂,但我们竟如此简单,以致乏善可陈,我为此感到惭愧。在小朱的上半身裸露出来时,我问了一句:你不是说,我们男人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吗,为什么……她的小脸马上就变得煞白,眯起眼来,恶狠狠地说道:feel lonely!说着一把把床上的破被子扔到了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显然不合时宜。至于我们做的事,众所周知,那是不能用文字来表达的。唯一可以补充的地方是,我们在五点到九点之间共做了两次,第二次开始之前,我想过要把那个无梦睡眠器戴上。这样我们的性爱就带有了科学试验的性质,比较不同凡响;但我又怕她问我在这种时候头上为什么要戴个铁丝筐。所以,这个爱情故事也只好这样了。
我这样对待浪漫爱情是不对的,因此必须再试着描写一下。如果我说,小朱躺在我身边,裸露出一对半球形的乳房,这就是格调低下的写法。因为从这些实际情况之中,可以引申出各种想象。另一种写法是这样的:在我身边绵亘着一个曲面,上面有两个隆起的地方,说是球体有欠精确,应当称之为旋转抛物面。格调还是不高,因为还有想象的余地。最好直接给出曲面方程,这样格调最高,但是必招致小朱的愤恨,因为假若她把我想象成一堆公式,我也要恨。再说,我也不想和一堆公式做爱,所以,这个爱情故事也只能这样了。
做过爱之后,我和小朱相拥躺着。此时我又问她:为什么要和我做爱。听了这句话,她全身立即僵硬了,似乎马上就要和我闹翻——但是马上又松弛下来,轻描淡写地说:聊点别的吧。——不管她怎么说,我感到了她刚才有股冲动,要把我从床上扔下去——然后我问道:聊什么?她更加轻描淡写地说道:比方说,南瓜和豆腐。然后我觉得肚子上疼痛不已,原来是被她咬住了。这使我想起了有一种动物叫做香猪。此种动物和原产于丹麦的长白猪虽是一个物种,终其一世却只能长到二十来斤。死掉后烤熟了就叫做“烤乳猪”,虽然名不副实,却是粤菜中一大美味,十分酥脆,肚子上的皮尤为可口。等她咬够了,松了嘴,那块皮还长在我肚子上。这说明我还不够酥脆。然后她又摸摸我身上的牙印说,谈谈你的南瓜豆腐。这使我想到,她大概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饼干。但她不肯吃饼干,反而一再掐我。对于这些古怪的行径,她的解释是:心里痒痒,要发狂。我很怀疑,自己痒了来掐我,是不是真有帮助……
有关我自己,可以补充说,我很正常,有住房、有收入,既不偷也不抢。唯一的不足是说自己梦到了南瓜豆腐。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问到南瓜豆腐,这使我痛恨他们。小朱问过南瓜豆腐之后,我立刻就恨死了她;但表面上却装得心平气和,并且说:南瓜是个红皮南瓜,豆腐是块北豆腐。她听了爬到我身上,并且说:红皮南瓜北豆腐,是吗?然后就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想道:既然大家如此仇恨,就让她掐死算了。然而一个壮年男子又不那么容易被掐死。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我又和她做了一回爱。这件事说来格调不高,但实情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睡着了。
什么格调高,什么格调不高,你想必已经知道:什么像梦,什么格调就不高。因为我还会做梦,所以我格调不高。而做梦的诀窍就是,假如有人问你梦到了什么,你说:南瓜豆腐!这样就能做梦。这是做梦的不二法门。我把这个诀窍传给你,你以后再不会feel lonely。但是我恐怕你不会这么办。因为做梦耗费你大量的精力,妨碍你大把地捞钱。那天夜里我梦见的就是这个:有很多的人轮番来问我做过什么梦,我一一答道:南瓜豆腐。后来把我问烦了,就说是西瓜奶酪。于是他们就翻了脸,动手来揍我……
那天夜里我醒来时,看到黑夜里有一颗烟火头,还有很浓烈的香烟味。过了一会儿,我才想到是小朱坐在床上吸烟。我问她为什么坐着,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先把烟捺灭,然后躺下来。直到我搂住了她冰凉的肩膀,她才说:你睡觉打呼噜。我觉得她的语调是冷冰冰的,就把她放开。过了一会儿,她又问:又梦到南瓜豆腐了?我说对,然后接着说:睡觉吧。于是她翻了个身,把后背给我,让我从后面搂住她,并且说道:这件事你是不想告诉我了,是吗?我明白,她说的是梦。这种事我经过得多了,有很多人来问我的梦,我不肯说,她们就走开了。这一回不同的是,我不希望她走开,我有点爱她,是做爱时爱上的。为此我做出了努力,尽量编些像梦的东西说说。听着听着,她哭起来了。说实在的,我编得也很不像样子。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按捺不住发作起来:你们都是怎么了!想要知道什么是梦,自己去做嘛!她说,自己不会做,怎么办呢?而我想了一会儿说道: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载于1995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