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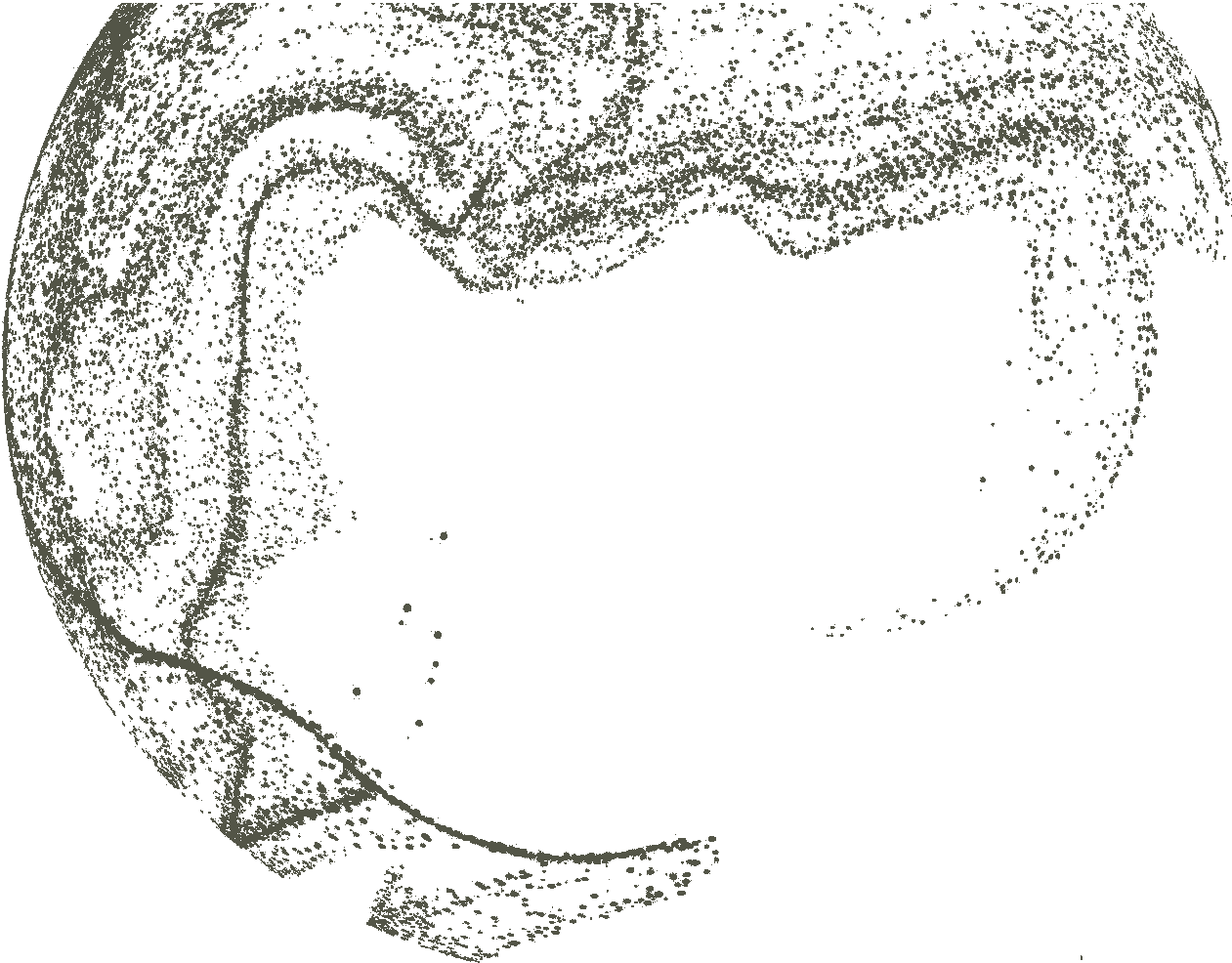
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半,一个身材高瘦、头发花白、名叫布鲁斯·罗布(Bruce Robe)的华尔街职员把一叠厚厚的文件塞进黑色手提包,从衣架上取下外套,然后离开办公室。这个习惯延续了三年。离开办公室后,他先乘电梯由29层到1层,然后穿过拥挤的街道,10分钟后到达华尔街直升机场搭乘直升机,8分钟后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改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过了1小时10分钟,该航班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机场降落。他下了飞机,穿过候机室,然后坐上一辆等候已久的汽车。半个小时后,他便到达目的地——他的家。
罗布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店每周住4晚,其余的三个晚上则与妻儿在500英里以外的哥伦布市团聚。他的工作地点位于美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他的家却在美国中西部的安静郊外。他两处奔波,每年总共旅行5000英里。
罗布的情形很特殊,但并非独一无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农场的主人,每日清早从他在美国西海岸的家飞行120英里,到坐落于圣贝纳迪诺谷的农场去巡视,然后晚上又飞回家。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工程师的孩子,经常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接受牙齿矫正手术。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授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每周飞行1000英里去纽约的社会研究学院授课。一个旧金山的年轻人与在檀香山的女友,每周轮流去见对方一次。他们每次都要横越太平洋,飞行2000英里。还有一个住在新英格兰的家庭主妇也定期到纽约做头发。
空间距离在历史上从未如此短过,人与其所处位置的关系也从未如此烦琐、脆弱、短暂。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尤其是在“未来居民”组成的社会中,往返、旅行以及定期在异地而居等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事实上,我们“用完”一个地方而将之舍弃的情形,正如丢弃纸制品或空罐头一样。我们亲眼看到,地域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下降。一个新的游牧民族出现了,而他们的移动性到底有多大、多广、多重要,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据巴克敏斯特·富勒统计,1914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旅行1640英里,包括上下班路上行走的1300英里在内,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每年骑马或其他交通工具仅340英里而已。以1640英里为基数来计算,当时的美国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才走了88560英里而已。
 然而今天,有私家车的美国人平均每年约行10000英里,而且现代人的寿命比上一代或上两代更长。“以我来说吧,”富勒在几年前曾写道,“我已经是数千万个走过300万英里以上的美国人之一了。”这个数字比1914年的美国人,高出了30倍以上。
然而今天,有私家车的美国人平均每年约行10000英里,而且现代人的寿命比上一代或上两代更长。“以我来说吧,”富勒在几年前曾写道,“我已经是数千万个走过300万英里以上的美国人之一了。”这个数字比1914年的美国人,高出了30倍以上。
如果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结果更为惊人。1967年,1.08亿的美国人总共旅行3.6亿次,包括100英里以上的隔夜旅行在内,总里程数共约3120亿英里。撇开飞机、货车、汽车、火车、地铁及其他种种交通工具不谈,就以我们在道路上的社会投资来看,这个数据也着实惊人。过去20年来,美国平均每天铺路约200英里,加上每年新增的道路7.5万英里,足可环绕地球三圈。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口增长了38.5%,而道路英里数却增加了100%。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据更为惊人:过去25年里,美国人旅行里程数的增长率较人口增长率快了约6倍以上。
在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每个人的空间流动量均在激增。过去,斯德哥尔摩的斯坦维格区平静如乡村,而如今交通的繁忙情景简直判若两地。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两地,最近5年来所建造的街道已经到了非常密集的程度,而车辆的增加数量更令人难以想象。除了每天固定两地通勤之外,商务及旅行也日渐增加。夏天约有150万的德国人在西班牙度假,还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荷兰及意大利境内旅行。瑞典每年的观光客多达120万人,而美国约有100万以上的人旅行,而每年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几乎达到400万人。一位作家在《费加罗报》( Le Figaro )上,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巨大的人类交换”。
这种在地上(有时在地下)忙碌奔走,可谓超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相反,在一些工业落后国家,往往呈现冻结状态,其居民总是守在同一个地方。运输专家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曾谈过流动性国家及非流动性国家之间的断层。他指出,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的国家若要在公路总里程数上赶超欧盟国家,必须增开公路4000万英里。这种差距不仅在经济上有所反映,即使在文化及心理结构上也可体现出对人们不同的影响。因为移民、旅客及游牧民族与长期固守一处的人实在大有不同。
在一切迁徙活动中,对个人最具有心理影响力的或许是家庭住址的改变。这种地理位置的迁移以美国等发达国家最频繁。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谈到美国时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发生于‘二战’,而这种现象迄今仍未衰减。”政治科学家丹尼尔·伊拉扎(Daniel Elazar)就美国人的大量迁移描述道:“在每一个(都市)地带,美国人已经开始自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开始过着一种都市的游牧生活,而不再长期定居一个城市……”
1967年3月到1968年3月的短短一年之内,3660万的美国人(不满一岁的婴儿不包括在内)改变他们的住处。这些改变住址的人数,已超过柬埔寨、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伊拉克、以色列、蒙古、尼加拉瓜及突尼斯等国当时加起来的人口。这种情形正如这些国家的所有居民突然来一个大迁移一样。而这种大量迁移的情形在美国每年都在发生。自1948年以来,每年约有1/5的美国人变更住址,全家搬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即使历史上仅有的13世纪蒙古帝国扩张及19世纪的欧洲人西迁,与此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比起美国人的迁移率,虽然其他国家很可能无法与之匹敌(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进行统计),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这种现象。即使在一些较传统的发达国家,人与地域之间的古老束缚也完全破裂了。伦敦发行的一份社会科学报《新社会》( New Society )曾指出:“……出乎国人意料,英国是一个非常乐于流动的国家。1961年,英格兰及威尔士两地的居民在一年内变更住址的差不多占英国人口的11%……事实上,在英国某些地方居民的迁移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在肯辛顿,一年内易地而居的居民约有25%以上,汉普斯特德约有20%,切尔西约有19%。”安妮·拉平(Anne Lapping)撰文写道:“新一代的人比上一代的人对搬家显然更有兴趣。一般房屋的抵押期为8~9年。”此种情形真可以与美国相媲美。
法国最近由于住房紧张,所以迁移之风略微缓和,但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盖伊·波舍(Guy Pourcher)的研究,法国人每年迁居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8%~10%。
瑞典、德国、意大利以及荷兰等国,迁移的人数都有升高的趋势。自“二战”爆发以来,国际移民的热潮正席卷整个欧洲。北欧由于经济繁荣,劳工大量缺乏,所以从地中海地区及中东地区吸引了大量劳动人口。
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土耳其人等云集而来。每个星期五下午,千余名土耳其工人在伊斯坦布尔搭乘火车,向北驶向他们的极乐之乡。洞穴式的慕尼黑火车站已经成为许多土耳其失业工人的落脚点,而事实上,今日的慕尼黑早已开始发行以土耳其语报道的报纸了。科隆的福特大工厂,约有1/4的员工是土耳其人。其他地方的外国人也纷纷涌进瑞士、法国、英国、丹麦,甚至北达瑞典。我和妻子曾在英国古城的一家餐厅用餐,服务生全是西班牙人。后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的一家餐厅吃饭,却发现该餐厅已变成西班牙移民的聚会场所,晚餐时的音乐也是弗拉门戈舞曲。当时,该餐厅没有任何瑞典人在场,除了少数阿尔及利亚人及我们之外,全是讲西班牙语的人。由此看来,难怪瑞典社会学家经常为了是否要强制外来移民接受瑞典文化,还是任由他们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问题而争辩不休。这种现象与当初美国实行自由移民政策时所争辩的问题如出一辙。
美国境内的迁移现象与欧洲的大规模迁移现象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的大部分迁移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持续过渡现象,是由过去向现在的过渡。欧洲只有少数地区才发生由工业社会向超工业社会的过渡现象。相反,美国境内所发生的人口迁移并非起因于农业的没落,而是起因于自动化工业及新生活方式的盛行,而自动化工业及新生活方式则产生于超工业社会的冲击。
这种情形只要看看美国所发生的人口迁移现象,即可一目了然。不错,美国境内某些技术较落后的地区也有高度迁移现象,但迁移范围仅限于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但是,这些居民在全部的人口比例上只是极少数而已。倘若将这种地域流动性完全归结于贫穷、失业或知识缺乏等因素,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一年以上的人往往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富有流动性;从事专业性职业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美国人的流动性往往高于其他人。而这些经常迁移的专业性人才已日渐增多。在超工业社会出现之际,最突出的人才要算是专业人才、技术人才以及管理型人才这三类。而他们不管在人数上或在工作中发挥的重要性,皆与日俱增。他们在当今社会的突出表现,同过去身着工作服的技术工人一样。
正如数百万贫苦的农村劳动者从过去的农业社会涌向欧洲的现代工业社会一样,欧洲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也开始流向美国及加拿大等超工业化国家。欧洲的一些政治领袖已开始为“技术”问题忧心忡忡,他们抱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美国联合化学股份公司、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高薪从伦敦及斯德哥尔摩等地吸引无数的专业人才。
美国本土也有人才流动的现象发生,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在美国境内流动、迁移,就像微粒子在原子里运转一样。事实上,这样的流动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南方和北方,集中于加利福尼亚及西海岸的几个州,中转站在丹佛;另一种从南方绕向芝加哥、剑桥、普林斯顿及长岛。此外,还有一种逆向潮流,将人才带回佛罗里达一带的太空及电子工业。
与我熟识的一个青年航天工程师,辞掉普林斯顿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工作,转到通用电气公司。他卖掉两年前买的房子,举家迁移费城附近的一处出租房屋里。这是5年来他们第4次搬家。目前,加利福尼亚州的航天事业正在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
管理型人才的流动状态目前较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其流动率将更为惊人。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曾在《组织中的人》( The Organization Man )一书中说:“在美国,离家从业的人员不是例外情况,而是理所应当的。几乎从定义上就可看出,管理型人才是离家而不停迁移的人……”他的描述在现在看来更为正确。《华尔街日报》将这种人称为“企业的吉卜赛人”。该报曾登载了一篇名为《职业人士的家庭如何适应经常迁居问题》( How Executive Family Adapts to Incessant Moving About Country )的文章,该文描述了一个叫M.E.雅各布森(M.E.Jacobson)的职业人士的生活状况。他跟太太在该文报道时都是46岁。在26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前前后后共搬家28次之多。他的太太对记者说:“我觉得我们简直是在露营。”这种情形虽不多见,人们每两年搬一次家的情形却为数不少,而且在激增中。此类迁移情形,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事业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上司认为,经常迁移住所有助于训练企业的继承者。
这些企业从一处迁到另一处,有点儿像棋盘上的棋子。有位心理学家曾突破性地提出一种省钱、省事的计划,名为“组合性家庭”。在这个计划里,企业人不仅离开自己的住所,同时离开家眷,由他所属公司在其上任之后代为物色一个“毫不逊色”的家庭(该居所的所有成员都经过仔细挑选,以期各个成员的性格特征都能与他自己的妻儿相符),而他自己的家庭则由其他合适的巡回性职业人士“补缺”。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考虑采用这个计划。
除了这些专业人才、技术人员、职业人士等过着迁移生活之外,我们社会里还有其他许多特殊的流动阶层。不管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成千上万的随军家属都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我再也不需要装修屋子了,”一个陆军上校的太太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几乎搬一次家就要换一次窗帘,地毯不是尺寸不对,就是颜色不符。从今以后,我只要装饰汽车就好了。”目前,又有好几万名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加入了这个迁移的行列。另外,至少有75万的美国学生到外州念书,而虽在州内念书但不住在自己家里的学生至少有几十万人。对现在几百万的人,尤其是“未来的人”而言,所谓家,就在你以之为家的地方。
人口迁移的热潮带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副作用。很多厂商因为顾客住址的变更不知耗费多少成本才能将商品送到他们的新住处,电话公司也因此痛苦不堪。1969年,华盛顿市的电话簿约有客户88.5万名,而在短短一年内,变更号码的客户约占一半。还有许多组织及团体都因其会员的住址变更而大感头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会员约有1/3改变地址。即使是亲朋好友,有时在联络对方时也深感不便。
虽然有以上诸多不便,但速度、行动甚至迁移已为许多人带来肯定的意义。这个事实可以从美国人及欧洲人所喜爱的汽车上看出来。汽车正是人们享受空间自由的一种技术性表现。美国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曾大力宣扬弗洛伊德学说,而他所说的“汽车是有力的控制工具”,在现在看起来,极具慧眼。“汽车俨然已变成现代的标志,而驾照也变成进入成年人社会的有效许可证。”
对于富裕国家,欧内斯特·迪希特写道:“一般人衣食无忧,在实现了人类千年的梦想之后,民众便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他们要旅行、要探寻,要独立且无拘无束。而汽车则是最富有流动性的象征……”事实上,一般美国家庭面临经济困境时,最后放弃的东西才是汽车。一般美国父母处罚子女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他们“动弹不得”——不准他们开车。
当你问美国女孩说,她认为哪些事情对男孩比较重要时,答案里必然有“汽车”。据调查显示,约有67%的女孩认为汽车极为重要。一个19岁的男孩垂头丧气地说:“你要是没车的话,就别想交女朋友。”17岁的男孩因驾车超速被吊销执照后,他父亲不准他再开车,他居然因此而羞愤自杀,这个男孩在用0.22口径的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曾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没有了执照,我再也不能开自己的车,也无法找到工作,更别谈社交生活了。我想,还是趁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比较好。”这个悲剧充分表明,普通的少年对汽车的狂热程度。
固定的社会地位与固定的地理位置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超工业社会中的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迫感时,他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迁移。这种事情在乡间的农民或矿区的矿工身上很少发生。“迁移可以解决一切,走,旅行去!”过去,一名和平队的学生志愿者曾这样呼吁。但有时,迁移本身能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成为一种自由的宣言,而非仅是逃避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
这种狂热的迁移在搭便车的女性身上表现得最为极端,而搭便车的行为已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英国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少女杰基(Jackie),辞掉为杂志社推销广告的差事后,决意搭同伴的便车去往土耳其。到了汉堡以后,两人便分手。杰基乘飞机飞过希腊半岛之后直达伊斯坦布尔,然后返回英国,在另一家杂志社谋到一份差事。她工作的目的是攒够下一次旅行的费用。当她又一次旅游归来之后,就在一家餐厅当女侍应生,她拒绝被升为女招待,理由是“我不想在英国待太久”。杰基在23岁时就是一个搭便车的人,她仅仅扛着一个行囊,装着一把气枪,就几乎跑遍了全欧洲。回到英国住上半年或8个月后,她又动身旅行去了。28岁的露丝(Ruth)过这种生活也有好几年了,她在外最长的一次逗留长达三年。她说,搭便车的生活方式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样,你可以跟很多人交往,但又不会被拖累。
这种对流动生活的热爱也可以从普通美国人对旅行者的羡慕态度上表现出来。据密歇根大学的报告所示,一般人往往以“幸运”或“幸福”来称呼旅行者。旅行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因此许多美国游客在旅行归来很久以后,还舍不得把行李袋或提包上的标签摘下来。有人甚至开玩笑地建议旅行社制造一些铁制的航空标签,以供爱出风头的人好好表现自己的身份。
然而,一般人对搬家者抱以同情,而非庆贺的态度。我们通常安慰搬家者的辛劳与艰苦。但奇怪的是,搬过家的人通常比没搬过的人更乐于搬家。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解释道:“搬过家的人通常不会固守一地,他们更易于搬家……”英国一位商会官员R.克拉克(R.Clark)曾在国际人力会议上说,迁移的习惯可能是在学生时代形成的。大学时代在外求学的人往往比那些未在外求学而在本地工作的人更富有流动性。他同时指出,不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此,他们甚至能将这种迁移的习惯传给子女。对许多劳工家庭而言,搬家可能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找工作或其他困难不得不搬,但对收入在中等以上的家庭而言,搬家通常是为了生活的改善。对他们而言,旅行是一种乐事,而迁移也意味着高升。
总之,在向超工业社会过渡的国家里,在未来的人看来,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摆脱过去的自由,是迈向更富裕的未来的必经阶段。
社会上一些“安居者”对迁移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现象多见于长期或终生固守一地的农民、蓝领工人以及不发达工业地区的劳工。当技术变革的旋风吹过经济发达地区,横扫整个工业界并在一夕之间使整个地区焕然一新之后,无数的技术不熟练及半熟练劳工便不得不开始迁移。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政府,像瑞典、挪威、丹麦及美国等,便花费大量资金为劳工培训新技能,因此劳工迁移的现象便发生了。对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的矿工或法国边境的纺织工人而言,这种迁移无疑是极端痛苦的事。有些大城市的工人有时甚至因城市重建需要搬到别处而大感头痛。
社区研究中心的马克·弗里德(Marc Fried)博士说:“简单地说,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悲哀的表现。他们垂头丧气、失落、无助,并且时常在心理上、社交上或身体上表现出受挫的迹象……有时他们会怒火中烧,并且有将故居理想化的倾向。”这些反应,他认为与沮丧的人极为相似。法国社会部的莫妮克·维奥(Monique Viot)指出:“法国人喜欢住在故居。他们不愿意,应该说极不愿意到三四十英里以外地方工作。工会甚至将离家很远的工作称为‘放逐’。”
有些受过较高教育及生活较富裕的人在必须迁居时,会表现出沮丧的神情。作家克利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记述他从康涅狄格迁移到洛杉矶时写道:“不久,我身体及心理强烈地感到一种被击碎的痛楚……这种痛楚一直延续了半年。神经科医生说我患的是一种‘文化的冲击’的病症……因为即使搬到最适宜的环境,一个人也会面临许多心理适应上的困难……”
社会学家J.R.西利(J.R.Seeley)、R.A.西姆(R.A.Sim)及E.W.卢斯利(E.W.Loosley)在对加拿大的一个郊区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指出:“过渡时期的变革对人格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除非我们的人格具有最大的稳定性,我们的行为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否则将无法应对。一切意识形态、语言习惯、饮食习惯以及室内装饰风格等,都必须随着这种变革而改变。在没有直接指导下,个人行为更需入乡随俗。”
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詹姆斯·泰赫斯特(James S.Tyhurst)说:“在对移民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移民最关切的、也是最开始(第一阶段)做的是找工作、赚钱、找房子,而这些都是极其费神的活动……”当一个人在陌生环境开始感到孤独或不适时,第二阶段的“心理因素”便开始渗入。“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移民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沮丧,身体感到不适,行为表现出恐慌、退缩的倾向,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猜忌与敌意。此外,冷漠及无助感也随之强烈起来。这个阶段的特色是心烦意乱、无所适从。这种不安可持续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之后,第三阶段便开始了。这时适应新环境的形式开始出现,他们开始与陌生人接触,开始适应新环境。但如果适应不来的话,他们“便会感到更大的不安,内心极为混乱,甚至开始出现心理反常的特征,想法与现实完全脱节”。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适应不来。
即使迁移者能够适应,也无法和他过去的状态保持一致。因为任何迁移势必会破坏过去关系的组织网,还要重新建立一种新关系。倘若这种破坏性一再重复,迁移者将会丧失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而这一点许多作家在阐述高度流动性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时都曾强调过。一个经常迁移的人通常不能扎根于任何一个地方。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都避免参与居住地的政治生活,因为“几年后,我可能不住在那儿了。连你自己种的树,都无法看到它成长”。
有些人认为,这种“不介入”或“极为有限的参与”,对“草根民主”的传统理想危害极大。但是,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些拒绝参与社区事务的人,很可能比那些表面参与但不久便溜之大吉的人更富有道德感和责任心。这些迁移者表面上赞成提高税率,最后却不承担苦果,因为他们已经搬走了。他们赞成提高学费,最后却让别的家长叫苦连天。或许有人会提议,准备搬走的人必须事先放弃投票权,但要是一个人完全不参与、不加入组织,与邻居不相往来,取消自己的一切参与的权利的话,那么他与整个社区靠什么来维系关系呢?倘若没有任何约束关系的话,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
参与意识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种就是人与地域的依附关系。只要明白一个固定地方在过去人类的心中居于中心地位,我们便可以明白流动性对现代人的影响。那种中心地位可以从文明的许多层面表现出来。文明本身发源于农业,而这正代表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游牧民族,经过千万年的长途跋涉之后到达的终点。它是恒久的安居之乡。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视的“扎根”就是源于农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游牧民族,在听到我们讨论“扎根”的问题时,很可能无法抓住这种概念的真正含义。
扎根意味着一个固定之所,一个恒久的家。在一个野蛮、饥饿且危险的世界里,家,即便是一个简陋的小屋,却是最终的避难所。它扎根于土地,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成为人与自然和过去的唯一联系。固守家园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文学艺术也一再讴歌家的重要性。16世纪,托马斯·塔瑟(Thomas Tusser)写的《主妇训谕》( Instructions to Housewife )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寻家以憩,居家最宜。”而当时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亦是歌颂家庭,如“家是城堡……”“走尽天涯,还是自己家最好”“家……甜美的家……”这样文化风气在19世纪的英国达到高潮,因为当时正值工业主义盛行,处于将过去宁静的家园转变成大都市的过渡期。大众诗人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曾写道:“人心皆在轻唤,家,家的到来……”而丁尼生(Tennyson)更是将此情此景描写得令人无比神往:
英国的家园鱼肚白的曙光轻泄在
沾满朝露的杂草间、树叶里。
轻软若眠,万物井然而依。
嗯,这是静幽古梦的重温。
但在工业革命的袭击之下,万物已经不可能“井然而依”了。不错,家是避风的港湾,是定居之所,它却处于激流之中。倘若没有其他影响的话,家或许还能停留在原处。然而,这只是诗歌而非现实,在激流的冲荡之下,即使有家也是归不得了。
过去的游牧民族在风雪、酷暑及饥饿的逼迫下迁移别处。他们连同自己的毡房、家属以及部落等一起迁走,整个社会环境及家庭结构都没有改变。相反,今日的游牧民族却将“毡房”留在原地。除了家属之外,整个社会环境都随之改变了。
地域及其约束关系的重要性已逐渐下降,而这种趋势可由许多方面看出来。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一向的联合决策便是一例。常春藤大学联盟在入学条件方面已经大大降低对地域的考虑。这些世界一流高校在传统上一向比较欢迎距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便集各地学生于一堂。20世纪30—50年代,哈佛大学录取的来自新英格兰及纽约地区的学生的名额数量降低了一半。今天,哈佛大学的一位行政人员却说:“我们早已取消地域分配制度。”
今天大家都承认,地域已不是“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最主要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与地域环境没有绝对密切的关系。申请表格上的地址只是暂时的而已。耶鲁大学的招生部主任说:“当然,我们仍吸收像内华达州等偏远地区的学生,但从哈莱姆、公园大街、皇后区招收的学生其实也是多样化的。”据这位负责人说,耶鲁大学在选择学生时已不再考虑地域因素。普林斯顿大学也宣称:“我们所考虑的不是学生来自何方,而是不同的背景。”
在流动性的影响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再由地域条件决定。地域对人的约束关系已大大降低,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迪克曼教授(John Dyckman)所述:“目前,一般人对城市或州郡的忠诚度远不如他们对自己所属公司、职业或团体的忠诚度。”由此看来,约束关系已由地域性的社会结构(城市、州郡、国家或其他邻近地区等)转变成富有流动性、实用目的而无地域限制的事务了。
然而,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当我们在文化的熏陶下,培养了对持续时间的预见能力时,我们便对较为永久的或持久的关系投入感情,并尽可能少地对短暂性的关系投入感情。当然,这也有例外,夏天里的短暂恋情便是一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搬家确实会改变人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与地域之间关系的削弱,不是与迁移本身有关,而是与迁移的附带现象有关,即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
举例来说,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70个主要城市,市民平均居住于一个地区的时间不超过4年。这种现象与终生固守一地的农民正好成对比。而且,居住地的改变导致其他许多地域关系的改变,因此当个人与一处住宅的关系结束之后,他与邻近的其他许多关系亦告终止。超市、加油站、公交车站、理发店等跟他的关系也因其迁移而改变。因此,我们虽然有了在更多地方居住的经历,但我们与每一个地方的关系在时间上越来越短。
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加速推动力对个人的影响。由于人与地域关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人与物关系的持续时间也随之缩短。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与外界关系的形成与断裂将更加快速,短暂性的局面越发增多,这将使个人经历更快速的生活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