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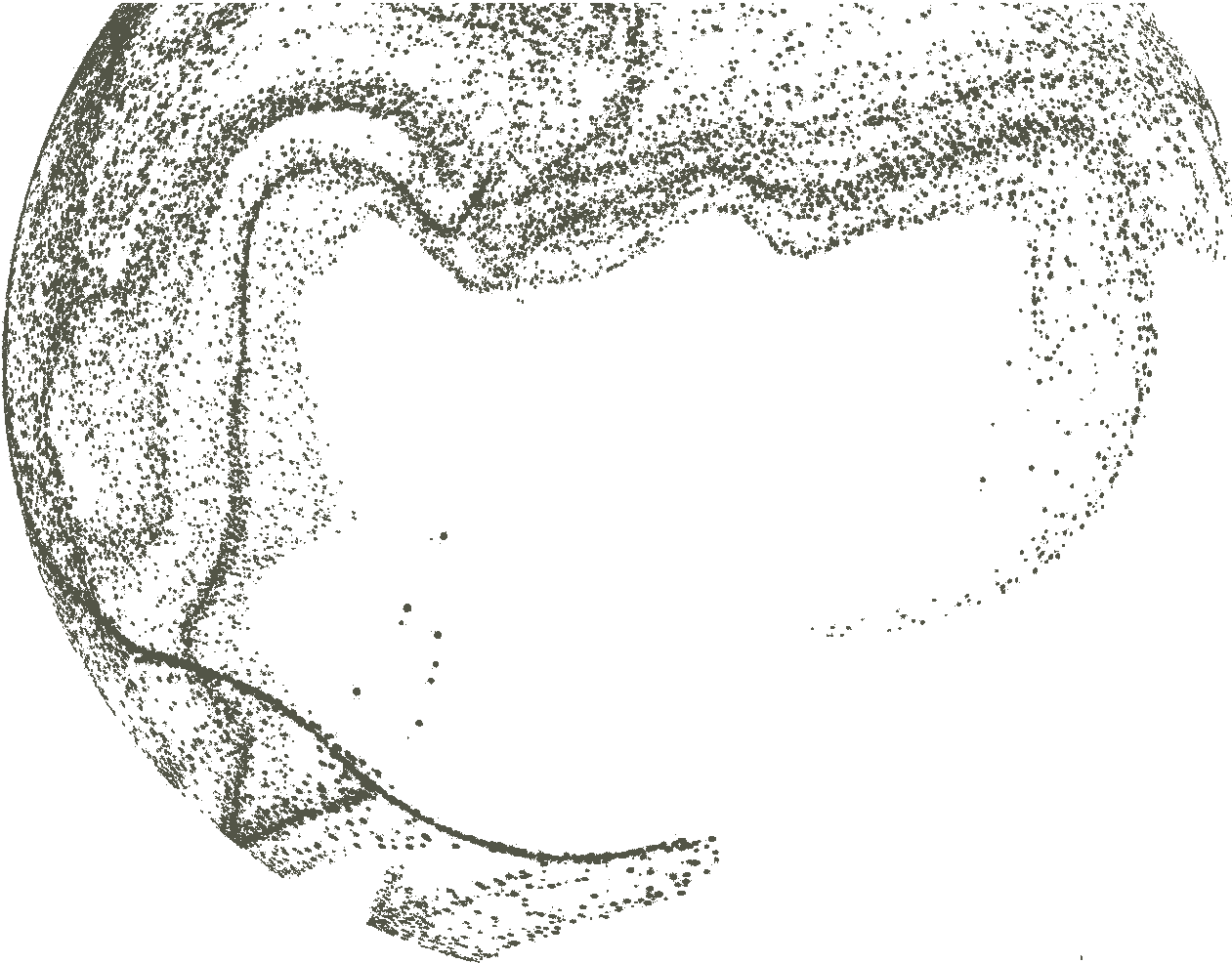
芭比娃娃,一种12英寸
 高的塑胶玩具,是有史以来最知名且最畅销的洋娃娃。自1959年问世以来,全世界已生产的芭比娃娃比洛杉矶、伦敦或巴黎的人口数量还要多。小女孩都很喜欢芭比娃娃,因为这样的娃娃栩栩如生、衣着华丽。芭比娃娃的制造厂马特尔公司兼售娃娃的日常服装、礼服、泳装及滑雪服等在内的全套衣服。马特尔公司后来还推出一种改进的新型芭比娃娃。新型芭比娃娃身材较为苗条,有仿真的睫毛,伸缩自如的胸衣等,凡此种种都比以前的产品更酷似人类。马特尔公司还宣布,人们以后若想购买芭比娃娃,可先用旧的娃娃换取抵用购物券。
高的塑胶玩具,是有史以来最知名且最畅销的洋娃娃。自1959年问世以来,全世界已生产的芭比娃娃比洛杉矶、伦敦或巴黎的人口数量还要多。小女孩都很喜欢芭比娃娃,因为这样的娃娃栩栩如生、衣着华丽。芭比娃娃的制造厂马特尔公司兼售娃娃的日常服装、礼服、泳装及滑雪服等在内的全套衣服。马特尔公司后来还推出一种改进的新型芭比娃娃。新型芭比娃娃身材较为苗条,有仿真的睫毛,伸缩自如的胸衣等,凡此种种都比以前的产品更酷似人类。马特尔公司还宣布,人们以后若想购买芭比娃娃,可先用旧的娃娃换取抵用购物券。
很可惜,该制造厂没有宣布可以通过抵用购物券换购新型芭比娃娃。现在的小姑娘,即超工业社会的市民,通过这件事可以学到新社会的重要一课:人与物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
如今,我们已经置身于种种人造物品的海洋中。随着技术的发展,由技术造就的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水泥、塑胶制品,夜晚中车灯的闪烁、从飞机窗口看到的城市景观……这些都与个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人造物品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改变我们的看法,目前人造物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取代自然物品。这种现象在超工业社会里更为显著。
一些反物质主义者极力轻视物品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物品的重要性却丝毫未减。因为物品具有实际用途,而且对人们的心理具有高度影响。我们无法与物品断绝关系,物品影响了我们的连续感或断绝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况,缩短我们与物品的关系,同时使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此外,我们对物品的态度也反映出我们基本的价值观。过去的小女孩爱不释手地照顾芭比娃娃,直到坏了才肯搁置一边。现在的小女孩却满心欢喜地抢着去买新款芭比娃娃,两者的对比足以看出其中价值观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实际上就是长久性的旧社会与短暂性的新社会之间的差别。
我们从小女孩换购芭比娃娃的现象便可看出,人与物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其实,小女孩不久便会发现,芭比娃娃并不是唯一在生活中很快出现又很快消失的东西。尿片、围裙、纸巾、可乐瓶等几乎都是用完即弃的日用品。简便的晚餐也常用一次性盘子盛放。现代家庭可以说是各种东西进进出出的一个大型过滤性机器。新一代儿童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完即弃的文化里。
用完即弃的观念与过去贫穷时代的一般观念正好相反。不久以前,尤里尔·罗尼(Uriel Rone),一位法国广告公司的市场调查员告诉我:“法国的家庭主妇一般不喜欢用一次性的产品。她们喜爱保存东西,即使是古老的东西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替一家厂商策划一种塑胶材料的一次性窗帘的广告,事前做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发现这种材料的窗帘颇受敌视。”而目前发达国家对人造材料的敌视越来越普遍。
一位名为爱德华·梅兹(Edward Maze)的作家曾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许多访问瑞典的美国人都惊讶于该国环境的整洁,“街旁看不到一个可乐瓶或啤酒瓶,真叫我们美国人感到羞耻。但到20世纪60年代,老天!瑞典的高速公路旁到处都是冷饮瓶……这是怎么搞的?瑞典也像美国似的变成一个用完即弃的社会了”。今天的日本,一次性物品十分普遍,手帕已经过时;在英国,只要花6便士便可买到一次性牙刷,并附有牙膏;在法国,一次性打火机也十分普遍。从纸制的牛奶杯到火箭,都是短期使用的物品,随着其产量的增多,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全盘否定。
最近问世的纸制及半纸制的服装,使这种趋势更推进了一步。充斥于大百货公司的轻便工作衣又使纸制服装更加多姿多彩。时装杂志煞费苦心地设计了种种纸制的外套、睡衣,甚至结婚礼服。其中有一幅照片是一个穿着酷似花边纸的白色长袍的新娘,照片旁标着:“婚礼之后,这件衣服将变成厨房的窗帘。”
纸制衣服对孩子们尤其适用。一个服装设计师写道:“小女孩可以随意在衣服上涂抹冰激凌、画画,甚至剪洞,母亲会站在一旁,高兴地看她们表演。”要是成年人想露一手,可以花两美元买来一套附送水彩笔的“自己画衣服”式的纸制衣服。
当然,价格也是导致纸制品呈爆炸式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将来,有些百货公司会出售名为“随遇而安”的尼龙纤维质衣服,每件仅售1.29美元,几乎比洗一件旧衣服的价钱还低。用完即弃的文化一旦盛行以后,问题不只产生于经济方面,还会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影响。
为了适应用完即弃的产品,我们自然而然会养成用完即弃的心理,价值观会随着物品的性质而改变。“用完即弃”一经流传,人与物品之间的持续时间将大为缩减。过去我们与物品之间的长期关系,将被物品的连续更换的短暂性取代。
从建筑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短暂性的趋势。建筑在过去可说是维持人类持久感的最重要的物体。换购芭比娃娃的孩子们免不了会发现,周围的建筑物也越来越短暂化了。我们将历史性的建筑物拆除,将整条街道甚至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更是以极为惊人的速度建造新建筑。
“住房的平均年龄已逐渐下降,”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E.F.卡特(E.F.Carter)写道,“洞穴时代,人类的居所可无限期使用……到了殖民时代,美国的房屋年龄约100年左右。而现在,每幢房子仅仅住40年而已。”英国作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评论道,美国人“昨天刚刚建立一个世界,今天却感到不稳定。纽约的建筑物可在一夜之间消失,而一个城市的风貌可在一年以内改头换面”。小说家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愤愤地抱怨道:“住在纽约简直跟住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一样……我的祖先都住在这个城市,他们那时的房子到现在仍屹立不倒的只剩一幢了。我所说的‘消失的过去’正是这个意思。”后来移民到美国的波多黎各人、东欧人或南欧人等对建筑的这种印象或许更深。过去的消逝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现象。
设计师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将纽约描写成一个“拆除、毁坏、移动、暂时真空、再建立的连续进化过程。这种过程与庄稼每年轮种的原理相同。先是耕犁,然后撒种、收成,再来一次深耕,换另一种庄稼……许多人以为纽约的建筑施工只是暂时封堵街道而已,竣工后便可平静下来……他们仍然认为持久性才是正常的,他们的观念似乎还停留在牛顿的宇宙论上。但是,20世纪初就生活在纽约的人,都已深刻体验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事实上,我本人就曾亲身体验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久前,我太太曾让12岁的女儿到距离我们曼哈顿公寓不远处的一个超市购物,她以前只去过那儿一两次。半个小时后她回来了,一脸困惑地说:“一定被拆掉了,我怎么也找不到。”是的,超市的确被拆了,但我们新搬来的邻居以为自己走错路呢。我女儿是生长在一个“短暂性时代”的小孩,她的直觉猜测超市被拆除了,这就是生长在现代美国的12岁小孩的自然反应。这种想法在生活于50年以前的小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因为过去物质环境的持续时间较长,而我们与它的关系维持时间也较长。
在过去,凡是持久的总是好的。不管制造一双鞋或盖一幢教学楼,大家的精力与创意都在设法让该产品的持续时间增加。“建”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长久”使用。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少有变动,每一件物品都有明确的功能,这样的经济逻辑便形成一种持久性的方针。即使东西偶尔需要修理,但总的说来,50元一双的鞋子穿10年,总比10元一双的鞋子穿一年要便宜许多。由于社会加速变革的影响,持久性的经济势必会被短暂性经济所取代。
第一,先进的技术使制造成本的降低速度快于修理费的降低速度。因为前者已形成自动化,而后者尚停留在手工阶段,也就意味着重购比重修更便宜。此外,制造并销售价格便宜、不可修理、用完即弃的东西,在经济上更为划算,虽然没有可修理的东西耐用。
第二,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也跟着时代一再改进。第二代电脑比第一代要改良许多,而第三代电脑又将比第二代先进一步。由于技术一再改进的结果,进步所需要的时间比以往大为缩短。因此,短暂性的产品将比持久性的产品更符合现代经济原则。匹兹堡都市设计协会的都市计划师、建筑师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曾说,迈阿密的某个公寓楼房只使用10年便全部拆除。由于新型的房屋配有更完善的空气净化设备,因而这些“老”房子已经租不出去了。几经考虑之下,屋主还是觉得拆除重建要比重修划算得多。
第三,由于变革在加速且花样一再翻新,未来需要什么将越来越难以预测。虽然我们知道未来势必变革,却无法确定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不敢花费大量资金制造固定不变的产品。为了避免形式与用途的固定,我们都尽可能制造短期性物品,或者设法使产品本身有适应性。在技术上,我们要尽量“老谋深算”。
除了物品的使用具有短暂性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设计、制造和使用物品的心理。例如,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一种专供短期使用的大型产品,而且它们不是用完即弃的东西。它们通常规模较大,价钱也较为高昂,构造具有“可拆除性”,也就是不需要时可以整体拆下来。洛杉矶的教育局已经决定,今后25%以上的教室将建成一种临时性的建筑,在需要时可随时移动。目前,美国一些学校已开始使用临时性的教室,而且使用这种教室的学校将越来越多。临时性教室对于学校建筑而言,正如纸质衣服之于服装制造业一样,都是未来的前奏曲。
临时性教室主要是用来帮助学校解决人口快速迁移问题的。但正如纸质衣服一样,临时性教室意味着人与物的关系持续时间将会缩短。因此,临时性教室即使在没有教师时,也可以教会学生一些东西。前面谈过,芭比娃娃的故事间接暗示了小孩子,他们的周边环境并不是永久的。同样,学生可以从临时性教室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例如教室是如何安装的,夏天时桌子会怎么样,教室里的回音又是怎么回事等。
临时性教室并不只是在美国出现。在英国,普莱士建筑公司已设计了一种名叫“思考带”的建筑,是一所可供两万人上课的流动大学。该公司说:“它将使用临时性建筑物,而不使用永久性的。”它将利用一种“流动的、可改装的建筑材料”,比如所有教室将盖在火车里,随时可在4英里长的校园里移动。
专供建造展厅用的圆顶,专供建造战役指挥中心或建筑设计总部用的塑胶泡沫以及其他许多种临时性建筑材料,目前已经从建筑师及工程师的制图桌上应用于实际建造。纽约市公园与娱乐管理局已经决定建造12个“可移动的运动场”,计划在城市的空地上设立一种临时的小型运动场,只要场地另有他用,即可拆除。运动场一向是附近居民运动的所在地,有时甚至沿用了好几代。但是,超工业化时期的运动场不愿独占土地,其设计已趋于临时性。
临时性结构及一次性产品的盛行,导致人与物的关系持续时间缩短,而这种趋势更因组合性的急速推广而愈演愈烈。组合性,是指将具有短暂性的基础结构组合起来形成较为长期的整体结构。普莱士建筑公司的“思考带”所提供的设备及学生公寓,都是由钢铁组成。这些钢铁先由起重机举起,然后接入建筑构架上,而构架是全部结构中唯一较为固定的部分。在必要时,钢铁可以前后转动,甚至可以全部拆下来。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的是,“一次性”与“流动性”在持续时间上的差别非常小。当这些钢板重新搭建和组合时,就会形成新的构造,好像一个物理构造被拆除并建成一个新的一样,虽然里面的组成元素未变。
即使现在许多被视为“永久性”的建筑,但大部分也是依照组合性原则来建造,所以里面的墙壁及物体可随意移动而构成一种新的构造形态。事实上,这些可移动的物体正好可以视为短暂性社会的象征。可移动的隔墙在一般建筑物里已十分普遍。现在,瑞典的组合性产业已十分发达,乌普萨拉的新型公寓大部分都已装上一种可移动的墙壁及壁橱。房客仅需一把螺丝刀即可改变生活空间,塑造一个新的公寓。
有时候,组合性与一次性直接配合从随处可见的圆珠笔上就可以看出来。过去,鹅毛笔曾被使用很长一段时间,钢笔的发明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钢笔比较便于携带,且备有墨水管,因此扩大了普及范围。圆珠笔的问世更是一种进步,它除了自身备有墨水之外,更因为价钱便宜,笔芯用完之后便可随时丢掉。从此,第一个装有墨水的一次性的笔真正出现了。
但有些人似乎仍不习惯这种浪费,有些人仍舍不得将用完的圆珠笔丢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设计师便把组合性应用到圆珠笔上:在圆珠笔笔芯用完后,外部的笔杆可以继续保留下来,内部的笔芯此时便可丢掉。如此一来,笔芯便成了消费品,用完丢弃之后,整个笔的寿命还可延续下来。
相比之下,零件总比整体结构的数量多得多。调换零件也好,或整体丢弃也好,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将不断感受到种种物品的快速进出,而我们与物品之间的持续时间将更为缩短。这种结果将一连串地造成新的流动性、改变性及短暂性。
在英国戏剧演员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结构工程师弗兰克·纽比(Frank Newby)、系统工程顾问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以及“思考带”建筑师普莱斯等人的通力合作之下,一种利用以上所有原理建造的新建筑即将问世。
利特尔伍德计划建造一种“全能”的剧院,从普通戏剧到政治集会,从舞蹈表演到摔跤大赛,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而且最好能同时进行。正如评论家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所说,利特尔伍德就是要一个“全能地带”。于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剧院”计划开始了。这个计划所要求的不仅是一个能实现“多重目的”的建筑,还要求一种可任意拼接的组合系统。这种“永久性”的直立塔几乎包含一切的服务性设备,如盥洗室、电控室等。不但如此,该建筑物的底部由一种高架移动起重机所支撑,因此整个建筑可随时移动,甚或可以整体拆散成许多临时性的、相互独立的部门。在晚上娱乐节目结束之后,大礼堂、展览厅以及餐厅等都可以拆开,各自独立。
班汉姆曾就这个建筑物描写道:“事实上,这个剧院只是使用10年的都市设备之一,但这个未来建筑里会拥有很多可移动的构造,诸如墙壁、地板、过道、电梯、座椅、屋顶、舞台、银幕、照明设备及音响设备等。”倘若大家觉得围墙及楼梯露出来不雅观,只要一按钮,便会完全改观。
当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以后(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社会将会产生一种新的现象:没有永久性的纪念馆,也没有英雄的半身像……因为唯一可见的永久性要素也只限用一个时代而已。
一些所谓“可拆装”建筑的拥护者已打算按照“短暂性建筑”的原理,设计整个“可拆装”的城市。他们计划利用游乐场的概念来建造各种不同形态的小型建筑,这些建筑各有各的寿命。建筑的主要结构或许可“活”到25岁,但其余零件的适用年限仅有三年。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甚至想设计一种可移动的摩天大楼,但大楼的地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一种具有地基效果的机器或活动地基上。他们的最终理想是使整个城市免于固定一隅,希望利用原子能的力量使整个城市浮在气垫上,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城市景观会变得更快。
不管这些愿景是否会实现,但目前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现在的社会正朝这个方向前进。用完即弃的文化在逐渐扩大其影响范围,短暂性及组合性的结构越来越普遍,而它们具有相同的心理影响力,都会造成人与物的关系短暂化。
还有一种发展同样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租赁革命。迈向超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租赁风气的盛行,这与前面所述的种种趋势有密切的关系。租车、一次性尿布和利特尔伍德的剧院乍看起来毫不相关,但仔细一想,它们之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因为租赁风气会强化短暂性。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因此,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一个住处便成为最有力的经济动机。即使在当今的美国,人们拥有房子的欲望仍十分强烈,但“二战”后的美国,公寓出租的风气突然盛行起来。1955年前后,美国的公寓出租率每年约增长8%,到1961年,这个增长率达到了24%。1969年,美国出租公寓的数目首次超过私人住宅。公寓生活之所以流行,原因很多,但最特殊的原因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伯纳姆·凯利(Burnham Kelly)教授所说的,大部分人都需要一个“简便且经济”的住所。
简便、经济正是“用完即弃产品”消费者的价值观,也是短暂性和组合性的产物。从定义上,我们即可看出,租赁房屋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自用住宅的持续时间短。租赁房屋的趋势使居民与其物质环境的关系也越发缩短。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有些租赁活动几乎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曾写道:“一般人都喜欢汽车,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主要话题,但这种喜爱只有5分钟的热度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一般美国的车主使用一部车子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年半,有许多人甚至只使用一年而已。因此,美国花在二手车上的消费约达200亿美元。这种汽车工业首次打破“购置贵重物品须考虑该物品的长期使用性”的传统观念。由于新车型的改进,对新车型的大力宣传,再加上厂商本身也愿意让顾客以旧车换购新车,因此美国每年换新车的人数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不但缩短了购物的时间间隔,也缩短了车主与汽车之间的关系持续时间。
最近几年,一种新力量开始挑战汽车行业根深蒂固的固有经营模式:出现了汽车租赁企业。现在,美国数百万人开始租用汽车,时长从几小时至几个月不等。许多美国大城市的居民,尤其是纽约,由于停车不便,人们不愿自己拥有汽车。人们更愿意租一辆汽车到乡间旅行一周,或在全城做短期旅行。目前,美国可以以极简便的手续,在机场、火车站或大饭店等地租用汽车。
当然,美国也把这种租赁企业推广到国外。美国分布在全球的租赁公司,已开始与外国的同业展开激烈竞争。欧洲的汽车厂商开始竞相模仿美国。不久以前,《巴黎竞赛》( Paris Match )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是一个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站在飞碟旁询问一个警察,哪里可租到汽车。虽是一幅漫画,却足以显示租赁之风流行到何种程度。
与汽车租赁企业同时兴起的还有美国市场上出现的综合性商店。这种商店不销售任何商品,一切商品都只用于出租。美国约有9000家这种商店,出租的订单总额高达10亿元,营业额每年增加10%~20%。今天,市场上的产品几乎都能租到,从扶梯、除草机一直到貂皮大衣都租得到。
洛杉矶的租赁农场还为顾客准备了各种树木的幼苗以供栽植,任何想暂时过一下田园生活的人都可亲身体验其中的乐趣。旧金山一个铁道旁的广告牌上写着:“增添田园之乐——活树出租。”而在费城,甚至连衬衫都租得到。目前,外套、拐杖、珍珠、玉石、电视机、露营设备、空调、轮椅、床单、滑雪用具、录音机、香槟起瓶器、银制食器等,几乎在美国每一个地方都能租到。西海岸的成人俱乐部居然出租人体骸骨,以供游行示威之用,《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广告栏甚至出现“奶牛出租”的广告。
瑞典一家女性杂志曾经连续5次报道未来的世界。该文指出,到那时,“我们将睡在一种睡橱里。这种睡橱有一个按钮,按钮一按我们便可在里面吃早餐或阅读,我们还可在同一处租到桌子、挂画以及洗衣机等”。
没有耐性的美国人似乎等不到未来了。事实上,在所有租赁企业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家具租赁业的兴起。有些制造商及租赁公司以每月20~50元的价格出租备有家具、地毯、窗帘及烟灰缸的小型公寓。“你在早晨抵达某个城市,”一个空姐说,“到了晚上,即可找到满意的临时住所。”一个刚从加拿大飞抵纽约的旅客说:“真奇妙,即使我环游世界也用不着担心要搬运东西。”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以‘有’为生的人将不会比以‘行’或‘做’为生的人来得自由。”在租赁风气盛行的今天,人类已经远离了“有”的生活,而开始走向“行”或“做”的生活。未来的人比过去的人生活得更快,他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比过去的人更富有弹性。正像长跑竞赛者一样,负重太多的话将无法更快。他们要过着有科技含量、最富裕、最时髦的生活,但他们不愿背负随之而来的重荷。他们深知,生活在不确定的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首先要学会“驾轻就熟”。
显然,租赁风气势必会缩短人与其所用物品之间的持续时间。这一点只要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可一目了然:在美国男性的一生中究竟使用过多少汽车(无论租用的、购买的或借用的)?这个答案是:购买的汽车在20~50辆之间,租用的则高达200辆以上。购买汽车的车主与汽车的关系一般约持续几个月或几年,而租用车车主与汽车的关系,在持续时间上更是大大缩短。
在租赁风气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将与同一物品产生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持续时间也将大大缩短。当我们将这种原则推广到更多的产品时,便可发现租赁的兴起强化了用完即弃物品、短暂性结构以及组合性的影响力,并与它们齐头并进。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过时性”的概念。一般企业为了避免产品过时,往往致力于产品改革。同时,一般消费者为了赶上时代的发展,也往往选择租赁,或使用一次性的或临时性的产品。对持有永久性理想的人而言,过时性的观念无疑会带给他们极大的困扰,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这种“过时性”是有计划的,他们将更为震惊。“人为性商品废弃”已成为社会评论的争论焦点。
当然,无可讳言,有些生意人为了不断推出新产品以占领市场,往往刻意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同样,美国市场上每年推出的新产品也并非都是由于技术上的实质改变。10年来,底特律汽车的外形设计虽然翻新了10次,但每升汽油可行驶的里程数却毫无增加。石油公司虽然宣称,他们的产品已经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分,但汽油的油质并无多大改变。麦迪逊大道经常鼓吹新产品外形的重要性,并鼓励消费者抛弃半旧不新的物品,以便重购新品。
这时,消费者很容易掉入一种精心布置的陷阱里:制造商加速旧产品的死亡、新产品的问世,也同时被渲染成进步技术带来的天赐之物。
但以上的理由并不足以说明,我们生活中物品的高速周转率。快速的过时性只是整个加速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整个加速过程不仅包括引起加速变革的导火索,也包括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历史进程紧紧跟随着科学的兴起及知识的推进,绝不能单方面地归罪于少数奸商的恶作剧。
很明显,过时性有时是有计划的,有时却没有。一般而言,过时性会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发生。首先,当产品自然而然地落伍到无法发挥其功能时,如轴承被烧坏、纤维被撕毁或管道生锈等。为了维持使用,消费者必须更换产品,而这种过时性可以说是由于产品功能丧失所致。
其次,当新产品性能超过旧产品性能时,新的势必淘汰旧的,因而发生过时性。新的抗生素对传染病的治疗效果远远好于旧的抗生素,新电脑比20世纪60年代的旧电脑在功能上进步许多,价格也便宜许多。这种过时性是源于实质技术的进步。
但是,过时性也可能在消费者的需求或产品所具有的功能改变时发生。事实上,这种过时性的产生绝不像一般人认为的计划过时那么单纯。一件东西,不管是汽车或开瓶器,都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辆汽车绝不只是交通工具,它还可以表现车主的个性、所处的社会阶层。汽车还可提供触觉、嗅觉及视觉上的种种感官刺激。消费者从这些方面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可以超过从汽油消耗量的减少或加速力增大上所获得的满足感。
传统观念认为,每件物品都有一种固定且明确的效用,但这种观念已不适用于今天我们的内心想法和价值观。今天,所有的产品都具有多重功能。不久以前,我在一家小文具店看到一个男孩买了半打粉红色的橡皮。我好奇地走过去拿起一块看了看,并问他:“很好用吧?”他说:“不知道,但闻起来味道很好!”味道的确很好,日本制造商为了掩盖化学气味,特别在橡皮擦上加了很浓的香味。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随着购买者的喜好和时代的改变,产品所满足的需求也开始改变了。
在一个物资匮乏的社会里,需求与“纯”用途息息相关,所以需求具有普遍性,而且很难改变。当物资充裕时,人类的需求与物品用途的关系便逐渐减少,与个人喜好的关系逐渐提高。同时,在一个复杂而快速变革的社会里,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产生于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社会变革越快,个人需求便越短暂化。在一个物资充裕的新社会中,个人往往能享受许多临时性的需要。
消费者对自身的需求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要改变而已,所以广告便利用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造成这种趋势。事实上,关系持续时间的短暂化趋势,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人为性商品废弃的争论或麦迪逊大道的操纵阴谋,而是因为根源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
消费者的需求迅速改变,可由他们随时丢弃用品及经常更换所使用商品的品牌上看出来。倘若权威的广告评论家唐纳德·F.特纳(Donald F.Turner)说得没错,那么广告的主要目的之一,的确是要创造“持久性的偏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广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人们经常更换品牌的结果,正如一家食品工厂的负责人指出的那样,会变成“广告界最大的困扰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品牌失去了踪影。即使目前还存在的品牌,在市场上的地位也时常变化。根据亨利·M.沙赫特(Henry M.Schachte)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品牌能稳居于它们10年前的地位。”就以过去美国最畅销的十大香烟来说,目前只有长红这个牌子尚能保持以前的市场地位。骆驼牌香烟的市场销量早已降低了一半,其他牌香烟的地位升降情况都各不相同。
这种不断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受到广告的影响,但又不完全受其影响。尽管从历史学家的长期观点来看,这些变革不值一提,但这些持续的变革造成商品的短暂化,并使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改变,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上的高速、动荡和短暂之感。
商品地位的迅速改变,一方面源于技术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又与技术的快速变化相互作用,结果不仅导致普通产品及品牌的流行程度经常改变,也缩短了产品的存在周期。自动化专家约翰·迪堡(John Diebold)曾一再对企业界强调,他们应该赶快动动脑筋,设法生产短期性商品。史密斯兄弟公司生产的日用品在市场上长盛不衰,所以这家公司变成一个标准的美国公司。它的创办人曾指出,今后将很少有产品能如此经久不衰。许多顾客之所以更换商品的品牌,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老品牌,而是因为他们在超市里已经找不到老品牌的商品。1966年,在美国超市出现的新产品约有7000种以上。今天超市所出售的55%以上的商品是10年前没有的。而当时买得到的商品,约有42%的商品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这种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正因如此,仅在1968年,包装商品约增加了9500种。这种默默而迅猛的消亡战使一切旧商品消亡,又使新商品如海潮般涌上来。
经济学家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写道:“过去可以持续25年的商品,现在只能持续不到5年。而在多变的医药行业和计算机行业,商品的持续时间不到半年。”倘若这种变革速度再加快,以后厂商所出产的商品即使再好,也顶多维持几周而已。
即使在现在,我们已经大概看到未来的景观。各种新潮流已经后浪推前浪地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里推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在美国、欧洲及日本境内都可看到“芭铎发型”“埃及艳后式打扮”“007”“蒂凡尼式灯罩”“铁十字架”“流行太阳镜”及其他许多新奇、古怪的玩意儿,而这足以反映并推动急速变革中的流行文化。
在媒体及市场的推波助澜下,这种流行风潮在一瞬间爆炸开来,然后以同样的速度销声匿迹。在流行性企业使出层出不穷的花招之下,产品生命线变得越来越短。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之下,加利福尼亚州圣加比城居然出现了一家别开生面的惠姆奥制造公司,专门生产流行性玩具。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生产的“呼啦圈”风靡全球。后来该公司又推出了弹力球,虽然只是一种弹得较高的橡皮球而已,但小孩和大人都玩得兴高采烈。惠姆奥制造公司及其他类似的公司,对于商品的“死亡”并不在意。他们甚至故意设法让商品死亡,因为他们的专长是设计及生产“短暂性”的产品。
正因为流行风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为的,所以它们的意义更加深远。即使是工业用的流行品,也不是现代才有的时髦玩意儿,但在过去,它们并没有以如此强大的火力穿梭于我们的意识之间。过去,制造流行品的厂商、媒体以及广告公司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配合得如此完美。
制造并推广流行品需要一套运转流畅、各方配合默契的工作程序,而这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大家了解产品短暂化的必然趋势后,所有厂商必定会竞相采用这种工作方法。如此一来,流行品与日用品之间的界线越来越难以区分。我们已经迅速步入一个使用短暂流行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将采用短暂性的方法满足短暂性的需求。
生活用品的周转率越转越快,我们面临着一种用完即弃的潮流,面临着非永久性建筑、具有可移动性及组合性的产品、租赁用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市场寿命短暂的商品。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人与物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短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