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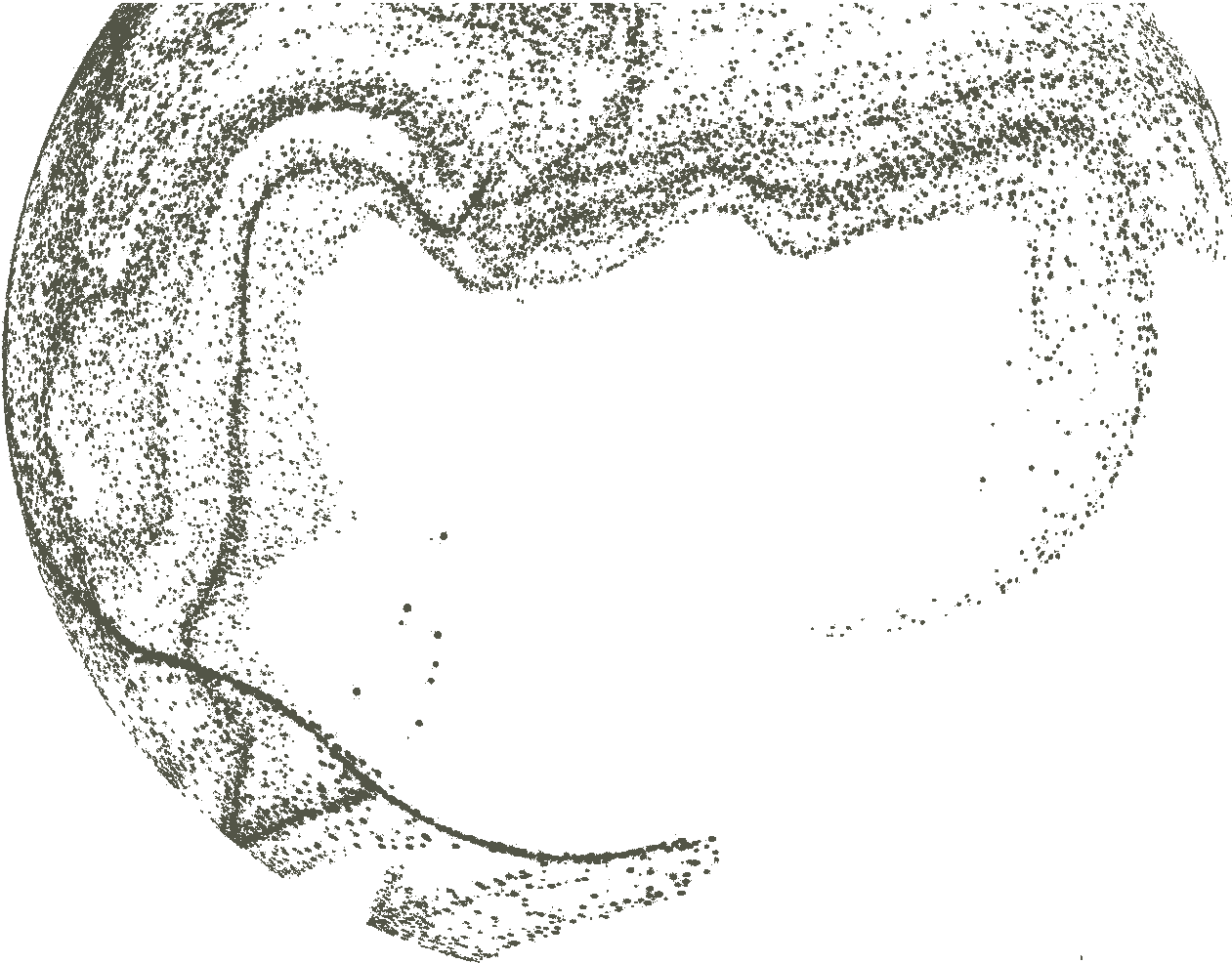
在电视、机场及火车站的广告栏、各种宣传单及杂志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一种照片。照片里的人物是麦迪逊大道
 的得意之作,也是无数人梦想的未来的造型:年轻、英俊、挺拔,提着“007”式的皮箱,看来像一个商人要赴约的样子。但是,他肩膀的两侧露着一个蝴蝶状的、用来给玩具上发条的大钥匙。照片旁的文字部分写着:请“神经紧张”的人来喜来登酒店放松一下。这位行走的被上了发条的人,正是未来许多人的潜在形象。未来,人们将终日匆匆忙忙,一直背着一把大钥匙,被人上足发条,匆匆赶路。
的得意之作,也是无数人梦想的未来的造型:年轻、英俊、挺拔,提着“007”式的皮箱,看来像一个商人要赴约的样子。但是,他肩膀的两侧露着一个蝴蝶状的、用来给玩具上发条的大钥匙。照片旁的文字部分写着:请“神经紧张”的人来喜来登酒店放松一下。这位行走的被上了发条的人,正是未来许多人的潜在形象。未来,人们将终日匆匆忙忙,一直背着一把大钥匙,被人上足发条,匆匆赶路。
一般人很少关心技术改革的循环周期,或对知识的获得与变革速度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生活节奏却了解得一清二楚,不管节奏的快慢如何。
生活的节奏常受到普通人的关注,奇怪的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却很少重视。行为科学最大的漏洞就是忽视了生活的节奏,而生活的节奏本身也影响着个人行为,引起人们许多不同的反应。
如果我们说,生活节奏给人类划了一道分界线,使人们分属不同阵营,使父母与子女之间、麦迪逊大道与缅因街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可以产生误解的话,也并不是言过其实。
地球上的居民不仅可以按种族、国家、宗教或意识形态来区分,也可以按他们所处的时代来区分。当我们考察目前地球上的居民时,可发现有一小部分人仍以狩猎或觅食为生,就像几千年前的人类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以农耕为生,就像几百年前的祖先一样。他们是属于过去的人。
和他们相比,还有很多居民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他们过着现代的生活,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产物。他们在机械化和群众化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却依稀记得过去的农耕生活。他们是属于现代的人。
还有少数人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他们身处技术变革与文化变革的风暴中心,集中在圣莫尼卡、加利福尼亚、剑桥、马萨诸塞、纽约、伦敦及东京等地,过着未来式的生活。这些未来生活的先驱者选择的生活方式,正是其他人未来生活的写照。他们现在的人数虽然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已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未来社会。他们是人类的先进分子。这些超工业社会的最早期居民,目前正处于“临盆之痛”中。
这些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呢?自然,他们比较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性较大,也比较长寿。然而,这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的主要特点是,他们已开始步入一种新的、加速的生活节奏中。他们的生活比其他人过得更快。
有些人被这种快速的生活节奏深深吸引,千方百计地追寻,而一旦生活节奏缓慢下来,他们便感到紧张、焦虑、不适。他们拼命想要跟上“行动的前锋”。(事实上,有些人几乎不管它是什么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是快速的就可以。)例如,詹姆斯·A.威尔逊(James A.Wilson)发现,快速的生活节奏是“人才外流”的潜在原因之一,无数名欧洲科学家移居到美国或加拿大便是力证。在研究过517名移居英国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后,威尔逊得出结论,高薪及优良的研究设备还是其次,对这些移居的人才而言,最主要的吸引力是更快的生活节奏。威尔逊写道:“这些移民并不因为到达了节奏较快的北美洲就肯歇脚,倘若还有其他地方可去的话,他们还是会迁移。”此外,参加过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一个退伍军人也曾指出:“过惯了快速都市生活的人……无法在南部的乡村久居。”这正是有些人喜欢漫游的原因,看来像是无所事事,其实可以起到一种补偿作用。当我们了解某种生活节奏对个人的吸引力之后,我们便能明白其他许多难以解释的或漫无目的的行为。
虽然有些人标新立异、刻意求变,但还有些人对变革唯恐避之不及,拼命要摆脱这种“旋转游戏”。加入紧张的超工业社会就像加入高速的变革世界一样,他们宁愿弃权,选择闲散、舒服的生活。曾经,一个名为《停止地球,我要下车》( Stop the World—I want to get off )的歌舞剧在伦敦及纽约风行一时。
嬉皮士都主张寂静主义,并率先领导大家追求一种“遗世”或“遁世”的新生活,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宣称厌恶技术文明,但他们真正要逃避的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节奏。他们讽刺现代社会,指责它是“鼠类的竞争所”,而这个词指的就是生活节奏。
对于变革的加速趋势,老年人甚至更加反对。根据严谨的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往往站在保守主义这一边。因为时间对老年人而言,似乎过得更快。
当一个50岁的父亲告诉他15岁的儿子,再过两年儿子便可以拥有自己的汽车,而这730天对于父亲而言,只不过占了他之前生命的4%而已;对于儿子而言,却足足占了13%。同样的时间段,父子的感觉却相差3~4倍。同样,一个4岁的孩子对两个小时的感觉几乎等于一个24岁的母亲对12个小时的感觉。这个孩子等了两个小时的糖果,就像他母亲等了12个小时的咖啡一样。
个人对时间主观反应上的差异在生物学上也可寻找依据。曼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约翰·科恩(John Cohen)写道:“年事越高,日子便过得越快。由于新陈代谢作用迟缓的结果,日子也在一年一年地缩短。”由于代谢功能的节奏逐渐缓慢下来,这个世界对老年人而言,似乎变得越来越快,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不管原因如何,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老年人会比年轻人感觉发生了更多的事。由于社会变革的速度一再提高,许多老年人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变革。因此,他们往往变成弃权分子,隐居在自己的世界,尽可能地与高速变革的外界切断联系,最后便只有终日无所事事地等待死亡来临。
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老年人的心理问题,除非我们能发现一种方法,通过生物、化学方法或再教育的方式来改变他们对时间的感觉;或者可能的话,为他们提供一个特殊的避难所,来控制他们的生活节奏。这种特殊的避难所,可以根据老年人对时间的主观感觉来设计。
此外,许多其他令人费解的冲突,如代沟、夫妻之间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差异等,都可以溯源到他们对加速的生活节奏产生的不同反应。同样,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根源于此。
每一种文化皆有其独特的节奏,伊朗小说家埃斯凡迪亚里(Esfandiary)曾提到两个不同节奏的系统之间的冲突。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有一批德国工程师到伊朗帮助他们建造铁路。一般情况下,伊朗人或中东人没有美国人或欧洲人时间观念那么强。当伊朗工人晚了10分钟才开始干活时,守时的德国人一气之下,要把他们全部解雇。伊朗工程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那些德国工程师解释说,以中东的标准而言,这些工人已经非常守时了。如果要继续这样解雇工人的话,恐怕不久之后,来工作的人就只剩下女人及儿童了。
快节奏和急性子的人更难以忍受对时间满不在乎的人。因此,意大利的米兰或都灵等北方工业区的居民,往往看不起生活节奏较慢的西西里人,而这些西西里人仍过着农业时代的慢节奏生活。此外,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或哥德堡居民对芬兰的拉普兰地区的居民也有这样的看法。美国人经常嘲笑墨西哥人的“明天”,即使在美国本土,北方人也常常认为南方人慢吞吞的。而在其他地区的人看起来,美国人及加拿大人无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野心家。
有些人甚至开始攻击生活节奏的变革。许多人对欧洲的美国化几乎持着病态的敌意。超工业化主要产生于美国的实验室,是现代新技术的基础。这种新技术不可避免地触发了社会的加速变革,并加速了个人的生活节奏。反美运动虽以电脑或可口可乐为攻击对象,但事实上是因为欧洲已经遭到舶来的时间观念的侵扰。美国,这个超工业化的龙头,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快速的却非常不受欢迎的节奏。
显然,这个问题也象征性地表现在法国人对巴黎到处林立的美国式冷饮店所持的反对态度上。对许多法国人而言,这些存在无疑是一种恶毒文化侵略的证据,但美国人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软饮料会招致人们如此强烈的反感。现在,口渴的法国人往往跑到超市里,匆匆地买一瓶可乐,而不再闲情雅致地走到街旁的小酒馆,泡上个把钟头,细细品尝甜酒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新技术盛行的结果,至少有三万家街旁小酒馆已经宣告关门大吉,正如《时代周刊》( Time )所说,它们是“短命文化”的牺牲品。事实上,甚至连《时代周刊》杂志本身也使欧洲人深恶痛绝。这并不是因为这本杂志的政治报道,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含义。《时代周刊》的文笔简洁有力,很容易把美国式的生活输出他国,甚至把美国式的生活节奏一起抛售出去。
为了了解生活节奏的加速会导致许多不愉快,增加许多烦扰的原因,我们必须先抓住“持续时间观”这个观念。
前面已说过,人类的时间观念与自己的内在节奏有很大关系,但人对时间的反应是受到文化制约的。这种制约性有一部分形成于孩提时代。当我们经历种种事件与其他事物保持种种关系时,持续时间即已形成。事实上,我们灌输给孩子最重要的知识之一,就是事物的持续时间。这种知识的获取往往是在一种非正式的、巧妙的,而且通常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对这些生活中持续时间的估计,我们将无法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
例如,孩子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知道父亲在早晨几点上班,也知道父亲在几个小时内不会回家。(万一父亲回家了,表示有点儿不寻常,他的常规被打破了。孩子一定可以感到这一点。即使是家里的宠物,也会形成对一些持续时间的估计。它能知道常规情况,也知道反常情况。)孩子知道吃饭不是一分钟,也不是5个小时可以完成的事,吃饭所花的时间通常在1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孩子知道,看一场电影要2~4个小时。孩子知道,看一次医生几乎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孩子知道,学校每天需要上课约6个小时,自己与老师的关系要维持一个学年,与父母的关系则要持续一生。成年人的行为,从寄信到谈情说爱也是以持续时间为前提。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对持续时间的估计不同,但持续时间的概念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当生活节奏有所变化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便会动摇。
当生活节奏加速之后,有些人痛苦万分,有些人却额手称庆,其原因就在于此。除非一个人能适应他对持续时间的估计,小心注意持续时间的缩短,否则他可能会以为,两种性质相似的情境必然花费同样的时间,但加速力意味着,某些性质不同的情境将压缩在同样的时间内。
凡是能意识到加速原理的人,就是熟悉世界已经走得更快的人。他们能因时间的压缩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某种补偿。由于深知一切状况持续的时间均将缩短,因此他便能格外提高警觉,步步为营。反之,那些缺乏对持续时间的估计能力、无视持续时间缩短的人,便将被时代淘汰。
总之,生活节奏绝不只是一个口头禅、一个笑柄,或无病呻吟、危言耸听之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变异,但它完全被忽略了。过去,当外在社会变革较慢时,人们也许感受不到这种变化。一个人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发现生活节奏有任何改变。今天,变革的加速已使这种现象完全改变。正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人类才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及社会的变革已加速许多。今天,许多人的行为动机不是源自对生活节奏的向往,便是源自对生活节奏的仇视。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运用教育学或心理学为人类即将到来的超工业社会铺下坦途,那么人类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我们有关社会变革及心理变革的大部分理论都侧重静态的社会层面,这并不是现在的人的完整画像。它完全忽视了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及未来的人之间的重大差别。这个差别可以用“短暂性”概括。
短暂性的概念可用于填补社会变革理论与个体心理学研究之间的长期断层。在把社会变革理论和个性心理学研究整合之后,我们便可以用一种新的方法分析高度变革的种种问题,从而可以找到一种粗糙却有效的方法推测情境变化的速度。
短暂性,是指生活中的一种新的“临时性”,是一种非永久性的感觉。当然,哲学家及神学家也都知道,人是无常的。在这个层面上讲,短暂性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然而在今天,这种非永久性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尖锐。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在其著作《动物园的故事》( The Zoo Story )中,将主角杰瑞的性格描写成一种“永久的短暂性”。评论家哈罗德·克勒曼(Harold Clurman)在一篇批评阿尔比的文章中写道:“没有人拥有安全的居所,即真正的家。我们都是寄居在公寓里的人,我们绝望地甚至野蛮地想要与邻居保持深入的交往。”事实上,我们全是短暂性时代的居民。
不仅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越来越脆弱或越来越短暂,如果对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剖析,便可看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不仅与他人有所联系,还与各种事物有联系。经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出人与其活动地点的关系,可以分析出人与周围环境的关联性,甚至可以进一步研究人与某种观念或信息的关系。
这5种关系加上时间便形成了社会经验的结构。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事物、活动地点、人、环境及观念是一切情境的基本组成部分”便是基于这个理由。而个人跟上述5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构成情境的最主要基础。由于社会加速变革的结果,这些关系在时间上被缩短。过去维持某种关系需要很长时间,而现在已被大大缩减。由于这种时间的缩减,我们才真切地感到自身生活的不确定性。
短暂性也可以很明确地用关系的周转率来解释。如果现在证明事情的发展要比过去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也许很不容易,但我们可以先拆开这些组成部分,然后测算它们进入和离开我们生活的速度,即测算这些关系的持续时间。
“周转”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短暂性的概念。例如,在杂货店里,牛奶的周转速度通常比芦笋罐头的周转速度快。因为牛奶的进货与销售较快,所以流动就快了许多。精明的生意人对于自己售出的每一件商品的周转速度及整家店铺的周转速度都了如指掌。他很清楚,营业周转速度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最主要的指标。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可将短暂性视为个人生活里各种不同关系的周转速度,而且每个人的特点都可以用这种速度来表明。有些人的生活周转速度低于其他人。现在的人及过去的人的生活相对来说是“低度短暂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未来人则生活在“高度短暂性”的环境中,他们的关系持续时间将大为缩短,流动性将大大加快。他们的生活、周围的事物、活动地点、人群、观念以及他们所在的组织等,都将变化得更快。
这样的变革不仅影响了人类感知现实及对自我约束的方式,同时影响了人们的责任感和适应能力。这种高速的生产能力加上日新月异、趋向复杂的环境,我们的适应能力才被限制,从而带来未来的冲击。如果我们可以证明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短暂,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情境流通得越来越快,也就能透彻地观察自己和别人。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高度短暂性社会的生活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