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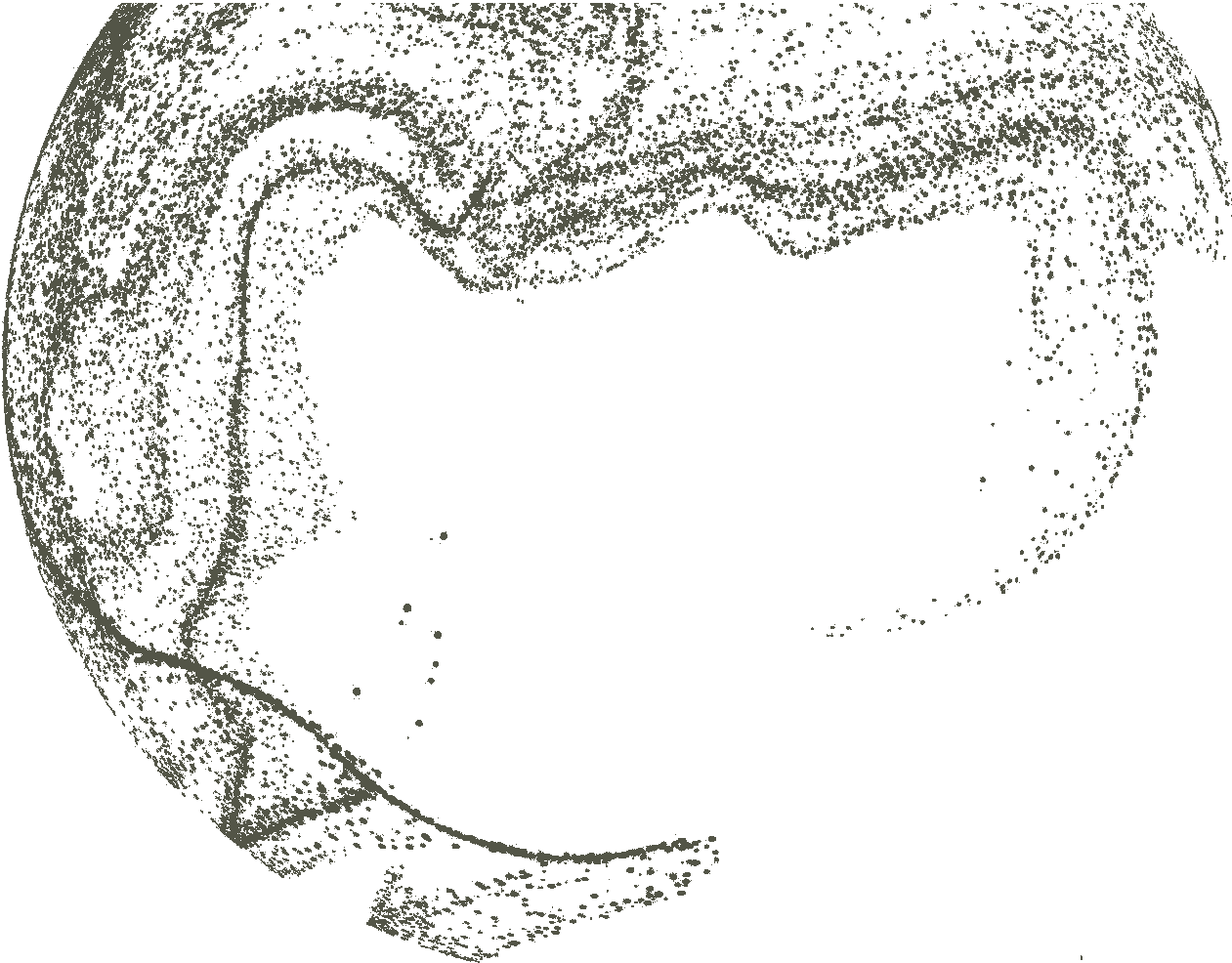
1967年3月初,加拿大东部,一个11岁的儿童因“衰老”而去世。
从年龄上看来,这个孩子名叫里基·加伦特(Ricky Gallant),仅仅11岁而已,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儿童早衰症”,一种使人急速衰老的病。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高龄老人特有的症状:动脉硬化、脱发、行动迟缓、皮肤松弛。实际上,当这个孩子去世时,他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漫长人生的生理变化在他身上居然压缩到短短11年。
儿童早衰症在医学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的人都患有这种奇怪的疾病。他们虽不是真正的衰老,却经历了一种非常规速度的变化。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隐约“感到”事情变化得比以前快多了。专家、学者都开始抱怨他们已经赶不上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了。每场会议或研讨会少不了会提到“变革的挑战”之类的话。在这些老生常谈的会议中隐含着一种危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变革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危机,仍有千千万万的人如梦游般地在街角游荡。在他们看来,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虽然这些人生活在人类史上最令人紧张的时代,他们却想尽办法将这种紧张气息堵住,使自身摆脱出来。他们似乎觉得,只要对此不予理睬,便可安逸自如。他们努力寻求“与世隔绝的安宁”,好像要寻求一种“外交豁免权”般不受变革的干扰。
这种现象几乎随处可见:老年人对于新的潮流唯恐避之不及;35~45岁的中年人把学生闹事、性泛滥、迷幻药、迷你裙等视如毒蛇、猛兽。他们永远把年青一代看成“叛逆的一代”,以为今天的一切与以往并无不同。即使在年轻人中,我们也极少发现那些对变革有所觉悟的人。他们对过去懵懂无知,因此也看不出现在的时代有何异样之处。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大多数人,包括教育阶层及贤明之士在内,虽然已经意识到变革的威胁,却极力否认它的存在。即使有些人明白变革已在加速推进中,但他们并没有客观地去研究变革的内在本质。他们没有真正地把变革当回事,也没有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我们如何知道变革是在加速进行的?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的方法可以衡量变革。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每个社会都同时有无数的变革之流在躁动着。从最细微的病原体到最巨大的银河系,一切“事物”都不是其本身,而是种种变革过程而已。世界上没有静止点,没有不变物,更没有所谓的“以静制动”的准则。因此,变革必然是相对的。
同时,变革是不平衡的。倘若一切过程都以相同的速度发生,或以相同的加速度或减速度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观察。实际上,未来是以不同的速度向我们袭来的。因此在发生时,我们才能比较出不同变革的速度。例如,当比较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的速度时,我们便可看出社会进化比生物进化快了许多。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和技术在某些社会的进步要比其他社会更快。同理,我们可以看出,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系统,其变革的速度也有不同。这就是威廉·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正因为变革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才能衡量它。
在完全不同的变革过程,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变革过程进行衡量,而这个标准就是时间。倘若没有时间,变革将毫无意义;倘若没有变革,时间也将会停止下来。
时间可被视为事件发生的“间隔”。正如金钱能使我们赋予苹果或橘子价值一样,时间能使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变革过程。当我们说,建造一座水坝需要三年时间,意思就是,这个时间是地球公转一周所需时间的三倍,或是削一支铅笔所需时间的3100万倍。时间是一种通货,可以让我们比较各种不同变革的速度。
即使以上的条件都已具备,我们在衡量变革时仍会遭遇一些难题。当谈到变革的速度时,我们指的是各个不同事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范围”里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界定这些“事件”,必须适当选择“时间范围”,小心验证和衡量变革所得的结论。我们会发现,衡量具体事物的工作比衡量社会进程的工作要先进、准确多了。例如,大家都知道,衡量血液在身体内的流动速度比衡量谣言在社会上的传播速度要准确多了。
虽然有以上的种种限制,但现在一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都认为,我们的社会进程已在急速的变革之中。
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用艺术家的夸张笔调写道:“根据考证,人类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进化速度要比史前时代的进化速度高10万倍以上。”他认为,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花费50000年时间所完成的改革与进步,“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以前的1000年内皆已完成;而在现代人类文明产生之后,这种成就仅需100年即可完成”。而人类5000年的成就,“只需用刚刚过去300年的成绩即可囊括”。
小说家兼科学家C.P.斯诺(C.P.Snow)也曾就变革的新态势发表评论。“20世纪以前……”他写道,“社会变革是如此之慢,以致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都没有感受到任何改变。但是,目前情形已经不同,变革速度的加快,已使我们的想象力望尘莫及。”此外,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也说过,最近几年潮流变动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任何修饰手法、任何形容词可以准确描述这种变革的程度与速度……事实上,夸大其词反而更接近事实”。
到底是怎样的变革需要如此“夸大其词”?首先,让我们先举例看看城市的变革过程。
现在,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深刻且最快速的都市化进程。185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4个;19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9个;到1960年,已有14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根据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统计,当今世界的都市人口每年将以6.5%的幅度增长,而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城市人口每11年将增长一倍。
为了了解变革的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城市维持现有规模而不扩张,将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城市面积不增加,为了容纳激增的人口,我们必须建造新的城市——新的东京市、新的汉堡市、新的罗马市,而且每11年就要建造一个。(法国早已按照城市计划开始建设地下都市,商店、博物院、仓库、工厂皆建于地下;日本也早已开始填海造城市……这些都是人口激增的后果。)
此外,人类消耗的能源也在激增之中。印度原子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Dr.Homi Bhabha)曾分析这种趋势,他说:“如果以Q为单位代表燃烧330亿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那么在1850年以前,每个世纪人类平均消耗能源所产生的能量不到半个Q;到1850年,消耗已增加到每个世纪一个Q的水平。然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值已经高达每个世纪10个Q。”这意味着,人类在过去2000年所消耗的能源的一半,已在过去的100年里被消耗掉了。
另一方面,在迈向超工业化的国家中,经济增长非常显著。虽然这些国家的发展基础相当雄厚,但其经济的年增长率仍然十分惊人,而且这个增长率还在不断增长。
以法国为例,从1910年至“二战”开始的29年间,工业增长率仅为5%而已,而1948—1965年的短短17年间,工业增长率却达到220%。现在的工业发达国,每年的工业增长率提高5%~10%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偶尔有降低的情况,但变革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1960—196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属的20个国家和地区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增长率都在4.5%~5%。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4.5%,而居首位的日本则高达9.8%。
以上数据足以表明,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差不多每15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增长中。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十来岁的孩子所使用的人造产品的数量将是他们父母在年幼时所使用的两倍。也就是说,今天十来岁小孩长到而立之年时,这些国家的生产总量还会再翻一番。若在一个人70年的人生里,此种情形会出现5次。不但如此,由于这种增长是多方面的,那么一个人到了老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将比他出生时提高31倍。
新旧两代之间以这样的速度发生变化,对千百万人的习俗、信仰及自我形象的设定来说,都有冲击性影响。这种情形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的。
在这些惊人的经济现象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变革动力:技术,但这并不表示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事实上,大气中化学成分的改变、气候的变化、土壤肥力的改变及其他种种因素都会导致社会动荡,但不可否认,技术仍是加速冲击的主要力量。人们往往将技术与浓烟密布的钢铁厂和叮当作响的机器混为一谈。这种典型的技术象征或许是亨利·福特所创造的,或者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里塑造的一种潜在的社会印象。但事实上,这种印象并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技术并不只是工厂与机器。中世纪马轭的发明曾促进农业的重大改革;几个世纪后,贝塞麦法
 的出现也促进了技术革新。技术除了技艺之外,还包括有用的或无用的机械、促进化学反应的方法、养鱼、植树造林、剧场照明、计算选票或教授历史等方面的方法。
的出现也促进了技术革新。技术除了技艺之外,还包括有用的或无用的机械、促进化学反应的方法、养鱼、植树造林、剧场照明、计算选票或教授历史等方面的方法。
今天,最先进的技术程序是在远离传统的装配线或敞炉等设备的地方进行的,因此旧的技术观念更不能应用于今天。在电子科技、太空技术和大部分的新兴产业都有工作环境安静、整洁的特点,这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条件。现在,我们应该改变人们心目中固有的、旧的技术形象,赶上技术本身日新月异的变化。常常有人引用交通的进步阐释加速的变革。约公元前6000年,人类最快的长途交通工具是骆驼,每小时约行8英里
 ;约公元前1600年,双轮马车问世,最高速度也不过每小时20英里。
;约公元前1600年,双轮马车问世,最高速度也不过每小时20英里。
然而,这个发明可谓空前的创举,后来的人类几乎无法超越这个极限。直到3000多年以后,当第一辆邮政马车于1784年在英国问世之后,它的速度也不过每小时10英里而已;1825年,首辆蒸汽火车投入使用,其最高速度不过每小时13英里,而当时帆船的速度还不及其一半。直到19世纪80年代,更先进的蒸汽火车发明问世,时速才增加到100英里。然而,人类花费近万年的时间,才达到了这个纪录。
后来,人类仅仅用了58年便超越这个新纪录4倍。1938年,人类飞行的时速达400英里;又过了仅仅21年,这个时速又翻了一番。1960年,火箭的时速已高达4000英里,而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甚至每小时可飞行18000英里。如果以坐标来形容这种进步的话,那么过去人类的发展就是横坐标,现在的发展却是纵坐标。
我们考察人类的行程距离、飞行高度、矿产开采或动力控制等,都可同样看出这种加速趋势。无论是哪种统计,情形都是如此。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前,人类一直呈平行式发展,而如今却突然一飞冲天。
其中的原因就是,技术在今天开始反作用于技术本身了。技术不断使自身更加“技术化”,只要看看技术改革的过程即可一目了然。技术改革包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汇成一种循环性的“自我强化”结构。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具有实际用途的、创造性想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性想法得到实际应用、产生技术的阶段;而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在社会上普及的阶段。
当这个过程大功告成之后,三个阶段便会倒转过来:由技术的普及来刺激新的创造性想法。而在当今社会,每个阶段之间的过渡时间正在缩短。
人们常说,过去90%以上的科学家至今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因此每天都会有新的科学发现问世。在今天,科学家的想法往往比以前更易于实际应用。从概念提出到实际应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这就是今天我们与过去祖先截然不同之处。从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Appollonius)发现圆锥曲线原理到真正应用于工程学,用了2000年;从帕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发现了乙醚具有麻醉作用到实际应用,也隔了好几百年。
即使到了近代,类似的理论难于应用于实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1836年左右,人类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来割草、打谷、捆绑麦草的联合收割机,制造这种机器所应用的原理在当时被人知晓至少20年了,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机器才被推广到市场上。1714年,第一台英文打字机获得专利,但过了整整150年才开始在市面上流通。糖果商人尼古拉斯·阿珀特(Nicholas Appert)发明了食物罐装保存法,但真正将这项发明应用于食品工业则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今天,这种从发现原理到实际应用所需的时间已经缩短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过去的人更勤勉或更热衷于此,而是说明,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实施了种种社会措施来加速这个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循环的第一个至第二个阶段,即原理与应用之间的时间间隔已大为缩短。在研究食物冷冻、抗生素、合成皮革等20种重要发明之后,弗兰克·林恩(Frank Lynn)发现进入20世纪以来,至少60%的新发明从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技术的实际推广所需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了许多。今天,由于不断对工业进行研究、改进,这种迟缓应用和推广的现象更在不断减少之中。
由于新原理的发现与实际应用的时间间隔缩短,因此商品或服务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流行所需要的时间也大为减少。因此,第二个阶段至第三个阶段的间隔——实际应用到普遍流行之间的时间间隔也随之缩短了许多时间,传播速度更是不断提高。
罗伯特·B.扬(Robert B.Young)在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任职期间,曾研究家用电器从发明至大量推广应用所需的时间。他发现,1920年以前美国销售的日用品,包括吸尘器、电热炉、电冰箱等,自最初上市至普遍流行所需的时间约为34年。但1939—1959年,类似的日用品包括电炒锅、电视机及洗衣机等,从上市到普遍流行所需的时间仅仅8年而已,比过去缩短了超过76%的时间。他同时指出:“战后的新产品足以表明,现代循环速度激增的特点。”因此,发明、应用及传播速度的加快带动了整个循环的速度。新机器或技术已不只是一种产品而已,其本身已成为一种资源、一种新的创造理念。
从某方面而言,每种新机器或新技术都因要与旧机器或旧技术相互结合,而产生新的联合体,从而改变了一切现存的机器及技术。因此,当新机器与新技术成等差级数增加时,新的联合体便成等比级数增多,事实上,每种新的联合体本身也是一种新的机器。
例如,计算机与其他机器匹配的结果能在太空科学领域发挥神奇的功能。当计算机与测向装置、通信工具、动力源等组合使用后,其本身便成为另一种超级机器的一部分,可进入并探测外太空。但是,为了以新方法配置新机器、运用新技术,原本的机器便需要经过种种改造、重组、升级或重装。因此,在将旧机器改造为新机器而进行种种调整时,无形中便刺激了技术的进一步改革。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技术改革并不只意味着组合及再组合种种机器和技术,更意味着对社会、哲学甚至个人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它们改变了人类的整个知识环境,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想法和看法。
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从中得到启发并将其作为我们模仿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并不只是我们周围的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事实上,机器已经越来越有喧宾夺主之势,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已经逐渐被机器控制。在牛顿将宇宙视为一个大时钟般的机器之前,人类已经有了计时的仪器,这种计时观念对人类的知识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计时观念的影响之下,产生了因果观念和外部刺激重于内部刺激的观念,而这两种观念至今仍在左右我们的日常行为。此外,计时器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概念。一天有24小时,每小时有60分钟的观念已彻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近几十年来,电脑的普及又开始触发人们许多新观念,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大系统的互动部分,因此人们的学习方式、记忆方法、决策方式等都无形中受了影响。随着电脑的发明及在社会上的普及,每一个知识领域,从政治学到家庭心理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计算机的影响,而这还只是部分冲击,其影响力迄今尚未达到顶峰。如此,发明过程的循环便靠着自身的动力加快了速度。
因此,如果技术本身被视为一种巨大的动力、一个强大的加速器的话,那么知识本身便可被视为燃料。今天的我们已经被推入社会的加速过程中,因为知识作为社会变革的燃料在日益增加。
一万年来,人类一直在积累有关自身及宇宙的有关知识。文字出现以后,知识的积累曾出现第一次飞跃,但之后又慢慢爬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5世纪,约翰内斯·谷登堡成为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人类在知识的追求上才有了第二次飞跃。在1500年以前,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每年出版新书约1000种。这就是说,按照粗略估计,要出版10万种图书,需要整整一个世纪。4个半世纪后的1950年,出版速度急剧上升,欧洲每年约出版新书12万种。过去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出版的图书数量,到1950年,只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可完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世界每天的出版图书已达1000种(包括欧洲在内)。
我们很难说,每出版一本图书就增加了一本图书的知识,但我们可以断言,图书出版量的增长曲线与人类挖掘新知识的速度是平行的。例如,在谷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之前,已发现的化学元素仅有11种,而第12种化学元素——锑,是谷登堡在研究活字印刷术时发现的。锑的发现距离第11种化学元素砷的发现,足足有200年之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算,我们到今天只不过多发现了两种或三种化学元素而已。但事实上,在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450年,人类共发现了约70种化学元素。而在1900年以后,人类所发现的新的化学元素不是以每200年发现一种的速度,而是以每三年发现一种的速度在增加。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速度还在不断提升。例如,科学杂志及论文的数量在今天正如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量一样,几乎每15年增加一倍,生物化学家菲利普·西克维茨(Philip Siekevitz)曾说:“在最近30年中,我们对生物属性的了解,就知识广度而言,足以使人类历史上任何可与之相比的科学发现时期都相形见绌。美国有关机构每年出版约10万份报告、45万篇论文以及数以万计的书籍。从世界范围来说,有关科学及技术的文献,每年平均约增加6000万页以上。”
20世纪50年代电脑问世后,整个社会又有了新的改变。电脑能在不同的资料中以惊人的速度从事分析及整理工作,因此成为推进知识追求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电脑与其他分析性工具配合使用,帮助我们观察周围不可见的宇宙的同时,又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说法来解释就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结构里,“知识就是变革”。对知识的追求促进了技术动力,也意味着加速的变革。
发明到应用、普及,再到发明,这是一连串变革反应,是人类社会发展急剧升高的加速曲线。到现在为止,这种加速的推动力已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了,不再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正常组织应有的现象,它在逐渐动摇我们的社会组织。加速的推动力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却最不被了解的动力,我们可称之为“加速力”。
情况远不止这些,因为变革的加速也是一股心理力量。尽管心理学几乎完全忽视这股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引发世界变革的加速度已经开始破坏我们精神上的安宁,改变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因此,外部的加速常转变成内部的加速了。
这种事实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果将个人生活假设为一条流通经验的渠道,那么这种经验流通将包括无数个“情境”。因此,周围社会变革的加速将剧烈地改变渠道中的情境流通。
对于情境,虽无简洁的定义,但倘若我们无法运用知识和智慧去控制的话,我们将无法应对。更令人头痛的是,每个情境自身虽具有某种一体性、完整性,但情境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
每个情境都有某些可供辨认的组成部分,包括“物品”,即由自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每个情境都发生在一定的“场所”里,也就是行动发生的位置或地点。(由此看来,拉丁语词根situ用来表示“场所”实非偶然。)此外,每个情境还有许多角色——人,人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种种观念或知识。任何情境皆可以用上述5个成分来分析。
情境还包含另一种范围,由于这种范围独立于其他范围,因此常被忽略。这就是“时限”,也就是情境发生的那段时间。各方面皆相似的两种情境倘若发生的时限不同,那么它们的性质便不相同,因为时限的不同往往会改变情境的内容与意义。正如丧礼进行曲如果演奏得太快会变成欢快的音乐一样,如果太缓慢的话便会像断音一样地忽起忽落,而使其味道与意义全然走样。
当今社会变革的加速力之所以能粉碎现代的生活经验,其原因便是如此。众所周知,这种变革的加速力可以缩短许多情境的时限,不仅能大幅度地改变“时代特点”,而且可以提高经验渠道的流通速度。如果将这种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与另一种缓慢变革的社会生活进行比较,在同样一段时间之内,前者比后者通过经验渠道的情境更多,这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通常,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一个情境上面。当各种情境在我们身边不断增加将使整个生活结构复杂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及非做不可的抉择数量便会增加,结果导致了现代生活令人窒息的复杂感。
由于各种情境的加速流动,我们势必要用许多复杂的机器从事更多的工作,我们的注意力便必须时时由一个情境转向另一个情境。由于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无法平心静气地注意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之间的转变。过去,大家模模糊糊地感到“一切改变得越来越快”便是这个意思。它们围绕着我们,川流不息地流过去。
另外,社会变革的加速力也给我们应付生活问题增加新的困难,因为它常常以种种新奇的姿态出现。虽然每个情境都是独立的,但彼此间依然有相似之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经验中获得学习的机会。倘若每一个情境都是完全新奇、与先前经验毫无相似的话,那么我们的应对能力将完全瓦解。
因此,变革的加速很快会打破陌生情境与熟悉情境之间的平衡。变革的不断推进使我们不仅需要应对急速的变革本身,而且要迫使我们应对许多与先前不同的情境。
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赖特(Christopher Wright)曾说:“当外部事物开始变化时,你的内在亦随之变化。”这些内在的自我变化的影响,足以测出我们应对生活变革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也说过:“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事物的自然过程’意味着变革速度可持续增大到人类及其组织所无法适应的程度。”
为了生存,为了避免未来的巨大冲击,人类必须加强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方法使自己安身自处。因为过去的社会基石——宗教、国家、团体、家庭或职业目前都已在加速力的猛烈冲击下摇摇欲坠。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事先了解加速力是如何穿透生活、左右行为及如何改变生活品质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了解变革的短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