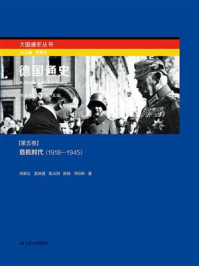摘录
摘录
1884年11月,爪哇各报刊载了一则消息,说荷兰派驻东万律的一位县官被华人杀害了。这使荷兰当局和新闻界大为震惊,荷印政府的机关报——《爪哇时报》(Javasche Courant)之前曾报道,说兰芳公司管理处已于1884年10月3日隆重移交给荷兰政府了,且说荷兰县官利兹克(J. C. Rijk)也已在东万律就任,并未遭受华人方面的任何抵抗;但几天后又说府尹(Resident)接到一个消息,说县官利兹克和四五名土著宪兵已于10月23日被华人惨杀了。于是立即由府尹、军事首长、几位官员和五十来名士兵组成一支军事侦察队,赶赴东万律了解情况,但他们所能证实的,也只是暴动的规模相当宏大,整个东万律地区已卷入反荷运动而已。
一如常规,对这些一向忠顺于政府的人民何以会在几星期内突然变成一群叛徒的内幕原因人们毫不进行了解,却派了一支远征军到东万律去,把华人的人民运动扼杀在火海与血泊之中。
荷兰政府对婆罗洲的华人,特别是对建立于该岛西岸的那些公司,这还不是它所认为必要的唯一远征了。远自1822年以来,它就已用兵好几次了,但仅在1854年那一次,才由安特生(Andresen)将军把那些华人殖民地全部消灭。可是也并非未遭到华人的顽强抵抗的。华人在作战中曾屡次表现出他们高度的军事素质,但人们却总喜欢对其加以否定。
一个世纪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一带仅享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实际上它是从未真正地占有这个岛屿的。它所能享受的权利,也局限于和西岸那些马来人的所谓统治者签订一些友好条约而已。因此,这块地方仍然是向一切先来者开门的处女地。当乌玛•亚拉母亭苏丹(Oumar Alamoudin)在位时,曾有一艘中国帆船到三发(Sambas)湾来停泊,那些因长途跋涉而疲劳得面色苍白、精神委顿的船员曾谦逊地到苏丹王宫进谒,并向苏丹请求赐他们一小块地方居住,且声言愿意服从他的统治。苏丹就指定拉腊(Laras)地区给他们居住。继第一批华人之后,不久又有其他华人接踵而来,他们也都被准许在那边居住。由于他们既能按规纳税,又能以其辛勤劳动为地方繁荣作出重大贡献,不久苏丹就觉得他们是非常忠顺的属民。他们在那边开发金矿,开辟原始森林,耕种土地,建筑道路,使地方面貌在几年中完全改观。
他们在和土著的达押族贸易中显得非常内行。他们又和达押族妇女联婚,生出了一些肖父而不肖母的儿女,这种混血将肯定是会成为比原有的达押族更为忠顺的属民的。但由于苏丹的残暴和贪得无厌,终于使华人不能忍受了。他们觉得离开祖国后,不仅更换了主人,还碰上了一个比刚离开的中国皇帝更加贪婪的人,因此就决定把该地据为己有。
在一个全体居民都被邀请参加的中国大节日里,华人组织了一个埋伏,乘大家都在狂欢时,伏击队猝然冲出,无情地把土著居民杀害了,并从那天起宣布脱离苏丹而独立。在这儿,我们看到,华人所做的事和我们欧洲人是不同的,盖我们不论在西方或东方,对于一个只能危害其治下被压迫人民的无能土著统治者,总是干脆地夺掉他的政权的,但华人并没有这样做。马来统治者曾屡次企图收复失地,但都毫无结果,至1818年,苏丹阿布•巴嘉•达如亭(Abou Bakar Taduoudin)才决定向爪哇的荷兰政府求援。
尽管婆罗洲的马来统治者直至那时仍未履行其与荷兰政府签订的义务,但人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支援他们,这支远征军在那边所能做的也只是造成了一种协商休战的相持状态。1826年,爪哇的大战在我们的干涉下宣告结束,到了1850年荷兰政府才又在婆罗洲重启战端,而至1854年才把那边华人共和国的独立政权取消而建立起荷兰的霸权。——这对马来人的苏丹说来,不过是更换了主人而已。——可是由于兰芳公司在战事一开始时就站在我们这方面,因而为了酬答他们的协助,我政府就允许他们把独立权保持至他们的首领刘亚生
 (即刘寿山)死亡为止。1884年9月,刘亚生病死了,荷兰政府就立即占领其领土,这也就造成了本文开端所说的叛乱了。
(即刘寿山)死亡为止。1884年9月,刘亚生病死了,荷兰政府就立即占领其领土,这也就造成了本文开端所说的叛乱了。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次突然的暴动呢?戴•格鲁特先生的那本书为我们指出了原因,他的精明见解也再一次地告诉我们,说由于我们东印度政府对当时情况缺乏特殊认识,使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犯了多少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招致我们在金钱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人力上也牺牲了不少英勇战士,使他们的英勇行为被湮没在这样一个阴晦的游击战之中。
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说来,在阅读戴•格鲁特先生的那本书时,首先碰到的问题将是:“什么叫作公司?”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中国名词,因而在我们殖民地时,人们到处都不加翻译地将其原来名称挪来使用。按照它的字面意义是“公共管理”,但这个译法只是一个表达公司性质的微弱概念。盖公司是一个赋有行政管理权,有时甚至赋有司法权和政治权的商业组织或工业组织。从其组织形式来说,很像以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属东印度公司,而公司这个名称事实上也是中国的广东人用来表示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称号的。
我们的东印度公司与华人公司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在于前者隶属于祖国并直接受其指挥,而中国公司则完全脱离其祖国而独立或甚至是彼此对立的。
这种公司是从中国政治基础的农村社团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不论外族的或本族的中国统治者,对这种农村社团都是加以接受、承认和尊重的。它是绝对民主的,因而能对君主独裁产生一种可靠和有效的抵制作用。首先以“中国行政组织和市政组织”为题对这种社团提供全面深入描写的,应归功于巴人先生。
……
一个村社首领的选举也还是无须进行竞选的,一般都是听取公众的意见,在现任村长死亡或退休前几年就已指定了继任的人选了。
……
戴•格鲁特先生告诉我们,在今天,新村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日期是由村中的耆宿和缙绅事前以布告指定的,选举大会则是在祠堂里举行的。也就是在乡间以木牌子代表着死亡村人的灵魂的庙宇里举行的。
……
他们即使在出国时,也把这种村社联盟的思想带到各处,并在他们的命运促使他们所至之地和他们觉得需要的野蛮民族或半野蛮民族地域中,建立起这种社会制度。婆罗洲的公司只不过是其祖国村社制度的一个复本而已,何况移入婆罗洲的绝大部分华人都是来自中国(本土)各省的呢?
戴•格鲁特先生说:“当我国到婆罗洲建立政府时,已在那边殖民的主要都是乡下人,也就是那种承袭其祖先传统,永远和他们的宗族或部族围绕着一个中心(族长)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人。这就使他们有一个能抵抗官吏和中央政权的压迫且能防御强邻的坚强保证。……例如1772年兰芳公司创始人罗芳伯就是带了100名族人一起到婆罗洲来的。他一到达岛上,就立即组成了一个后来发展为兰芳公司的社团核心了。”
在中国村社里,甲长或里长负有处理日常事务、审理轻微案件之责任。婆罗洲的公司也一样,一区之长或称甲必丹(即副头人或二哥),也赋有法官的权力。他们对于不甚重要的案件,可以自行决定;较重大事件则须移交首领决定;至于最严重案件,如盗窃、凶杀、政治罪犯等,则只能移交给下级首领和耆宿联席会议审理,最后才在公司首领的主持下宣判。总而言之,婆罗洲的公司不是别的,也就是其祖国的村社。但在婆罗洲它们负的责任更多罢了。公司从其本身属民征税所得的款项,是用来建立大规模的金矿企业和支持小型特殊企业的投资。婆罗洲的金矿之所以能孳息发展,所依靠的就只有这种支援而已。
在这儿,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不够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到婆罗洲来的华侨除了带来其毅力、谋生的决心和顽强的劳动之外,是没有其他资本的。可是,在婆罗洲诸公司被破坏后,情况又是怎样呢?
1854年,婆罗洲西岸华人人口估计为49 000人,在公司解散后两年,即1856年,缩减为23 778人,两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戴•格鲁特先生告诉我们从那时起只增加一两千人,且说有不少华人离开了他们的旧家园而迁居到英王统治下那较为自由的沙劳越去了。
“过去在三发、坤甸诸苏丹国中多么繁荣的华人区,”戴•格鲁特先生告诉我们:“今日已没有以往那种人烟稠密和业务繁荣的矿区了。自从反对公司的屡次战争结束以来,这些地区已变成死气沉沉的贫瘠农业区了,而其降到最低数目的居民,也几乎完全放弃了矿务经营而在从事几乎抵偿不了付出的汗水与劳力的不出息土地耕种了。另外,由于土地所有权没有足够的保证,他们也没有一点垦殖的热情和积极性。而这种热情和积极性是只有土地所有权获得保证时才能发挥的。”我们要求殖民地政府慎重考虑戴•格鲁特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因为我们完全同意他在第163页所提的看法:“各个公司的取消以及由这一取消而引起的人口减缩,已对婆罗洲的繁荣和发达带来一个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打击了。”
现在是回头来谈我们五十年来在婆罗洲西岸导演的悲剧的最后一幕的时候了。从1820年至1840年我们武装干涉的整个时期中,东万律地区都是和我们合作的,他们完全了解,用装备恶劣的农民和矿工去和荷兰政府派出的反对他们的正规军相抗衡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我们就是考虑到兰芳公司负责人刘亚生(又名刘寿山)对我政府的宝贵协助,因此才承认该地区的自治权,并允许他继续在那边直接主持到他死亡为止的。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和平状态逐渐在东万律恢复了。那边的人民对荷兰政府交给公司管理处执行的各种措施,从来都不曾反抗过。
当荷兰直接统治的各个地区每年都必须花费浩繁的行政费时,东万律的行政却不必花一文钱。而且没有一个县份的税收能像它那样按时交纳,即使是异常苛重的职业税也是时有时无,然而公司的管理费用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边的警务也不消花费分文,因为按照中国村社的习惯,任何人都是义务警察。正如1858年克鲁生将军(General Kroesen)在移交婆罗洲西岸政权与政府时所作的报告中曾说:“刘亚生负责的警务是非常良好的,事无大小,都瞒不过他。”1882年,卡特(Kater)府尹也提到中国人管辖的那些地区说:“那边的安全和公共治安效率绝不低于荷兰本国。”
可是这些繁荣景象和良好的行政管理不久之后也就告终了。1884年9月,东万律公司负责人刘亚生病死了。荷兰政府便于次月(10月)3日前往接管。这个突然的举动就像一阵冷风似的吹遍全区。我们应该指出,因为那边的中国居民对荷兰政府与公司负责人之间所订的密约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的最大财产——自治权和村社自由都被这一举动所侵害了,再加上我们在接管时那种草率、鲁莽和匆促的工作方法,更增加了人民的不满。于是暴动发生了,工事构筑起来了,两位荷兰县官被杀害了,一个加强师从爪哇调来了,军事管制代替了行政机构,许多毫无抵抗的中国村社人民被放任给野蛮的达押人劫掠,人民运动终于被淹没在血泊中了。这个被剥夺独立的地区,也似一切被吞并后的华人区一样,完全解体了,它的和平秩序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恢复。
这对谁有利呢?荷兰政府为什么对中国人的小共和国采取这样凶暴的行政而同时却让马来人的小王国享有完全的特权呢?是否因为他们系当地的原始所有者呢?完全不是,他们也和后来的中国人一样,是以殖民者的身份从别处移来的。那么是否马来人的小国家管理得比中国人的好呢?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作者也都证明是完全相反的。
政府为什么让爪哇人的村社存在而不让婆罗洲的中国村社存在呢?对这些对荷兰政府毫无可怕之处的人民为什么这样歧视和害怕呢?这些都是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可能连荷兰政府本身也回答不出来。
可是凡有欧洲人和中国人发生竞争接触的地方到处都表现着这种歧视情绪,不论在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到处都可被觉察到。1873年马地耶戴蒙左(M. Madier de Monjau)在巴黎所作的一篇题为“从欧洲人的利益看中国的对外移民”的报告里曾特别强调这种排华情绪,他在其中表露出似乎中国人已向欧洲进军的恐惧情绪。事实上倒是由于被高度欧洲文明姑息坏了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本国太懒于谋生,又耽溺于酒色及其他坏事,因而不得不出外,但又不懂得和精力充沛、体格强健、勤劳活泼、节俭朴素的中国人一起生活的缘故。
……
另一种恐惧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荷兰政府之所以对婆罗洲的华人采取这么凶暴的举动,当它把一个中国公司推翻并消灭之后,就立刻陷入一种比此前的公开抵抗可怕得多的潜伏势力包围中。这种势力破坏了他们最可靠的联络,使远征军经常处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中,甚至在办公室中也会感到它的威胁,这种势力就是代替了被解散的公司而产生的秘密会社。这种秘密会社很快地就组成了。爪哇岛外的大部分华侨过去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中国革命宣传组织的社员,这种宣传革命的组织是在明朝被推翻后为了反抗清朝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曾在1866年一本由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协会出版的著作中对其组织加以阐述过。
华侨在离开中国时原已把他们对清朝的痛恨和恢复明朝的企图放弃了,因而在他们仅要求工作和自治权的我们的殖民地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组成会社。可是一旦荷兰政府打击了他们的独立性,威胁了他们的社团自由,阻挠了他们的工作时,这种在他们看来是无理和非法的干预,立即引起他们以惊人的姿态展开了反抗,于是秘密会社一转眼就组成了。而且像是法定似的全部依照其祖国会社的形式。甚至连章程都不必更改,事实上也无须更改。在中国实施的,自然也可以在婆罗洲实施。这种会社起初原系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仅由于满人的迫害才变成一种政治团体的。因之它无须更改章程和原来的徽号。在中国,它曾与清朝压迫者斗争过,现在又得重新和荷兰压迫者进行斗争了。戴•格鲁特先生在这一点上说得对(同上书第175页),可是他却错误地认为婆罗洲的秘密会社和中国的秘密会社是毫不相干的。情形恰恰相反,它们都是有着同样的徽号、同样的宗旨、同样的印章和名称的会社。
……
戴•格鲁特先生以可嘉的预见性把婆罗洲最后一个公司的年册全部翻译并发表在他的著作中,这无异于把它从遗忘中拯救了出来。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其他公司的年册也许已在1853—1854年我政府对诸公司的兵燹中散失了。
那些文件如果存在的话,对于当时婆罗洲西岸马来苏丹治下诸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也许是个宝贵的资料哩。可能那些文件大部分还藏在巴达维亚或陆军部的档案里也说不定(至少,如果没有被白蚁及其蛆虫毁坏的话)。
这是值得寻找并把那些文件让戴•格鲁特先生去进行研究的一件事,尤其从我们屡次的远征中吸取“前车之鉴”,更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即使我们已无法补救过去的错误,但至少也可以防止重犯以前的错误。由于我们对婆罗洲诸中国公司的鲁莽行为,已使这块美丽地方的繁荣遭到无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再以同样的行为去对待日里和勿里洞的华侨,以免使他们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工厂企业和繁荣景象再受到破坏。
……
1885年9月于莱登

此文是对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的评述,除了高延此书外,立论的其他依据是作者在西婆罗洲活动的所闻所见,参考资料不多。
1850年,大港的势力已经发展起来,三发苏丹以往所取得的大笔鸦片税款,因露骨的走私活动而逐渐丧失。我相信我可以这么说,这种走私活动已引起一个问题,究竟哪一方将统治这个地区?因此,荷兰人和三发苏丹决定维护政府的权威,并压下公司的气焰。在这之前,大港公司一直是成功的,它不仅击退了由陆路进犯的荷兰军队,而且也攻击和惩罚了所有站在合法政府一边的华人,结果,邦戛镇的居民还是在惊慌失措中逃到砂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