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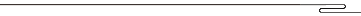
法官运作的是缜密细致的判例,背后的支撑确是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常识”。
在香港高等法院实习时,有一天汤宝臣法官在审完一起刑事案件后,脱下法袍,换上西装,从高高的法官席走到公众的旁听席,与我们面对面交流。他问起我们学习普通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普通法的精髓莫过于“常识”(common sense)二字。汤官颔首微笑,深以为然,还鼓励我去读一读圣经和原汁原味的英国小说,看看所谓的“常识”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对“常识”的认识,来自在港大法律学院一年的普通法学习。Common Law 说白了,就是Common Person(普通人)的 Common Sense(常识)。
在侵权法中,判定一个人是否存在过失从而要承担侵权责任,关键就是看这个人是否“take reasonable care as a common person”。所谓的“reasonable care”,在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应当作出的正常反应。法官作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common sense”,即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对人的行为预测和利益衡量。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如果是高等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有权要求组成陪审团审理案件。陪审员虽有一定的遴选标准,如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必须熟练掌握语言等,但都是通过任意抽签产生的,来自社会的普罗大众、各行各业。法官把认定案件事实的任务交给陪审团,他们的任务也就是根据“common sense”(常识)来判断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供述是否可信。

像蜗牛一样追寻“常识”,马韬摄影
法官运作的是缜密细致的判例,背后的支撑确是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常识”。怪不得霍姆斯大法官要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但是,没有对世事人情的深刻体验和细致观察,没有自治的司法群体和良好的职业操守以及作为基石的司法公信力,法官又怎么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辨别事实,运用判例,赋予“例外”,寻求个案的公平和正义?普通的民众又如何会信服于由法官认定的“常识”所作出判决?如此说来,“常识”的背后还有深厚的文化心理根源和道德信任基础。但反过来说,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才会增强民众的认受程度,避免机构的道德风险,真正做到程序正义。
其实“常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加重要。面对突发事件和矛盾纷争,绝不能一味标签化,有时只要想想常识,就会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比如说,政府和普通公民一样应该有道德底线,不撒谎、不欺骗、说实话等对幼儿园小朋友的要求,必须要能做得到,否则就违背了“常识”。执法不能“钓鱼”,事故不能瞒报,这些应该都是“常识”之下的基本要求。
常识,真的不是件难事。当公民在为人处世、政府在决策执法时,能多想想“常识”,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侮辱公众智商、贬损自身公信的事件出现了吧。但常识,似乎真的也很难。为什么我们会一次次违背“常识”呢?缺乏宗教基础和文化传统?还是我们的道德底线和容忍度在不断下降?
其实和很多人一样,我所期待的,只是常识的力量。
(本文发表于《晶报》2009年12月25日“法眼旁观”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