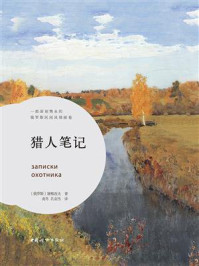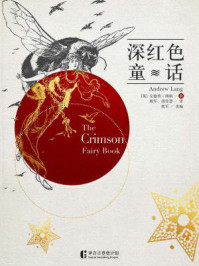你想了解加尔各答吗?
那就准备好忘记她。
——苏希尔·罗伊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和阿姆丽塔一起坐在前门廊上,她正在给维多利亚喂奶。萤火虫在树影间闪烁,蟋蟀、树蛙和几只鸟儿的鸣叫声组成了婉转的夜曲。我们的房子离新罕布什尔的埃克塞特只有几英里
 远,但有时候这里显得如此安静,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埋头写作的冬天,这样的与世隔绝让我觉得享受,但现在我坐立不安;可能正是这几个月的隐士生活让我变得蠢蠢欲动,渴望旅行,渴望见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你真的想去吗?”我问道。夜色中我的声音响亮得有些突兀。
远,但有时候这里显得如此安静,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埋头写作的冬天,这样的与世隔绝让我觉得享受,但现在我坐立不安;可能正是这几个月的隐士生活让我变得蠢蠢欲动,渴望旅行,渴望见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你真的想去吗?”我问道。夜色中我的声音响亮得有些突兀。
宝宝已经喝完了奶,阿姆丽塔抬起头来,窗户里透出的朦胧灯光照亮了她高耸的颧骨和柔软的棕色皮肤。她的黑眼睛看起来晶莹闪亮。阿姆丽塔有时候真是美极了,以至于一想到我们有可能不曾相遇、不曾结婚生子,我的头就会真的痛起来。她轻轻托起维多利亚,在她的衣襟合上之前,我瞥见了乳房的柔美曲线和挺翘的乳头。“去一趟也没什么,”阿姆丽塔说,“我也想见见爸妈。”
“但是印度,”我说,“加尔各答。你想去吗?”
“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去一趟也可以。”她说。她把一张叠好的干净尿布搭在我肩上,然后把维多利亚递给我。我轻轻揉着宝宝的脊背,感受着她的温暖,嗅着她身上的乳香和婴儿气息。
“你确定这不会妨碍你的工作?”我问道。维多利亚在我怀里扭动起来,胖乎乎的小手伸向我的鼻子。我朝她手心里吹了口气,她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开始打嗝儿。
“没问题的。”阿姆丽塔回答。但是我知道,她只是为了让我宽心。劳工节以后,她就要开始在波士顿大学教一门新的研究生水平的数学课,我很清楚她要做多少准备工作。
“你期待重回印度吗?”我继续问道。维多利亚已经把头奋力凑到我颊边,高兴地在我的领子上蹭着口水。
“我很好奇,它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会有什么不同。”阿姆丽塔说。她的嗓音柔和,剑桥的三年让她的英语带上了一点儿口音,但绝不是那种平淡乏味的纯粹英式口音。听她说话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涂满油的手掌有力地抚过你的身体。
阿姆丽塔七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把自己的工程公司从新德里搬到了伦敦。她曾跟我说起过儿时记忆中的印度,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别无二致:文化光怪陆离,到处都嘈杂混乱,种姓歧视无处不在。这一切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阿姆丽塔是安静与高贵的化身,她讨厌噪声,以及任何形式的杂乱;世间的不公令她惊骇,语言与数学井井有条的韵律规范了她的头脑。
阿姆丽塔跟我讲过她在新德里的家,夏天她也曾和姐妹一起住在孟买一位叔叔的公寓里:光秃秃的墙上到处都是陈年的污渍,窗户大开,床单粗糙,晚上有蜥蜴在墙上匆匆爬过,一切都那么廉价而杂乱。相比之下,我们在埃克塞特郊外的家就像北欧设计师的梦那样干净开阔,闪烁着原木特有的光泽,椅子整齐舒适,墙壁雪白,隐藏式光源照亮艺术家的杰作。
阿姆丽塔的钱支撑着我们的房子和小小的艺术收藏。她曾开玩笑说,这是她的“嫁妆”。起初我不愿意花她的钱。1969年,也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的总收入是5732美元。那一年我辞掉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职,开始全职写作和编辑。我们住在波士顿,公寓矮得连老鼠都得蹲着走。但我不在乎,我愿意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吃苦。阿姆丽塔却不愿意。她没有争吵,也听从我的意见没有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但是1972年,她付了这幢房子和四英亩
 土地的首期款,并买下了我们的第一件藏品,那是杰米·韦思的一幅小型油画。后来我们又陆续买了其他八件藏品。
土地的首期款,并买下了我们的第一件藏品,那是杰米·韦思的一幅小型油画。后来我们又陆续买了其他八件藏品。
“她睡着了。”阿姆丽塔说,“你可以停下来了。”
我低下头,发现她说得对。维多利亚入睡得很快,她张开小嘴,半握着拳头,婴儿急促的呼吸软软地喷在我的颈间,我继续轻晃着她。
“我们把她抱回去吧?”阿姆丽塔提议,“外面开始凉了。”
“再等一分钟。”我说。我的手掌比宝宝的背还宽。
维多利亚出生的时候,我三十五岁,阿姆丽塔三十一岁。多年来只要有人愿意听——也有一些不愿意听的——我就会喋喋不休地一再强调,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高谈阔论人口过剩、强迫年青一代直面惨淡的二十世纪是多么不公平,不想要孩子又要生的人有多蠢。对于这件事,阿姆丽塔依然从来不曾争辩——不过以她接受的正规逻辑训练,我怀疑她能在两分钟内把我的所有论点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在1976年初的某个时间,大约是在本州初选那会儿,阿姆丽塔自顾自地停了避孕药。1977年1月22日,杰米·卡特完成就职仪式重回白宫两天以后,我们的女儿维多利亚出生了。
“维多利亚”这名字绝不是我选的,但暗合我的心意。七月里炎热的一天,阿姆丽塔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名字,当时我们都一笑了之。坐着火车到达孟买的维多利亚车站,这似乎是阿姆丽塔最早的记忆之一。那幢宏伟的建筑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迹,迄今仍是印度的地标之一。每次想起它,阿姆丽塔总会心生敬畏。从那时候起,维多利亚这个名字在她心中就成了美丽、优雅和神秘的化身。所以最开始,我们只是开玩笑说要给宝宝起名叫维多利亚,可是到了1976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发现,如果宝宝是个女孩的话,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维多利亚出生之前,我总爱抱怨那些有了孩子就没了自我的朋友。明明都是些聪明人,我们曾无数次愉快地讨论各种话题,政治、散文、剧院之死,或者诗歌的衰落,可现在他们却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儿子长了第一颗牙,或者花好几个小时事无巨细地描述小希瑟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发誓,我绝不会沦落到这等地步。
但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维多利亚的成长值得所有人精心研究。我发现自己完全沉醉于她的呢喃儿语和笨拙的动作。换尿布这事儿确实令人生厌,但只要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挥动肉乎乎的胳膊,深情凝望着我,那什么都不在话下。是的,我觉得她深情地凝视着我,因为她的父亲,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竟然甘愿屈尊为她做这等凡俗琐事。七周后的一个清晨,维多利亚第一次赏光露出了真正的微笑,我立即打电话给阿贝·布龙斯坦分享这个喜讯。众所周知,阿贝从不会在早上十点半之前起床,据说是为了保持语感,但那天他依然祝贺了我,然后礼貌地指出,这会儿才凌晨五点四十五。
现在,维多利亚七个月大了,她的天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差不多一个月前,她就学会了比画“这么大”;而在那之前好几周,她俨然已经成了“躲猫猫”的大师。六个半月大的时候,维多利亚学会了爬——这显然是高智商的标志,虽然阿姆丽塔并不赞同——尽管她总是倒退着爬,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她的语言能力每一天都在突飞猛进,虽然我还不能从她的牙牙儿语中分辨出“爸爸”或“妈妈”的音节(哪怕我把录下来的磁带放慢一半的速度也听不出来),但阿姆丽塔狡黠地微笑着向我保证,她曾经听到维多利亚说过几个完整的俄语或德语单词,甚至还有一整句的印地语。而且我每天晚上都会为她读点儿东西,有华兹华斯的《鹅妈妈歌谣》,有济慈,还有我精心挑选的庞德的《诗章》片段。她似乎很喜欢庞德。
“上床去吗?”阿姆丽塔问道,“明天我们得一早起来。”
我留意到了阿姆丽塔的语调。有时候她是真的在问“我们现在睡觉吗”,而有时候她其实是在说“我们做爱吧”。现在显然是后者。
我抱着维多利亚上楼走到摇篮边,把她放进摇篮。然后我站在原地凝望了片刻,维多利亚趴在摇篮里,身体微微有些倾斜,周围放满了毛绒玩具。她的头靠着防护垫,月光温柔地洒在她身上,仿佛上帝的恩赐。
片刻之后我走下楼梯,锁好门窗,关掉所有的灯,然后回到楼上。阿姆丽塔在床上等我。
在我们做爱的最后几秒钟里,我翻身看着她的脸,希望为我不曾诉之于口的问题找到答案,但一片云从月亮上飘过,将一切掩埋在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