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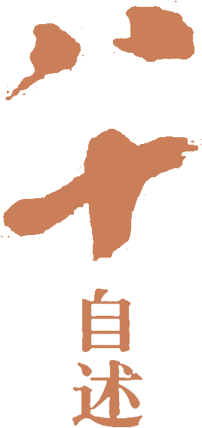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近郊一个名叫“土贤庄”的小村庄。我年幼时,那里不叫“土贤庄”,而是呼作“杜贤庄”。“杜贤庄”,顾名思义,村里的原住民,主要应是杜氏人家,但当时只有一家姓杜,且是年老的绝户。
说起杜氏绝户,村民常讲到一桩故事。我们村东有一条通往帝都的大道,道边还有很宽的人行道。八国联军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就是经由这条大道回銮北京。为了迎接圣驾,沿途村落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匍匐在地,跪于路边,而且不得抬头仰视。人们只能从眼角里睨视一点点宏大景象。老人们说起来,都带着无限敬仰和崇敬的口气描述,先是步兵,接着是举幡的,再是马队……数不清的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的仪仗队,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居于中间的是太后、皇帝的御驾,殿后的又是数不尽的方队。官宦们络绎不绝地巡视着两边跪拜的民众,对耄耋之年的人抽样给予赏赐。全村只有杜家一位老者受到恩宠,赏赐的是一块大洋。这块大洋成为供奉的圣物,人们都垂涎三尺,羡慕至极。
遗憾的是,杜家似乎没有福分来承受皇恩,后来反成了绝户,令村民们无限惋惜。到我能听懂这个故事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大清也灭亡了三十多年,那时是日本侵占时期,可老一代的村民们讲起往事,依然肃然起敬,似乎能有一次五体跪拜,是自己一生的荣光。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历史课,也是我最初所接受的“臣民意识”的教育。
杜家绝户了,可村名是最好的纪念。一九四〇年,日本人修筑石家庄至德州的铁路,我们村是第一站,不知何故,将“杜”改为“土”。虽然乡亲们认为“土”字不吉利,但村里头面人物与日本人交涉无效,时间一久,便约定成俗,村名随了站名。大概搞“治安村”时,村子正式更名为“土贤庄”。土贤庄原属正定县,滹沱河东西流过,将正定县分为南北两块,我们村在河南。滹沱河南,土地平整且肥沃,采用井水灌溉。主要的大车道,同时肩负排水渠道的作用,遇到大雨,街道如滔滔河道,流畅无阻。我们河南住民,维持着旱涝保收的生活状态,鲜见极端贫困之家。我们村距正定县城和石家庄都是十五里,属于近郊,后来又傍石德铁路线,村子虽小到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但相对其他村庄通达、活分。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四日(公历二月十七日),我来到这个世上。家里没有钟表,不知确切时间。那年生肖为猪,生我正值晚饭后,乡人所谓“人畜皆饱”。我爹非常高兴,说:时辰吉利,以后不会挨饿。据我娘叙述:当我呱呱落地时,一看又是一个秃小子,极其扫兴,懒得看我一眼。因为我前边已有了四个哥哥,娘想要个女儿。我爹是重男主义者,十分称意。娘不甘心,还要生,在我四岁时,终于有了个妹妹,我似乎成为这个家中可有可无的一根鸡肋。
我父母是一对老夫少妻,父亲比母亲大三十一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二年,母亲生于一九〇三年,都是大清的子民。母亲是续弦。我的外祖母体弱多病,每逢冬天喘得透不过气,坐卧不宁,整日围着被子蜷缩在炕上,痛苦至极。我母亲是长女,下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外祖父是个老实人,比较窝囊,支撑不了家。田有两亩,但没有井,也没有牲口和大型农具,因而收成甚微,日子很难过。家里的事情全由我母亲操持。为了外祖母和这个家,母亲耽误了婚期。当时习俗是十七八岁出嫁,过了二十就难了,属于现在所谓的“剩女”。大约在这前后,母亲患了莫名的病,根本请不起医生,拖着、耗着,人瘦得不成人形,几乎没有生的希望。那个年代,闺女是不能死在娘家的,死了不能入祖坟,没有安魂之处,只能做野鬼。对一个大姑娘来说,这比生时没有出嫁更残酷。我们那里实行冥婚,找一个异性单身冥鬼,结为夫妻。据说外祖父已为我母亲筹划冥婚的事。正当此时,我父亲丧偶,时年已经五十有五。他有二男二女,都已成家和出嫁。那时家乡有个习俗,男人丧妻之后,最好不出三个月能续弦。男人不空房是一种吉利。于是有媒人撮合,很快就把婚事说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总比等待冥婚要强得多。
据说我父亲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声言:就是一个“棺材瓤子”,我也要娶回来!迎亲那天,他不便去,便派自己的孙子前往。婚后,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关怀备至。他那时已有良田几十亩,生活得不错,又当家做主,于是到处给母亲请医生。奇迹出现了,母亲的身体日见好转,婚后不到三年接连生了我三哥和四哥(前边有两个同父异母哥哥),母亲身子骨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了。经过死亡线考验的人多半长寿,我母亲活到人瑞——九十五岁时辞世。
我娘一进刘家的大门,立即坐在了祖母的位置。我爹与前妻生的二男均已儿孙满堂。爹的长孙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无几,也已结婚生子。这个大家庭有二十多口人。爹得了一个年轻媳妇,娘也把他当作自己依赖的靠山,心满意足。可是,这个大家庭的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接受这个事实,哪里来的“娘”和“奶奶”?可是我娘是一位好强同时又极其注重名分的人。在她看来,我是明媒正娶过来的,身份和地位无可争议,就要当这个“娘”和“奶奶”!但在自己没有生儿育女时,只有我爹疼爱,自己空居名分,有气无力。当我的同母长兄来到这个大家庭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几个亲哥哥在这个家庭中具有万钧之重,爹又钟爱小儿子们,娘也以子为贵而有恃无恐。她要真正做一家之长了,于是像开了锅的水,这个家沸腾起来了。在我多少懂一点事时,我多次听到我娘讲如下一件事:一群孙子媳妇们不知从哪里弄出一个说法,说我娘未进刘家门之前,即大姑娘之时有“不正经”的事。这类事传起来最快,村里人议论纷纷,最后传到我娘耳里,一下子引起大爆炸。贞节问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我娘公开挑战,宣称传言者能找出证人,我立即去死!然后在家庭范围内一个一个正面对质,几乎把家里所有的女人都卷进来了,可是谁都无言以对,此时不得不向我娘求饶。所有传言者都跪在我娘面前,请求原谅。我娘在气头上横竖不答应,转身离开,所有跪求者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这一跪就是半天。我爹出来说情,我娘的气也消了一点,说可以,每人要自己掌脸,于是一片掌脸声响起。此事很快传遍村子,传言自然平息。我爹事后反复称赞我娘有骨气,刚强,敢做敢当。对家内女眷之间的事,我爹从不直接介入,他常说一句话:“看你们谁能争过谁!”我的异母大哥效仿老爹也从来不介入,我的异母二哥是位聋哑人,当然也不会介入。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婆婆妈妈的事时常发生,拖到一九三七年不得不分家,我的两位异母兄长另立门户。我爹已经六十四岁,与我娘带着我们五个小崽子(同母大哥只有十一岁)单过。老骥伏枥,该多难啊!

我的老娘与我的两个哥哥(摄于一九八九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