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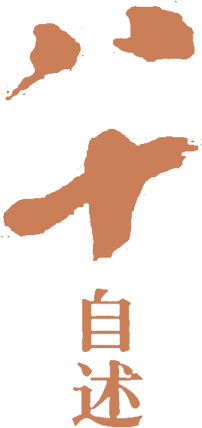
我们村是个小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有一家土豪,在清朝后期曾有一千多亩地,传说靠卖瓜子发家,俗称“卖瓜子的”。到我出世的时候,他家经几代析产,基本上都是庄稼人了。由于是土财主,与诗书基本无关,没有功名人物,只有一位老童生(考秀才落榜),我小时他还健在,六十多岁,夏天总穿夏布衣,拿着一把蒲扇,悠闲自在,常到我们小学转悠一回,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既崇敬又羡慕。他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位上过初中,是村里的文化“巨人”。他在外边谋职,村里很少有他的身影。他家里还有两三位读过小学三四年级的,也是村里的佼佼者。除了这么几位“文化人”,其他人家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半文盲是指能记个流水账、看看皇历、打打算盘的人,这样的人也不多。村里的小学办办停停,停的时候居多。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有时在村外一个年久失修的破庙,有时在全村唯一的郝家家庙,有时借人家的闲置住宅,我上二年级时曾在我家空院借办。
,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有一家土豪,在清朝后期曾有一千多亩地,传说靠卖瓜子发家,俗称“卖瓜子的”。到我出世的时候,他家经几代析产,基本上都是庄稼人了。由于是土财主,与诗书基本无关,没有功名人物,只有一位老童生(考秀才落榜),我小时他还健在,六十多岁,夏天总穿夏布衣,拿着一把蒲扇,悠闲自在,常到我们小学转悠一回,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既崇敬又羡慕。他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位上过初中,是村里的文化“巨人”。他在外边谋职,村里很少有他的身影。他家里还有两三位读过小学三四年级的,也是村里的佼佼者。除了这么几位“文化人”,其他人家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半文盲是指能记个流水账、看看皇历、打打算盘的人,这样的人也不多。村里的小学办办停停,停的时候居多。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有时在村外一个年久失修的破庙,有时在全村唯一的郝家家庙,有时借人家的闲置住宅,我上二年级时曾在我家空院借办。
至少从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开始,村学就停了。我同母大哥长我九岁,他上到二年级学校就停办了,二哥、三哥没有上过学。没有学上的孩子们,只能在庄稼地摸爬滚打。我和我四哥之所以能上学,还得感谢一次机缘巧遇。我娘多次说起,有一次她领着我和四哥在街头玩,刚巧一位相面的人经过,他见到我们哥俩,立即驻足同我娘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你要让他们上学,将来会有出息。说完,没有索取任何报酬,扬长而去。我娘回家,立刻同我爹讲了,激起了我爹的特别希望,当即表示,以后卖房子卖地,也要供两个小儿子上学。转眼到了一九四〇年,我四哥七岁(虚岁说八岁),可是村里没有学校,我爹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耽误了上学,于是决定送我四哥到县城上小学,寄宿在一个辗转相识的人家。一个七岁的小孩,该是多么孤单,但还是坚持了一年。不知村中的长者们是如何发动的,一九四一年春节之后,村里重新办起小学,那年我六岁,正好赶上,我四哥也由县城回到本村。说来也怪,一九四八年十五岁的四哥参加革命,随军入川,现在是离休的厅级干部;我也当上了教授,难道真应了相面人的预言,还是一个巧合?此为后话。
由于村学停办了好几年,所以那年学生比较多,总共有二十多人。除了一年级,还有二、三年级。小的如我,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学校借用一家空院,有五间北房,两头是耳房,中间三间没有槅断,顶头一间放着一口棺材,用砖墙隔开,我们的教室用其他两间。所有的学生都在一起,实行复式教学,老师给一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每次上课,老师要轮流给三个年级讲。自习的时候要大声朗读,各念各的,念起来抑扬顿挫,不过很单调,我们称之为“念经”。三个年级一起念,也就有“乱作一团”之感。
老师有三位,一位是前边说到的那位土豪家的初中生,名曰郝子兴,是名义上的老师,很少来学校,也不记得他曾给我们上过课。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小学毕业,名曰郝子恒,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校长,是他的堂弟,名曰郝子恩,读过小学三年级。
办学总要有点开销,经费从哪里来,我们小孩子不管不问,从大人们的言谈中也知道一点点。一是村里有一些“公地”,公地缘何而来,遗憾的是从来没有打听过,后来学历史,也没有做过调查和细究,真是不可救药的“失责”。这些公地有点收入,用于村里的公共开销,其中也会用于办学。二是按每家土地多少,捐点钱粮。三是减免担任教师的赋役,当时赋役很重,减免是一项不小的报酬。四是自愿资助,在我家闲院办学时,就有“自愿资助”的意思。
老师教课,应该说是认真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体罚。特别是校长打人很凶,木板一下子可打成几截,有时用藤鞭打还不解气,竟用木棍。我虽没有挨过,但那种可怕的场面——老师恶狠狠吼叫,学生凄惨的哀号,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恐惧记忆。相形之下,罚站、罚跪是很温和的方式,课堂门口,常常有一排学生跪着。我们的教室旁边,停放着那口锃亮的红漆棺材,开始我们都有点害怕,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孩子们会跳过半截砖墙,围着棺材追打哄闹。不知是谁在棺材上划了一道纹,老师火冒三丈,罚所有的学生下跪,要人检举是谁划的。不知是谁说了一个名字,老师立即把那位同学揪出来,劈头盖脸,用藤鞭抽个不止,学生号啕大哭:“不是我!不是我!”但校长不容其分辩,越叫打得越凶,血渗透单衣,透出一道一道的血迹,直到那个学生瘫在地上才松手。校长经常打人,又爱喝酒,酒后打得更凶,我们背后管他叫“野蛮校长”!在当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对体罚都是认同的,认为老师体罚同家长打骂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手段。我不记得有哪位家长为自己挨打的孩子出来辩护过,多半是在学校挨了打之后,回家还要遭到家长的训斥或打骂,所以在学校挨了体罚,回家后是不敢作声的。
除了老师体罚,大一点的学生也可以对小同学实行体罚,有时罚站或罚跪,有时也会给几巴掌。小学生还要向几位厉害的大学生“进贡”,每个星期要送一次好吃的。
我不记得挨过重罚,但罚站和罚跪是常有的。一次我背课文,虽然背出来了,但老师一看我的课本破烂得不成样子,训斥不够解气,顺手拿起正在抽的烟袋锅,向我头顶扣下来,瞬间头上就起了个小包,好几天没有下去。回想起来,上小学是件恐怖的事。
另外,军事操练时挨打也是经常的。日本人在我们学校开办了“日曜小学”,由日本人教日语和军事操练。对日本人要有一套礼仪,让人处处担惊受怕,稍有闪失就要挨罚。军事操练对我这个还分不清左右的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动作经常与口令相反,教鞭于是就会随之落在身上。每个星期日,都像过鬼门关那样令人慌恐不堪。
也有一件受宠的事,我至今难忘。三年级读完之后,学校没有四年级。离我们村六里地的西兆通村有一所高级小学(即有五、六年级),校长送我一个人去考插班生。我跟着他走十分害怕,出乎意外的是他对我态度挺好,嘱咐我考试要仔细看题,做完之后要检查一遍。我按校长的嘱咐,平静地参加了考试。考完之后稍等片刻即被告之我被录取了,校长十分高兴,我给他磕了一个头,用农村感激长辈最隆重的礼仪答谢他。那时正是中午,校长要我跟着他去饭铺吃饭。令我心惊胆战的“野蛮校长”,原来也有温情的时候。
我们村在西兆通上学的有五、六位,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早去晚归,中午自带干粮。学校不供应开水,实在渴了,就喝几口凉水。学校按时上课,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家都没有钟表,很难掌握时间,迟到是常有的事,因此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通常的办法就是不让进教室,只能站立在教室门口听讲。打骂还是有,但比村里的小学好多了。不过有一次也很吓人,早晨出操,一位同学迟到,老师训他,他竟敢自辩,近于顶嘴。老师上去向他的胸部猛击一拳,学生顿时昏厥在地,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同学们屏住气息,谁也不敢吭声。
那时候雨雪很多,雨下得很大就自动停止上学,学校不算旷课。小雨还是要去的,我们都没有雨伞和雨衣,一般只能用一个布口袋折成蓑衣,披在身上,这多半是要淋透的。到了学校,没有可换的衣服,冷得浑身打哆嗦,皮肤表面都变得像紫茄子一样,只能用自己的体温把湿漉漉的衣服暖干,很是受罪。冬天来了,上学更是困难,积雪常常有一尺深,走起路来十分艰难,雪化时又是泥泞不堪。好在有几个同伴,互相鼓励和比赛,这些都一一克服了。回想起来,也着实是个锻炼。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学校为照顾路远的同学,实行寄宿,我和四哥参加了,那年我十岁。学校对寄宿的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天还没亮就起床出操,之后要上早自习。让我最恐惧的是夜宿。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姓周的大地主的院落。他家的住宅连成片,占了一条街。地主家的人常年在北京和县城,这些院落是空闲的,清冷清冷,没有人气。由于不生火,屋里屋外一样冷。我们睡在地上,用一层草做地铺。我住在南屋,见不到一点阳光,比屋外还冷。一冬天就一身贴身的棉衣,时间一长,棉衣变铁皮,根本不保暖;手脚生冻疮,整天流清水鼻涕,可也不患大病,看来人就是锻炼出来的。
这些大宅院有许多闹鬼的传说,我从小就听神呀、鬼呀的故事,所以那时信以为真,也十分害怕。走进周家大院,就有阴森恐怖的感觉。每到夜里,都是在恐怖中度过。钻进被窝就蒙住头,似乎这般就能挡住鬼。更为麻烦的是解夜,不敢出来,总想憋一会儿,等有人也起身时再起来。那时,睡觉时间不足。一清早还满天星的时辰就起来,晚上还要上自习,课外活动很多,又跑又跳,很累,自己无法控制醒与睡,尿床的事也时有发生。
还有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是在上学的路上发生的。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们几个同伴边走边说笑,走到村口,一个小伙伴突然大叫一声:“人头,人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在墙上挂着一个人头。大家惊恐万状,一时都瘫了,几乎无法挪步。放学时,我们不敢再走这个村口,于是绕道另一个,结果也挂着一个。第二天,当我们走到第三个村口,同样又是一个。那些天里,人头在我眼前晃动,天一黑,不敢离开大人一步,夜里也常做噩梦。当时国共双方时有冲突,我们学校周围,许多村驻着不少国民党的“还乡团”,以县为单位,称作“某某县还乡团”。这些还乡团经常向中共占领区出击,返回时常抓一些人,说是八路军或共产党。被抓的人多半被处死,常听说的是枪毙,偶尔也听说活埋,像斩首示众的虽少,可偏偏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见了,真是吓破了胆。
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绑票、撕票现象也多有,还有报私仇的。在我们上学的沿途有多起人命案,有的是被枪杀,有的是被投井,一路都很恐惧,特别是出现旋风之时,阴云密布,风尘飞扬,恐惧心情愈益严重,因为大人们总说,旋风是冤鬼现形。每当这时,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往前跑,落在后边会哇哇大哭。
共产党对国民党也不手软,对支持国民党的人多半采取夜里“掏窝”办法,拉到村外枪毙,陈尸荒野,也有很大的震慑力。
一九四七年初春,刚开学不久,我十二岁,刚上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一天上午,操场突然连声巨响,人们狂喊:“八路军来了!”老师们也慌作一团,都集中到校长那里。我们紧缩在教室里,等老师的消息。很快,老师来了,话很简单:“八路军来了,你们立即回家,学校停课。以后是否复课,等候通知。”我哥哥是六年级的学生,他们行动更快,这时已在教室门口喊我,我连书桌中的课本与笔墨也来不及收拾,蹿出来跟着他往家里奔跑。到家后才听大人们说,八路军攻占了县城,一时间,大家都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回忆起来,西兆通这所高级小学办得还是很不错的,每个班有单独的教室,老师也比较固定,每一门课都有专门老师教,课程很正规,各种制度也比较健全,管理很严。学生经常搞各种比赛,如作文比赛,选出模范文章贴在走廊里,供大家学习。还有体育比赛、歌咏比赛,五、六年级还有话剧演出。每周有周会,由老师训话或学生进行讲演。日本投降后,每天早操举行升旗仪式,集体背诵“国父遗嘱”。音乐老师教的都是一些鼓舞人心的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期终成绩进行总排名,分甲、乙、丙、丁四类。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我们的校长上过初级师范,二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领导过本县农民暴动,被捕后脱党,但一直坚持进步,是从事教育的地方名人,一九四九年后以进步人士身份当过县教育局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办得很出色,深受老百姓欢迎。
本村的小学虽然没有留下愉快的记忆,但说起来我还属于幸运儿。我上学之前,已停办多年,恢复办学,我正好六岁,否则我只能下地干活,失去上学的机会。我转学到西兆通的高级小学之后,村里的小学又停办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以后才恢复。所以,不管老师怎么“野蛮”,恰恰复学这三四年被我赶上了,不能不说是个幸运。
我有幸在西兆通上到五年级,本以为能毕业,继续考中学,但停学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从此我又失学了。以后命运如何?天也未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