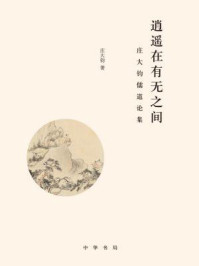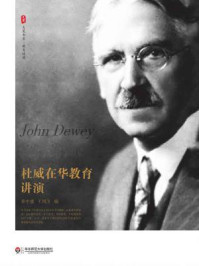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是一个很辽阔的地方,一年只有春、夏两个季节。11月,第一场暴风雨过后,春天就要来了。短短几个月里,谷里的各种树木开始生机盎然,到处都是葱茏绿意和绚丽的花朵。到了5月底,夏天来了,植被和花儿们被太阳烤得奄奄一息,开始干燥、泛黄,就像被放进了烤箱一样。
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把在高温炙烤下萎靡不振、气喘吁吁的牛羊赶到空气更加凉爽、植被更为茂密的内华达高山牧场去。此时我也非常想去那个地方,但囊中羞涩的我该怎么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呢?
流浪者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计问题而烦恼,此时我也是如此,首先就是要解决吃喝问题,我甚至想到是否能靠吃野生动物维生,我还考虑是不是可以采集一些植物的种子和浆果吃,或者放下所有的钱财和其他行李,毫无牵挂地去游荡。
德莱尼先生突然在此时来访。他是一个农场主,以牧羊为生,我曾在他的牧场工作过几个星期。那时候我和其他牧羊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羊群赶到默塞德和图奥勒米河的上游,我向往那里已久,所以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能让我到那山上去,我都不会介意。前一个夏天我到过约塞米蒂山区,那里可真是美,那风景让我久久难忘。德莱尼先生说:“由于积雪正在融化,羊群会顺着长长的林带一路往山上去,一直走到景色最好的地方,停留几个星期。”
德莱尼先生的话让我开始思考,可以筹划以营地为中心、围绕周边八到十英里
 范围内的短途旅行,那一定是一段愉快的行程。我能专心地研究植物、动物和石头。德莱尼先生也向我保证,我可以自由从事研究。
范围内的短途旅行,那一定是一段愉快的行程。我能专心地研究植物、动物和石头。德莱尼先生也向我保证,我可以自由从事研究。
不过,权衡过后,我还是向德莱尼先生坦白自己并非最佳人选:我既不熟悉高山地形,也不确定是否能成功渡过那些河流,森林里可能会有捕食羊群的野兽……另外,我告诉德莱尼先生,我害怕熊、野狗、山洪、峭壁,还有那些布满荆棘、容易使人迷路的灌木丛。我担心这些会让他的羊群走失,甚至损失大半。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我坦承了自己的不足,德莱尼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忠诚于他,让他可以充分信任的人。德莱尼先生向我保证,在我未来的行程中,我所顾虑的那些危险和困难自然会逐渐消失。而且,和我同行的牧羊人也能帮助我,我只需要专心钻研植物、动物和石头,并好好地欣赏美景。此外,他还准备和我们一起出发,走到第一个主营地。之后到了高山营地,他也会隔三岔五地上来给我们提供补给,看看我们的情况。既然德莱尼先生都这样说了,我便答应了。
在羊群出发之前,牧羊人和德莱尼先生清点数量,我在旁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生怕这两千零五十只羊会一去不复返。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只圣伯纳德牧羊犬做伴。这只狗的主人与我仅有一面之缘,可他一听说我夏天要到内华达山区去,就立刻带着他最心爱的这只名叫“卡罗”的狗来见我,让我带着它上山。
他担心平原夏天的炎热会要了卡罗的命,于是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照顾卡罗的,卡罗也一定能帮到你,它既忠诚又能干,熟悉这山区的所有动物,它还可以帮你守着帐篷,看着羊群。”
他这样说的时候,卡罗就静静地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那一刻,我相信它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轻轻地喊了它一声,想知道它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卡罗的眼睛里顿时闪着光,它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主人。主人摸了它几下,又拍了拍它,示意我可以带走卡罗了。就这样,我带着卡罗一同上路了。
清晨,我们在马背上稳稳地捆绑了干粮、水壶、露营用的毛毯还有植物标本压制器等,然后跟随前行的羊群,从容地行进在褐色的山麓上。德莱尼先生又瘦又高,脸上的轮廓十分清晰,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他走在最前面,牵着那两匹载着装备的马,跟在他后面的是高傲的牧羊人比利,比利后面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掘食族的印第安人,我们需要他们协助在灌木丛生的山麓、丘陵地带赶羊群,而腰带里别着一本笔记本的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们的出发点位于图奥勒米河的南面,就在法兰西沙坝附近,那里是一片丘陵地带,含有大量变质的含金板岩,一直延伸到中央谷积层矿的地下。才出发一英里左右,羊群当中的领头羊就时而快速奔跑,时而向前张望,用行动表达了兴奋之情,因为它们曾在这个地带品尝过甘美的牧草。一时间,羊群在领头羊的带动下也开始兴奋和躁动起来。母羊呼唤小羊,小羊回应母羊,声音十分美妙,好似充满了人类的情感,这微微发颤、情感四溢的声音因为拽食满嘴的枯草而时断时续。山坡上尽是四处奔跑的羊群,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母羊和小羊之间仍能辨认出彼此。有时小羊因为过于疲惫而没有及时做出回应,母羊就会立刻穿过羊群,回到小羊最后一次回应的地方去寻找。母羊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抚慰,只有在羊群中找到它的那只小羊,才是唯一的慰藉。在我们眼中,羊儿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别提小羊的叫声了。
羊群在向山区行进时会分散成一个底边长约一百英尺
 、高约一百五十英尺的不规则三角形,前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英里。在这个三角形最前端的是几只最强壮的觅食羊,尽管走起来歪歪扭扭,但它们是羊群的“领袖”。它们和那些活跃在三角形主体两侧参差不齐的觅食羊会不断地从灌木丛中和石头缝里寻找各种食物,有草叶,也有树叶,如此“排兵布阵”是为了保障“三角形”底边那些孱弱的母羊和小羊羔的基本需求。
、高约一百五十英尺的不规则三角形,前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英里。在这个三角形最前端的是几只最强壮的觅食羊,尽管走起来歪歪扭扭,但它们是羊群的“领袖”。它们和那些活跃在三角形主体两侧参差不齐的觅食羊会不断地从灌木丛中和石头缝里寻找各种食物,有草叶,也有树叶,如此“排兵布阵”是为了保障“三角形”底边那些孱弱的母羊和小羊羔的基本需求。
接近中午,酷热来袭,羊群艰难地喘着气,纷纷向树荫奔去。在烈日的炙烤下,我们几个人则急切地寻找近处白雪皑皑的山峦以及潺潺的溪流,只可惜除了明晃晃的日光之外,只能看到那向远处延伸的山麓、丘陵,其中还布满了灌木、树丛以及外露的板岩,山麓看起来崎岖不平。山麓上生长的大多是三十到四十英尺高的蓝橡树,树叶泛着淡淡的蓝绿色,树皮是白色的,在最贫瘠的土地或岩石缝隙中顽强地生长。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被青苔覆盖的尖锐板岩在黄褐色的草丛中凸起,乍一看这些板岩就像乱葬岗上的墓石。尽管山麓、丘陵上的植被和平原上的看上去区别不大,但除了那稀稀拉拉的橡树,还有几种熊果属植物和美洲茶属植物。初春时节我到过这里,当时这里仿佛是一个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的公园。
可是,现在因为暑气,万物都变得萎靡不振了。地面裂开,裸露的岩石上只有爬行动物——蜥蜴的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微小的蚂蚁,它们似乎不惧怕炎热。蚂蚁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努力寻找食物,就在那如烈火一般的日光下,它们居然不会被烤干,表现得顽强不息,实在叫人感叹不已。还有几条蜷缩着身体的响尾蛇,也都躲在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在春天喧闹的乌鸦和喜鹊现在也不见了动静,只是静静地躲在树荫下,耷拉着翅膀,张着嘴深深地呼吸着。鹌鹑们也都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池塘里寻找最佳的阴凉处,而棉尾兔在阴凉的鼠李属灌木丛中跳来跳去。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两只长耳朵野兔优雅地在开阔的林间慢跑。
到了中午,我们在一片小树丛中小憩了片刻,随后又赶忙驱赶羊群向前行进,争取尽快翻过长满灌木的那座小山。不过,我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前方的山路突然消失了,这下我们只能先停下来辨明方向。那个帮助我们的中国人似乎感觉到我们迷路了,于是,他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说了许多形容灌木太多、太密的话,印第安人则是相对安静地扫视着周围的情况,企图从层层叠叠的山脊和峡谷中找到出路。我们穿过布满荆棘的丛林,才发现一条通往科尔特维尔的大道。既然找到了这条路,我们就趁着太阳还未下山继续赶路,直到找到干燥的农场,我们才开始扎营,准备在农场过夜。
我们和羊群一同在山麓丘陵里扎营,虽然这样露营很简单,但却不能说是愉快和舒适的。待太阳下山的时候,牧羊人要驱赶羊群去周围寻找食物,而剩下的人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捡柴、生火、做饭、拆包和喂马等。接近黄昏的时候,羊群已疲惫不堪,它们被牧羊人赶到距离营地最近的高地上,很兴奋地挤到一起,母羊都找到了自己的小羊,兴奋地给自己的孩子喂了奶,然后它们开始休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都不用去照顾它们。
一句“开饭了”开始了我们的晚餐。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锡制的盘子,先从锅里盛出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然后围坐在一起聊关于露营的话题,比如喂羊、矿藏、丛林里的狼和熊等,自然也少不了要谈那些在淘金时代大赚一笔的冒险经历。那个印第安人似乎始终和我们不属于一个物种,他总是一言不发。吃完晚饭,喂完卡罗,有人在篝火边上抽烟。或许是因为烟草的作用,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得很平静,那是一种常常在圣人脸上出现的表情,一种陷入沉思柔和、淡定的神采。随后又一瞬间从梦境中惊醒,我们不是叹气就是嘟囔,都默默地把烟斗中的烟灰倒出来,注视了一会儿篝火,打了声哈欠,自言自语道:“睡吧,睡觉吧。”话音还没落,人就已经缩进毯子里了。篝火一直烧着,时明时暗,直到两个小时后才熄灭。那时候,天上的星星也开始闪烁,浣熊、山狗和猫头鹰都在树林中不断地叫着,打破夜的沉寂,蟋蟀和雨蛙也演奏起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快乐的音乐,成为这美好的夜的一部分。唯独那不知是谁入睡后的鼾声,还有一些羊因为白天的尘嚣而发出的咳嗽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星空下,羊群看上去仿佛是覆盖在高地上的一床巨大的灰色毯子。
黎明的到来让原本安静的营地顿时骚动起来。大家吃完咖啡、腌肉和豆子组成的早餐,洗好餐具,开始打包。太阳微微露头,羊群开始发出咩咩的叫声。母羊刚醒,小羊就兴奋地凑过来,用头去蹭妈妈的身体,想从妈妈那儿获得自己的早餐。上千只小羊都喝完奶后,羊群就开始吃草。其中,最躁动不安的要数那些阉羊了,饥饿使它们的行动更加迅速,只不过它们始终不敢远离羊群。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都围着羊群,驱赶它们继续朝那令人感觉疲惫的路前行,三个人都尽量把羊群圈在一个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羊群也只能在那样的范围中觅食。前面已经有不少人驱赶羊群走过这条路,所以剩下的不论是绿色的还是枯黄的叶子都为数不多。而对我们来说,必须尽快将这群饥饿的羊驱赶过这片酷热的山丘,这才有希望到达二十到三十英里之外的绿色牧场。
德莱尼先生牵着那两匹驮着我们所有人行李的马,此外,他瘦削的肩上扛着一支重重的来复枪,这枪是用来防范熊和狼的攻击的。今天和第一天的天气几乎一样,同样是酷热难当,且尘烟弥漫。我们今天要翻过一道道平缓的棕褐色丘陵,路上的植被同第一天并没有大的不同,只不过我们还看见了长得十分奇特的塞宾松。塞宾松在这里不是散长在蓝色的橡树中间,就是自己形成一片小小的树丛,它们的主干长到十五到二十英尺高的时候,就会分叉成更多的枝丫,有的笔直生长,有的斜着生长,每根枝丫上都长满了长长的灰色针叶以及杂乱的枝杈,这些都不足以形成树荫。塞宾松和其他的松树长得并不相似,它更像棕榈树。它的松球会长到六七英寸
 长,直径大概五英寸,重量比一般的松球重,就算从树上掉下来很长时间,它也不至于完全腐烂,所以塞宾松树下一般都铺满了掉落的松球。塞宾松的松球富含油脂,可以用来生火,照明效果在众多的燃料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我所知道的燃料中只有玉米穗比它强一些。德莱尼先生告诉我:“印第安人喜欢大量收集塞宾松的松球,因为他们以其中大小同榛子一般的松子为食。”太神奇了,这种果实既能用作食物,也能用作祭神之火的燃料!
长,直径大概五英寸,重量比一般的松球重,就算从树上掉下来很长时间,它也不至于完全腐烂,所以塞宾松树下一般都铺满了掉落的松球。塞宾松的松球富含油脂,可以用来生火,照明效果在众多的燃料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我所知道的燃料中只有玉米穗比它强一些。德莱尼先生告诉我:“印第安人喜欢大量收集塞宾松的松球,因为他们以其中大小同榛子一般的松子为食。”太神奇了,这种果实既能用作食物,也能用作祭神之火的燃料!
早上,羊群就如移动的云朵一般随着我们在山麓上攀爬。几个小时后,我们和羊群都到达了皮诺布兰克山侧面的一块台地,那里轮廓分明,可供我们休息一下。突然,我对塞宾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忍不住要为这种长得像棕榈树一样外形奇特且身姿挺拔的松树画一张素描。可是,兴奋过头的我显然画不好。幸运的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里停留,最终,我还是完成了一张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素描,画里除了有塞宾松,还有从西南角俯视下的皮诺布兰克山峰。言归正传,台地上还有一块小小的田地和一片葡萄园,它们边上有一条小溪,可以满足灌溉的需要。溪流顺着峡谷奔涌直下,挂出了一道风景绚丽的瀑布。
就在我爬上台地最高、最开阔的顶部时,海拔一千英尺的高度所带来的开阔视野叫人兴奋,而那些收入眼底的景致也让人心生诸多的憧憬。默塞德山谷中的一段位于被人们俗称为马蹄弯地的地方。站在高处,这一地带的雄壮、恢宏尽收眼底。在我看来,这一地带仿佛正奏响一千种优美的乐音以发出自己最为磅礴的呼唤。在那陡峭的斜坡之上,松树仿佛羽毛一般装点着山坡,还有那丛生的熊果属灌木,阳光落在它们中间的空地上。更有那层层叠叠形状优美的山丘和山脊,向远处绵延,越来越高,渐渐地同远处的山峦融在一片朦胧之中。还有一簇簇的沙巴拉灌木生态群覆盖整个山间,其中不少是艾德诺斯特马属植物,它们的习性很奇特,紧紧地挨着彼此,密得就仿佛地上覆盖了一层细腻柔软且厚实的长毛绒,其间既没有高大的树木,也没有裸露的地面。远远望过去,那连绵起伏、布满长毛绒的山峦就像蓝色的海洋一样向前延伸,整齐划一,完美地将高山的雄伟、壮观都融合在了一起,此外,水光潋滟的河流在其中衬托、点缀,水的柔软融合在山脉优雅的褶皱当中,磨光了每一个可能裸露在外的岩角,那所有变质板岩中的凹槽和凸脊也好像是被用砂纸仔细打磨和雕刻出来的。整个地貌所呈现出来的无一不是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它所传递的艺术美是何等震撼人心啊!我怀着敬畏之心,久久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现在哪怕让我放弃一切我也愿意。我愿意竭尽全力去找寻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淬炼了大自然的神奇,创造了如岩石、植物、动物和天气之间这样完美的搭配。这几乎无处不在的美是那样不可思议,上到天边,下到山间,不论是已经造就的,还是正在造就的,绵延千万年,生生不息!我凝视、我怀想、我憧憬、我渴望、我沉浸其中,直到羊群离开我的视线,我才回过神来匆匆画下了一幅素描。只是这样做仿佛是多余的,因为那片充满神圣色彩、线条和风貌的景致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天让人陶醉不已。到了晚上,天气变得凉爽,天空中几乎没有云彩,可是,闪电一直在其中闪耀着,仿佛光团一般射入树丛和灌木丛中,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看到无数只来自威斯康星州牧场的萤火虫振翼高飞,而非我们所常见的野火。马尾上四散开的长毛和毛毯上不时擦出的火星都在向我们表明因为有了这闪电,空气中的静电无处不在。
一路上,我们翻过了一座座如波浪般起伏的小山,最终到了这组山脉的第二块台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此前不一样的植被。部分空旷的地区覆盖着较多低地植物,其中有低地菊科、大百合以及其他品种的百合科植物。山麓丘陵地带最为常见的蓝橡树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加州栎树,高大优美,长着边缘呈裂状的叶子,树干上有较多分枝,树冠丰满厚实,看起来很是秀丽别致。这里的海拔已经高约两千五百英尺,覆盖着大片的针叶林,其中大部分是黄松,还有一小部分糖松。
那一刻我们被群山包围着,已融入群山之中,它们燃起了我们心中的热情,触动了我们的神经,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填满。这种美将我们的肉体变得如玻璃一般透明,成为这种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和空气、树木、溪流和岩石一样,在太阳的照射下以同样的方式颤动着。大自然和我们合二为一,我们既不老态龙钟,也不青春年少,既没有疾病,也无所谓健康,总之一切都处在不灭的永恒之中。此时,我仿佛和大地、蓝天一样,不需要食物或呼吸,天哪!这个变化是那样神秘、那样突然、那样彻底!曾经肉体的牵绊在记忆中已经慢慢模糊,仅能作为我在这个世界存在的凭据。因为生命所处的环境发生如此突变,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松林中有一块空牧场,沿着它向远处望去,我看到了约塞米蒂堆着皑皑白雪的山峰,它就在默塞德河源头附近,在蓝色的天空下,更确切地说,是在蓝色的空气中,我感觉它们离我那么近!此刻它们的轮廓是那样清晰!这蓝色的天空、蓝色的空气好像和它们也融为一体,正用一种令人难以自持的撩拨引诱着我,我在思考是不是要前去看看。为此我每日每夜都在虔诚地祈祷。如此的机会几乎让我无法相信它真实地存在着。能承担此神圣任务的人必定是贤达的人,自然可以欣然前往,可是我呢,只不过是流浪在这些爱情纪念碑中的一个普通人,但我愿意成为一个最卑微的随从,欣然前往。
科尔特维尔附近有一丛艾德诺斯特马属植物,我在那儿的背阴处找到了一株卡勒修图斯属百合,还在百合的旁边发现一株智利铁线蕨。卡勒修图斯属百合花为白色,花瓣底部内侧微微泛紫,因此花儿看起来如雪的结晶一般纯净,让人过目不忘。如此圣洁的花朵,谁见了能不爱上它呢,更何况它的芳泽还足以让人的心灵变得更加纯净。粗鄙的登山者见到它之后会变得检点。有了它,即便没有其他植物,世界也会变得丰饶富足。它们在路边生长着,仿佛在向我布道,想追上那如云朵一般的羊群确实困难重重。
下午,我们路过一片草木丰茂的牧场,周围环绕着树姿挺拔、呈箭镞形的黄松,其中不乏一些形貌高贵的糖松。糖松的枝丫如羽翼一般向高处伸展着,遮盖了其他松树的枝头,显得与众不同。糖松看起来十分尊贵,松球长达十五至二十英寸,挂在枝丫的末端,像摇曳的流苏,有着华丽的装饰效果。我曾经在格里利锯木厂见过糖松的原木,除了底部因为砍伐而造成几处支棱和参差不齐之处外,其他的部分都保持着浑圆匀称的样子,看上去像加工过的一样。锯木厂和伐木厂都弥漫着糖松甜丝丝的味道。在糖松的树下,硕大的松球和纤细的松针铺满地,呈现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绚丽。如鳞片般的果鳞、种翅、果壳等在树下堆积着,很明显,松鼠们常常在这里大快朵颐。松鼠们把松球那规则排列的螺旋状果鳞一点点剥下,取出松子,那就是它们的口粮。一般果鳞的基部会有两粒松子,所以一颗松球里就有一两百粒松子,这足够松鼠们开心地饱餐一顿啦!道格拉斯松鼠吃松子的方法与众不同,它们更喜欢把黄松以及其他松树上掉落下来的松球放在地上一直滚,直到果壳裂开,露出松子。
松鼠喜欢背贴着树身坐着,这是它们的习惯动作,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吧。奇怪的是,它们这么做,身上却从来不会沾满树胶,即便是爪子和腮边的胡须也从来没有弄脏过,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习惯把自己吃过的果壳、果屑整齐地堆起来,像古人堆积贝壳那样,非常整齐利索,还十分赏心悦目。
我们正一步步接近那个布满朵朵白云且流淌着清凉溪流的地区。中午时分,我们突然发现约塞米蒂上空出现了壮观的积云,如飘浮流动的泉水滋养着这片大地。在珍珠色的层层云山之中,溪流突然现身,在碧空之下流经大地,给予这片土地最凉爽的云影和最甘甜的雨水。此时的云朵变化多端,美不胜收,不论地面上的岩石线条如何变化多端,造型多么精致细微,都无法与之媲美。云彩构成的苍穹同高耸的山峰一同升起,如优质大理石那样洁白且轮廓鲜明,又仿佛初创世界时所展示出的那样叫人难以忘怀。尽管雨云转瞬即逝,可是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千万繁花绿树因为有了雨云而有了生命,溪流和湖泊因为有了雨云而水量丰沛。无论我们是否察觉,岩石上都有雨云遗留的足迹。
我始终在细致地观察艾德诺斯特马属灌木丛,只因它的奇特,见了它之后,我就不能忘怀。它第一次吸引我的注意力是在马蹄弯地附近,就在靠近科尔特维尔第二台地的低洼山坡那里,艾德诺斯特马属灌木丛在那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几乎已经成了一片无法跨越的丛林,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黑暗丛林。艾德诺斯特马属灌木属于蔷薇科,高六到八英尺,长八到十二英寸的白色小花按照总状花序排列,叶子呈圆形针状,树皮微微泛红,树龄较大的灌木主干上会出现斑驳的条纹。炎炎烈日之下,灌木生长在暴晒的山坡上,虽然和草地一起被骄阳灼烧,但是它能由根部再生。很多生长在灌木丛中的树木却在烈日的暴晒下走向死亡。无疑,这顽强的灌木丛最终会长成一片连绵不断的灌木林,其中不会有其他的树种,秘密就在于它们生命力的差异。能和它们一样生存下来的还有几种熊果属植物,它们同样能浴火重生,只有它们能与艾德诺斯特马属灌木共存。此外,还有一部分菊科植物夹杂在灌木丛中,比如,香根菊属和麻菀属,另外还有百合科的植物,譬如,卡罗修图斯属和卜若地属植物。它们之所以能存活,是因为自身的鳞茎深深地扎在土壤最深处,因此,似火的骄阳对它们来说没有巨大的摧毁力。还有不少鸟类会选择在这片巨大的灌木丛中栖身,就如“体形小巧、皮色油亮、怯生生的动物”。在这片灌木丛边缘有几条小径,冬天的时候,因为躲避暴风雪而从高山牧场下来的鹿群会在这里找到食物和避难所。这植物太让人敬佩了!它们此时正处于花期,于是,我要把这些美丽且香气袭人的花儿扣在我的扣眼儿上。
还有一种让我难忘的灌木丛,那就是欧洲杜鹃,它们通常生长在清凉的溪流边,那一片的海拔要比约塞米蒂高得多。傍晚时分,我们开始准备在距离格里利锯木厂几英里的地方扎营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些盛开的欧洲杜鹃。它们和北美杜鹃是近亲,花姿妖娆,芳香浓郁,非常迷人。欧洲杜鹃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其特色,还因为总有多荫的桤树、柳树以及布满蕨类的草地、涓涓细流围绕着它们。
我们今天还发现了一种被称作拟肖楠的针叶类植物。这是一种非常高大的植物,扁平呈羽毛形状的树叶泛着暖黄绿色,这和有着肉桂色树皮的崖柏属树的树叶颇为类似。老树的树干如果没有枝丫,就像引人注目的巨柱挺立在林中,每当阳光透过林中的缝隙照射到它们身上时,树干便会泛着光,即使和有着君王一样高贵气质的糖松和黄松并列,也不逊色。这种树对我而言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我看到那棕色木材的纹路很细密,它们和鳞片状的叶子一样,都散发着香气。老树扁平羽毛状的叶子重叠起来似一张舒服的床垫,还能作为挡雨的篷子。如果此时有人在风雨中无法前行,那么这种树宽阔的枝丫就会像帐篷一样垂下来为他遮风挡雨,显然,如此有高贵气质且好客的大树会带给暴风雨中的人们惬意的感觉。掉下来的树枝如果可以用来生一把火的话,人们不但可以取暖,还能在袅袅升起的香气中感受到来自头顶最为真诚的风之颂歌。
只是今晚并没有暴风雨,非常平静,我们的营地也只是一个简单的牧羊营地罢了。我们扎营的地方靠近默塞德河北支流,微微的夜风吹来时,它们就好似在诉说高山上的奇妙景色,还有雪中的泉水、花园、森林和树丛,这曲调高高低低,甚至在诉说那里的地形、地貌。繁星仿佛是夜空中永远绽放的百合花,它们在远离低地尘土的我们眼里是那样晶莹、明亮。地平线被重重叠叠如尖塔一般的松树林环绕着,装饰着,松树和谐整齐地排列着,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清晰的图景,仿佛神圣的象形文字。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领悟这些文字的含义啊!涓涓细流从蕨类植物、百合和桤树身边流过,流经我们的营地,无时无刻不在演奏沁人心脾的音乐。松树林在天边环绕着,谱写着怡人的乐章。啊,这神圣的美!在我看来,只要待在这里,尽管只有面包、清水相伴,我就不会寂寞,那样我对万物的爱会逐渐加深,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会因为这样的爱而感觉和朋友、邻居的关系越来越近。
前一晚,羊群突然生病了。直到今天羊群还病着,它们只能待在营地里咳嗽、呻吟,生病的羊楚楚可怜。或许是吃了杜鹃花叶子的缘故,这受了诅咒的叶子让它们生了病,这是牧羊人比利和“堂吉诃德”的想法。离开平原之后,羊群能吃的青草就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它们总在挨饿,因为只要看到绿色的东西,它们就会饥不择食。畜养羊的人认为杜鹃花对羊来说就是毒药,所以,他们始终不明白造物主为何要创造这样一种植物。牧羊这个职业已经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显得越来越落后,尽管我们也从书中认识到在遥远的古代,这无疑是最高雅的教化事业中的一种。但现在放牧不再需要太多的成本就能成功,宜人的气候让畜养羊的人不再需要准备过冬的饲料,挡风遮雨的羊圈和谷仓自然也不需要了。加利福尼亚畜养羊的人更多的是出于致富的需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确实如愿了。小小的花费就能换来丰厚的利润,大群的羊能让他们投资的钱每两年翻一番。短时间的利润回报激起更大的对金钱的欲望。这些人已经可怜到了像被羊毛遮住了眼睛,只见羊毛而不见其他所有值得欣赏的东西了。
而牧羊人的情况甚至更糟。到了冬天,他们在小木屋里独自度过,那情况可想而知。即便有一天,他们能像他们的雇主即畜养羊的人一样,羊儿成群,发家致富——这美好的未来时时激励着他们,可是眼下的境况只会让他们步入堕落之途,他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梦想成真,实现名利双收,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实现,何况这些所谓的好处还不如说是坏处呢!堕落的牧羊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显而易见: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很孤独,这种生活对谁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在此期间,他们很少动脑,更不会去看书。干了一天活儿,晚上回到环境和羊圈不相上下的简陋小屋里,疲惫、木讷,甚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消遣,自己的生活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在放了一天的羊以后,还要吃晚饭,可是他们也是消极地应付过去,抓到什么就吃什么,目的只是填饱肚子。食物可能是没有烤好的面包、煎饼,不管是不是脏兮兮的,他们都在平底锅上胡乱煎一下,煮些茶,再配一些已经变味的腊肉。他们还会在自己的小屋里存一些桃干或苹果干,即便如此,他们也懒得煮。他们只是就着前面说到的那些食物,胡乱地把大饼和腊肉塞进嘴里,剩下要打发的时间基本就交给了烟草,唯有那忘却一切的麻醉感能消磨剩余的时光。大多数时候,他们就那样睡过去了,连白天工作的脏衣服也不脱。牧羊人的健康状况可想而知,就更别提心理健康了。一个人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和其他人接触,最后只会是半痴半癫,很多牧羊人因此精神失常。
苏格兰的牧羊人很专心于自己的牧羊事业,极少再去做其他的工作。或许是因为牧羊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职业,苏格兰人对牧羊的热情以及所掌握的牧羊技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似乎和那些体大毛长、头部尖瘦的柯利牧羊犬一样。苏格兰人牧羊的时间一般不多,因此有时间探望家人和邻居,等天气好的时候还会读点儿书。苏格兰牧羊人在牧羊时常常会带上几本书,和书中的国王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我们读过的书中提到东方的牧羊人习惯给自己的羊起名字,然后在放牧时呼唤它们的名字,羊儿听到呼唤以后就能紧紧地跟着牧羊人。只有放牧一小群羊的牧羊人才能用这种管理方式,他们才会有足够宽裕的时间到山上吹笛子、看书或者思考。无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牧羊业即便再发达,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还是认为加利福尼亚的牧羊人不会让心智健全、清醒的情况维持过长的时间。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可是他们真正能听到的只有一种,那便是羊儿的叫声。如果稍微用点儿心聆听,在他们身边,上帝还赐予了郊狼的犬吠声,这仿佛也是天籁之声!只可惜他们的眼里只有羊肉和羊毛,再没有心思去聆听大自然的万籁之音。
羊群的病情渐渐有些好转了,牧羊人比利对我们说起了高山牧场上的各种“毒物”,比如,杜鹃花、山月桂属植物以及碱土。我们继续赶着羊群前行。穿过默塞德河的北支流,我们开始向左走,前方就是派勒特峰。在满是岩石和灌木丛的山脊上,我们耗费了很长的时间,随后到达了布朗平原。我们的羊群第一次看到绿草如茵的平原。德莱尼先生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于是,他开始在附近找扎营的地方。
在中午之前,我们穿过了鲍尔山洞,那儿仿佛是一座令人舒适的大理石宫殿,阳光从南面宽大的洞口洒入洞内,使整个山洞内部都变得很亮。洞里有一泓深深的湖水,水面清澈见底,湖岸长满青苔,在枫叶的掩映下若隐若现。这洞里的一切景象都在地下,和我曾经看到的众多山洞的景象迥异。在肯塔基州的很多地方都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山洞,我却没见过像这个山洞一样的景致。如此独特的地下奇观正好在一条绵延的大理石带上,据说这一条长长的石带纵贯整个山脉的北端和南端,两端还遍布其他众多的洞穴。只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洞穴的景致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有广阔明亮的空间,还生长着植物,更有如水晶一样瑰丽的地下世界。曾有一个法国人对外声称自己拥有这个山洞的所有权,于是用栅栏封了洞口,在湖岸周围摆上了椅子,在湖面上停了一艘小游船,门票定为一美元。就此这个山洞成了前往约塞米蒂多条线路中的一条。当夏日旅游旺季到来的时候,除了约塞米蒂,这个山洞也成了游览线路中一个有趣的景点。
“毒漆”也被称作毒藤,它既是灌木,也是攀缘植物。从山麓丘陵到海拔三千英尺以上的高地都能看到这类植物,它们能攀爬树木或山岩。这种植物常常会使人们的皮肤和眼睛发炎,所以旅游者都很讨厌它们。可是,它们和周围的植物和谐相处,很多美丽的小花依偎在它们身旁,求得庇护和阴凉。经常看到一种奇特的蔓百合攀附着它们,两者和谐地生长,显示出一副十分甜蜜的模样。羊儿将它们作为食物,吃下后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马尽管对它们不感兴趣,但吃下后也不会感到不适。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植物也是无毒的,只是它们对人类而言始终没有明显的用途,所以,它们和其他类似的事物一样缺少朋友。所以总有人看到它们后会问:“造物主为什么要创造它们呢?”这些人难道就没有想过造物主创造它们仅仅是为了创造吗?
在默塞德河的北支流和牛溪分水岭顶部的肥沃浅谷就是布朗平原,不管身处哪个方向,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里壮观的景象。多年来,探险先驱大卫·布朗先生把自己的大本营扎在这里,他主要做的两件事情就是淘金和猎熊。猎人通常都是独来独往,所以他们总是离群索居,这个地方显然是最佳的选择。在这里狩猎,在岩石中淘金,还能感受到清新的空气,有利于健康,且能振奋精神,望着天空中多彩的云朵随着气候而千变万化的样子,得到有益的启示。大卫先生十分老练,他同众多的拓荒者一样非常务实,只不过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过分依恋这片不同寻常的自然风光。德莱尼先生对布朗先生很是了解,他告诉我,布朗先生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爬上山脊的顶端,因为那里视野开阔,利于极目远眺。在那里,视线可以轻易地穿过树林,远远望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和河流的源头,还可以越过近处的山谷沟壑,再根据看到的炊烟、篝火和听到的斧头声做出判断,了解何处是矿工开工的地方、何处是被废弃的矿山;当来复枪响的时候,布朗先生还可以依此判断是印第安人的枪声还是盗猎者的枪声。布朗先生有一条名叫桑迪的狗,无论布朗先生走到哪儿,桑迪都跟到哪儿。桑迪不仅是个登山能手,而且对它的主人十分忠诚和热爱。布朗先生去猎鹿的时候,桑迪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只要在布朗先生穿过森林的时候,也同主人一样脚步轻盈,避免发出大的声响就可以了,同时,它也伺机用敏锐的双眼扫视灌木丛中的动静,因为猎物常常会在日出和黄昏时分到这个地方寻找食物。在布朗先生到达新的瞭望点的时候,桑迪会跟在主人身后谨慎地观察山脊和那长满绿草的溪流两岸。在布朗先生猎熊的时候,桑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也因为有了这个帮手,布朗先生成了猎熊高手。布朗先生曾经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德莱尼先生也没少借宿过,这也是他会知道那么多布朗先生旧事的原因。在德莱尼先生的描述中,每次狩猎,布朗先生都会带上桑迪、来复枪以及几磅
 面粉,小心翼翼地穿过熊最爱出没的草场。他先找到熊出没的痕迹,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到猎到猎物为止,从不介意整个过程耗费多长时间。不管熊在哪些地方出没,桑迪都会帮他找到熊的足迹。桑迪的嗅觉非常敏锐,哪怕是在怪石路面也从未有过错误的判断。布朗先生和桑迪在到达地势开阔的地方后,就会先仔细检查附近是不是有猎物藏匿之处。尽管熊出没的地方随着季节交替发生变化,但是猎人大概能掌握它们的活动规律。春天和初夏,熊都喜欢在靠近溪流和泉水旁的开阔空地吃苜蓿和羽扇豆等杂草,也可能在干燥的草地上找草莓吃;夏末时节,干燥的山脊是它们最爱去的地方,它们会在那里找熊果属植物的浆果,它们用爪子拽下长满果实的枝条,拢在一起之后塞进嘴里,丝毫不顾及吃进去了多少枝叶;小阳春时节,松树下被松鼠咬掉的松球是它们的最爱,当然它们也会爬上树去把果实累累的枝条咬断;深秋时节,熊最爱去的就是挂满成熟橡树果的橡树林,所以它们常常出没在如同公园的峡谷平原,因为那里有一整片加利福尼亚橡树林。猎人对熊的习性很熟悉,很容易找到它们,很少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强烈的刺鼻气味出现的时候,猎人就知道附近一定有危险的猎物出现,于是,他们会在原地久久静立,不慌不忙地对周围的环境和植被进行扫视,目的是搜寻到毛茸茸的游走动物,或者至少需要判断出它可能藏匿的地方。布朗先生曾经说过:“只要能在熊发现我之前发现它的踪迹,那么猎杀它对我来说就毫无困难。首先我要熟悉地形,无论它距离多远,我都会选择绕到它的下风区,再一点点谨慎地往上移动,尽量把我和它之间的距离缩短为几百码
面粉,小心翼翼地穿过熊最爱出没的草场。他先找到熊出没的痕迹,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到猎到猎物为止,从不介意整个过程耗费多长时间。不管熊在哪些地方出没,桑迪都会帮他找到熊的足迹。桑迪的嗅觉非常敏锐,哪怕是在怪石路面也从未有过错误的判断。布朗先生和桑迪在到达地势开阔的地方后,就会先仔细检查附近是不是有猎物藏匿之处。尽管熊出没的地方随着季节交替发生变化,但是猎人大概能掌握它们的活动规律。春天和初夏,熊都喜欢在靠近溪流和泉水旁的开阔空地吃苜蓿和羽扇豆等杂草,也可能在干燥的草地上找草莓吃;夏末时节,干燥的山脊是它们最爱去的地方,它们会在那里找熊果属植物的浆果,它们用爪子拽下长满果实的枝条,拢在一起之后塞进嘴里,丝毫不顾及吃进去了多少枝叶;小阳春时节,松树下被松鼠咬掉的松球是它们的最爱,当然它们也会爬上树去把果实累累的枝条咬断;深秋时节,熊最爱去的就是挂满成熟橡树果的橡树林,所以它们常常出没在如同公园的峡谷平原,因为那里有一整片加利福尼亚橡树林。猎人对熊的习性很熟悉,很容易找到它们,很少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强烈的刺鼻气味出现的时候,猎人就知道附近一定有危险的猎物出现,于是,他们会在原地久久静立,不慌不忙地对周围的环境和植被进行扫视,目的是搜寻到毛茸茸的游走动物,或者至少需要判断出它可能藏匿的地方。布朗先生曾经说过:“只要能在熊发现我之前发现它的踪迹,那么猎杀它对我来说就毫无困难。首先我要熟悉地形,无论它距离多远,我都会选择绕到它的下风区,再一点点谨慎地往上移动,尽量把我和它之间的距离缩短为几百码
 。然后我要找一棵小树,必须是我能轻松爬上去但熊认为过小的树,我就在那棵树下面,开始仔细检查来复枪,脱掉靴子,做好一切准备。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等着熊转身,它一转身,我就一枪命中它。如果我发现熊企图攻击我,我就要爬上小树以避免被伤害。熊的反应比较迟缓,视力也不太好,所以它总是很笨拙,更何况我所处的地方是它的下风区,它不会闻到我的气味。我通常会在它嗅到火药味之前就发第二枪。受伤的熊习惯逃跑到灌木丛中。为了保证安全,我会任由它逃跑一段时间,随后再跟上去,桑迪也会跟着我,它很快就能找到熊的尸体。假设熊还活着,桑迪可以吸引它的注意力,我就可以给它最后致命的一枪了。就是这么做,凡是按照安全的方法来办,猎杀熊的过程就会很安全。但是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生,这和其他行业一样,我和桑迪也曾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时候。通常熊会避开人类,不过如果遇到的是一只又老又瘦且极度饥饿的母熊,身边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小熊,它们一定会抓住人并且吃掉他。这样做是公平的,因为人也吃熊!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身边有人被熊吃掉。”
。然后我要找一棵小树,必须是我能轻松爬上去但熊认为过小的树,我就在那棵树下面,开始仔细检查来复枪,脱掉靴子,做好一切准备。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等着熊转身,它一转身,我就一枪命中它。如果我发现熊企图攻击我,我就要爬上小树以避免被伤害。熊的反应比较迟缓,视力也不太好,所以它总是很笨拙,更何况我所处的地方是它的下风区,它不会闻到我的气味。我通常会在它嗅到火药味之前就发第二枪。受伤的熊习惯逃跑到灌木丛中。为了保证安全,我会任由它逃跑一段时间,随后再跟上去,桑迪也会跟着我,它很快就能找到熊的尸体。假设熊还活着,桑迪可以吸引它的注意力,我就可以给它最后致命的一枪了。就是这么做,凡是按照安全的方法来办,猎杀熊的过程就会很安全。但是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生,这和其他行业一样,我和桑迪也曾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时候。通常熊会避开人类,不过如果遇到的是一只又老又瘦且极度饥饿的母熊,身边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小熊,它们一定会抓住人并且吃掉他。这样做是公平的,因为人也吃熊!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身边有人被熊吃掉。”
就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布朗先生离开了小木屋,不过还是有许多掘食族印第安人在平原的边缘地带徘徊,他们住在雪松树皮搭成的窝棚里。最初他们是被这位白人猎人吸引来的,慢慢地,这位白人猎人就成了他们敬重的对象,他可以保护和指引他们以对抗帕犹他族印第安人,他们再也不用畏惧对方会突然袭来,掠走自己储存的物品,甚至是自己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