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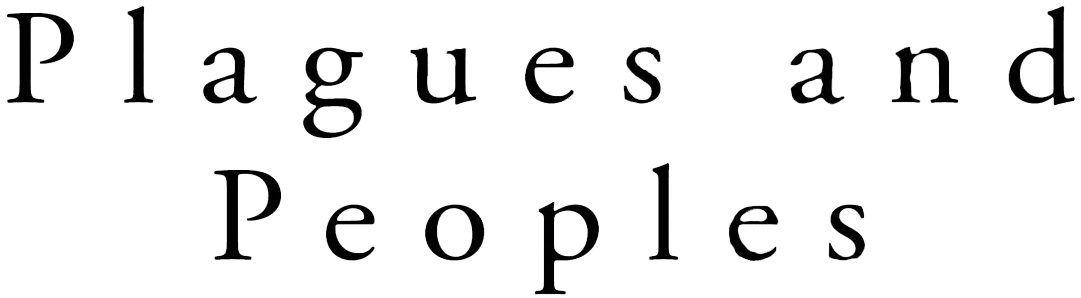
将近20年前,为撰写《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 )一书,我开始涉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以充实相关史料。众所周知,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横行异域?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常的解释似乎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蒙特祖玛
 和他的同盟者开始时将西班牙人视作神明,然而一经直接接触,现实情况就自然会让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说西班牙人的战马和枪炮在初次交战时令对手惊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会暴露无遗——当时的枪炮其实相当原始;当然,科尔特斯联合其他印第安民族的“以夷制夷”之术对胜局意义重大,然而除非科尔特斯的那些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盟友认定他一定取胜,又怎么可能与他结盟?
和他的同盟者开始时将西班牙人视作神明,然而一经直接接触,现实情况就自然会让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说西班牙人的战马和枪炮在初次交战时令对手惊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会暴露无遗——当时的枪炮其实相当原始;当然,科尔特斯联合其他印第安民族的“以夷制夷”之术对胜局意义重大,然而除非科尔特斯的那些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盟友认定他一定取胜,又怎么可能与他结盟?
实际上,征服墨西哥的传奇只不过是更大的谜团中的一部分——不久,皮萨罗(Pizarro)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国。相对而言,越洋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并不多,然而他们却把自己的文化成功地强加给了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譬如,为什么墨西哥和秘鲁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此彻底?村民为何对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庇佑他们的土地丰收的神祇和祭典不再虔诚了?或许,在基督教教士们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他们认为使几百万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无须解释,但事实上,他们的布道以及基督教信条和仪式的内在吸引力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切。
不过,在有关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我已记不起具体出处了)令我茅塞顿开,而后通过进一步缜密思考这一解释及其背后的含义,我的新假说逐渐变得合理而有说服力了。因为,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天晚上,天花这种传染病正在城内肆虐,那位刚刚率领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人展开进攻的将领和好多人一道死于那个“悲伤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后来以此称呼这场疫病)。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恰好解释,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乘胜追击,而让敌人得以喘息并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进而联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对城市的合围,赢得最后的胜利。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显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且以后每一场来自欧洲(不久后也来自非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一经验。
可见,传染病一边倒地只对美洲印第安人造成伤害这一史实,为我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这种征服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钥匙。不过,这一假说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引发相关问题: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时获得了这种使他们在新大陆如入无人之境的免疫力?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西班牙人?只要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随之而来的就将显现一个尚未被历史学瞩目的人类历史中的新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以及当传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时,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
由是观之,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与十六七世纪发生于美洲的这一幕类似的事例。本书就将描述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结论可能会使许多读者大感意外,因为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却将在我的叙述中占据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长期以来那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皓首穷经于各种遗存的文献时,对于人类疾病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自然,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著名案例从来没有被欧洲人遗忘,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虽然破坏性大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现代而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从未将其归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因为那些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那时资料残缺不全,以致事件发生的规模与意义都很容易被忽略。
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疫病体验的影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那些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力,这使他们能很快地终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说法未免夸张。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造成的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确实,如果现代医药出现之前的传染病均与欧洲的传染病模式并无二致,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关注疫病的历史呢?因而,历史学家也往往以一种不经意的笔调处理这类记载,一如我在那本描述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著作中所读到的那样。
于是疫病史便成了偏好“掉书袋”的老学究们的专利,他们热衷于就手头掌握的资料摘录一些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不过,毕竟还有黑死病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军营里突发的疫情不仅扭转了战局,有时甚至决定了战争最终的胜负。这类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遗漏,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却使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
不过,还是有诸如细菌学家汉斯·津瑟(Hans Zinsser)这样的圈外人士,搜集一些表现疾病历史重要性的史料,扮演了抬杠者的角色。他在那本极具可读性的大作《老鼠、虱子和历史》( Rats,Lice and History )中,描绘了斑疹伤寒的暴发如何经常打乱国王和将领的如意算盘。但是,这类著作并未试图将疾病史纳入更宏大的人类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与其他著述一样,它们仍将疫病的偶然暴发视为对历史常态突然而不可预测的扭曲,本质上已超出史学的诠释范围,因而也就很难吸引以诠释历史为本业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视线。
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我在此提出的许多猜测和推论仍是尝试性的,对它们的证实与修正还有待有关专家对语言晦涩的古代文献做进一步地爬梳。这类学术性的作品既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主题予以确证,又需要提出一个反面的靶子以便有的放矢,我在本书所做的推理与猜测应该符合这一要求。与此同时,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关注那些人类历史的传统观念与当下认识之间存在的鸿沟。
除了我必须描述的细节外,想必大家都会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且毋庸置疑,无论过去与现在,传染病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叙述故事之前,对寄生、疾病、疫病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或许有助于避免读者的混淆。
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所有的动物都以别的生物为食,人类也不例外。对于人类的觅食以及觅食方式变迁的论述充斥于经济史的著述中,相反,避免为别的生物所食的问题却比较少见,这基本是因为人类自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怎么畏惧狮子和狼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或者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应,导致自己被消灭。有时,此类致病生物体不知怎的寄生到某个特殊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自己却基本不受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感染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的发挥。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存下去。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捕猎的技巧和威力就已超越了其他食肉动物。于是人类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就很少再有被天敌吞食的危险了。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同类相食几乎构成人类相邻族群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类作为成功的狩猎者,几乎与狮、狼处于同等的水平。
后来,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那些出现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胜利者只是从臣服族群那里掠取部分收成,而留下足够的粮食让被掠夺者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在早期阶段,这种人类文明的巨寄生基础还相当严峻和明确,后来随着城市和农村间互惠模式的日趋发展,只是上缴租税所体现的寄生单向性才逐步消除。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那些饱受压榨的农民,供养着神甫、国王以及跟随这些阶层生活在城里的仆从,除了受到某种不确定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其他更加残忍和短视的掠夺者的侵扰之外,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曾经巩固了人类的文明史,类似的情形亦可发现于人体之内。白细胞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有力地消解人体的入侵者。它们不能消化的部分就变成了寄生物,反过来消耗人体内对它们来说有营养的东西。

然而,就入侵特定人体的特定生物来说,这不过是影响其能否顺利侵入并在其中繁殖的极端复杂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尽管医学在过去百年间成就辉煌,但还是无人能完全说得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分子
 、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这种均势中,任何来自外力的变动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补偿性变化,借以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当然,如果变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此类灾难,既可能将原系统分解成更简单、更微小的单元,这些单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将原有相对较小的单元组合成更大或更复杂的整体。实际上,这两个过程也可能同时共存,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动物消化过程一样,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细胞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合成为自身体内的新蛋白质和新细胞。
、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这种均势中,任何来自外力的变动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补偿性变化,借以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当然,如果变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此类灾难,既可能将原系统分解成更简单、更微小的单元,这些单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将原有相对较小的单元组合成更大或更复杂的整体。实际上,这两个过程也可能同时共存,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动物消化过程一样,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细胞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合成为自身体内的新蛋白质和新细胞。
对此类机制的解释,显然简单的因果分析远远不够。既然同时存在许多变量,它们又不间断地交互作用,而且还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它们的规模,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它,结果往往是引人误入歧途。对多过程的同时态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更接近真实,但这样做,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对大部分组织层次而言,仅仅是对组织模式的确认及观察其存在或崩解,就让人感到有些力所不逮了,更何况在包括社会在内的某些层次上,连哪种模式值得关注或者能够被可靠地观测,也都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不同的术语会引导人们关注不同的模式,然而,要想找出一个逻辑上富有说服力并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试验方案,用以测定一套术语是否优于另一套,通常是不可能的。
然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类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及其符号体系,因此,当有些问题无法依靠逻辑来确定时,生存定律终将出面解决。对人类来说,那些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所处环境中利害攸关方面的术语,无疑具有巨大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相互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人类才得以主宰生物世界。然而没有哪一种术语体系有可能穷尽或涵盖我们所处情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地运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和概念,而不必为寻求一个能在任何时空环境下让任何人满意的所谓“真理”而枉费心机。
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假如史书中的许多圣人生活在今天的美国,恐怕很难逃脱因“精神不正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运;相反,被狩猎先祖们视为生理残疾的近视眼和味觉迟钝,在今天却不会被认为与健康理念有冲突。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历史性差异,“疾病”概念的核心内容仍是确定而普遍适用的。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将被同类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触。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体和社群对同样的传染病所表现出的敏感程度和免疫水平相当不同。这种差别部分缘于遗传,更多则是与以前是否接触过入侵生物体有关。
 不断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个体进行,在整个族群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相应地改变。
不断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个体进行,在整个族群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相应地改变。

正如个人与群体为对付传染病而不断进行机能调整一样,各种致病微生物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典型的,比如这一环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就是宿主体内的状况。毕竟,对于包括病原体在内的所有寄生体来说,都必须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宿主几乎都是互不相连的独立个体的情况下,它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转移?
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一个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其宿主,也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非常迅速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延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让寄生物无处藏身,显然也会对病原体造成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这类极端情形的出现,使得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未能延续至今;而一些曾经恶名昭著的病原体,由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疫苗注射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推行,正在濒临灭绝——如果某些踌躇满志的公共卫生官员的言论是可以信任的话。

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人的肠道下端通常带有大量的细菌,但这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在我们的口腔中和皮肤上,也附着了众多通常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微生物,其中有些可能有助于消化,另一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们体内的恣意繁殖。不过,一般来说,对于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感染生态学”的这类论题,我们目前还缺少确凿有力的数据来加以论证。

不过,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很多最致命的病原体其实还未适应它们作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处在与人类宿主的生物调适进程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应就此假设,长期的共存必定导致相互间的和谐无害。

譬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甚至前人类)最古老的寄生物,
 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至少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杀伤力。不难想见,由于镰状疟原虫侵入人体血管相对较晚,所以它们还无法像其他疟原虫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类宿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的进化调适,还会因宿主的多样性而更加复杂,而寄生物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适应宿主体内的环境。而且,有利于疟原虫长期寄居于人类红细胞中的调适,对其实现在不同宿主间的成功转移并无助益。
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至少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杀伤力。不难想见,由于镰状疟原虫侵入人体血管相对较晚,所以它们还无法像其他疟原虫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类宿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的进化调适,还会因宿主的多样性而更加复杂,而寄生物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适应宿主体内的环境。而且,有利于疟原虫长期寄居于人类红细胞中的调适,对其实现在不同宿主间的成功转移并无助益。
事实上,在通常主导性的转移模式中,人体一旦为疟原虫感染,红细胞就会成百万地周期性坏死,由此导致宿主怕冷发烧,并让疟原虫得以在血管中自由运动,直到一两天后,它们重新寄居在新的红细胞里。这一过程会给宿主带来热病和四肢疲软的症状,但同时也会让疟原虫以一种独立自由的形式趁着疟蚊饱餐人血时“搭便车”转移到别处繁衍。疟原虫一旦进入疟蚊胃部,就会展示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完成有性生殖(sexual replication)。结果是几天后,新一代的疟原虫就会游移到疟蚊的唾液腺里,以备在疟蚊下次“就餐”时侵入新的宿主体内。
就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看,疟原虫在被疟蚊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时,并不会对疟蚊造成伤害。疟原虫生活史的完成有赖于疟蚊体内组织的滋养,但这对疟蚊的寿命及其活力却并无不利的影响。这样说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疟原虫要被成功地转移到新的人类宿主身上,携带它的疟蚊必须拥有足以供自己正常飞行的精力。一个沉疴在身的疟蚊不可能将疟原虫成功运送到新的人类宿主以助其完成生活史。但是,一个身体虚弱、浑身发烧的病人却丝毫不会妨碍疟原虫完成其生活周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种古老的传染病对疟蚊毫发无损,却一直维持着对人类的杀伤力。
人类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染病也像疟疾一样,病原体必须让自己适应多个宿主。假如人类之外的宿主对这类寄生物更为重要,其适应性行为的重心将会集中于同非人类宿主达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上,一旦它们侵入人体,则可能对人类造成剧烈的伤害。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就是这样,引起这种疫病的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通常只感染啮齿动物以及它们身上的跳蚤,偶尔才染及人类。在穴居啮齿动物群体当中,这种感染可以长期延续下去。鉴于同一洞穴中可能混居着不同的啮齿动物宿主,这类感染及康复的模式必定极端复杂,我们对此至今也未能完全了解。然而,不管怎样,对生活于“地府”中的某些穴居啮齿动物来说,腺鼠疫就像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天花、麻疹一样,乃一种常见“儿童病”(childhood disease)。换言之,啮齿动物与这种寄生杆菌之间已经形成相当稳定的适应模式。只有当疾病侵入从未感染过该病菌的啮齿动物和人群时,才会酿成惨剧,就像历史上曾令我们的祖先倍感惊恐的腺鼠疫大暴发。
由于血吸虫病(通过钉螺传染)、昏睡病(通过采采蝇传染)、斑疹伤寒(通过跳蚤和虱子传染)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体拥有两种甚或更多的宿主,以致它们与宿主的适应模式极为复杂。因此,这类疾病对于人类来说,仍然十分可怕。斑疹伤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品系相同或近似的引发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rickettsial organisms)能稳定地寄居于某些种类的壁虱身上,代代延续而且基本相安无事;当老鼠及其身上的跳蚤被感染后,虽会发病,但可以自行康复,也就是说,它们在感染后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将入侵的病原体拒于身外。但是,一旦伤寒寄生菌转移到人体及人身上的体虱,总会导致体虱毙命,而对人来说,也常常是致命的。上述模式暗示斑疹伤寒病原体曾存在这样一种渐进式的转移:从最初与壁虱稳定的共存,再到与老鼠及其身上跳蚤的次稳定调适,最后到与人及其体虱间的极端不稳定适应。这似乎也意味着该病原体直到晚近才感染人体及其体虱。

当然,也有一些人类疾病并不需要传播媒介便可直接在人类不同宿主之间迅速传播。结核病、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和流行性感冒等都属于这类疾病。事实上,它们也是现代人极为熟悉的传染病。除了结核病和流行性感冒,人类只要被这类疾病感染一次,即可获得长期乃至终身的免疫力。于是,这类疾病通常只感染孩子。这在那些没有采用疫苗接种或其他人工方法改变天然的疾病传播方式的地区,依然如此。
这种儿童病一般不会特别严重,通常只要精心护理就可以康复。然而当其侵入以前从未接触过它们的族群时,则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和死亡,而且正值盛期的青年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感染并导致死亡。换言之,一旦某一“处女”族群初次接触这些传染病,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遭受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就像天花和随后的其他疾病对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毫无疑问,无论是慢性传染病、精神紊乱,还是老年性功能衰退,它们对今天人类造成的痛苦会更多,它们构成了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某种“背景杂音”(background noise)。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日趋长寿,这种痛苦变得更加显著。不过,我们祖先所经历的疾病模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情况根本不同。在先祖那里,不时暴发的瘟疫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无时不在的震慑力。尽管我们无法得到统计和临床资料(即便到19世纪也是零星的),以对19世纪以前瘟疫的发生情况做出准确说明,比如何种瘟疫在何时何地杀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仍有可能把握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实际上,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