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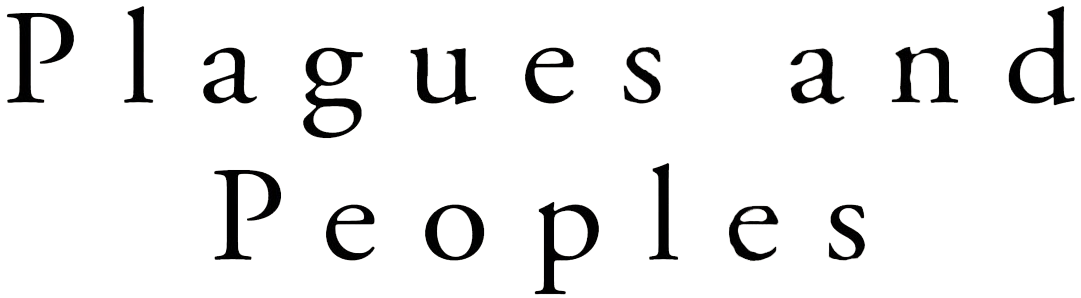
人传人的“文明”型的传染病确立的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年。而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不同的疫病就在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中确立下来了。这样说的证据在于,差不多公元纪年前后,原本孤立的文明社会之间出现定期和有组织的交流后,凶猛的传染病很快开始从一个文明蔓延到另一个文明,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几乎可以与1950年之后澳大利亚野兔的遭遇相类比,尽管未必有那么严重。
对这些事件更详尽的探讨将在下一章进行。在此只想稍稍思考一下,在公元前3000—前500年间,这些特殊的“文明病”在几个人口异常稠密的地区的确立,造成了怎样普遍性的历史后果。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影响是:和文明病的接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的损失,而人类的生殖方式必须适应这种损失。直到晚近,若没有周围农村移民的大量涌入,城市将无法维持自身的人口规模。因为,城市的健康风险实在太大了,除了存在像儿童病那样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借由吸入空气中由喷嚏或咳嗽喷出的传染性的飞沫所致的疫病外,古代城市还经受着因水质污染而强化的传染循环,以及许多以昆虫为媒介传播的传染病。而且,任何长途运送粮食的交通的中断,都可能让城市立即陷入饥馑的危机,而当地的收成往往很难给予充足的补充。因此毫不奇怪,城市很难自我维持人口的数量,而只能依靠农村移民来弥补由饥馑、流行病和地方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
因此,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要求农村耕作者生产出超过他们自身消费的粮食来供养城市人口,而且还要求他们生育更多的子女移居城市以维系城市的人口规模。此外,农村生产的剩余价值还能够承受巨寄生(即战争和掠夺以及总是尾随这些行为而至的饥荒)所造成的损失。不过,那种农村人口出生率与农村过剩人口在城市取得的生存空间之间稳定的平衡,只是在偶然并有限的时间内才会出现。另外,空旷而可耕的荒地(这在过去4个世纪里,对欧洲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一旦有可能得到土地,过剩的农村人口就会前往垦荒(实际也去了),并由此扩展社会的农业基础,而不再冒险尝试移居城市的道路(虽然也有少数人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出现相对可信的人口统计数据的1650年以前,我们似乎都没有办法去猜测上述人口流动的规模。尽管如此,这种人口流动的模式,显然从城市形成的那天起就出现了。公元前3000年,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闪米特人令人吃惊地取代了苏美尔人,
 可能就是这种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可能有太多的闪米特人迁往苏美尔人的城市,以致淹没了说更古老语言的人。作为学术和祭祀用语,苏美尔语长期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被闪米特的阿卡德语取代了。这类语言的转换可能源于城市人口的暴增,或更可能源于原先城市人口在疾病、战争或饥馑中的大量死亡,不过,这类因素是否适用于苏美尔人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就是这种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可能有太多的闪米特人迁往苏美尔人的城市,以致淹没了说更古老语言的人。作为学术和祭祀用语,苏美尔语长期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被闪米特的阿卡德语取代了。这类语言的转换可能源于城市人口的暴增,或更可能源于原先城市人口在疾病、战争或饥馑中的大量死亡,不过,这类因素是否适用于苏美尔人就不得而知了。
19世纪的情形或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此的理解。自19世纪30年代,甚至可以说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加上霍乱这种新疫病的肆虐,瓦解了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屹立于欧洲的文化模式。
 迁移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境内城市的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学习日耳曼语,几代以后,他们的后代在语言和感情上都日耳曼化了。这一过程从19世纪开始发生动摇。当生活在王朝城市的斯拉夫语和马扎尔语的移民数量超过一定界限,新来者不再为日常生活的缘故学习日耳曼语了。不久,民族主义思想的扎根使认同日耳曼语成了不爱国的标志,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布拉格成了捷克语城市,布达佩斯则成了马扎尔语城市。
迁移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境内城市的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学习日耳曼语,几代以后,他们的后代在语言和感情上都日耳曼化了。这一过程从19世纪开始发生动摇。当生活在王朝城市的斯拉夫语和马扎尔语的移民数量超过一定界限,新来者不再为日常生活的缘故学习日耳曼语了。不久,民族主义思想的扎根使认同日耳曼语成了不爱国的标志,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布拉格成了捷克语城市,布达佩斯则成了马扎尔语城市。
显然,在语言上更趋统一的早期文明,并不曾出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那样的语言变迁。不过,无论是远古还是晚近,城市人口损失的事实都毋庸置疑。只要城市以及由其强化的疾病传染方式存在,就足以导致这种结果。只是对病原体而言,发现并把自己植入城市人口为它们准备的有利的生存环境,仍需等待适当的时机。
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如何被启动和维持,我们现在仍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农村肯定更有利于健康,泛滥于城市的各类传染病不太可能波及农村居民。但另外,当传染病真的传入农村,就会产生比在城市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城市人口已有患病经历而且部分获得免疫力;许多农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对任何传染病都格外敏感。显然,处在文明社会控制下的农民可能已自发意识到,养育超过传宗接代所需要的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不会比生产出超过维持生计所需的粮食来得容易。
然而,他们却普遍完成了这两大任务。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离开了食物和移民,文明也就无法延续。因此,鼓励农村高生育率的道德准则成为文明社会得以维持的必要基础。无论如何,狩猎和采集群体用以控制人口数量的各种方法在文明的农业社会中不再流行。相反地,在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农业社会里,早婚和多子一直被视作道德高尚和天赐福佑的标志,以及防范老来无助的最佳选择,因为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仍可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这类态度,也是与对个人或家庭的土地产权的认可相联系的,这些权利反过来也经常被政府用租税的形式来加以规范和强化。
至于文化、社会和生物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准确的情形则无法描述。所能确信的只是:所有成功的文明机制都能借助宗教、法律和习惯等力量,来确保人流与物流从农村流向城市。
正如我们在人口爆炸的当代很容易理解的那样,文明社会的生育模式会产生农村人口过度膨胀的危险。任何长期削减农村剩余人口就业机会的情况,无论是发生在城市、军队或迁移拓荒中,很快就会让过剩人口流回农村。要事先防止农村人口过度膨胀,替代的职业必须具有高死亡率,且不至于妨碍男男女女接受背井离乡可能产生的风险,无论这样做出于自愿还是无奈,自觉还是无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稳定的人口平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其困难的。这要求城市和战争中的死亡率必须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匹配,而同时整个社会必须防范可能颠覆国内人口模式的大规模的“外来”侵略。
在世界任何地方,满足这些条件的真正稳定的巨寄生模式很少能长期存在,相反,当和平繁荣时期人口增长超过巨寄生的吸收(破坏)能力时,文明史通常显示出剧烈的上下波动;结果是死亡率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而提升了。当对农业人口温和的控制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平衡时,总会通过农民起义、内战、外来掠夺,以及相伴而行的饥馑和瘟疫等方式,让人口灾难性地骤减。
一般说来,在成功的政治统一再一次容许人口增长以巩固其自身以前,提高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可以把人口削减到远低于以前的水平。不过,无论是源自病原体还是武装军人的外来入侵,显然都能打断这一循环;而且导致作物严重歉收的气候异常也能做到这一点。在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不仅频繁而且猛烈,以致掩盖了农民数量的波动与公共秩序安宁程度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有在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它的地理屏障保护了这个文明群体免受重要的外部压力的影响,因而外部的政治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才使得这一循环能够清楚地展现出来;不过,即便在这里,外部因素也从未完全缺席,有时也会阻碍其人口的恢复达几个世纪之久。
此外,文明社会还有别的消化农村过剩人口的方法。通过对邻近地区发动战争,国王和军队有时能够扩大其治下的疆域,为他们的臣民拓展可定居和开发的土地。这种事业的确为国内的人口膨胀提供了全面而可靠的解决方法,只要发动征服战争,无论最终胜负为何,死亡人口的显著增加也都是可以预期的。
贸易有时候也可以消化过剩人口。不过,直到最近,由于陆路交通的成本过高,只有居住在海边或可通航的大河边的人才可能凭贸易致富。从文明射出第一道曙光起,船只就能够把食物和别的有用商品从远处运往一些港口,文明社会的商人和水手通过用制成品交换食物或原材料,与外国人从事互利贸易。但是,要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中保持贸易平衡,就像在单一政治共同体中保持稳定的人口平衡一样,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扩张与收缩的迅速交替,既是政治与战争的规律,也是贸易的规律。
由于插入了如此多重的不稳定因素,文明社会在巨寄生的层次上便很难达到和谐的生态平衡。从历史记载来看,就像一种疾病侵入缺乏罹患经验的宿主人群的情形一样,文明型的巨型寄生模式的影响力,常常处于剧烈的波动之中,有时会杀死超量的以其劳动支撑该体系的农民和其他的劳动者;而有时却又未能保持与可利用的食物相当的人口数量。
尽管曾有过无数的区域性挫折,但受制于文明型组织的地区,确实在世纪的推进中渐趋增多。然而各自独立的文明种类却总是数量有限,根据区分文明种类的标准的不同,有人计为半打,有人算作两打。这么小的数字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文明的扩张并不是把此前存在于各地的制度、观念和技术提高到新的更精致的程度,相反,文明通常只是把关键性的文化因素从精致的文化中心地区输出到新的地盘。通常,或许总是,借鉴和模仿比另起炉灶更容易,不过这种情势下,还有另一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文明社会比较容易扩张到新地区的原因,即它并非是有意识的政策或巨型寄生方式扩张的结果,而是源于微型寄生方式的推动。这一点,我们稍加思考便不难明白。
当文明社会逐渐与那些只能存在于大量人口中的“儿童病”共存共容时,它们便获得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生物武器,每当与以前封闭的小群体接触时,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一旦在缺乏相关病史的人口中肆虐开来,文明病便很快展现其猛烈的一面,将老老少少一起杀死,而不再是只感染孩子,产生虽然可能严重但尚可忍受的病症。

这种瘟疫的破坏性后果往往比单纯的生命损失更为严重,尽管生命已经不堪其重。通常,幸存者将变得意志消沉,对其传统习俗和信仰失去信心,因为这些习俗和信仰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应对这些灾难。有时候,新的传染病在青年人当中表现得烈性最大,某些医生相信这是由于这个年龄群体对入侵病原体的抗体反应更为强烈。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失去20到40岁这类青壮年,显然要比失去同样多的老人或孩子损失更大。任何一个社会,若在一次瘟疫中就损失相当多青壮年,都会感觉其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将难以维系。当初次遭逢一种文明病后,又有其他类似颇具杀伤力的遭遇尾随而至,该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崩溃几乎毋庸置疑——在文明史上最初的几千年中,其结果则是不时地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产生半真空地带。淳朴乡民与城里人接触,总是要冒着感染毁灭性并导致人们士气低落的疾患的危险。即使是幸存者,也往往无力抵制而只能彻底融入文明的政治实体中。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失去20到40岁这类青壮年,显然要比失去同样多的老人或孩子损失更大。任何一个社会,若在一次瘟疫中就损失相当多青壮年,都会感觉其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将难以维系。当初次遭逢一种文明病后,又有其他类似颇具杀伤力的遭遇尾随而至,该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崩溃几乎毋庸置疑——在文明史上最初的几千年中,其结果则是不时地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产生半真空地带。淳朴乡民与城里人接触,总是要冒着感染毁灭性并导致人们士气低落的疾患的危险。即使是幸存者,也往往无力抵制而只能彻底融入文明的政治实体中。
无疑,战争经常与流行病的蔓延过程相交错,并且掩盖它;即便是战争掠夺也不能截然分开的贸易,则是文明人探求新领地的另一种常见方式。由于战争和贸易往往被载入史册,而发生于无知无助的边疆乡民中的瘟疫却无人记载,所以历史学家至今未能充分注意城市环境植入文明人血液中的生物武器。然而,缺少史料不应该妨碍我们认识传染病让文明社会所拥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那些在文明的生活环境中经历了儿童病困扰的人群所创造出来的。
即使当地人口由于与一种或多种文明病接触而损失惨重,或士气低落,邻近地区防范文明社会入侵的有效障碍有时仍然存在。如果土地过于干燥、过于荒废、过于潮湿,或过于崎岖,以至于不适合文明社会的农耕方式,那么殖民仍会受阻,当地人口就可能有机会在生物意义上恢复元气,或者因接收了从更远地区输入的其他人口而力量大增。如果文明中心和这些边远地区的接触长期化,反复的接触也会使文明病失去大部分可怕的后果。当然,在这些边远地区,偶尔的灾难仍可能发生,或由于新传染病的出现,或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到新的疾病传播方式能够自我维持的程度,或由于前后两次传染病暴发的间隙过长,而它们的永久性病灶仍存在于文明城市当中。
但是,当缺乏地理或气候条件来防止业已确立的文明的耕作方式传入边境地区时,那些横遭新疾病摧残的人们,不太可能抵制疾病进一步的入侵。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动物消化过程颇为近似。首先,邻近社会的组织结构由于战争(相当于咀嚼)和疾病(相当于胃肠的化学和物理消化)的共同作用而崩溃。有时候当地人口会被彻底灭绝,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通常的情况是,在经过同文明社会最初的毁灭性接触之后,残存了大量在文化上无所适从的人。而后,这些人作为“原料”(material),或以个体形式,或以家庭和村落这样的小群体形式,被吸纳进扩大了的文明肌体本身。在与来自文明内部的移民和难民混合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人就同文明的政治统一体的其他农村和偏僻地区的人无从区分了。这一历史过程与人类的消化方式颇为相似,即为了让食物的分子和原子融入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会拆解开食物的较大的化学结构。
从边疆文明的视角来看,最初当地社会抵御能力的土崩瓦解,开辟了农业社会中过剩人口移向新土地,并在那里找到新的谋生机会的道路。大体看来,这一现象仍然不乏偶然性和地域性,适宜的土地和过剩的劳力绝非随处可得。但它在若干世纪里经常出现,使得以前的文明社会出现周期性的扩张。这基本是因为历史上的文明社会总是倾向于扩展它们的地理界域。
当然,趋于扩展的文明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较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大约公元前1300年以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古埃及帝国政府就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产生了冲突。而且,一个社会被另一个社会在流行病和文化上的“消化”(digestion)有时也能瓦解文明社会,这正是1500年后美洲印第安人诸文明的命运。而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发生在当它们逐步被并入越出原有边界的帝国疆域之时,这个过程只是在公元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以后才告完成。
有些读者可能对上述论断和推理心怀疑虑,特别是当这些推理应用于整体的文明社会,而没有考虑地域差别和岁月变迁时。这些差别无疑存在,但现有史料无从觅见它们的踪影,因为当时少数具有书写能力的人,当然不可能意识到今天我所要尝试分析(哪怕是拙劣的分析)的这场生物进程。我们必须面对下列事实:直到近代,因欧洲的大洋探险突破了无数的流行病障碍,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空前规模之时,现存的材料仍旧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弱小而不幸的文明民族的邻居所遭受的痛苦。
通常情况下,作家们会认为文明(当然是他们自己的文明)的扩张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其价值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也这么看。但是考虑到人们对自己成长的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一般性依恋,这些自在的社会,如果未曾受到侵扰,它们是否愿意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便这个社会拥有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技术、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
毫无疑问,野蛮人在军事上经常成为征服者,结果却反过来被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诱惑力所征服。这些入侵者很少能预见到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而当他们最后意识到时,他们通常会抵制文明的侵蚀。但是,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比起边界地区穷苦而卑微的人们有着更炫人的前景,后者命中注定的角色就是被吸收进文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可以想象,这些人只要有能力,总在抵制与文明社会合流。
因此,如果要纠正现有材料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就需要解释文明何以能成功地把边民纳入都市社会之框架。只有对上述流行病的模式给予适当考虑,文明社会的文化扩张才可以理解,其他解释至少是不充分或是不能与人们的通常行为相吻合的。
印度的情形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测试案例。在这块次大陆上,文明首先出现在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在这里,印度河从高高的喜马拉雅山流经沙漠入海。这样的地貌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似,支撑印度文明的灌溉农业也可能与古代的这两个中东文明几无分别。印度历史的基本形态是由公元前1500年后野蛮人(雅利安人)的入侵所界定的,其后则是文明生活方式缓慢地重新确立。这也与其他河谷文明所经历的古代历史的节奏相符。

然而,公元前800年文明社会再次出现在西北印度之后,它与其他大河文明的分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与这些城市社会接壤的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各种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中的“森林民族”,若处于温带地区,则极易遭受文明病的浩劫。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文明病只在亚欧大陆的更北部而不在印度造成破坏性后果。但印度的森林民族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崩溃和分裂,相反,他们也拥有对文明社会的生物武器的反制利器。各种盛行于湿热气候条件下的热带病和到处出没的寄生物帮助他们抵抗住了温带文明的入侵。正如后来非洲所发生的那样,由于大量的死伤在等待来自印度干燥的西北部文明社会的士兵,他们无法大规模地或快速地入侵湿热地区,只得小心地远离这些传染病。森林人可能因与文明人的接触而感染和死亡,而文明的入侵者同样容易遭受森林人热带病的袭击。
结局众所周知,印度文明并没能像对喜马拉雅山北部居民那样,将印度南部和东部的原始社群消化掉,而是把森林民族以种姓方式兼并,即把他们作为半独立的有机体纳入印度的文化联合体当中。因此他们地域性的文化和社会传统在进入印度的文明社会之前没有被摧毁,大量的原始仪式和习俗延续了几个世纪,而且这些因素不时出现于印度的文献中。每当这些口耳相传的观念和习俗引起文人的注意时,就会被充分地记载下来,并加以进一步的完善或修正,以融入历史悠久且渐趋复杂的印度教中。
其他的因素和态度自然也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规范和维持产生了影响。然而有关跨种姓接触的禁忌,以及在非有意破坏禁忌的情况下有关身体净化的复杂规定,显现了恐惧传染病的心理在维持各社会群体(即后来的各种姓)间的安全距离上面所起的作用。只是在长期的感染接触之后,抗体免疫力和对寄生传染病的忍受程度逐步相等(或与起初的差别相比急剧减少),雅利安入侵者才能安全地与说泰米尔语和其他古语的人共同生活。与这种疫病的交流一起出现的,无疑还有血缘的混合(尽管存在禁止乱婚的种姓制度),而相当顽强的天择性生存肯定已经改变了森林民族以及代表文明生活方式的入侵者的基因组合。
然而这些均质化(homogenizing)过程都没有达到其他古代文明的彻底“消化”的程度。比起亚欧大陆北部诸文明更为统一的构造,印度文明的文化统一性和社会凝聚力始终较弱。有人可能把印度文明的这一特殊性归结于概率使然或有意的选择。概率和选择可能在形成种姓原则上真的起了作用,但印度文明在早期扩张阶段所面对的独特的疾病环境肯定也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这种制度以不同于别处的方式形塑了印度文明的社会结构。
美洲的情况在另一意义上有所不同。出现在欧亚城市中心的那类文明病未能在1500年前的墨西哥和秘鲁扎下根来,否则蒙特祖玛肯定会以瘟疫为工具,对入侵的西班牙人进行更为有效的报复。相关细节还是留待后文探讨欧洲人抵达美洲造成的疫病方面的后果时再加以详细论述。
在此,我们还是根据现代传染病理念对上述的推理和论证做一归纳。尽管缺少结论性的文献或考古材料,但似乎可以肯定,从城市兴起到大约公元前500年之间,旧大陆的主要文明地区都各自发展了特殊的人传人(person to person)传染病。此外,在拥挤的城市和邻近密集的农业定居区中,通过水、虫和接触传染的疫病也有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在生物学意义上,携有这些疾病并产生抗体的文明社会,对于不曾遭遇过这些可怕疾病的邻居而言是危险的,这使得文明社会的地域扩张更加容易。
不同疾病库之间的准确界限很难划定。往往特定传染病的地理范围将依人类的活动、文明中心地区的发病方式和严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文明的社会结构所创造的新式生物平衡,无论是微型还是巨型的寄生关系,都可能随着每一次交通和交流的重大改变而受到干扰,因为没有一种重要的新传染病曾达到其地理的或其他的天然极限。这些平衡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间变化的情形,将是下一章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