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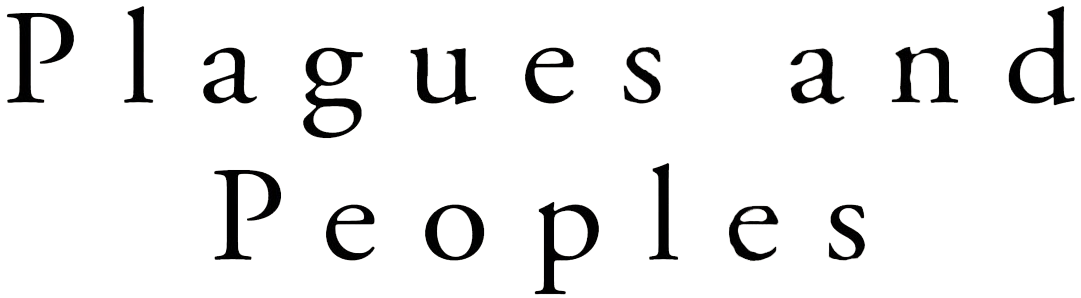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当我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概括,而提出诸如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些怎样的疾病?流行于哪些地方?在什么时候?以及对人类生活和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时,知识的模糊性使我们很难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即便不去考虑影响作物和驯养的动物的疾病,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创作一部人类的传染病史。
显而易见,长期或永久性地定居在一个村庄里,就会卷入新的寄生物侵扰的风险。比如,当人类的粪便在居住地周围堆积时,人们与它接触的增多有助于肠道寄生物顺利地进行宿主间的转移。相反,一个不停流动的狩猎群,在任一地点的逗留时间都不长,自然不易受这种循环感染的威胁。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生活在定居社会里的人们,比起他们处于同一气候区的狩猎先人或同时代的狩猎族群,更易受寄生物的感染。有的寄生物通过污染水源在宿主间随意转移,这种情况在经年累月依靠同一水源生活的定居社会中,自然就更容易出现。
尽管如此,代表原始农业特色的小型村落社会,可能并没有过多地受累于寄生物的侵扰。近东的刀耕火种者在一生中要屡迁其地;中国的小米种植者,以及美洲种植玉蜀黍、豆类和马铃薯的印第安人也相当分散地居住在前文明的小村庄里。各类感染在这些社会中可能是存在的,尽管寄生物的数量因地而异,但在每个小村庄里大家在年幼时都会患上同类的寄生虫病,至少这是今天原始耕作者的情况。
 但这类感染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生物意义上的负担,因为它们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规模的增长。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
但这类感染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生物意义上的负担,因为它们未能阻止人口空前规模的增长。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
 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在早期农业中依赖灌溉的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秘鲁沿海地区,与简单的、或多或少封闭的村庄相比,显然需要更完善的社会控制。运河与沟渠的规划与维修,尤其是灌溉水源在使用者之间的调配,都需要有权威性的领导者。于是,城市和文明诞生了,比起乡村生活,它们要求更广泛的合作和生产的专业化。
不过,灌溉农业尤其是相对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灌溉农业,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重构了有利于病原虫传播的环境,这种环境普遍存在于孕育人类远祖的热带雨林中。充足的水分(甚至比热带雨林还要充足)加快了寄生物在宿体间的转移频率,众多潜在的人类宿主在温暖、浅缓的水域中驻足,为其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媒介。在这种环境中,寄生体并不需要胞虫囊一类能够长期抵御干旱的生命形式即可顺利传播。
古代的寄生方式可能与今天稍有不同。但以人类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生物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5000年前在灌溉农业的特定环境下的寄生形式,与当今仍困扰着稻田农夫的寄生形式,几乎是一样的。
目前已知的这些寄生物已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导致血吸虫病的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的、令病人虚弱的病症,即便在今天,它也许还在折磨着上亿的人口。血吸虫的生活史,是软体动物和人类轮流担任宿主,它以微小的、自由游动的形体,通过水实现宿主间的转移。
 一旦感染上它,有时会让钉螺(最一般的软体动物宿主)送命,但对慢性感染的人来说,它的最严重症状出现在儿童期,其后表现得持续而相对缓和。像疟疾一样,血吸虫的寄生生活史相当精致。它具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它们的宿主:软体动物或人,以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连同它在人体内产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征表明,在现代血吸虫的行为模式形成之前曾经过长期的进化。像疟疾一样,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于非洲或亚洲的雨林;但这种疾病分布得异常广泛,
一旦感染上它,有时会让钉螺(最一般的软体动物宿主)送命,但对慢性感染的人来说,它的最严重症状出现在儿童期,其后表现得持续而相对缓和。像疟疾一样,血吸虫的寄生生活史相当精致。它具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游动形式,各自寻找它们的宿主:软体动物或人,以便一旦侵入宿主即可进行活跃的运动。这种复杂的情形,连同它在人体内产生的慢性病症的特征表明,在现代血吸虫的行为模式形成之前曾经过长期的进化。像疟疾一样,其寄生的模式,可能源于非洲或亚洲的雨林;但这种疾病分布得异常广泛,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是在何时何地扩散到今天盛行的这些地区的。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元前1200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有把握地指出它是在何时何地扩散到今天盛行的这些地区的。古代埃及的灌溉者早在公元前1200年(可能更早)即受此感染;
 古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是否同样受此感染还不敢断言,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两大河谷间通过接触而同时感染的可能性;
古苏美尔和巴比伦人是否同样受此感染还不敢断言,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两大河谷间通过接触而同时感染的可能性;
 同样,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于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尽管死因是心脏病,但同时也携有血吸虫及其虫卵。
同样,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安葬于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尽管死因是心脏病,但同时也携有血吸虫及其虫卵。
 今天,农民需要长时间地浸泡于水田作业的灌溉区,这种病仍能迅速传播。
今天,农民需要长时间地浸泡于水田作业的灌溉区,这种病仍能迅速传播。
 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古代的灌溉技术与血吸虫病很早就在整个旧大陆紧密联系起来了。
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古代的灌溉技术与血吸虫病很早就在整个旧大陆紧密联系起来了。
无论古代的血吸虫病以及类似的病症曾如何分布,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它们泛滥的地方都容易造成农民出现无力和疲怠的症状,使他们既不能长时间地在田里劳作和挖掘沟渠,也无力胜任那些对体力的要求并不亚于劳作的任务,比如抵抗军事进攻或摆脱外来的政治统治与经济掠夺等。换言之,由血吸虫病和类似感染所造成的倦怠和慢性不适,
 会有助于为人类所惧怕的唯一大型天敌的成功进犯,他们就是自己的同类,为了战争和征服而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掠食者。尽管历史学家不习惯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征税和掠夺的问题,但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的相互支持,肯定是正常的生态现象。
会有助于为人类所惧怕的唯一大型天敌的成功进犯,他们就是自己的同类,为了战争和征服而武装和组织起来的掠食者。尽管历史学家不习惯于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征税和掠夺的问题,但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的相互支持,肯定是正常的生态现象。
农民被寄生物传染这件事,如何加速早期大河文明的建立,其作用尚难以合理估计。但似乎也有理由怀疑,显现灌溉农业社会特征的专制政府的存在,除了与经常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治水所需技术有关外,也包括这类令人虚弱的疾病的功劳,多亏它们侵扰了长期光脚在湿漉的田间劳作的农民。
 简言之,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古代希伯来人没有想过,现代历史学家也从未关注过。
简言之,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古代希伯来人没有想过,现代历史学家也从未关注过。
只要寄生物小得无法辨认,人类对瘟疫的应对严格说来便是盲目的。但人类有时的确能摸索出饮食和卫生规则以减少感染机会,最耳熟能详的例子,便是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这看起来令人费解,除非你意识到猪是近东村庄的腐食者、喜食人粪和其他“不洁”之物,它们的肉如不经彻底烹煮便当作美食,就很容易把许多寄生虫吞进肚里,现代的旋毛虫病(trichinosis)就证明了这一可能性。不过,禁食猪肉的古代习俗与其说是建立于某种试错法之上,毋宁说是建立于对猪的本能恐惧之上;至于由遵守禁忌带来的健康上的好处,尚无法从现有史料中看出端倪。
将麻风病人
 驱逐于正常社会之外这一做法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的情绪。这是另外一条古老的犹太人戒律,想必它减少了通过皮肤接触而感染的机会。沐浴——无论用水还是沙子,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仪式中均有重要地位,这可能也有防止传染的功效。
驱逐于正常社会之外这一做法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的情绪。这是另外一条古老的犹太人戒律,想必它减少了通过皮肤接触而感染的机会。沐浴——无论用水还是沙子,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仪式中均有重要地位,这可能也有防止传染的功效。
但另外,为庆祝神圣节日,成千上万的朝拜者聚集一处共同沐浴的仪式,却又为寄生物寻找新宿主提供了绝佳机会。
 在印度,很大程度上霍乱的传播曾是(现在仍然是)宗教朝圣的“职能”。
在印度,很大程度上霍乱的传播曾是(现在仍然是)宗教朝圣的“职能”。
 因此,那些传统的习俗,即便被宗教和无人记得的仪式奉为神圣,也并不见得总能有效地阻止疾病的传播;而且,那些实际上扩散疾病的做法也同那些对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仪式一样,可能,也的确被神圣化了。
因此,那些传统的习俗,即便被宗教和无人记得的仪式奉为神圣,也并不见得总能有效地阻止疾病的传播;而且,那些实际上扩散疾病的做法也同那些对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仪式一样,可能,也的确被神圣化了。
当然,农业环境中有利于在人类中传播的,并不只是这些多细胞寄生物。当畜群、作物和人口大量繁殖时,原虫、细菌和病毒的感染的空间也相应得以拓展,一般来说,其结果并不直接,未曾也无法预见。除了极特殊的情况,要复原新传染方式赖以形成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然而,仍有某些例外。譬如,在西非,当农业扩展到雨林环境时,刀耕火种的农作方式显然对旧生态平衡施加了新的压力,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疟疾获得了全新的流行强度。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把森林夷为平地为喜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扩大了滋生的地盘。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将疟蚊视为“杂草”类的物种,它们在人类为农业所开辟的非洲雨林中的空地上恣意繁殖,并随着农业的进展,取代了别的喜食动物血而非人血的蚊子。结果,人—蚊子—疟疾这一循环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切实地影响到每个深入雨林空地的人。

虽然非洲的劳动者仍能出于农业目的而继续努力征服雨林,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伴以基因上的调整,使得制造镰刀形红细胞的基因(异形合子形式)出现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红细胞对疟原虫,显然不像普通的红细胞那样友好。于是,疟疾令人衰弱的症状在体内含有这类红细胞的人身上减弱了。
然而,得到这一保护的代价十分高昂。一个人若从父母那里同时继承了双方的镰刀形红细胞基因,那他(她)往往会在青年时早夭。不过,那些生来完全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疟疾的致命感染,这也使得儿童死亡率进一步攀升。在西非疟疾最猖獗的地区,约有半数的新生儿携有镰刀形红细胞基因,他们在生理上是很脆弱的。由于农业对雨林的入侵仍在继续,当前疟疾、疟蚊以及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分布情形,让我们得以重构当年随着旧的生态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的异常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目前仍在显现中)。

在19~20世纪的中非和东非,欧洲殖民当局所推行的改变传统畜牧耕作方式这一错误的做法,也说明了农业向新的地域扩张所带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一活动加剧了嗜睡病在乌干达部分地区、刚果坦干伊喀、罗得西亚和尼日利亚的流行;最终的结果是,随着殖民政权的结束,这片大陆更深地受到了采采蝇的感染,而在当局决定更有效地开发这一片看似优良的农业地区之前,情况并非如此。

显然,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和临近的草原地区——这个地球自然生态中最严峻和最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能成功,并依然以持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因为在其他地区,主流的生态系统从未如此精致,因而也不会与人类的简化行为
 如此抵触。
如此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