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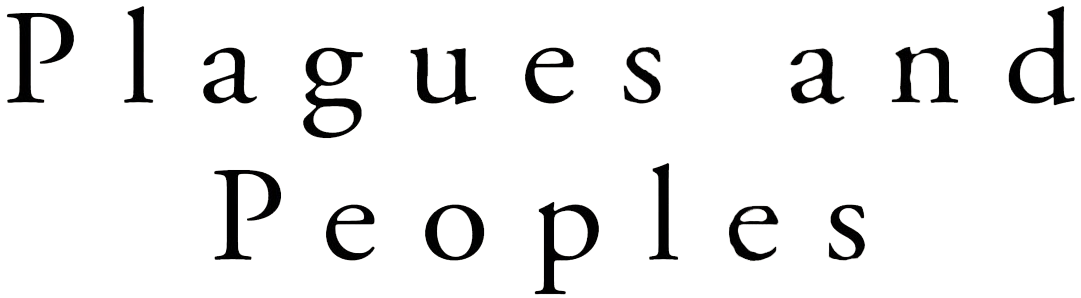
在每一个地方,古代的狩猎者都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习惯以更充分地利用正在变化的环境。当大型动物灭绝时,就必须找到可替代的食物。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祖先再度成为杂食动物,就如同他们的猿人祖先,开始食用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特别是,海边和海洋的食物资源第一次被系统地利用,这一点可从被抛弃的软体动物的贝壳和不那么显眼的鱼骨堆中得到证明。不仅如此,人类还发展出了制作食物的新方式,比如,某些族群认识到,长时间的浸泡可以除掉齐墩果和木薯中的有毒成分,从而可以食用;另一些蔬菜通过碾磨、蒸煮和发酵,会变得更可口或更容易消化。

然而,所有这些补偿性措施与通过畜牧和种植发展起来的食物生产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社群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不过产生的结果,则随着各地最初的野生状况中可资利用的动植物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说来,新大陆相对缺乏可驯养的动物,但有用的植物却不少,旧大陆则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的粮食作物。
我们对早期驯化的细节仍不清楚。我们必须假设,在人类与可种植和驯养物种之间存在着相互适应的过程,这包括被种植和被驯养的动植物会出现快速且有时影响深远的生物特性上的改变,这是因为人类对它们的某些生物特性做了偶然或有意的选择;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假设,人类自身也做出了根本的(即使很少是有意的)选择。比如,那些拒绝从事辛苦的农业劳作的往往难以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或不愿为来年的耕作备足种子而宁愿吃掉所有余粮的人,也将很快被依靠每个年度的收成生活的社会所淘汰。
牧人、农夫以及各种各样的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依其气候、土壤和人类技能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与动植物的野生背景相适应。而其结果,在村与村之间、地块与地块之间,甚至同一地块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不过,仍有一些普遍现象值得注意。首先,当人类以增殖某些动植物的方式改变自然景观时,另一些别的动植物也就被取代了,其一般性影响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区域内的动植物渐趋单一。与此同时,当人类的活动降低了其掠食者的角色,而又把越来越多的食物储存起来仅供人类自己消费时,其食物链也就缩短了。
食物链的缩短将人类拖入了永无休止的劳作当中。保护畜群和庄稼不受动物掠食者的侵害,对于熟练的猎人来说,虽然要求其始终保持警惕,但算不上是什么大问题。然而,要防范来自人类自身的侵害就不同了,防范同类掠夺的努力正是催生政治组织的主要动力,这一进程至今仍未完成。
但对人类生活更重要的还是除草工作,即试图消灭那些与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争夺生存空间的敌对物种,这是因为其需要整个族群大部分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手除草似乎真的是“农业”的最初形式,但当人类学会了刈除自然界中最茂盛的植物而为他们喜好的作物拓展生态空间,从而更彻底地重塑自然环境时,人类的力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两种方法证明这些手段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对干燥的土地实施人工灌溉,以挖掘和犁地的方法机械地改变土壤的表面状况。
灌溉有助于淹死竞争的物种。一段时间内土地淹在水下,而在其他时间里则放水以晾干土地,当这样安排农时时,杂草就不再是大问题了。很少有植物能在极湿与极干环境的交替下还能照样生存;而当农夫只通过开关巧妙设计的水闸,便可以随意调整旱涝以适应作物需要时,此时能存活下来的杂草就更是少之又少。当然,只有在浅水中能长势良好的作物才能获益于这种方法,水稻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对别的不那么有价值的根茎类作物,这一耕作方法也同样适用。
以铲子、锄、锹或犁等机械力量来改变土壤的做法,更为西方人所熟悉,因为这种农耕方式最早出现在古代近东,随后被传入欧洲。此外,它也盛行于美洲和非洲的早期农业中心。在更早的刀耕火种的阶段,人类是用剥掉树皮的方法来毁掉落叶林,这有助于阳光直射森林地面,在没有杂草竞争的环境下促进谷物的成长。然而,即使可以靠焚烧枯树来更新土地的肥力,这种耕作方式也不够稳定,风中洒落的种子不久就会在森林空地繁殖起蓟及类似杂草,只需一两年不受控制的疯长,这些入侵者就会完全鸠占鹊巢。于是,最早的近东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农夫只有另寻处女地,重新开始新一轮只有第一年没有杂草的种植,才得以生存下去。
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犁耕的发明,最早的局限首先在古代近东取得了突破。犁耕可以年复一年地有效地控制杂草,从而使土地无限期地得到耕种。原因很简单:犁耕用畜力代替人力,这样就能让古老的近东农夫可以耕种两倍于他们所需的农田,多余的土地则处于休耕状态(即在生长季节犁耕以毁掉杂草),以便为来年的作物生长预留适宜的生态龛,而不致被杂草所侵扰。
大部分教科书仍然对休耕是如何让土地通过休息来恢复肥力进行解释,这种说法证明了人类的泛灵论倾向。任何人只要稍做思索就可以认识到,在一个季节里地质气候的变化及随后的化学变化,无论过程怎样都不会对来年的植物生长造成显著的差别。诚然,在“旱播”的情况下,呈裸露状休耕的土壤更容易保有水分,否则水就会通过植物的根系和叶子从土壤里发散到空中,在由于水分不足而影响作物产量的地方,休耕一年可以通过积聚底土里的水分以提高肥力。而在别的水分并不对植物生长构成关键性制约的地方,休耕的巨大好处在于可以用犁耕阻断杂草的自然生命周期,使其枯死。
翻土(或引水灌溉)自然能达到相似的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凭人的体能尚不足以翻掘足够的耕地,以允许一家人只靠耕地的一半收成就可以维生,而让另一半休耕。当然,特殊的土壤和生态环境确实容许出现某些例外,两个最重要的例外是:第一,在中国北部,肥沃而易碎的黄土使人们无须借助畜力即可以小米维生;第二,在美洲,玉蜀黍和马铃薯比旧大陆的小麦、大麦和小米一类作物含有更多的单位热量,所以,即使这里的土地不像中国的黄土那样容易耕种,仍能达到相似的结果。

上述的技能的确令人钦佩,人类借助它们在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过程中发现并利用了其原有的种种可能性,成倍地提高了食物供应,尽管这也意味着人类从此将不得不持久地接受没完没了的劳作的奴役。毫无疑问,一旦在犁耕中使用了畜力,那么耕作者的生活就要比东亚的稻米生产者轻松得多,后者需靠自身的体力来完成水田劳作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引水和犁土。但辛劳——日常性的、没有尽头的、与狩猎经历所造就的人类天性严重冲突的辛劳,仍然是所有农业人口的命运。只有如此,农夫们才能成功地改造自然的生态平衡,缩短食物链,提高人类消费能力,增加人口数量,直到这个在自然平衡中原本相对稀缺的物种,成为称霸于广大农耕地区的大型物种。
人类同杂草(包括可以称为“杂草”的动物,如象鼻虫、鼠类)的斗争需借助于工具、智力和经验;尽管其过程还了无尽期,却已经为人类带来了一系列胜利。然而,农业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还有另一方面:缩短食物链,增加驯养和种植的动植物的数量,也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更重要的是,由于大部分重要的寄生物都微不可见,长期以来人类仅凭智力无法有效地对付它们的滋扰。
因此,在现代科学和显微镜出现以前,先祖对杂草和敌对的大型掠食者的胜利,尽管成果辉煌,但也遭遇了劲敌。这种微寄生掠食者在农夫成功改造的环境中找到了更多的生存机遇。实际上,一种或少数几种物种引起的超级大侵扰,可谓是生命之网中的自然平衡发生突然的和影响深远的改变的正常反应。杂草往往就是利用灾患对正常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缝隙而生存,在不受干扰的自然植被中,杂草总是稀少和不显眼的,但一旦当地的终极群聚期
 的植被毁坏,它就能够快速地占领因此而产生的空隙。既然很少有物种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就使得仅有的几种杂草在裸露的地表上肆虐开来。然而杂草并不能长久维持这一强劲的势头,复杂的补偿性调节很快就出现了,在缺乏进一步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程度不同的稳定而多样化的植被将重新出现,通常仿佛回到破坏前的样子。
的植被毁坏,它就能够快速地占领因此而产生的空隙。既然很少有物种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就使得仅有的几种杂草在裸露的地表上肆虐开来。然而杂草并不能长久维持这一强劲的势头,复杂的补偿性调节很快就出现了,在缺乏进一步外部干扰的情况下,程度不同的稳定而多样化的植被将重新出现,通常仿佛回到破坏前的样子。
只要人类继续改变自然环境,并使之适合于农业,他们就会阻挠重新建立自然的终极群聚期的生态系统,因此仍会随时遭受杂草泛滥的困扰。
 如前所述,当对付人们可见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时,观察和试验让早期农夫们很快就能将杂草(以及老鼠这样的动物害虫)置于其控制之下,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探讨:在现代医学弄清疾病传染的某些重要途径之前,人们对疾病一筹莫展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前所述,当对付人们可见和可控的大型生物时,观察和试验让早期农夫们很快就能将杂草(以及老鼠这样的动物害虫)置于其控制之下,但几千年来人类的智慧在对付致病微生物上,仍然还停留在摸索阶段,因此,疾病在作物、畜群和人类当中的滋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事务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探讨:在现代医学弄清疾病传染的某些重要途径之前,人们对疾病一筹莫展时,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