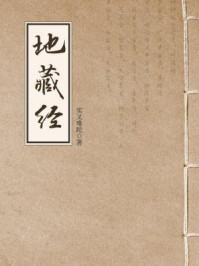西汉初年,天下一统。汉帝国和秦帝国一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维护国家统一成为重大政治课题。任继愈指出,农业小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分散性、家庭血缘关系,都不足直接用来维护国家稳定,国家统一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这时,从经济以外的社会领域寻求治国良方,就是必由之路。秦朝书同文、车同轨政策,就是历史经验。汉代则进而从制度建设、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
 董仲舒所谓“制度”,既包括礼仪制度,也包括礼仪制度的理论基础、精神基础——宗教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董仲舒所谓“制度”,既包括礼仪制度,也包括礼仪制度的理论基础、精神基础——宗教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尊神”,这是精神上的规范建设。尊神适所以尊君,因为神被看成天,而君被认为是天子,即天的儿子。西周以来,祭天就是天子的特权,敬天、“尊神”成为王权的辅助。西汉初年“尊神”的努力,在思想上推动了汉代儒家“天命”观的神学化,在文化上则促进了汉代宗教文化建设。如汉武帝亲临黄帝冢祭拜黄帝,使黄帝崇拜升华为国家进行的各民族共祖崇拜,黄帝被司马迁描述为中华历史的开端、华夏民族的祖先、汉帝国各民族的共祖、华夏文明的创造者等,有意识地借用黄帝,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此外,地方政治制度中,诸侯国被削减,受抑制,郡县制得以加强;人事上,朝廷举贤良,用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上,三纲五常观念得以形成,诸子学演变为经学等——这些无不具有宗教文化建设意义。
二是具体的正朔、服色、爵位、礼仪、道德、法律、考试等制度建设,推动儒学礼法思想礼教化或名教化。
为此,董仲舒以《春秋》褒贬为中心,广泛吸收荀子的礼法思想、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墨子的“天志”思想、法家以君主为中心的赏罚手段、黄老以君主为中心的无为而治思想等,改造孔子、孟子的“天命”论,提出“天人感应”论,努力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根据。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将儒家“天命”观念和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阴阳五行说的宗教化进程。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以研究《公羊春秋传》著名。他对孔子以来的儒学思想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体会。比如,他揭示国家治理之“道”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在他看来,夏、殷、周、秦、汉之间的朝代更替,则从朝代历史方面体现了以“有道伐无道”的“天理”
在他看来,夏、殷、周、秦、汉之间的朝代更替,则从朝代历史方面体现了以“有道伐无道”的“天理”
 。董仲舒的这些论述,是先秦儒家“道统”观在汉代的进一步发展。
。董仲舒的这些论述,是先秦儒家“道统”观在汉代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董仲舒强调儒学道德规范的自我反省功能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他认为,在儒家道德规范中,“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爱主要是对待他人的规范,不宜用来照顾自己;“义”(应该)主要是儒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宜用来要求别人。对待自己要严格,用人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对待他人则要宽厚,给予实在的恩惠。这是很符合儒家思想要旨的。后来的“名教”、礼教,却违背了这一原则,用行政手段,将“义”建设成为国家制度,规范百姓的言行活动,要求民众必须如何如何,有意无意地将规范的对象搞错。依照董仲舒的意思,这根本违背儒家人学精神。
,仁爱主要是对待他人的规范,不宜用来照顾自己;“义”(应该)主要是儒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宜用来要求别人。对待自己要严格,用人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而对待他人则要宽厚,给予实在的恩惠。这是很符合儒家思想要旨的。后来的“名教”、礼教,却违背了这一原则,用行政手段,将“义”建设成为国家制度,规范百姓的言行活动,要求民众必须如何如何,有意无意地将规范的对象搞错。依照董仲舒的意思,这根本违背儒家人学精神。
关于人性修养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仁义与功利的关系,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的观点。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的观点。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董仲舒这样说,贯彻了他“以义正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则。20世纪不少学者批评董仲舒的这个观点,他们批评的出发点都在于以为这个观点是要求他人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董仲舒这样说,贯彻了他“以义正我”,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则。20世纪不少学者批评董仲舒的这个观点,他们批评的出发点都在于以为这个观点是要求他人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关于一个人内在综合修养(“德”)与才能的关系,董仲舒强调“德”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而很有才能,便如“狂而操利兵”“迷而乘良马”“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辞,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
 后来国人形成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人才观,这是正确的。
后来国人形成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人才观,这是正确的。
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朝廷所出的题目里有“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之类的问题。董仲舒在献策里,本着儒家精神,依然强调人的努力。他说:“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此盖受命之符也。”
 在君权来源上,儒家虽然讲天命,但所强调的却是人现实的人性修养、理性努力,以及民意、民心的作用
在君权来源上,儒家虽然讲天命,但所强调的却是人现实的人性修养、理性努力,以及民意、民心的作用
 。董仲舒将民心所向看成是“受命之符”,显示出他并没有完全局限于阴阳五行说的符应观念,依然传承发展了儒家宗教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大儒的风采。
。董仲舒将民心所向看成是“受命之符”,显示出他并没有完全局限于阴阳五行说的符应观念,依然传承发展了儒家宗教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显示出他作为一代大儒的风采。
从儒学发展的历史看,董仲舒这些看法都符合孔、孟儒学精神,十分精当。董仲舒不愧为当时“群儒首”
 。
。
董仲舒应诏进献“天人三策”,最后提到意识形态的统一,他大胆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建议,本来是针对当时朝廷所举贤良的人才任用而言,并没有用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的意思。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只是在朝廷提倡儒学,设立经学博士官职,让他们在朝廷备咨询、在太学讲课等,并没有禁绝百家之学,只是朝廷、太学中不用百家学者罢了。到明清时期出现“文字狱”,就完全异化为专制主义皇权一统学术思想了,这是历史的倒退。
董仲舒的建议,本来是针对当时朝廷所举贤良的人才任用而言,并没有用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的意思。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只是在朝廷提倡儒学,设立经学博士官职,让他们在朝廷备咨询、在太学讲课等,并没有禁绝百家之学,只是朝廷、太学中不用百家学者罢了。到明清时期出现“文字狱”,就完全异化为专制主义皇权一统学术思想了,这是历史的倒退。
《春秋公羊传》是一部解释儒家经典《春秋》的今文经学著作,成书于战国时。公羊春秋派认为,孔子作《春秋》,常用一些关键的字词表示褒贬,这些字词里面暗含有“大义”。《春秋公羊传》是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儒家经典诠释著作。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看,“天人感应”论,是他发挥的“微言大义”之一。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认为,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关系。天主宰着人,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祥瑞和灾异,分别表示上天对人的嘉奖和惩罚;但人的努力可以影响上天对人的赏或罚。他认为,“圣者法天”,五帝三王如能够法天而治,“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
 如果治国者失道背德,“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如果治国者失道背德,“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那么,如果治国者失道背德,会出现哪些“灾异”或“怪异”呢?在董仲舒看来,水灾、旱灾、日食、月蚀、陨石雨、地震、山崩、河雍、彗星、气候异常等,都是“天”给人降下的“灾异”或“怪异”。“天”降下这些“灾异”或“怪异”,根源于政治失德。因为政治失德,导致阴阳不调,五行失序,于是产生“灾异”或“怪异”。这时,君王若能省天谴,畏天威,修身正德,革弊而图治,“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
 改革措施可以有:正纲纪,减刑罚,薄赋敛,赈穷困,举贤良,远小人,兴礼乐等。在他看来,天命并非不可改变,“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他还明确肯定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改革措施可以有:正纲纪,减刑罚,薄赋敛,赈穷困,举贤良,远小人,兴礼乐等。在他看来,天命并非不可改变,“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他还明确肯定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董仲舒改造传统的“天”和人的观念,突出“天”的人格神色彩;同时,强调天命“可得反”,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天命,仍然保存了一部分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
董仲舒改造传统的“天”和人的观念,突出“天”的人格神色彩;同时,强调天命“可得反”,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天命,仍然保存了一部分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明显受到墨子宗教思想的影响。墨子早已明确提出,人“法天”能获得上天奖赏,被“立为天子”,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墨子说: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家室丧灭,绝无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在墨子看来,上天对人不“法天”的惩罚,除了“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家室丧灭,绝无后世,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之外,还要降下自然灾异。墨子说:“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在墨子看来,人法上天,则上天奖赏人,风调雨顺,成为万民之主——天子等,享受富贵荣华;人不法天,则上天惩罚人,自然灾异不断,个人则遭遇贫贱衰败。墨子已经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
在墨子看来,人法上天,则上天奖赏人,风调雨顺,成为万民之主——天子等,享受富贵荣华;人不法天,则上天惩罚人,自然灾异不断,个人则遭遇贫贱衰败。墨子已经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
不过,董仲舒也有和墨子不同之处。法家、黄老为治国者(“王”)出谋划策的精神,在董仲舒那里有综合的表现。董仲舒“天人感应”中的“人”,主要指当权的君主,而可以改变天命的人的努力,则主要指统治天下的帝王的祭天仪式、惠民措施、道德修养等。
董仲舒是有民本思想的。比如,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在天、君、民的关系中,董仲舒强调天“生民”“为民”而“非为王”的因素,强调王位的给予或剥夺,在于君王的德行是否足以“安乐民”。这是有浓郁民本思想色彩的说法。但这只局限在政治哲学层次上,流于一种纯粹的抽象说法。一旦落实为现实“天人感应”中具体的“人”,他就悄悄将“人”限制为当权的君主。
在天、君、民的关系中,董仲舒强调天“生民”“为民”而“非为王”的因素,强调王位的给予或剥夺,在于君王的德行是否足以“安乐民”。这是有浓郁民本思想色彩的说法。但这只局限在政治哲学层次上,流于一种纯粹的抽象说法。一旦落实为现实“天人感应”中具体的“人”,他就悄悄将“人”限制为当权的君主。
他以现实的眼光发现:“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内之心,悬于天子。”
 而“民”,似乎缺乏与“天”交通的能力。按照董仲舒看,“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瞑”,意思是闭眼,眼睛昏花,昏暗,睡眠,比喻没有认识到真理的蒙昧状态。因为没有认识到真理,所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目标、方法、准则、出发点等,都缺乏认识、觉悟,就像一无所知、脑子一片空白的人,只能“守事从上”,“受成性之教于王”,听“王”的话,跟着“王”走。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确实如董仲舒所说,理性认识上处于“瞑”的状态。但也不能说所有的民众都是如此,所有民众都永远如此。
而“民”,似乎缺乏与“天”交通的能力。按照董仲舒看,“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瞑”,意思是闭眼,眼睛昏花,昏暗,睡眠,比喻没有认识到真理的蒙昧状态。因为没有认识到真理,所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目标、方法、准则、出发点等,都缺乏认识、觉悟,就像一无所知、脑子一片空白的人,只能“守事从上”,“受成性之教于王”,听“王”的话,跟着“王”走。缺乏文化修养的人,确实如董仲舒所说,理性认识上处于“瞑”的状态。但也不能说所有的民众都是如此,所有民众都永远如此。
关于民众“瞑”的问题,北宋大儒张载的认识就比董仲舒高明,体现出儒家民本思想在理学时期取得的进步。张载说:“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民众“瞑”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但“私己”的心胸,也有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从人的本性看,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才是人的本性;所以,民众知、情、意、欲等心理大趋向,都完全符合义理。张载赞成孟子“人性善”说,又充分考虑了荀子“人性恶”说的意义,认为“恶”主要根源于“气”在人身上的表现——“气质”。现实的人以自己本性的善为基础,“变化气质”
民众“瞑”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但“私己”的心胸,也有重要影响。尽管如此,从人的本性看,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才是人的本性;所以,民众知、情、意、欲等心理大趋向,都完全符合义理。张载赞成孟子“人性善”说,又充分考虑了荀子“人性恶”说的意义,认为“恶”主要根源于“气”在人身上的表现——“气质”。现实的人以自己本性的善为基础,“变化气质”
 ,即使一般民众也可以修养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张载有精微而正确的人性论,所以对民众“瞑”的问题也能有更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即使一般民众也可以修养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张载有精微而正确的人性论,所以对民众“瞑”的问题也能有更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董仲舒对“民”性的贬斥性描述,和他圣人至善、一般民众可善可恶、恶人至恶的人性三品论有关系。不过,即使如董仲舒说“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民众当然也有“善之质”,怎么能直接称民众为“瞑”呢?董仲舒认为“瞑”是民众的本质特征,这是对人民群众认识把握真理能力的忽视;董仲舒认为民众只有“善之质”,还必须“王”来进行教化,才能“善”,这是对一般民众人性地位的贬低,对国君教化民众地位的拔高。之所以这样贬低民众,瞧不起劳动者,既和当时劳动者文盲众多、文化水平十分低下有关,也和董仲舒不了解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有关。不和劳动群众相结合,即使是科学理论也难以产生实质的现实影响。古代儒学在这方面有众多教训。
也要注意,董仲舒是在应诏中谈论上述问题的,所以,他不得不总是想着“王”,为“王”们打算。他之所以反对孟子“人性善”说,原因之一是,“人性善”说对“王”不利。他自己透露说:“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
 原来,他不赞成人性善说,因为这个理论取消了“王”教化万民的必要性,进而有可能取消“王”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原来,他不赞成人性善说,因为这个理论取消了“王”教化万民的必要性,进而有可能取消“王”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天人关系,就被董仲舒独断地约化为重点讨论天和天子的关系了。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结论自然是,民命完全被君命所决定。从这一说法的影响看,董仲舒对天人关系进行的独断性约化,在教育上,有可能逐渐剥夺普通百姓自我学习提高、自我教化的权利;在宗教上,则有可能剥夺普通百姓与神交通的权利。结果,只能是从思想上帮助专制君主完全垄断人的教育权和人与神交通的宗教权,使儒学异化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
结论自然是,民命完全被君命所决定。从这一说法的影响看,董仲舒对天人关系进行的独断性约化,在教育上,有可能逐渐剥夺普通百姓自我学习提高、自我教化的权利;在宗教上,则有可能剥夺普通百姓与神交通的权利。结果,只能是从思想上帮助专制君主完全垄断人的教育权和人与神交通的宗教权,使儒学异化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将专制君主硬塞进天与人的联系中去,既作为与上天联系的“人”的代表,又作为与人联系的“天”或“神”的代表,给皇权赋予了神圣性。董仲舒的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为专制君主服务的色彩。如果说这是一种神学思想,那也只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神学。当然,也要注意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还有他特别的主观目的,即希望用宗教思想制约专制君主的恣意妄为,限制皇权的任性泛滥。但他在理论上将“人”约化为天子,事实上在努力证明君主专制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着君主的专制独裁。不管怎么说,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中的人文因素,较之先秦孔、孟等儒家的宗教思想而言,减少了很多。东汉时期出现的《白虎通》,沿着董仲舒的这一思路,用天神崇拜、阴阳五行学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神圣与合理,以官方经学的形式,将董仲舒赋予给专制君主的宗教权进一步法典化了。
董仲舒独断地认为,“天”不仅是“群物之祖”
 ,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而且还是“百神之大君”
,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而且还是“百神之大君”
 ,是世界的最高主宰。更重要的是,“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明确讲“天”是皇权的根据和根源。这种君权神授论,为君权的存在提供了宗教思想的根据。董仲舒这样讲,也有他自己的主观意图,他学习墨子,也希望利用天神的至高无上权威,抑制君权的无限性,要求君主“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
,是世界的最高主宰。更重要的是,“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明确讲“天”是皇权的根据和根源。这种君权神授论,为君权的存在提供了宗教思想的根据。董仲舒这样讲,也有他自己的主观意图,他学习墨子,也希望利用天神的至高无上权威,抑制君权的无限性,要求君主“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
 。他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他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墨子曾经主张利用宗教权威来治理国家,将“天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仪”,他认为,国家动乱,天下瓦解的根源,在于人们“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墨子曾经主张利用宗教权威来治理国家,将“天志”作为治理国家的“法仪”,他认为,国家动乱,天下瓦解的根源,在于人们“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利用宗教思想帮助处理政治问题,董仲舒的思路和墨子相近。不过,从实践效果和后来的历史看,专制君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根本制约。贤明君王会敬天畏天,大部分庸碌君王依然无所不为。仅仅依靠信仰和思想文化约束权力,而缺乏现实的制度、组织、权力等制衡的帮助,权力制约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所以,董仲舒苦心孤诣提出用天命制约皇权的设想,在思想上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天下仍然治世少而乱世多,君主专制独裁长期延续,反而愈演愈烈,说明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留下了历史经验,也有历史教训。
利用宗教思想帮助处理政治问题,董仲舒的思路和墨子相近。不过,从实践效果和后来的历史看,专制君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根本制约。贤明君王会敬天畏天,大部分庸碌君王依然无所不为。仅仅依靠信仰和思想文化约束权力,而缺乏现实的制度、组织、权力等制衡的帮助,权力制约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所以,董仲舒苦心孤诣提出用天命制约皇权的设想,在思想上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天下仍然治世少而乱世多,君主专制独裁长期延续,反而愈演愈烈,说明他美好的政治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留下了历史经验,也有历史教训。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根据之一,是“人副天数”原理。这种原理认为,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人的身体、生理、心理、精神、道德等都来源于天,与天类似。他发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情,春、秋、冬、夏之类也。”
 这种“化”具体指什么呢?董仲舒断定,天与人的中间环节是阴阳五行的变化,意思是说,天意要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表现出来。天有四时(春夏秋冬),王有四政(庆赏罚刑),人有四肢;天有五行,政有“五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人有五德(仁义礼智信),身有五脏;天有阴阳,而且“阳尊阴卑”,“贵阳而贱阴”
这种“化”具体指什么呢?董仲舒断定,天与人的中间环节是阴阳五行的变化,意思是说,天意要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表现出来。天有四时(春夏秋冬),王有四政(庆赏罚刑),人有四肢;天有五行,政有“五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人有五德(仁义礼智信),身有五脏;天有阴阳,而且“阳尊阴卑”,“贵阳而贱阴”
 ,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妇,而且君、父、夫为阳,为尊贵,臣、子、妇为阴,为卑贱。希望在天和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寻求两者间的联系,进而探寻世界的本原——道,再从道出发,全面而深刻理解人的社会政治活动,这表现了董仲舒高人一筹的哲学视野和眼光,应该肯定。但用今天的科学眼光看这些说法,可以发现它们几乎全是主观想象的比附。这种比附的进一步泛滥,就是东汉时期十分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潮。这说明,探讨世界本源问题,仅仅凭借日常生产生活经验,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不仅远远不够,而且还会闹笑话。
,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妇,而且君、父、夫为阳,为尊贵,臣、子、妇为阴,为卑贱。希望在天和人、自然和社会之间寻求两者间的联系,进而探寻世界的本原——道,再从道出发,全面而深刻理解人的社会政治活动,这表现了董仲舒高人一筹的哲学视野和眼光,应该肯定。但用今天的科学眼光看这些说法,可以发现它们几乎全是主观想象的比附。这种比附的进一步泛滥,就是东汉时期十分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潮。这说明,探讨世界本源问题,仅仅凭借日常生产生活经验,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不仅远远不够,而且还会闹笑话。
董仲舒通过这些比附,将阴阳五行说和“天”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阴阳五行说的宗教化由此定型。将“阴阳五行”硬塞进天与人的联系中去,作为“天意”在现实世界的形式化标志,使董仲舒的宗教思想带有强烈的自然宗教色彩。另一方面,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运用直观到的自然规律或联系来解释国家政治历史,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则进一步断定它是自然与人类所共有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天和人的“感应”关系,为国家、社会的政治稳定寻找自然理论根据,使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这一努力,超越关心个人生死祸福的层次,上升为对国家、社会历史命运的关注,也值得肯定。
1.阴阳五行说的局限性在哪里?依据阴阳五行说的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如何理解?
2.董仲舒将儒家的“天”人格化,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