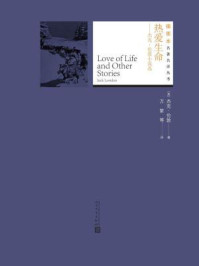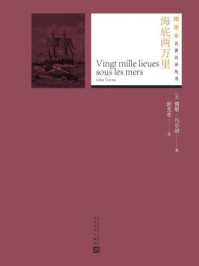这是一个跳蚤市场的入口。不收费。免费入场。懒散的人群。狡黠、闹腾。为什么进去?你指望看到什么?我正在看。我在查看世上有些什么。留下了什么。丢弃了什么。什么不再受到珍爱。什么东西不得不亏本出售。某人原以为什么也许能让另外某个人感兴趣。但它是垃圾。就算那里——这地方——有,它也已经筛选过了。但那里边或许有某件有价值的东西。未必是有价值。不过是我想要的某样东西。想抢救的。引起我注意的东西。打动我的东西。打动,提及。啊……
为什么进去?你有那么多闲工夫吗?你会看。你会迷路。你会忘记时间。你以为你有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花的时间总比你以为的多。然后你就会迟了。你会生自己的气。你会想留下。你会受到诱惑。你会心生不快。物品肮脏不堪。有的破裂了。胡乱修补一番或根本没修。它们会对我讲述我无需知道的一个个激情故事,种种奇思妙想。需要。啊,不。我根本不需要听这个。有些东西我会深情地看一眼。有些我肯定得拿起来,抚弄。此时会受到卖主很内行的注视。我不是小偷。很可能,我也不是个买主。
为什么进去?只是玩玩。一种识别的游戏。去了解它是什么,了解它以前是什么价,应该是什么价,以后又会是什么价。但可能不去出价、讨价还价,不去买下。只是看看。只是逛逛。我现在感觉轻松愉快。我没什么心事要想。
为什么进去?像这种地方多得很。一块地,一个广场,一条有顶篷罩着的街道,一个军械库,一个停车场,一个码头。任何地方都可以有跳蚤市场,只不过它正好在这里。任何地方都充斥着这种地方。但这里的这个我要进去。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曼哈顿,我穿着牛仔裤、丝绸衬衫,脚上是网球鞋。对纯粹的可能性的一次丢脸的体验。这个人有影星明信片,那个人的盘子里是纳瓦霍人戒指,这个人衣架上挂着二战的短夹克,那个人有刀具。他的汽车模型,她的雕花玻璃器皿,他的藤椅,她的大礼帽,他的罗马钱币,还有那边……一块宝石,一件珍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我能看到它,我可能想要它。我可能会买下作为礼物,是的,送给其他人。至少,我就会知道它存在过,出现在这儿。
为什么进去?难道已经有足够的了吗?我可能看出它不在这里。不管它是什么,我每每不能肯定,我都会把它放回到桌子上。欲望驱使着我。我告诉自己我所想听到的。是的,有足够的了。
我走进去。
·
一场绘画作品拍卖会结束了。一七七二年秋,伦敦。置于凸金叶框内的这件作品靠在大厅前面附近的墙上,这幅画名为《拿起丘比特之箭的维纳斯》,被认为是柯勒乔
 的作品,对此,画的拥有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未售出。误认为是柯勒乔的作品
的作品,对此,画的拥有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未售出。误认为是柯勒乔的作品
 。房间的人渐渐散去。一个四十二岁、面部轮廓分明的高个男子(在那个时代他称得上是高个子了)缓慢地走上前来,身后不远处恭恭敬敬地跟着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长相酷肖一家人的年轻人。他们俩都是瘦削的身材,苍白的肤色,一脸冷峻的贵族表情。
。房间的人渐渐散去。一个四十二岁、面部轮廓分明的高个男子(在那个时代他称得上是高个子了)缓慢地走上前来,身后不远处恭恭敬敬地跟着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长相酷肖一家人的年轻人。他们俩都是瘦削的身材,苍白的肤色,一脸冷峻的贵族表情。
我的维纳斯,年长的男子说。我当初就相信它会出手的。很多人感兴趣。
但是,唉,年轻的男子感叹了一句。
难以理解,年长男子思忖,这幅画的杰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真的迷惑不解。年轻男子在倾听,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与她分手我很悲痛,所以,我想它没有卖出去,我倒也应该很高兴,年长的男子继续说。但是,需要卖出,况且,我认为我的要价并不太高。
他盯视他的维纳斯。最困难的,年长的男子继续说,现在,他所指的不是难以理解画为什么没有卖出去(也不是指阻止债主们向他逼债的艰难),而是指做出卖画的决定;因为我把这幅画当宝贝,他说道。当时,我知道我应该卖了它,所以,我就让自己准备好舍弃它;现在,没有人肯出我明白它所值的价,于是它还是我的,应该一如既往地爱它,可是不会了,我打赌。为了把它卖了已经不再爱它,我现在无法同样地喜爱它了,但是,如果我卖不掉,我的确希望再爱它。假如因为这次运气不佳就觉得它的美受到了损毁,那我就显得小气了。
怎么办?爱它几分?他思忖。现在怎么爱它。
我倒觉得,爵士,年轻男子说,惟一的问题是把它存放在哪里。肯定会找到一个买主的。你是否允许我替你在你也许不认识、而我熟悉的收藏者当中试着找找?你离开后,我会很高兴慎重地探查一番的。
行,该走了,年长的男子说。
他们走了出去。
·
这是火山口。是的,口;以及熔岩舌。一个身体,一个可怕的活体,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身体。它喷,它射。它也是个山体内部,一个深渊。某个活着的东西,可能会死。是个时不时会被激活的惰性物。只是间歇性存在。一个永恒的威胁。如果可以预测,通常也未被预测到。反复无常,桀骜不驯,臭气熏天。所谓原始是不是就这意思?内华达德鲁兹火山,圣海伦斯火山,苏弗雷火山,培雷火山,克拉卡托火山,坦博拉火山。会从休眠状态醒过来的庞然大物。将注意力转向你的那个行动笨拙的庞然大物。金刚。喷吐,吞噬一切,然后又沉入昏睡之中。
我?可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碰巧在那里,陷在自己乡村日常事务中一筹莫展。我该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啊,我就在这里出生的,那个皮肤黝黑的村民悲叹。人总得住在什么地方吧。
当然,我们可以视之为一场壮观的烟火秀。这完全是个方法问题。一个足够远的景观。有些迷人的美景只适合远距离观赏,约翰逊博士说;没有什么景致比熊熊火焰更炫丽了。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这是绝顶的景致,既激动人心,又给人教益。在某某爵士的别墅里用完茶点后,我们走上架好了几台望远镜的露台,去观看。白烟袅袅,轰隆隆的声音常被比作远处急促的定音鼓声:序曲。接着,场面宏大的演出开始,缕缕白烟变红、弥漫开来,升腾而上,一根灰柱越爬越高,直到在平流层的压力下朝水平方向弥漫开(运气好的话,我们会看到一股股橙色和红色的熔岩沿斜坡开始流下)——这样持续数小时、数天。然后,渐慢渐弱,它平息下去。但是,上面靠近之处,里边惊心动魄。这喧嚣声,这令人窒息的喧嚣声,是你永远都无法想象,无法消受的东西。不断发出的密集、巨雷般的声音,仿佛音量一直在增大,但又不可能比已经达到的音量更大;一种响彻云霄、震耳欲聋、令人作呕的吼声让你的骨髓都要冒出来,令你魂飞魄散。即使自认为是目击者的那些人,也无法逃避向他们阵阵袭来的厌恶和恐惧的感觉;这些你以前从未感受过。在山下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可以冒险前往——从远处看似激流的东西是一片不断奔涌而来的黏黏的黑色、红色岩浆,是一堵堵向前推进的墙,它们刚刚还竖立着,可转眼间便令人战栗地轰然倒下,投进前面喷涌的熔液之中;冲进、吸入、吞噬、彻底冲散房屋、汽车、货车、树木,一个又一个。所以,这是不可阻挡的。
当心。用一块布捂住你的嘴。闪开!观看一座温和、如期喷发的活火山的夜间喷发是一次了不起的游览。我们跋涉而上,到了火山锥一侧上面时,就站到火山口的唇缘(是的,是唇缘),往下窥视,等待着最里面燃烧着的内核炫耀自己。它就是如此,每隔十二分钟一次。别太靠近!它这就开始啦。我们听见一名最低音歌手发出欢乐的咯咯声,灰色火山岩渣的外壳开始发出光热。巨人要呼气了。令人窒息的硫磺的臭味几乎难以忍受。熔岩淤积起来,但没有漫溢。炽热的岩石和熔渣飞飘上来,不是很高。这种危险,尚不太危险时,极其迷人。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时,那不勒斯。别墅里那座英国大摆钟的指针又一次在致命的时刻停下。又一次?它已经安静了这么长时间了。
像激情,它就是激情的象征,它也会死。大体上现在已经清楚,被视为一种疗法的缓解何时应该开始,但是,专家们犹豫不决,不敢轻易宣称一座长期不活动的火山是死火山。哈莱阿卡拉火山上次喷发是一七九○年,现在,官方仍将其归为休眠火山。平静是因为嗜睡?抑或是因为死了?几乎和死了一样——如果它没有死。火龙吞噬了它一路经过的一切,将成为黑石巨流。树木永远都不会在这里生长,永远不会。山成为它自己暴虐的墓地:火山造成的废墟也包括其自己在内。每次维苏威火山喷发,山巅就会削去一大块。它变得不那么巍峨,变小了,也更荒凉。
庞培被埋在大量落下的灰烬下面,赫库兰尼姆则被埋在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顺着山坡冲下的泥流之下。但是,熔岩吞噬一条街的速度很慢,一小时才几码远,每个人都来得及逃开。我们也有时间抢出我们的物品,一些物品。带有神像的祭坛?没吃完的鸡肉?孩子们的玩具?我的新上衣?所有手工制品?计算机?坛坛罐罐?手稿?母牛?我们需要重新开始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不信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它往那边去了。看。
你要走吗?我准备留下来。除非它到……那里。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它过去了。
他们逃跑。他们悲悼。直到悲痛也变得坚硬如石,于是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对这种彻底的毁灭望而生畏,凝视着那块肥沃的土地,地下,他们的世界成了坟墓。他们脚下的灰烬,仍然温热,但不再烤焦他们的鞋子。它进一步冷却。种种犹豫不决不见了。公元七十九年后不久——当时他们的这座香气充溢的山上爬满了藤蔓,山顶浓荫覆盖,正是在这里,斯巴达克斯和数以千计加入他的奴隶设法躲过那些追赶他们的古罗马军团,这座山第一次呈现为一座火山——大多数幸存者开始重建家园,重新开始生活;就在那里。现在,他们的山顶上有个丑陋的洞。树林也焚烧得精光。但是,它们也还会重新生长。
一种灾难观。这已经发生。谁会料到这种事情。绝不会,绝不会。没人会。这是最糟的。如果是最糟的,那么也就是惟一的。这意味着是不可重复的。我们把它抛到身后吧。我们别当灾难预言者吧。
另一种观点。现在看是惟一的: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你会看到的。就等着瞧吧。可以肯定,你也许得等好长时间。
我们回来。我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