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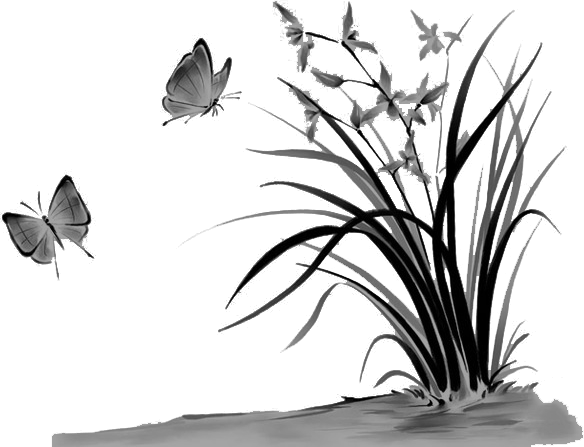
西汉王朝元、成、哀、平日趋衰落,自汉武帝以来如日中天的今文经学也随着西汉的衰落而日趋衰落。
今文经学之所以日趋衰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迷信,二是烦琐。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等以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糅合的今文经学、独尊儒术,盛言天人感应的儒生很多是齐人,齐地是邹衍阴阳五行说泛滥之地,也是方士宣传神奇怪力的发源处,《齐诗》和《春秋公羊传》都来自齐人,在西汉也时有发挥,又由于《齐诗》《春秋公羊传》中多“微言”,易于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随意阐释,从而杂有不少“怪异”之论。如翼奉传《齐诗》,用阴阳灾异比附解释,对《齐诗》五际说是“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以阴阳变化为政治变化的征兆。
。以阴阳变化为政治变化的征兆。
然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虽曾得售于一时,但不能得售于永久,因为它毕竟是迷信的假托,而没有科学的依据。从而,当阴阳五行说带来困惑时,今文经学家又宣扬起谶纬。
“谶纬”,经常联称在一起,事实上它并不是一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案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有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议,非其实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是正确的;以谶为“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以纬为“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也有见地。
当社会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人民对自然缺乏预测以至征服能力之时,迷信落后是必然现象。“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随之而起。因此,“谶”早于“纬”,来源应很久远,而每逢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发生之际,“预决吉凶”的“谶”也随之而作。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上自有贡献,但他横征暴敛,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些六国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有反击发生,还蒙上宗教神学的外衣。《史记·项羽本纪》:“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是“谶”。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论衡·实知》篇:“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云:‘亡秦者胡也。’”由上可知,《录图书》即河洛谶纬一类之书。
《论衡·实知》篇:“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云:‘亡秦者胡也。’”由上可知,《录图书》即河洛谶纬一类之书。
《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夜过华阴,有“今年祖龙死”谶语。
从上述《史记》所载,这些谶语都是对秦统治的不满,对当时的反秦斗争也起过影响。刘邦反秦时,也曾有斩蛇的传说,《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此而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四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
这就是所谓“高祖斩蛇”的故事,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对刘邦加以神化。
但是,刘邦只是“亭长”,出身也较低下,于是又鼓吹“”刘为尧后的传说,说什么:
尧之长子监明早死,不得立,监明之子封于刘。朱又不肖而弗获嗣。
 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
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

在《诗纬》和《春秋纬》中也有记载:
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

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执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王。

把刘邦说成唐尧之后。刘季的姓名又见于图谶,那么,刘邦之为天子,也是天意所归了。
由上可知,“谶”早于“纬”,“谶”“纬”并非一类。“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经过传播、演变,并借用“经义”,写成文字,演而为“纬”。“谶”“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经的地位也就日深。经是“圣经”,只能解释,不能更改,而“纬”却可任意发挥,并加编造。
本来,汉武帝以前,已有谶语,但还只是片言只语,尚未成书。所以申公说:“受黄帝言,无书。”
 武帝以后,随着儒家的“独尊”,谶纬也就随之泛滥。他们不但对汉的称帝加以刻划,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话。
武帝以后,随着儒家的“独尊”,谶纬也就随之泛滥。他们不但对汉的称帝加以刻划,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制造了不少神话。
《纬书》把孔子说是“黑帝”之子,是殷朝的子孙。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龙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以孔子之父叔梁纥、母颜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而生孔子。这样,孔子就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黑龙”所生的神,他不但出生与一般人不同,容貌也与一般人不同:
孔子长六尺,大九围,坐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甚至说:孔子是海口、牛唇、舌七重、虎掌、龟背、辅喉、骈齿
 。这种形状,与众不同,为人类所无。纬书如此刻划,无非是说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孔子所修订的经书,也就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如《诗》为“天地之心”,《书》为“上天垂文象”,《礼》则“日月为明,上下和洽”,《易》则“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至于《春秋》,经过孔子笔削,更是含有“微言大义”了。
。这种形状,与众不同,为人类所无。纬书如此刻划,无非是说孔子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神”,是教主。孔子所修订的经书,也就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有着深刻的含义。如《诗》为“天地之心”,《书》为“上天垂文象”,《礼》则“日月为明,上下和洽”,《易》则“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至于《春秋》,经过孔子笔削,更是含有“微言大义”了。
“经”是经过“法定”的,只可解释,不可增损,是不能修改的,而“纬”却可自行编造,任意发挥。尽管“纬书”中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天文、历史和地理知识,又保存有很多古代的神话传说,但大部分充满神学迷信,因为它是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之书,而且它是随着儒家经学的“独尊”而愈益发展,谶纬流行,迷信充斥的。
董仲舒开始把《周易》的阴阳学和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混合,把经学灾异附会到《春秋》上,比附社会关系,鼓吹“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宣扬“三纲”,视为“天意”。夏侯始昌又以阴阳五行灾异解释《尚书》,翼奉以阴阳灾异比附《齐诗》,发挥“五际”;戴德、戴圣传《礼》,源自后苍,而后苍又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曾宣扬一时。然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西汉政府的日益腐败,给阴阳灾异说带来困惑,从而今文经学家转而宣扬谶纬迷信了。
。宣扬“三纲”,视为“天意”。夏侯始昌又以阴阳五行灾异解释《尚书》,翼奉以阴阳灾异比附《齐诗》,发挥“五际”;戴德、戴圣传《礼》,源自后苍,而后苍又是夏侯始昌的弟子。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曾宣扬一时。然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西汉政府的日益腐败,给阴阳灾异说带来困惑,从而今文经学家转而宣扬谶纬迷信了。
如上所述,经是不可增损的,纬却可任意造作;经是经过“法定”的“天书”,纬就把儒经神秘化。如说:《易》为“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期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尚书》,“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书者如也,如天行也”
。《尚书》,“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书者如也,如天行也”
 。《诗》则“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诗》则“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礼》则“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
。《礼》则“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
 。《春秋》为孔子笔削,更不同一般书籍,“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春秋》为孔子笔削,更不同一般书籍,“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把经书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经学信用谶纬,经学失去了学术和理论上的价值,堕入灾异考符的宗教神学。
。把经书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经学信用谶纬,经学失去了学术和理论上的价值,堕入灾异考符的宗教神学。
今文经学日趋衰落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烦琐。
西汉经学传授,重“师法”。某一经的大师,被立为博士后,他的经说便叫“师法”。《汉书·胡母生传》:“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即指嬴公能传其师景公时博士胡母生的《公羊春秋》。师之所传,不能出入,只能尊从师说,不能怀疑,只能就师法化解,不能别出新意,只能就师说疏解,不能自行发挥,这样不但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并且愈释愈细,愈演愈碎,愈来愈烦琐。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恭,据记载:
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

颜师古注曰:
言小夏侯本所说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万言也。
桓谭《新论》也说:
秦近〔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

四个字的经书,解释了三万字,全书“增师法至百万言”,分文析字,烦琐不堪。
经学的烦琐,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尽管他带有政治目的而写这篇“移让”,但上述数语,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班固也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确成为“学者之患”
 。他们把经书说成永恒不变,绝对正确,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从,不能独立发挥,势必束缚思想,锢蔽学术。
。他们把经书说成永恒不变,绝对正确,只能疏解,不能自出新意,只能本本是从,不能独立发挥,势必束缚思想,锢蔽学术。
迷信、烦琐,是今文经学衰落的主要原因。今文经学在盛行一时之后,走向保守、没落,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正当今文经学如日中天之时,据说已有古文经书发现,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馀扩建宫殿坏孔子旧宅,在宅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文”经书,《汉书·艺文志》说:
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编,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汉书·景十三王传》也说: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同为景帝之子的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又得到“《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汉书·景十三王传》说: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如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这些古文经传的发现,在汉代以至清代虽引起不少的怀疑,但在西汉逐步传播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却是事实。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
 ,古书纷纷出现。等到他的儿子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争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也就必然引起古文经学争取政治地位、今文经学保持原有政治地位的斗争。
,古书纷纷出现。等到他的儿子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争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也就必然引起古文经学争取政治地位、今文经学保持原有政治地位的斗争。
今文经学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落而消替,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却逐渐兴起。
古文经学的由民间流传到宫廷争立,始于刘歆。
哀帝建平时,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残缺,说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多十六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礼经》(《仪礼》)十七篇多三十九篇。说是有的古文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简,如用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知脱去“无咎”“悔亡”;用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今文《尚书》,知《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说是或者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左氏春秋》较《公羊》《穀梁》“信而有征”云云。当时“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激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是今古文的第一次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刘歆虽得到哀帝的支持
 ,却遭到大司空师丹等猛烈的反对,斥为“改乱旧章”,迫使刘歆请求改放外任。
,却遭到大司空师丹等猛烈的反对,斥为“改乱旧章”,迫使刘歆请求改放外任。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哀帝崩于未央宫。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大权落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重用刘歆。刘歆没有忘怀古文经学的提倡,王莽也想从古文经书中找些“改制”的依附,这样,古文经学又重起波澜,并逐渐代替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除了由于今文经学的本身弱点外,还得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加以探析。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的无限制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外戚、宗室、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为代表的上层豪强,和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等政治上势力较弱的人为代表的下层豪强,在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时,虽然存在着矛盾,但谁也不肯对农民让步;并在破坏中央集权时,起着一致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为了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他们纷纷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河南禹县)有铁官徒申屠圣等起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四川梓潼)有郑躬等起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又有山阳(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起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寿。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连京城长安的秩序都很难维持了。
。连京城长安的秩序都很难维持了。
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使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不能不感到严重的不安,有人甚至对刘家的统治也感到绝望。王莽的改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成帝的生母。他的叔伯曾先后在元帝、成帝时期担任过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凡九侯、五大司马”,朝廷大权几乎全部归王家掌管。“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得到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好感。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为太傅,号“安汉公”。四年,自号“宰衡”。五年,弑平帝,“居摄践祚”。六年,称摄皇帝。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新”。
。得到统治阶级中不少人的好感。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位。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为太傅,号“安汉公”。四年,自号“宰衡”。五年,弑平帝,“居摄践祚”。六年,称摄皇帝。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新”。
王莽建立起新朝,企图先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下令变法,颁布“王田”“私属”两个解决办法。前者将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后者规定民间奴隶改称为“私属”,也不得买卖。他的真实企图是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借以停止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但强迫停止的结果,却加速了社会的混乱,农民进行起义,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便取消了“王田”“私属”的禁令。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筦”法,企图限制商贾的兼并,分享商贾的利益,把持工商业,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小工商生产受到扰害,进行反抗;被打击的商贾和高利贷者也反对王莽。
“改制”的失败,农民起义的遍及全国,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和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离开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起义军的攻击下,欺骗性的政治改革彻底地失败了。
这里不拟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和实质进行详细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曾依附儒家经籍作为“托古改制”的假托;他很明显地利用经书,作为夺取西汉政权和改制的工具。
王莽是怎样利用经书作为他改制的工具的呢?
第一,王莽对《周礼》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6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 规定男子不满八口的人家,如果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就要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原来没有田地的人,便按照制度,一夫一妻授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汉书·王莽传》载:“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按:《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经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这说明王莽是曾援用《周礼》作为企图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基本问题的依据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方面因为“托名”《周礼》是周公所作,“周公摄政”可作为他夺取西汉政权的借口。《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所谓“制礼作乐”,既可认为“制”的便是“《周礼》”,而《周礼》又可作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假托
 。“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
。“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礼》中有很多典章制度可以作为他“改制”的借鉴。同时,在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一些人存在着复古思想,“托古改制”可以迎合一些人的复古心理。王莽特别重视《周礼》,并为之置立博士,并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礼》中有很多典章制度可以作为他“改制”的借鉴。同时,在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一些人存在着复古思想,“托古改制”可以迎合一些人的复古心理。王莽特别重视《周礼》,并为之置立博士,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王莽的援用《周礼》,固然是企图利用《周礼》,进行托古改制,符合其进行欺骗性改革的需要。 但《周礼》毕竟是王莽以前的东西,其中不尽适用于当时,因而王莽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照单全收”。甚至在其他儒家书籍中对他有利而与《周礼》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有时虽仍托名于“周”,其实并不源于《周礼》。最明显的,如“五等爵”问题。《汉书·王莽传》载:“(居摄三年)莽乃上奏曰:‘明堂之室,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又下书曰:“州从《禹贡》有九,爵从周氏有五……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
康有为曾说他本于《周礼》
 。但是,《周礼》所谓“封地五等”,却是:“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但是,《周礼》所谓“封地五等”,却是:“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
“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
 同样是封地五等,却没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记载,而是爵三等,地五等;以公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同样是封地五等,却没有周爵五等、地四等的记载,而是爵三等,地五等;以公为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莽“改制”的封地四等,不同于《周礼》,却大体同于《王制》:“公侯四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除掉“侯”和“附庸”稍有歧异外,与《王制》大体相同(与《孟子》也大体相同
除掉“侯”和“附庸”稍有歧异外,与《王制》大体相同(与《孟子》也大体相同
 。其他王莽的设施和《周礼》原文出入的还有不少,现不多举
。其他王莽的设施和《周礼》原文出入的还有不少,现不多举
 。
。
第三,王莽除了推重《周礼》外,对其他古文经传也是提倡的。
如古文《尚书》、《左传》、《逸礼》。他的提倡,也是因为这些经传中有着利于他夺取西汉政权的佐证。如他引《逸书·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接着说:“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援古即以证今。又如《左传》有“明文”,“明刘氏为尧后者”
 ,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第四,王莽的提倡古文经学,相对地压抑了今文经学,但并不意味他排斥今文经学。
对今文经典中认为有利的东西,也予汲取;今文经说中认为可取的地方,也要利用。西汉哀、平年间,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家是相信谶纬、用以解释灾异祥瑞、进行迷信宣传的。王莽就大加提倡,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封“宰衡”后,引《穀梁传》说:“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为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
 援引《穀梁》,刻授“宰衡”印章,以“通于四海”。翟义反对时,莽“抱孺子,告祷郊庙,仿《大诰》作策,而讨翟义”。居摄二年冬,又引《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臣莽敢不采用。”
援引《穀梁》,刻授“宰衡”印章,以“通于四海”。翟义反对时,莽“抱孺子,告祷郊庙,仿《大诰》作策,而讨翟义”。居摄二年冬,又引《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臣莽敢不采用。”
 《穀梁传》的今古文问题,虽还没有定论,但《大诰》《康诰》却都是今文《尚书》。上引的爵五等、封四等的“改制”与《王制》基本相同
《穀梁传》的今古文问题,虽还没有定论,但《大诰》《康诰》却都是今文《尚书》。上引的爵五等、封四等的“改制”与《王制》基本相同
 ,而《王制》又是今文学家用以诋击《周礼》、诋击古文的重要文献
,而《王制》又是今文学家用以诋击《周礼》、诋击古文的重要文献
 。由此,可知王莽尽管尊重《周礼》,但对其他西汉过去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且曾汲取。
。由此,可知王莽尽管尊重《周礼》,但对其他西汉过去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且曾汲取。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就要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势力。《汉书·王莽传》载:“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在这“千数”人中,应该有通古文经的人员在内。据《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徐敖……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徐)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但是,西汉立为“博士”的今文学家,对王莽政权没有危害的,他也不排斥。《汉书·儒林传》载:“(梁丘贺)……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欧阳生……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馀……地馀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世有欧氏学。”“(许商,传大夏侯《尚书》)……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家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章为王莽所诛。”“(冯宾,传小夏侯《尚书》)……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这些传今文经的今文经师,有的任讲学大夫,有的甚至位至“九卿”。一方面说明他们是拥护王莽的统治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莽也未将今文学家一概屏斥。
那么,王莽是否也曾屏斥今文学家呢?有的,上述吴章为王莽所诛,就是一个例子。又如传施氏《易》及《礼》的刘昆及其家属也曾为王莽所“系”。吴章为什么被王莽所诛,《汉书》没有明文可证,但“徒众尤盛”,应该是有着不利于王莽统治的言论而被诛的。刘昆的被系,则是“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
 又因他姓的是“刘”,遂致处罚。所以这些传今文的人为王莽所屏除,不足以说明王莽绝对排斥今文。相反的,古文经师中如果不满王莽,也不能幸免。《汉书·儒林传》载:“高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由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直)皆未尝立于学官。”传古文的高康,反被诛夷,说明王莽对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并不是因他传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主要看他的政治倾向而加以赏罚的。
又因他姓的是“刘”,遂致处罚。所以这些传今文的人为王莽所屏除,不足以说明王莽绝对排斥今文。相反的,古文经师中如果不满王莽,也不能幸免。《汉书·儒林传》载:“高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侯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由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直)皆未尝立于学官。”传古文的高康,反被诛夷,说明王莽对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并不是因他传授今文或古文而黜陟,而是主要看他的政治倾向而加以赏罚的。
应该说,在王莽统治时,有些今文学家,并不因保持禄位而取媚王莽,对王莽的统治表示不满。“(王良)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称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蔡茂)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除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蔡茂)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除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此外,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王莽时“避去”者,有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诩,传《鲁诗》《论语》的包咸。但是,也有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孔子建并对本来“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恋,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
此外,根据《后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王莽时“避去”者,有传孟氏《易》的洼丹,传欧阳《尚书》的牟长,传《鲁诗》的高诩,传《鲁诗》《论语》的包咸。但是,也有世传古文《尚书》、《毛诗》的孔子建。孔子建并对本来“友善”而仕王莽的崔篆表示:“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恋,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
 又如桓谭“莽时为掌乐大夫”,当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
又如桓谭“莽时为掌乐大夫”,当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
 。可知王莽尽管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的势力,并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可知王莽尽管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的势力,并在经学上对古文经学让步,但古文经学家也并不完全是“新臣”。
如上所述,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王莽拉拢一些治古文经的人,但对并不妨碍其统治的今文经师也仍保持其禄位。总之,他以“经典”作为其政治欺骗的工具,从而“取其所需”,并“托古改制”,企图解决土地的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的大量转化为奴隶,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在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的各部分势力,从而达到夺取西汉政权并巩固王氏政权的目的。“经学”只是他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的封建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曾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经学,作为维护或夺取政权的依据。西汉的封建政府利用过它;王莽改制也利用过它。但是过去很多学者为古文、今文的藩篱所囿,遂致不能透视各不同历史时期中经学的实质。
——原载《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