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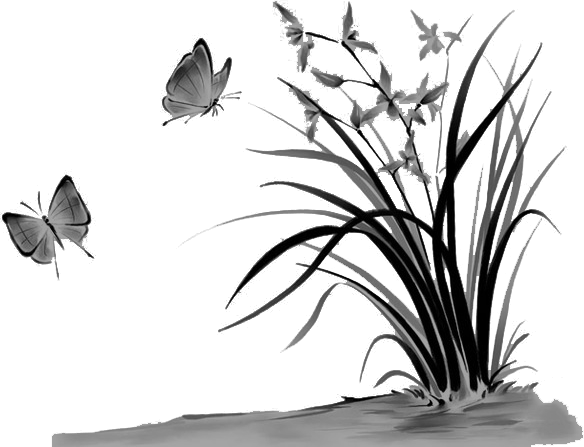

《四库全书》的经部、子部,搜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经学和儒家典籍。近年对这类经、史,时有新的结集。本文准备就接触到的清季、民初结集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清季、民初结集的来源,较古代人物结集有两点不同:一是手稿的存留,一是报刊的登载。
清季、民初人物,距离现在较近,他们的手稿尚有存留,这些手稿,有的没有收入别人为他编辑或他自己所编的丛书,原因是由于作者后来思想发生变化,对早先之作,“既而弃之”。
康有为的《教学通议》过去未见刊布,只是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二十九岁”中有这样的记载:“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自称有《教学通议》之作,但后来“弃之”。查康有为早年“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尔雅》《说文》”等古文经籍和解经之书,至于今文经学的主要著作《公羊传》,则“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知他早年信奉《周礼》等古文经籍,对今文《公羊传》的何休注,却曾“纠缪”。那么,康有为早年是信古文、崇周公,而对今文专书则曾“纠缪”。但《何氏纠缪》,已“自悟其非,焚之”了。《教学通议》如有存留,将是探究康氏早年经学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康有为家属捐赠的书稿中,逐卷细查,终于发现了这部手稿,确是他的早年字迹。《教学通议》刊目二十:《原教》,《备学》,《公羊》,《私学》,《国学》,《大学》,《失学》,《亡学》,《六经》,《经亡》,《春秋》,《立学》,《从今》,《尊朱》,《幼学》,《德行》,《读法》,《六艺》上(礼)、中(射御)、下。内《六艺》下有目无文。另“缺目”三,即《言语》《师保》《谏教》。《言语》《师保》“缺目”有文,正文另有《敷教》一篇,或即“缺目”中的《谏教》。全书约三万八千字,上署“光绪十二年正月辑定”。
康有为在《教学通议序》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教学通议》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康有为认为,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万民无不曲备”(《六经》)。“言古切今”,周公也是典范,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从今》)。
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为他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制作典章”,“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从今》),“教学大备,官师咸修”。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拜的偶像,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至于今文经学家则是尊《公羊》、崇孔子的。康有为既著书批驳何休,《教学通议》中对孔子也作如是评价:“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即射行明备,亦不过与史佚之徒佐翊文明,况生丁春秋之末造,天下失官,诸侯去籍,百学放黜,脱坏大半矣。孔子勤勤恳恳,远适宗周,遍游于列国而搜求之”(《六经》)。认为孔子“不得天位”,只是“搜求”遗文,退而讲学。
周公、孔子对六经的关系也有不同,康有为认为:如今的六经“虽出于孔子”,而其典章皆“周公经纶之迹”。过去六经都有官守,“以官为师,终身迁转不改”,“如《易》出于太卜,《春秋》出于外史,《诗》出于太师,《论语》《诗经》出于师氏”(《私学》)。但“自夷、懿以降,王迹日夷,官守渐失”,孔子就是生于“失官之后,搜括文、武、周公之道,以六经传其徒,其徒尊之,因奉为六经”的(《失官》)。那么,六经本是“周公之制”,孔子只是“搜括文、武、周公之道”,“宪章祖述,缵承先王”(《六经》)。它和古文经学家之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何其相似!
以周公为“有德有位”,以六经为“周公经纶之迹”,康有为是尊崇周公的;至于孔子,他对经书的功迹,则在于传授六经、讲明六经之道和“制作《春秋》”。然而,孔子处“王官失守”之时,“六经之治扫地”之际,他只是“缵承先王”,讲明其道。他写《春秋》,也是因“六经之治扫地”,从而“感乱贼,酌周礼,据策书,明制作,立王道,笔则笔,削则削”的。其中自有所谓“微言大义”,而“孔子微言,质之经传皆合”,他讲《春秋》之治,也只是“继周”,尊的还是周公。
如众所知,康有为是利用今文经学议政言事、进行变法活动的;但他早年却是尊周公、言古文。《教学通议》手稿的发现,不但可以弄清康有为思想演变的迹象,寻求言政依附的艰辛,并且可以证明他的援用今文,是在第一次上书不达以后,是在受到廖平启示以后;还可以看到,康有为的援经言事,尊孔改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那么,手稿的发现,对研究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发展是何等重要。尽管康有为后来思想变了,“既而弃之”,但如再结集,还是应该收入的。
近代报刊盛行,一些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每每跟随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表政论。但有的自己没有结集,有的在流传中散佚,致不为人所注视。例如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发表在《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8、9号,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署名章绛。而章太炎自己编的《章氏丛书》,却没有辑入。
章太炎为什么在辑集时不收《诸子学略说》?不是因为此文佚失,而是因为当时“深恶长素(康有为)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继而悔之,从而把它刊落的。
《诸子学略说》首谓:“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接着,对儒家、道家、纵横家、法家等加以说解。论儒家时,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教弟子,“惟有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还说“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以至“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等“批孔之辞”。
《诸子学略说》发表后,章太炎弟子黄侃曾向他责询,文中“孔子窃取老子藏书”出自何典?章氏只是支吾其辞。此后,这篇文章没有收入《章氏丛书》。
到了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对《诸子学略说》加以批判。章氏见到后,回复柳诒徵,略谓:
顷于《史地学报》中得见大著,所驳鄙人旧说,如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以有弟兄啼之语,作逢蒙杀羿之谈,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是说向载《民报》,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
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

应该说,对过去文章偶有的失实进行纠正,这是可贵的,也正是信奉古文的“朴学”实事求是的风范。但当年他批判康有为(长素),却是生气勃勃的,如今却因前文失检,深感“前声已放,驷不及舌”,而不收入《丛书》了。
信中所称“向载《民报》”,实际载于《国粹学报》。自称“《丛书》中已经刊削”,说明章太炎在结集时是因为过去“激而诋孔”,自感“狂妄逆诈”,自行刊削的。自行结集,将旧作抉择删落,是可以理解的。清季以前作者,也不会将旧作尽行搜入。但近代报刊所载,每有根据当时形势,有感而发,这类文章,针锋相对,对研究作者思想发展,极为重要。我认为,如果没有结集的,应该辑入;已经结集,内容有较大增删的,应该校注。就以章太炎来说,所撰《客帝》,最早发表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旋又发表在日本《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前者署名“章炳麟”,后者署名“台湾旅客来稿”。收入《訄书》原刻本时,增改颇多,如“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蒙古之主支那是也”。《訄书》原刻本作“客帝者何也?曰:满洲之主震旦是也”。改“蒙古”为“满洲”,易“支那”为“震旦”,并在“而支那旷数百年而无君也,如之何其可也”下,增加了一千五百余字,续予发挥
 。他揭露了清政府“奉表以臣敌国”的媚外丑态,指斥清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提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开始提出“逐满”的口号。
。他揭露了清政府“奉表以臣敌国”的媚外丑态,指斥清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提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开始提出“逐满”的口号。
《客帝》认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是“仲尼之世胄”。说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他在文章中,不但也谈“素王”,还引《中候》和《春秋繁露》,说明他还未摆脱康、梁的思想影响。这种“客帝”的论调,也是章太炎后来所说“纪孔保皇”的表露。这点,他自己也不否认:“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

这一段话,是章太炎写在后来写的《客帝匡缪》上,作为《訄书》重印本的《前录》刊发的,辛亥革命后,他手订《章氏丛书》,把《訄书》改为《检论》,却把它删除了。那么,如果把《訄书》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编入,再将此后多次改动辑录汇刊,无疑对研究章氏思想发展、演变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因此,我认为尽管他已自行结集,但搜辑寻求,校订编集,也是必要的。
手稿的发现,可以寻求人物的思想演变发展;报刊的登载,可以考察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针锋相对。经、子结集,对手稿、报刊文献不容忽视。但一经整理,也有几点可资探究:
有些手稿,曾不止一次地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演变。如果只收最初的结集,不易看到他在结集前的增订缘由;如果只看后来的结集,可能有的文篇已经删除。如上面提到的《訄书》,我就看到不止一次的修订手稿。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旅居台湾,曾将已刊、待刊论文,汇成《訄书》,共五十篇,于1900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付梓,这是《訄书》最早的刻本(即“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行),对早先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篇,已有较多增改,如《客帝》。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和自立军失败的影响下,思想发生变化,写《客帝匡谬》,并校订《訄书》。这部“手校本”,列《原学》第一,到《解辫发》第五十七,另附《客帝》,实为六十四篇。“手校本”的存目和部分新增文篇手稿,今藏上海图书馆。
1902年6月,章太炎由日本返国后,又在1900年《訄书》手校本的基础上重行“删革”。是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称:“余始著《訄书》,意多不称,自日本归,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这就是1904年在日本东京翔鸾社的铅字排印本。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对《訄书》亦多所修治矣”,增订了不少篇文,也删除了一些篇目,如拟增《原儒》《原经》《六经说》《小疋大疋说》《八卦释名》《孝经说》等自认为“闳雅”的传世之作。这部“手改本”改笔都是蝇头小楷,今藏北京图书馆。
1913年8月,章太炎“时危挺剑入长安”,为袁世凯幽禁,将所撰论著编成《章氏丛书》,1915年由上海右文出版社排印出版。不久,又由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其中《检论》,就是在《訄书》“手改本”的基础上修订印行的。从编目到内容,和原来的《訄书》都有显著不同,我在《章太炎年谱长编》和《章太炎传》中,都曾论及
 。
。
如果单看《章氏丛书》中的《检论》,不但删除了过去《訄书》中的一些革命文篇,而且看不到他自甲午战后到民国初年的思想演变。如果“结集”能把他的历次改本,一一搜集影行,那对深入研究章太炎思想,以至中国近代史,无疑是有帮助的。
或者以为,清季以前的结集,很多是作者晚年自订,他们对早年之作,也会有增删、修订,为什么近代人物结集要如此细致,岂非繁琐。其实,占有资料,繁琐非罪,问题是结集的目的何在?作为“全集”,总希望搜编齐全,清季距今较近,手稿存留,这是一件好事,不将这些作品搜辑齐全,怎能对作者作出正确评价?况且在历次修订的手稿中,可以察觉各该时期作者的思想活动及其周围环境,以至人物的关系,这是不容忽视的。况且,近代社会发展迅速,人物思想每随时代而有变化,这和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自有不同,思想的演变,修订的频繁,自非过去人物“结集”可比。
当然,在处理手稿以至刊本进行结集的时候,带来一些困难,如以初稿为底本,以历次修改脚注、正文、注文检查不易;如以历次改本照录,读者又必重新勘覆。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为好,可以探讨。但不能因为编校困难而任意放弃。作为近代人物的“结集”,对这种比较重要而历经修改的文篇,还需慎重对待,不能弃而不顾。
其实,报刊发表的文篇在结集时又经修改的情况,近代人物也不只是章太炎一人如此,其他人物也时有所见,如严复《原强》一文,最初登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八日至十二日(1985年2月4日至9日)的天津《直报》,后来收入《侯官严氏丛刻》,前后就有很多改动,除《物类宗衍》改为《物种探原》等名词改动外,很多牵涉词意的改动,如《直报》载:
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物为尤急切,何则?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未由见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
《侯官严氏丛刻》则作:
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借天地二字,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教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言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
可知修改异同,勘校探寻,还是必要的。
谭嗣同的《仁学》,最初刊登在《清议报》和《亚东时报》,但它们不是同源。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刊《清议报》,自第二册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899年1月2日)开始刊登,直到第一百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公元1901年12月21日)刊完,共登载十三次,历时近三载。较《清议报》略后,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自第5号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公元1899年1月31日)连载《仁学》,至第19号(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即公元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登载十四次,历时也有一年零两个月。但他们不是同源:《清议报》本源自梁启超所藏“副本”,而《亚东时报》本则源自唐才常。1901年10月10日,由“国民报社出洋学生编辑所”署名,在日本发行之本,以至后来各本,都沿自梁启超所藏“副本”。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建议“重印《仁学》,应以《亚东时报》本为依据,而将各本比勘”
,即公元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登载十四次,历时也有一年零两个月。但他们不是同源:《清议报》本源自梁启超所藏“副本”,而《亚东时报》本则源自唐才常。1901年10月10日,由“国民报社出洋学生编辑所”署名,在日本发行之本,以至后来各本,都沿自梁启超所藏“副本”。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建议“重印《仁学》,应以《亚东时报》本为依据,而将各本比勘”
 。中华书局重印的《谭嗣同全集》就曾按照这一意图进行,并从《湘学报》《湘报》《时务报》《农学报》《清议报》《亚东时报》增补和校订了一些文篇。
。中华书局重印的《谭嗣同全集》就曾按照这一意图进行,并从《湘学报》《湘报》《时务报》《农学报》《清议报》《亚东时报》增补和校订了一些文篇。
至于没有在以前结集登载的,也应补辑,如唐才常有《觉颠冥斋内言》,收录他在戊戌前的文篇。政变后,他续在《清议报》《亚东时报》发表诗文,如《论戊戌政变有益于支那》《答客问支那近事》《砭旧危言》《日人实力保华论》《正气会序》等,都很重要,即戊戌前的函札,《觉颠冥斋内言》也未收录。重编的《唐才常集》,也把这些补录进去了。
清季、民初报刊的寻求,并不那么容易,但不能由此忽视。只有比较全面地、系统地掌握资料,才能编成真正的“文集”或“全集”,只有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料,才能对各该人物有一正确的评价。
清季、民初人物结集,在如何写好前言或后记,以及编排、标校等方面,也有几点值得注意:
作者生平、著作情况、版本依据、编集源由,可在前言或后记中说明,但不要“趋时”。
经、子结集,是要传之久远的,“前言”或“后记”就不能随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作“趋时”之论。举例来说,《龚自珍全集》在1959年出版的,1974年重印,重新改写了“前言”。改写的“前言”说是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学是在二十八岁以后,断然说是他与“公羊学无关”。事实上,龚自珍从刘逢禄学公羊学确在二十八岁,《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诸文,也写在二十八岁以前;但不能说他与“公羊学毫无关系”。因为:
1.龚自珍同时期的人和受他影响的人,都强调他“好今文”。
魏源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
 ,梁启超说“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存与)、刘(逢禄)”,以为他是“今文学派的开拓者”
,梁启超说“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存与)、刘(逢禄)”,以为他是“今文学派的开拓者”
 。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也说:“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芒接董生(仲舒)。”即所学与之殊科、学宗古文的章太炎,也说龚自珍“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
。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也说:“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芒接董生(仲舒)。”即所学与之殊科、学宗古文的章太炎,也说龚自珍“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
 ,都承认他与今文经学的关系。
,都承认他与今文经学的关系。
2.公羊学的特点是援“三统”“三世”以言变革,它每易为隐忧国事、期待变革的人所接受,龚自珍年轻时就有“经世之意”,二十八岁以前的著作中,也有迹象可寻。 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从夏、商、周三代“夷兴”指出:“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有夏、商、周因革损益的微义。《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谈到“三世”,不能说它和《公羊》毫无渊源。
3.乾隆、嘉庆年间,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庄存与揭橥于前,刘逢禄、宋翔凤推衍于后,形成“常州学派”。 庄、刘久宦京师,里第也与龚自珍相迩。龚自珍于十一岁随父到京,此后屡来京、苏,对复兴的今文经学和庄、刘行事应有所闻。1817年,当龚自珍二十六岁时,写有《江子屏所著书序》,有讲三统循环论的迹象。同年冬至,看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认为以清代经学为“汉学”,“名目有十不安”,其中一条:“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唯其是而已矣,亦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宜指清代经今文学的开创者庄存与而言。他对“创获于经”的“绝特之士”是有所知的。就在遇到刘逢禄的前一年,庄存与之孙绶甲馆于龚家,为龚自珍“言其祖事行之美”,龚自珍即拟为写碑铭。次年,从刘逢禄受公羊学,并识宋翔凤。如果他对今文经学毫无品味,不会一遇到刘逢禄,即从之受学。也正由于从小有“经世之意”的思想基础,从而甫经遇刘,即从之受学,誉今文经学为“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之学,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显露了今文的“微言”、《公羊》的“奥义”了。
龚自珍受今文经学的熏陶是事实,他在二十八岁以前已和今文经学有关也是事实
 ,为什么《龚自珍全集》重印时,“前言”视而不见,特地加“与公羊学无关”这一段呢?查此书重印是在1974年,正是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之时,他们把龚自珍定为“法家”,从而在书籍难于出版之时,会把此书重印,如果说龚自珍和“公羊学”有关系,如果说他受了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岂非要影响龚自珍的“法家”地位?它特地加上这一段,不是没有缘由的。但序文的“趋时”,却影响了《全集》的发行,可知“前言”或“后记”还是稳定为是。
,为什么《龚自珍全集》重印时,“前言”视而不见,特地加“与公羊学无关”这一段呢?查此书重印是在1974年,正是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之时,他们把龚自珍定为“法家”,从而在书籍难于出版之时,会把此书重印,如果说龚自珍和“公羊学”有关系,如果说他受了常州今文经学的影响,岂非要影响龚自珍的“法家”地位?它特地加上这一段,不是没有缘由的。但序文的“趋时”,却影响了《全集》的发行,可知“前言”或“后记”还是稳定为是。
结集编排,应该根据材料的特点,力求保持资料的完整性为原则,不能任意取舍,主观编排。一般说来,“全集”中的专书,可按专书编入;“全集”中的单篇诗文以至奏稿、函电,可按年月编排。如果自出“专题”,那么奏札函电,每每不是专言一事,势必任意取舍,顾此失彼。同时,档卷、手稿整理时,还应与文物保管相结合,因为这些毕竟是近百年、甚至百年前的文稿,稍有不慎,即易带来研究时的困难。如有的函札,原有信封,邮票上有时日可稽,未加注意,甚至丢失,对考定时间、地点会带来极大困难。
当今重行结集,自宜进行新式标点。我认为标点时首先要弄清文义,辨明句读。其次,有的文稿,曾自行断句,应予注意,如章太炎的《客帝匡谬》,最后一句“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有人在“劾”下加点,而章太炎手校本则自己在“劾录”下加点,自宜按照作者原意进行标点。至于校注,宜力求简明,避免读者知道的去注、该注的却不注。过去引文,每凭记忆摘录,似加引号即可,不必另将原文注出,总之,编排力求合理,标校力求简明。
近年海峡两岸颇多经、子结集,因草此文,供讨论参考。
1997年5月31日于上海
——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8卷第1期,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