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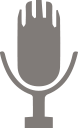 第二节
第二节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层面,国家形象和民族认同始终是主流文化所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大众文化的视觉表意实践对这一议题的编码过程,不仅带有主流文化的深刻烙印,而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不断融入更丰富的视觉话语内涵。可以说,自改革初期开启一个创造性的“大时代”以来,大众文化在社会转型的宏观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这不仅在于其拥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受众,更在于其难以替代的视觉表征方式。借助形形色色的视觉形象符号,大众文化不仅以一种更隐匿的“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普罗大众传达各种意识形态诉求,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文化一方面成为形塑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就形象类型而言,“英雄形象”无疑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形象符号之一。在历时性维度,这一形象符号既始终隐含着主流文化以“崇高感”为典型特征的宏大叙事,又不乏大众文化在叙事策略、形象特征等方面不断随时代而动的适度调整。由此所带来的对宏大叙事的“附魅”“祛魅”及“返魅”,以及大众视觉经验的启蒙、重塑和惯习化,将是我们理解大众文化在“大时代”状况之下如何进行视觉的社会建构的重要依据。在共时性维度,这一形象符号所呈现出的复杂面向则提醒我们:时至今日,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宏大叙事对总体性的诉求正在受到各种话语力量的挑战;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以一种更加多元生动的方式发挥效应并非不可能。事实上,大众文化通过形形色色的形象符号“编码—解码”过程所传递出的视觉政治,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大时代”,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和民族的“大发展”、“大变革”或“大转型”,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向的“大国崛起”时代。这个时代创造了独特的英雄形象的崇高叙事。
从历时性来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对于英雄形象的视觉符号生产,是有一个隐约可辨的发展脉络的。在文类上,它主要以电视剧和商业电影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包括动漫游戏、广告以及竞技体育等在内的其他文本类型,也都以自己的方式生产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形象。其中电视剧因为具有最广泛的受众人群、超强的文本叙事能力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当仁不让地成为最值得深入剖析的文本类型。毋庸置疑,电视剧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兴盛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的兴起离开电视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当代电视剧三十余年来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可谓不胜枚举。概括来看,其发展历程也可以大众文化的三个阶段分期为依据。
在大众文化的“萌芽期”,这一形象类型一方面受到过往主流文化对“高大全”英雄形象模式刻板化建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开始不断开拓更具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中国当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1981),在中国当代电视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所塑造的江波这一谍战英雄形象,既在整体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战争年代英雄形象的基本要求,又借助新的表现手段被赋予了更为鲜活生动的个性色彩。尽管这时电视机的普及率非常低,但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大众第一次通过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强烈体会到,原来那么严肃的主题,可以通过如此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扣人心弦的剧情设置,用一种带有强烈崇高感的宏大叙事方式加以视觉化的呈现。其人物塑造既符合人们长期以来关于英雄形象的固化认知,又引人入胜、如此“好看”。而早于该剧播出的单本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1980),则塑造了改革英雄乔光朴的形象。这部电视剧改编自蒋子龙的同名小说,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热烈的讨论,电视剧播出后更是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其重要性在于它可以算是中国当代电视剧发展过程中,首个随新时代应运而生的新型英雄形象。相较于《敌营十八年》中的江波,乔光朴这一英雄形象更具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即使是常见的军旅英雄的塑造,也因为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比如曾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高山下的花环》(1984),便以发生不久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塑造了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小北京”等一组新时代军人英雄形象。这一组英雄群像与过往“高大全”的战争英雄已经形成明显的反差。尽管这些视觉形象依旧通过残酷的战争场面营造出“崇高化”的叙事效果,但形象符号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处理,都在事实上增加了这一叙事效果的复杂性和可看性。
这种复杂性和可看性,首先表现在叙事手段上较之过去丰富得多。一方面,这些电视剧在故事线索、情节设置等方面的复杂程度都远远高于过去;另一方面,英雄人物的类型也开始多样化,从单一的革命英雄拓展到各行各业。这一阶段电视剧中所塑造的新型英雄形象至少包括“改革英雄”、“知青英雄”、“启蒙英雄”等类型。其次,这些形象在性格特征、情感生活等方面的复杂程度,同样是过去无法想象的。英雄形象开始摆脱了刻板的“高大全”模式。英雄不仅有七情六欲,而且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失误。因此,尽管英雄仍是人们所崇敬的对象,但他们不再是须仰视才见的“神”,而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甚至是可能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熟悉的陌生人”。正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一批类型各异、意指丰富的英雄人物形象经过最初几年的经验积累开始集中出现。比如陆续热播的《乌龙山剿匪记》(1986)、《新星》(1986)、《凯旋在子夜》(1987)、《便衣警察》(1987)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电视剧作品,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都明显融入了更具个性色彩的叙事策略。《乌龙山剿匪记》中对于反面人物钻山豹的塑造、《新星》通过李向南这一改革英雄形象对时代精神的敏感把握,等等,都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隐于其间的既有大众对于更具“可看性”或“娱乐性”的视觉形象的欲求,也有创作者力求突破过往主流文化束缚的自觉反思。而英雄不是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世界,他们就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其凡人化、丰富性和多样化,既是这种“可看性”的重要保证,也成为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突破口。对于电视剧而言,收视率及其受众效果至关重要,因为电视剧是产业化的文化产品。可以说,市场原则和视觉原则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说教模式,英雄形象以一种“寓教”服从“于乐”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他们在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双重意义上被理解为是一种“英雄在场”。
这种“英雄在场”的电视剧,几乎都既产生了巨大社会轰动效应,同时又充满争议,还不乏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这一形象符号已经开始突破过去以单向度的宏大叙事为主导的“崇高化”叙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一变化反映了大众的视觉经验模式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第一次解放。亦即从意识形态“说教”模式中解放出来,创造出丰富而又合乎人性的英雄,既让人们敬仰赞赏英雄,又让英雄的叙事给人以视觉愉悦。随着电视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明显提升,英雄形象的塑造融入了越来越多元的话语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当代电视剧发展过程中引进剧最为成功的一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引进剧可谓中国内地当代大众文化得以兴起的关键性外来文化力量之一,尤其是武侠英雄作为一种全新的英雄形象,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这其中,无论是《大侠霍元甲》(1981、1983年引进中国内地)、《上海滩》(1980、1984/1985年引进中国内地),还是《射雕英雄传》(1983、1984/1985年引进中国内地),都不仅风靡一时甚至引领一个时期的时尚潮流,而且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也为中国内地的当代电视剧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空间和思路。
如果说这一时期是大众视觉经验的第一次觉醒,它不仅是针对大众文化的受众,同时也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而言的。无论在哪个维度,这都是视觉经验的大众启蒙时期。这种视觉经验在相对严肃刻板的主流文化的英雄形象之外,创造了另一种富有崇高风格的英雄叙事,为大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化开辟了形象多元化的新时代。
在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勃兴期”,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延续了前一时期类型不断拓展的大趋势。包括军旅英雄、民族英雄、启蒙英雄、改革英雄、反腐英雄、谍战英雄、刑侦英雄、体育英雄、草莽英雄、武侠英雄、平民英雄等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形象符号可谓层出不穷。透过如此纷繁多样的形象符号,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电视剧在视觉形象的“生产—消费”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电视剧发展为大众文化成为一种主导型文化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括来看,这一时期电视剧的英雄形象塑造,表现出以下几个彼此呼应的总体特征:
第一,伴随着电视媒体的市场化进程,英雄形象的视觉符号生产呈现出日益“商品化”的特征。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关键性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市场”这一新的生存法则。电视剧不仅成为大众文化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的基石,而且其视觉形象的生产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尽管在叙事策略上仍力求遵循一种“崇高化”效果,但主流文化所主导的宏大叙事,却在市场逻辑的强势介入下进一步面临转变。对收视率的高度关注作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令大众文化日益向“市场为王”的“眼球经济”转型。一方面,英雄形象的符号生产越来越关注与经济生活有关的当下现实。无论表现反腐倡廉的《苍天在上》(1995)、刑侦打黑的《英雄无悔》(1996),还是反映军人风貌的《和平年代》(1996)、国企改革的《人间正道》(1998)等一批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电视剧,其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类型各异,但都触及了当代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其中植入大量吸引眼球的电视剧的类型剧情节模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表现出题材选择上极大的开放性,任何资源只要市场需要就可以为我所用。这一时期英雄形象的类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此直接相关。根据其他文类改编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当英雄形象作为一种商品被批量生产时,其立足点便不可避免地有别于以往宏大叙事的英雄形象逻辑。不仅某一英雄形象类型的电视剧获得成功,跟风之作便会泛滥,而且其表现形态也日趋“吸引眼球”。对于观众而言,观看越来越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易于接受并喜闻乐见成为英雄符号的新标准。主流文化所期许的英雄形象及其家国天下的崇高感,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一种“娱乐化”的快感体验所取代。
第二,伴随着电视剧创作的类型化发展,英雄形象的视觉符号生产呈现出日益“程式化”的特征。与前一特征相辅相成,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上日益向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类型剧发展。英雄形象也相应地在制作层面日益变得程式化。众所周知,《渴望》(1990)、《编辑部的故事》(1991)、《戏说乾隆》(1991)、《我爱我家》(1993)等在1990年代初期的集中出现,既为中国当代电视剧类型奠定了基础,也是大众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家庭伦理剧、戏说剧、情景喜剧以及神话剧、武侠剧等类型在1990年代的出现和发生,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电视文化领域的一个表现。”
 具体到英雄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刑侦剧、军旅剧、历史剧、神话剧、谍战剧、武侠剧等成为其最具典型性的电视剧类型;另一方面,它又依据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制作程式,在剧情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遵循各自的类型化要求。《突出重围》(1999—2000)、《刑警本色》(1999)等热播电视剧,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电视剧中英雄形象的符号,从改革初期至此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式的变化过程:原先由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样板化”英雄人物,在逐步向人性本来面目回归的同时,又因为大众文化所遵循的市场原则,以另一种方式进入“类型剧”模式当中。英雄形象二十年间从主流文化严肃刻板模式中突围,如今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大众文化的英雄形象“类型剧”的新模式,看来这类形象的生产终究逃脱不了模式化的命运。
具体到英雄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刑侦剧、军旅剧、历史剧、神话剧、谍战剧、武侠剧等成为其最具典型性的电视剧类型;另一方面,它又依据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制作程式,在剧情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遵循各自的类型化要求。《突出重围》(1999—2000)、《刑警本色》(1999)等热播电视剧,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电视剧中英雄形象的符号,从改革初期至此实际上存在一个悖论式的变化过程:原先由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样板化”英雄人物,在逐步向人性本来面目回归的同时,又因为大众文化所遵循的市场原则,以另一种方式进入“类型剧”模式当中。英雄形象二十年间从主流文化严肃刻板模式中突围,如今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大众文化的英雄形象“类型剧”的新模式,看来这类形象的生产终究逃脱不了模式化的命运。
第三,伴随着大众文化越来越走向娱乐化的发展趋势,英雄形象的视觉符号生产日益“偶像化”。高度娱乐化作为大众文化市场化之后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而言,在形象符号的编码和解码两端都对宏大叙事的崇高体验进行了“娱乐化”的消解,所以英雄形象符号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显著变化。英雄人物原本作为一种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形象符号,开始在商品化和程式化的形象生产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遭到市场逻辑祛魅的“偶像化”人物。一方面,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不仅进一步摆脱单一的叙事模式、形象更加丰满生动,而且在叙事策略上日益融入更多元的时尚、娱乐元素,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将英雄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进行一种偶像化包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电视剧生产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明星机制,对英雄形象符号的偶像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英雄形象的偶像化既是角色本身的变化所带来的,更是通过明星扮演真正实现这种偶像化效果的。
与《还珠格格》这类戏说剧的明星符号生产不同,英雄形象的塑造与这一形式之间的结合更具隐蔽性,但其运作规则又是保持一致的。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电视剧类型都既越来越依赖明星的参与,又成为明星生产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收视率。比如1999年热播的《永不瞑目》,在这方面堪称范例。在一定意义上,这部电视剧甚至可以看作大众文化自199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偶像化”代表性文本之一。英雄形象在角色设定层面的偶像化和明星参演层面的偶像化及其复杂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一案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前者而言,该剧几乎是将一部青春偶像剧包裹在刑侦剧的外衣之下,通过复杂的情感交集,将各种帅哥靓女编织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中;就后者而言,该剧不仅充分展示了电视剧作为明星生产机制一个环节的造星能力,而且通过演员向明星再向偶像的演化过程,不断强化了英雄人物作为一种形象符号所具有的偶像化特质。换句话说,一个角色由普通演员还是明星来扮演,无论对于其形象符号的编码还是解码,效果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因为在这里,普通演员与明星演员所拥有的“象征资本”是有天壤之别的。
 明星演员作为大众文化“眼球经济”在这一时期所建构的典型形象符号之一,其参与英雄形象的“编码—解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大众文化产业象征资本的增值过程。英雄形象的偶像化因此绝不能简单理解为视觉形象在创作手段或审美趣味上的形式变革。在其背后,既隐藏着大众文化“眼球经济”对英雄形象本身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即对彰显自我价值的英雄观的认可,反映出某种有别于家国天下的英雄叙事的转变;又包含了大众文化形象生产机制的自我完善过程,以及视觉形象的偶像化必然带来的后果:英雄作为精心装扮的偶像,最终成为文化产业流水线上可供消费的娱乐产品。
明星演员作为大众文化“眼球经济”在这一时期所建构的典型形象符号之一,其参与英雄形象的“编码—解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大众文化产业象征资本的增值过程。英雄形象的偶像化因此绝不能简单理解为视觉形象在创作手段或审美趣味上的形式变革。在其背后,既隐藏着大众文化“眼球经济”对英雄形象本身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即对彰显自我价值的英雄观的认可,反映出某种有别于家国天下的英雄叙事的转变;又包含了大众文化形象生产机制的自我完善过程,以及视觉形象的偶像化必然带来的后果:英雄作为精心装扮的偶像,最终成为文化产业流水线上可供消费的娱乐产品。
电视剧中英雄形象的符号生产所体现出的上述特征,在根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与此相互印证的是,电视媒体和电视剧产量在此阶段都得到了爆炸式的发展。就前者而言,至1999年,中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已经达到3.5亿台,有43套卫星电视节目以及8000多万有线电视用户。
 就后者而言,“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以上”。
就后者而言,“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产量一直居高不下,年产量都在6000部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继续引进港台地区影视作品的同时,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在电视剧创作方面的合作也开始进入一个日益深入的阶段。无论资本的介入,还是包括演员、导演等在内的业内人士的参与,港台电视剧的创作经验都为英雄形象塑造的另一种路径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创作,一方面,电视提供了足够丰富和具有诱惑力的视觉产品;另一方面,大众身处其中,却越来越缺乏选择的可能性,在被形形色色的视觉形象包围的过程中日益变得乏味。这一时期知识界多次围绕人文精神所展开的大讨论,直接动因便来自对大众文化高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病的反思。但立足于市场逻辑之下,这一切状况的出现皆有其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继续引进港台地区影视作品的同时,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在电视剧创作方面的合作也开始进入一个日益深入的阶段。无论资本的介入,还是包括演员、导演等在内的业内人士的参与,港台电视剧的创作经验都为英雄形象塑造的另一种路径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创作,一方面,电视提供了足够丰富和具有诱惑力的视觉产品;另一方面,大众身处其中,却越来越缺乏选择的可能性,在被形形色色的视觉形象包围的过程中日益变得乏味。这一时期知识界多次围绕人文精神所展开的大讨论,直接动因便来自对大众文化高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病的反思。但立足于市场逻辑之下,这一切状况的出现皆有其必然性:
拥有最大经济权力的那些人将能够提高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并确保让那些对阶级结构批评最少的媒介产品存留下来,而那些最具批评性的内容将没有生存的空间。最终的结果是,这将使得多元的观点、政见和文化更难进入市场,因为它们缺少必需的经济来源。高成本的压力意味着所有的媒介不得不覆盖面积尽可能大的受众群。它们可以将目标定在规模庞大的受众身上,也可以定在范围虽小却很有影响力的集团上。

以此观之,在“眼球经济”盛行、视觉消费狂欢化的大趋势下,英雄形象的符号日益走向“祛魅”和“还俗”,也就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了。
更重要的是,以“眼球经济”的兴起为依据,这种“祛魅”所导致的英雄形象的偶像化,凸显了大众文化对大众视觉建构的功能,它既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又揭示了如何通过英雄形象的新建构来进一步塑造人们对变迁的认知。英雄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英雄可以出现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中,也可以出现在武林甚至日常生活中;英雄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凡人所限,但他们最终总有一些高尚的事迹让人敬仰;英雄需要明星来抬举,英雄+明星的模式让英雄在形象呈现的过程中分享了明星的光环,更加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清楚地揭示了形象的变化,也揭示了大众对英雄的观念变化,以及他们的视觉经验模式从被动适应说教型形象叙事,日益转向更加主动、多元和开放的视觉经验。当然,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小觑,那就是电视剧的类型剧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大众对新英雄形象的适应、依赖和上瘾,重塑了他们的视觉经验。
进入大众文化的“成熟期”,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重塑“英雄”形象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视觉文化现象。“21世纪中国电视剧变化走向更是明显,即已经从教化走向情感消费,从严肃姿态走向娱乐表现,从艺术化走向生活化,从而实现了电视功能的回归。”
 在此语境下,电视剧中英雄形象的符号进入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阶段。如果说大众文化第一个阶段“萌芽期”还依附于主流文化,第二个阶段“勃兴期”随着经济腾飞和文化的俗世化而逐步摆脱主流文化的话,那么在晚近的第三阶段“成熟期”,二者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互利互惠的新模式渐趋形成。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主流文化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引入大众文化之中,以更为隐蔽的合作方式重塑了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主旋律不再是一个空洞说教,而是转向了大众文化的喜闻乐见,在制造快感愉悦中完成英雄形象的重新出场,形成了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并受大众喜爱的“英雄类型剧”。从《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亮剑》(2005)到《士兵突击》(2006)等一系列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塑造,无不彰显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成功结合所能实现的视觉话语建构效应。其中《士兵突击》对许三多这一后革命时代军旅英雄形象的塑造尤其具有代表性。电视剧成功地“将主旋律、励志故事与青春偶像等元素相互糅合,通过平民化、戏剧化、情感化、通俗化等方式完成了一次对革命题材经典模式的大众化改写”。
在此语境下,电视剧中英雄形象的符号进入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阶段。如果说大众文化第一个阶段“萌芽期”还依附于主流文化,第二个阶段“勃兴期”随着经济腾飞和文化的俗世化而逐步摆脱主流文化的话,那么在晚近的第三阶段“成熟期”,二者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互利互惠的新模式渐趋形成。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主流文化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引入大众文化之中,以更为隐蔽的合作方式重塑了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主旋律不再是一个空洞说教,而是转向了大众文化的喜闻乐见,在制造快感愉悦中完成英雄形象的重新出场,形成了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并受大众喜爱的“英雄类型剧”。从《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亮剑》(2005)到《士兵突击》(2006)等一系列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塑造,无不彰显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成功结合所能实现的视觉话语建构效应。其中《士兵突击》对许三多这一后革命时代军旅英雄形象的塑造尤其具有代表性。电视剧成功地“将主旋律、励志故事与青春偶像等元素相互糅合,通过平民化、戏剧化、情感化、通俗化等方式完成了一次对革命题材经典模式的大众化改写”。
 其影响力甚至达到了令年轻一代产生“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强烈冲动。
其影响力甚至达到了令年轻一代产生“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强烈冲动。
在娱乐性与“说教”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也成为这一时期英雄形象重构的特色。近些年来,兼具娱乐性和“说教”意味、收视率和口碑俱佳的电视剧中,主旋律电视剧所占比例及其影响不容忽视。这其中,以近现代革命史为背景的电视剧题材尤其受到青睐,而且叙事内容丰富,人物形象多元。以《潜伏》(2009)和《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为例,无论是前者所塑造的地下党人余则成,还是后者所塑造的革命英雄群像,在人物形象的符号生产过程中,都较好地处理了娱乐性与“说教”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些作品的出现意味着主旋律电视剧作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已经走向成熟。在其背后,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难以剥离的“融合”关系。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则是二者合力建构的大众传媒机制、评奖机制,以及主要代表主流文化立场的审查机制。自大众文化兴起以来,有关部门针对电视剧创作所发布的调控性规定和措施,从对境外剧的限制、电视剧题材的选择,到对剧本改编的细节要求、不同类型电视剧的审批,都是在市场之外对大众文化生产实行的行政管控。
 二者在英雄形象符号生产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现实关系,可以作如是观:
二者在英雄形象符号生产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现实关系,可以作如是观:
大众文化租用主流文化的资源以求利润的最大化,它获得了商业价值,同时也获得了安全生产的“政治正确性”;主流文化把资源出租给大众文化则是为了获得意识形态的剩余价值—当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新意识形态话语时,意识形态生产机制并不能马上提供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东西,于是在特殊年代里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出来的旧话语(比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等等)就成了一种补偿物和替代品。

假如说传统的主流文化是以某种强制灌输的方式让大众认可英雄形象的话,那么,当主流文化采用越来越成熟有效的大众文化手段和技法来重塑英雄形象时,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雄形象与其受众的关系,便从“要我认同”转变为“我要认同”。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值得关注,其一,从认知角度说,单纯的说教性英雄转变为大众喜爱并有亲民特质的形象,英雄不是神也不是超人,世俗的英雄特质更容易契合深受日常生活浸润的当代受众的认知经验;其二,从情感角度看,被重塑的英雄形象日益与手法娴熟并十分隐蔽的煽情性相融合,使英雄叙事的情感性更趋向于愉悦化和快感化,进而从情感上直击当代受众的内心世界;其三,俗世化的日常现实,使得那些指点江山的崇高英雄难觅踪影,平庸碎屑的日常生活暴露出其俗世性和平庸性特质,于是,一种相反的期盼英雄的乌托邦冲动成为当代大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倾向,此时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力重塑英雄形象,恰好顺应了这一心理冲动。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现阶段理解为视觉经验的惯习化时期,它带来的是大众视觉经验的第三次重构—视觉形象不仅已经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最重要途径,而且也成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建构自我社会化身份的基本方式之一。借用布迪厄的相关理论,所谓惯习意指某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
 因此视觉经验的惯习化,强调的是进入大众文化成熟期之后,当代中国受众对于视觉形象的接受已深入其身份和意识的自我建构。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经历了从“崇高英雄”到“多元英雄”再到“凡人英雄”的变迁过程,使得英雄形象越来越趋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越来越多的亲和力、真实感和娱乐性。英雄形象不但是主流文化的关注焦点,也是大众文化的成熟形象类型,尤其是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创造出了中国电视剧“英雄剧”的“类型剧”,并塑造了电视剧受众对这种类型剧的视觉惯习。其实,电视剧中英雄形象演变的三部曲,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从大改革大变动,向深化改革的新常态,这些社会变动都清晰地体现在电视剧英雄形象的演变逻辑中。
因此视觉经验的惯习化,强调的是进入大众文化成熟期之后,当代中国受众对于视觉形象的接受已深入其身份和意识的自我建构。电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塑造,经历了从“崇高英雄”到“多元英雄”再到“凡人英雄”的变迁过程,使得英雄形象越来越趋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越来越多的亲和力、真实感和娱乐性。英雄形象不但是主流文化的关注焦点,也是大众文化的成熟形象类型,尤其是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创造出了中国电视剧“英雄剧”的“类型剧”,并塑造了电视剧受众对这种类型剧的视觉惯习。其实,电视剧中英雄形象演变的三部曲,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从大改革大变动,向深化改革的新常态,这些社会变动都清晰地体现在电视剧英雄形象的演变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