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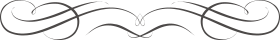
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伊里亚·普里高津
我十分高兴在此为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的这本书写篇前言。
时间有箭头吗?这个问题自从苏格拉底以来,一直迷魅着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今日,我们问这个问题,情况与以前不同。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20世纪的科学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两项思想方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产生的突破。其次是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物的发现,包括“基本”粒子的不稳定性、演化宇宙论,以及包括诸如化学钟、决定性混沌等的非平衡结构。最后——也就是现在,由于这些新的发展,我们必须对整个物理学作重新思考。
这里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是:所有这一切都强调时间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在19世纪,人们都已经承认时间在生物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的重要性。可是当时一般认为,物理描述的最基本层次是可以用决定性的、时间可逆的规律来表达,而时间箭头只相当于唯象层次的描述。这种立场在今日是很难站得住了。
现在我们知道,时间之箭在非平衡结构的形成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近来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结构的演化可以在计算机上用按照动力学规律写的程序来模拟。因此很显然地,自我组织过程不会是某些唯象观假设的结果,而是内禀于某类动力系统之中的属性。
熵的意义,我们现在更能体会了。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熵这个量总是在增加的,因此它赋予时间一个箭头。熵基本上是高度不稳定系统所具有的一个性质。这种系统,将在此书第6章和第8章详加讨论。要研究的东西还很多,许多问题仍是悬案。因此不足为奇,我不一定同意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但是对作者所提倡的一般立场,我是同意的,即时间之箭是某些重要种类的动力系统中一个精确的性质。
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热烈欢迎此书的问世。这本书科学水平很高,而同时能被较多的读者接受。彼得·柯文尼对此领域作过重要的贡献,因此他撰写此书,尤其胜任。罗杰·海菲尔德的文笔流畅,使此书精彩可读。
1989年10月在明尼苏达州圣彼得城的古斯塔乌斯·阿道尔夫斯学院举行的诺贝尔会议,专门讨论了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题目:“科学的终结”。会议组织人写道:“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科学已不再能被当做一种统一的、普遍的客观努力。”他们接着写道:“如果科学只搞‘超历史的’普适的定律,而不理会社会性的、有时间性的、局部的事物,那我们就无法谈及科学本身以外的某些真情实况,而科学仅仅是反映而已。”这句话把“超历史的”规律和有时间性的知识对立起来。科学的确是在重新发现时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对科学的传统看法的终结。但这难道是说科学本身完结了吗?
的确,我上面已经提到,经典科学的研究方针是把全力集中在用决定性的、时间可逆的规律来描述世界。实际上,该计划从未完成过,这是因为,规律以外还需要事件,而事件在对自然的描述中引入时间之箭。屡次三番,经典科学的目的似乎就快完成了,但结果总是出了岔子。这种情况给予科学史几分戏剧性的紧张。例如,爱因斯坦的目的是把物理学表达为自然界的某种几何,可是广义相对论给现代宇宙论开路以后,遇到的却是所有事件中最惊人的事件:宇宙的诞生。
“规律——事件”二重性是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在进行的争论的中心,这争论从苏格拉底以前的臆想,经过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一直进行到我们这时代。伴随规律的是连续的展开,是可理解性,是决定性的预言,而最后是时间本身的否定。事件却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任意性、概率以及不可逆的演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居住在一个二重性的宇宙里面,这宇宙既牵涉到规律,也牵涉到事件,既有必然,也有或然。我们所知道的事件之中,显然最关键的是和我们宇宙的创生和生命的形成有关联的事件。
“我们有一天能克服热力学第二定律吗?”——阿西莫夫(Asimov)的科幻小说《最后的问题》中的世界文明不断地在问一台巨型计算机。计算机回答道:“资料不足。”亿万年过去了,星辰、星系都死了,而直接和时空联结的计算机仍在继续搜集资料。最后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搜集了,不再“存在”任何事物了;可是计算机还是在那儿计算,在那儿找相关关系。最后它得到答案了。那时候要知道这个答案的人也都不存在了,可是计算机知道了如何克服热力学第二定律。“于是光明出现……”对阿西莫夫来说,生命之出现、宇宙的诞生都是“反熵”的、非自然的事件。
此书是新思维框架的一个极好的介绍。这个新思维框架将导致一套既包括规律又包括事件的新物理学,将使我们对我们身处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地点:的里亚斯特附近的都伊诺小镇
日期:1906年9月5日
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那时在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村庄里度假。这假期的用意是让他从维也纳的研究工作中散散心,帮他康复已有一段时期的病和排遣心情的忧闷。可是玻尔兹曼心绪还是很不安宁。
人的心理中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时间一去不回头。对此假设,只存在一个科学证据。玻尔兹曼自从他20来岁时当了教授以来,多年来就是为了了解这证据而苦斗。此项伟大的追求,他没有成功。他有关“熵”的工作(熵是衡量变化的一个物理量,它总是随时间增长的)非常精彩,可是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时间方向之谜始终是科学的缺陷。而对玻尔兹曼来说,时间已经到了尽头了。
玻尔兹曼身材魁梧,一脸的大胡子,可是人不可貌相,其实他性格柔弱,容易受人伤害。他工作过度,疾病缠身。那年他62岁,双目差不多完全失明,剧烈的头痛使他坐卧不安。起伏的情绪曾一度把他带到绝望的边缘,使他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疯人院里住过一段时间。一点不顺心的事也会使他大大伤心——例如今天他夫人为了要把他的外套拿去洗衣店干洗,因而坚持让他晚一些时候再回维也纳。
玻尔兹曼夫人拿走了外套,和她女儿一同去西司提亚纳海湾游泳去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她丈夫做了天下最不可逆转的事。他把一根短绳子系在窗框的横木上,围着自己的脖子打了一个死结。然后,就在那间租住的屋子里,他自杀了。他女儿艾勒萨回来,看见父亲在那儿上了吊。
玻尔兹曼的自杀,再次生动地表现了时间是如何在捉弄想揭示时间秘密的人。他的丧生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他在莱比锡的一个学生嘉菲(George Jaffé)写道:“玻尔兹曼的死是科学史中的悲剧之一,就像拉瓦锡(Lavoisier)上断头台,迈耶(R.J.Mayer)进疯人院,皮耶尔·居里(Pierre Curie)惨死在货车轮下一样。尤其可悲的是:这事就发生在他的思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
玻尔兹曼的思想牵涉到原子是否存在。有些评论家把玻尔兹曼看作一个智力的“三十年战争”的受难者,这战争是和不肯接受原子论的人打的。他的对手包括一大批19世纪思想界中的知名人士,其中有法国的督黑姆(Pierre Duhem)、孔德(Auguste Comte)和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德国的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荷耳姆(Goerg Helm),以及其他在美国和英国的诸如兰金(William Rankine)、史大罗(John Stallo)等人。他最大的敌手是他的同胞马赫(Ernst Mach),他们之间的论战使玻尔兹曼在知识界中形势孤立。玻尔兹曼有一次曾向一个同事表白,说懂他理论的人,实在是一个也没有。
玻尔兹曼对原子和分子的看法,终于占到上风。可是他希望能进一步解释时间的方向。对于自然界的这个特点,玻尔兹曼比其他任何科学家都下了更大的工夫。他这方面的雄心,终被狂躁抑郁症所击败,使他自杀。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玻尔兹曼在原子分子的概念和时间的方向之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决定性的关联。可是他的伟大梦想,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实现。
在努力想用原子分子语言来表达时间箭头和我们这世界其他特性的人中,玻尔兹曼还不是最后一个死于悲惨结果的人。加州工学院的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在他的《物质的状态》一书的开头写道:“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统计力学的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906年自杀身亡。艾伦菲斯特(Paul Ehrenfest)继续了这项工作,但也以类似的方式而死。现在轮到我们了……也许研究此项课题,谨慎为妙。”
对于我们笃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幻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