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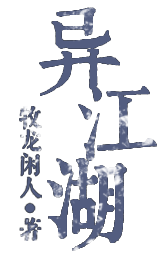
 第十五章 禅息惊梦
第十五章 禅息惊梦
南宫武的这种睡眠方式,乃是和一位云游僧人学来的。
那年,他只有十岁,锱铢门在中州还算不上大的势力。一日,天降大雨,他从商铺返回府中,见门前的檐下,有一位胖大的僧人在避雨,便将僧人请进屋中,好吃好喝招待。细问之下,得知僧人法号玄远,来自郑州嵩山少林寺,云游四海,普度众生。
南宫武久闻少林寺之大名,却因路途遥远,未曾去过,今见寺中僧人,顿感亲切,一番长谈,深被僧人广博的见识所折服。僧人见南宫武如此年幼,却是知书达理、谈吐不凡,觉此人他日必成大器,又见他眼圈发黑,脚步虚浮,便询问缘由。
南宫武回道,大概是因睡眠不足所致,家中产业庞杂,多处于上升阶段,而父亲手下又缺少人手,因此,我与兄长便各自打理了几家铺子,加之每天还要习文练武,这睡觉的时间,便只剩了三个时辰。
僧人道,你我今日相逢,也算缘分一场,贫僧从不白白受人恩惠,便将我佛门的禅息法传授于你罢!休息三个时辰,足够你一日精力充沛。
南宫武欣喜若狂,按僧人指点,以禅息法入眠,但只坐了一会儿,便觉浑身难受,再也坐不住。僧人道,施主心事太重,且身体尚未适应要领,如此,只会越睡越乏,难以入眠,还需静下心来,好生习练。
南宫武道,大师每日也以这禅息法入眠吗?
僧人点头应是。
南宫武又道,每日只睡三个时辰?
僧人道,贫僧三日睡两个时辰。
僧人走后,南宫武每日按其所授禅息法入眠,开始尚不习惯,醒来时便觉浑身酸痛,后来渐渐摸清了门道,每日睡够三个时辰,便精力旺盛,做起事来效率也有显著提升。
或许真如僧人所说,南宫武每日记挂的事情太多,三个时辰便已是他保证精力的最低限,再也无法缩短了。
除了提高睡眠质量之外,这种禅息法,给南宫武带来的另一个好处,便是出门在外时,更利于防护自身安全。
倘若遇到贼人突袭,坐姿的出招速度,能比躺姿快零点几秒,而正是这零点几秒,往往决定着最后活下来的,是哪一方。
大概是这一天过得太紧张,南宫武即便以禅息法入睡,却还是做梦了。这在以前是绝未有过的事情。
梦里很乱。刀光剑影,哭逃喊杀,残尸遍地,血流成河,他率领着锱铢门的门人,与敌人拼死苦战,却又不知敌人是谁,亦不知为何而战。
他的脚下堆积着厚厚的尸体,像一座小山,他站在这座尸山的顶部,挥舞着手中的钢锏,一下一下地朝着冲上来的敌人狠砸。红色的鲜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在眼前四散飞溅。他的头上、脸上都是血,衣服也被鲜血染得尽红,活脱脱一个血人。
他看到父亲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只紧握着手中长剑,晃着肥胖的身躯,疯了一般乱砍乱刺。有刀剑落在父亲的身上,父亲却不管不顾,只与敌人以命相搏。
他大吼一声,跳下尸山,杀入敌群中,救下父亲,却听远处轰隆声不断,抬眼望,见是一片血色的海潮,正翻卷咆哮而来。兄长的头颅,在潮水中上下沉浮,龇牙咧嘴,好不骇人!
“快走!”父亲朝他大喊。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他朝父亲大吼。
“这是命令!”父亲歇斯底里地喊道,用力将他朝外推去,“我将与锱铢门共存共亡,而你,是我南宫世家最后的血脉,活下去,他日替为父报仇,重振锱铢门!”
“啊——”他厉声痛呼,眼含热泪,但父命难为,只能咬牙应道:“孩儿、遵命……”他抹了一把眼中的泪水,而后抡双锏杀出重围,直朝锱铢门外跑去。
潮水转眼即至,将锱铢门化作一片血的海洋。他拼命朝前奔跑,却听身后轰隆声不断接近,却是那潮水奔着他席卷而来。
“这是你的宿命,你逃不掉的!”大水中,一个声音犹如地狱魔音,传入耳际。伴着这个声音,轰隆声越来越响,其中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咚、咚”声,宛如一个巨人的脚步,震得地动山摇。
脚下的震动令他站立不住,一个踉跄险些摔倒,急忙用钢锏撑住身子,然而这一耽搁,身后潮水已然赶至,他扭头一望,但见血色的浪头中,鬼影幢幢,它们挥舞着尖牙利爪,随着血水迎头扑下……
他骤然惊醒。
他随手抓过竖在身旁的钢锏,环顾四周,当确定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境时,身子便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瘫坐回去。他将钢锏杵在身前的地面上,双手握着锏柄,额头抵着手背,一颤一颤地抽泣起来。
仇恨,像火一样灼烧着他的心,令他一阵阵的刺痛。梦里的场景,他无法释怀,那灭门之痛,将是他此生不能承受之重。
白天,在人前,他必须时刻摆出一副坚强稳重的模样,因为,他是锱铢门的公子,肩上挑着的,是整个锱铢门的复兴大业。他要将信心与希望传递给追随自己的下属,要将豪情与斗志展示给截杀自己的敌人,这些,都要求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形势的脆弱与柔软。
然而,一到晚上,每一个午夜梦回,他的心都在滴血。
他将脸埋在臂窝,用手臂狠狠擦了一把湿润的双眼,却突然注意到,耳畔有一种“咚、咚”的声音在回响。他有些纳闷,自己明明已经醒来,为何那梦里的“咚、咚”声,还在耳边回绕?
不对!他猛地清醒过来。那不是梦里的声音,那声音就从前方传来!
他猛然抬头,望向了前方的林子。
篝火已近熄灭,只剩几截火炭,支撑着一缕火苗忽闪跳动。借着微弱的火光,他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树丛间冒出头来。那黑影身高至少有一丈,魁梧的就像一座小山。它以双足踏地,正伸出双臂,拨开身前的灌木,朝空地这边走来,随着迈动步子,脚下便有“咚、咚”的声音传出,那沉重的身体,将地面震得都在颤动。
这是……什么怪物?南宫武望着黑影,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未敢轻举妄动,只下意识地朝身侧不远的大树望去——那里,该是老丐值夜的位置——他在想,怪物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为何守夜人却没有提前预警?
树干上空空的,没有老丐。
他又急又恼:这老丐不好好守夜,关键时刻跑去了哪里?当真是害人不浅!
他又望向身侧。屠夫和镖师躺在地上,睡得很沉,根本没有察觉到怪物的出现。而掌柜的位置,也是空的。
掌柜的又去了哪里?
他有些担心起来,这二人同时失踪,怕是有些不对劲了。然而此刻情势危急,已容不得他细想,因为那怪物已从树丛后跨了出来,它喷出一股鼻息,晃着庞大的身躯,朝着众人的方向走来。
这次,南宫武看清了,那怪物圆眼獠牙,浑身生着黄白相间的皮毛,其模样有些像一头直立的熊,但下肢却比一般的熊长着许多,头颅与脖颈也要长着一些,这种体态,使得它看起来与人类倒有几分相似。
熊罴!这两个字迅速从他的脑海中划过。
这是一种近乎绝迹的生物,他并未见过实物,却在书中见过相关记载。《尔雅·释兽》有言:“罴(音同‘皮’),似熊而黄白文,长头高脚,憨猛多力,能拔树木,掠食牛马。”
“能拔树木,掠食牛马”八个字,令南宫武印象尤为深刻。他一直怀疑这八个字的真实性,认为是古人夸张杜撰,但今日见了这般壮猛的身躯,便丝毫不敢再怀疑了。
熊罴大概是循着生人的气息过来的,然而接近的时候,又被空地上的那团火苗吸引了注意力。它不知道那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有些好奇,也有些畏怯,只晃着身子,一步一步地朝篝火旁靠近。
南宫武没有动。面对这种庞然大物,他认为自己贸然出手并非明智之举。他听人说过,熊罴之类的动物,拥有十分灵敏的嗅觉,但听觉和视觉却很迟钝,如果猎物一动不动,它会错误地认定猎物是一具尸体,而对于尸体,如果它没有处于极度的饥饿中,是不会吃的。
从它目前不急不忙的动作来看,它并非处于饥饿状态。如果己方一直保持这种一动不动的状态,它会不会觉得无趣,很快离开?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它,同时在心里默默祈祷。
熊罴四肢着地,探着身子,歪着脑袋,打量着那一小堆火苗,像一个充满求知欲的孩子。南宫武就坐在篝火的一侧,与它离着不过五六尺远,能清楚地闻到它身上的骚臭味。
熊罴打量一阵,便伸出前爪,朝火苗拨去。只听“滋啦”一声响,伴着毛皮烧灼的焦糊味,一缕黑烟飘散而起。它痛得一挥爪子,将几截火炭打落一旁,火星四溅。
说来也巧,一枚燃着的火炭,正朝南宫武的头脸飞来。南宫武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侧身歪头,将火炭躲过。刚要回正身子,忽觉情况不对,立即僵在原地,如一尊歪斜的木偶,一动也不敢动了。
却是那熊罴听到异动,猛地转过头来。它直愣愣地盯着南宫武,似乎在琢磨,这东西刚才似乎是端端正正的,为何转眼功夫,便又歪歪斜斜的了?它迈动步子,到了南宫武身前,低下头,呼扇着鼻翼,在南宫武的身上嗅来嗅去。
腥臭的气味扑面而来,呛得南宫武几乎落下泪来。他屏住气息,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只盼着它快些离去。然而这熊罴被他刚才的动静闹得糊涂,只嗅来嗅去的不肯离开。他心中恼火,将手中钢锏攥紧,心想你若再不走,我便照着你的脑壳狠狠来一下。却又不知它这皮糙肉厚的,钢锏能否伤得了它。
南宫武歪斜着身子,眼看就要坚持不住,忽听身旁传来一阵怪响,宛如母猪拱食。熊罴一愣,猛地将头扭了过去。
南宫武松了口气,也顺着声音的源头望去,见是那屠夫没心没肺的,竟越睡越香,吭吭哧哧地打起了呼噜,不由得又气又急。
熊罴弃了南宫武,转而走到屠夫的身旁,低头瞅着屠夫的脸。屠夫张着大嘴,哈喇子都快流了出来,随着呼噜声,肚子一起一伏,像个吹了气的皮球。他睡得正香,哪里知道身旁有个大家伙,正像看情人似的看着自己?
熊罴伸着脖子,用长长的嘴巴拱了拱屠夫的肚子。屠夫的身子在地上晃荡了两下,这让他从沉睡中苏醒了些。他伸出手,无意识地去推身旁碰到自己的东西,却觉毛茸茸、热乎乎的,他觉得有些不对劲,迷迷糊糊地睁眼一望,吓得“呜嗷”了一声。
他的几根手指,正塞到了熊罴的鼻孔里。
熊罴猛地扬起头来,发出一声暴吼,震得山林都颤抖起来。口中喷出的涎液,喷了屠夫一脸。
屠夫吓得几乎昏死过去,起身便要逃,那熊罴却已抬起前爪,直朝他的肚子狠狠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