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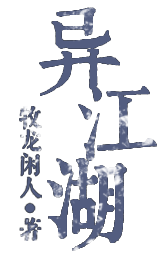
 第六章 唐门公子
第六章 唐门公子
南宫武率众迎出财源客栈的时候,铁檀镖车就停在门口,像一头气势汹汹的巨兽。
镖车一侧,并排站着一青一银两个身影。那二人装束古怪,一个枯面青眼,手摇黑扇,背上背着个宽口细腰的青色木筒;一个银衫如鞘,身形如剑,双目寒光炯炯,口鼻处遮着半副明光晃晃的银质面具。
这二人,南宫武未曾见过,但从他们周身向外流露出的气势,便足以令他断定,二人必是高手。他迎上前去,抱拳拱手道:“在下锱铢门南宫武,敢问二位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青衫人抱拳还礼道:“在下唐飞絮,来自巴州唐门。”又一指身边银衫人,道:“这位是我的同门师弟,唐飞镰。”
在听到“唐门”二字的瞬间,南宫武心头一动。
唐门,地处八台山,乃是中州一大豪门。这个家族式的门派,他虽未与之亲身打过交道,但关于它的传闻,却早已将他的耳朵磨出了膙子。此门派成立已愈千年,经数十代的动荡与发展,终以暗器、毒药、奇门遁甲三大绝学称霸巴州,雄踞天下。门派最重血缘,家传武学决不传于外人,历代惊才绝艳之辈频出,其门主、副门主之下,传有唐门七子,皆是手段奇诡之辈,实力雄厚。
唐飞絮,唐飞镰,这两个名字,南宫武一点也不陌生,正是唐门七子中的四公子和七公子!
南宫武有些讶异。唐门早年间发展迅猛,是以眼空四海,曾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州各大门派,终因寡不敌众,险遭灭门。此后,唐门沉寂百年,门下弟子闭门隔世,苦研功法,使唐门得以东山再起。但再度兴盛的唐门,一改往日飞扬跋扈的作风,门下弟子深居简出,除了一些江湖大事,很少会涉外走动,而像唐门七子这类级别的人物,更是鲜少在江湖中露面。此番,唐门七子中的两位一同出现,还驾着自己被劫失的镖车,却是何意?
南宫武心中盘算,脸上却丝毫没有带出来,挂着一脸的微笑道:“唐门七子,个个皆是人中翘楚,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久仰久仰!”
“不敢当、不敢当!”唐飞絮客套道,而后侧身指了指镖车,“这驾镖车,其上打着锱铢门的旗号,可是南宫公子所有之物?”
南宫武道:“此物正是在下所有!今日午后,我率人押运镖车,行经黑沙江悬索桥,突遇黑峰五鬼拦路,苦战一番,仍是被五鬼将镖车夺了去。却不知二位从何处寻得?”
唐飞絮道:“这便是了。方才,我与师弟途经黑沙江,见有贼人带着镖车顺江而下,鬼鬼祟祟,令我二人心中生疑,于是出手将之拦下,细一询问,才知这镖车乃是她从锱铢门手中劫掠而得。我二人斩杀了此贼,沿途扫听,得知公子行往财源客栈,这才特地将镖车给公子送还回来。”
南宫武道:“唐门二位公子仗义相助,南宫武感激不尽。”
唐飞絮道:“南宫公子不必客气。公子千里迢迢来我巴州地界,当属贵客,既有贼人敢对公子无礼,我唐门又怎会坐视不理?还请公子查验厢中镖物,看是否齐全安妥。”
南宫武道:“唐门凛然正气,护得巴州一方太平,着实令在下钦佩。但这镖车,便不必查验啦!”
唐飞絮疑道:“为何?”
南宫武道:“实不相瞒,在下这镖车,乃是空的。”他索性将空镖的事情直接说了出来,既显得自己坦诚,又能稍稍挽回些锱铢门的颜面。
唐飞絮笑道:“我便说嘛,堂堂锱铢门,怎会让一群毛贼将镖物劫了去?原来是公子特意安排。公子好智谋,在下佩服、佩服!”
南宫武道:“一些唬人的小把戏,不足挂齿。天色不早,二位不如随我到楼上,我备些酒菜,咱们边吃边谈。”
唐飞絮与唐飞镰对视一眼,而后朝南宫武道:“那我二人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言罢,随着南宫武,迈步走入财源客栈。
两名镖师将镖车停去客栈后院,离开的时候,南宫武注意到,一楼大厅中那几桌可疑人员,盯着镖车,似乎有些跃跃欲试,直到一个头目打扮的人用双指轻叩两下桌面之后,他们才安定下来。
“哎呀南宫兄,你瞅瞅,这下过雨之后,苍蝇蚊子臭虫钻得满屋都是,将这挺好的一家客栈弄得臭气哄哄,着实让人生厌。”唐飞絮一边走,一边打开扇子,象征性地朝周围扇了扇。
南宫武明白,唐飞絮是在指桑骂槐,以蚊虫比喻大厅中的这些毛贼。以唐门七子的修为,毛贼们私下的小动作,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进门的一瞬,便已发现了这群人来意不善。
屋内看不到蚊虫之类,然而,在唐飞絮挥扇的同时,南宫武却出乎意料地听到了“嗡嗡”的蚊蚋振翅声。那声音从耳畔一掠而过,直朝身后飞去,因极细极微,令人难以察觉。
这蚊虫声一定是有问题的。南宫武心想。他有心回头望上一望,却又生生忍住。作为锱铢门的二公子,在其他门派跟前,他代表的便不再是自己,而是整个锱铢门。这个时候回头,会给锱铢门掉价。
当众人穿过大厅,来到楼梯下方的时候,南宫武听到身后有人发出了一声轻哼;当众人迈上楼梯,来到二楼的时候,那种轻哼已化作了痛吟,且是多个人的痛吟;当众人沿着廊道,走到雅间门口的时候,楼下的痛吟声已然成片响起,低头望,便见那几桌毛贼,正在拼命地挠着脖脸、抓着身子,如同浑身生满了跳蚤,更有甚者,已然躺倒在地,一边打滚,一边哭哭笑笑,似乎痛痒难耐。
众人心中诧异,唐飞絮却是面上带笑,他站在楼上,朗声朝楼下道:“锱铢门的镖物,由我唐门保了,若有哪个再敢打南宫公子的主意,我唐门决不宽饶!这次小惩大诫,想活命的,速速滚远,回家以温水泡入金叶菊,擦洗浸泡全身,三个时辰后,痒消痛减。”
楼下群贼听了,如蒙大赦,呼号着狼狈逃窜,转眼便没了踪影。
“素闻唐门有活毒之术,以虫伤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南宫武赞道。
南宫武知道,唐门中有三支流派,主攻方向分别为暗器、毒药和奇门遁甲,其中这毒药,又分死毒和活毒。死毒为药,活毒为虫,刚才上楼前的那阵蚊蚋振翅声,让他猜测出,唐飞絮所用,必是活毒。不过,唐飞絮操毒的手法实在高明,自己近在咫尺,也仅险险听到一丝细微的动静,而楼下那些毛贼,更是在不知不觉间悉数中招,转眼丧失了战斗力。这着实是一种以一敌百、杀人于无形的技法。
唐飞絮笑道:“雕虫小技,让他们受些皮肉之苦,也好长些记性。”
众人进入雅间,袁崇宝命人将残席撤下,转而重新摆上好菜,款待唐门二人。
唐飞镰话语不多,整个人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只有当旁人主动问他话时,他才会简单地应付几句,一张脸几无神色变化,让人猜测不透在想些什么。唐飞絮却是很健谈,与南宫武交谈得也很投机。席间,他问起南宫武,锱铢门总商会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南宫武叹了口气,言锱铢门招惹了南海鲛族,鲛族引来灭世海水,将锱铢门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听南宫武详细讲完经过,唐飞絮也叹了口气。此中是是非非,他身为外人,并不好多做评说,只能宽慰了几句,而后道:“不知南宫兄接下来有何打算?”
南宫武道:“家父耗费毕生心血,使锱铢门一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如今骤然陨落,我这个做孩儿的,断然不会苟且偷生。锱铢门主干虽殁,分支尚存,我将前往巴州分会,以巴州分会为基,号召锱铢门其余各州分会,卷土重来,重振锱铢门旧日雄风!”
唐飞絮道:“南宫兄有鸿鹄之志,勇气可嘉。然而恕在下直言,巴州一带山险水恶、民风彪悍,南宫兄一路前行本就艰难,为何非要带上一驾镖车,平白拖慢了速度?我看那盛放镖物的车厢,不过四五尺高,便是装满了金银,又能有多少?如此劳师动众,怕是不值。”
南宫武心中暗嘲:“唐门中人久居僻壤,怕是不太了解外界的繁华,这世上的奇珍异宝,又岂是金银能够比拟的?”刚要出言回答,忽又觉得,唐飞絮贵为唐门七子,并非见识浅薄之人,似乎不应该说出这样掉份儿的话。
除非,他在装糊涂。
一念及此,南宫武悚然而惊。没错,他是在装糊涂。他故意用这个粗陋的问题来引导自己,将话题转移到镖物上,从而探听关于镖物的信息。
这个念头在南宫武的心中一闪而过,于是,那即将脱口而出的言语又被他咽了回去。他多留了个心眼,只换言道:“唐兄见笑了。所谓敝帚自珍,有些东西,对旁人而言可能一文不值,但对于自己,却是意义非常呢!”
他说话的同时,注意到对面的袁崇宝松了口气,朝自己微微点了一下头,眼神中带着赞赏。这说明,他也察觉到了对方探听镖物的意图。
见南宫武守口如瓶,唐飞絮便不好再继续深问,只点头道:“南宫兄此言极是。”
众人边吃边谈,待到吃完了饭,已是掌灯时分。袁崇宝为众人安排下客房,众人劳累一天,各自回屋中早早休息。
唐飞絮表示,唐门与巴州分会相隔不远,双方正好同路而行,相互照应。对此,南宫武心中虽有不愿,脸上却装作一副高兴的模样。
夜里,袁崇宝敲开南宫武的屋门,进屋后将门窗关严,低声道:“公子,按您的吩咐,我已令人细细查验了镖车。”
“如何?”
“车厢上的锁头,被人强行打开过。”
南宫武冷笑道:“唐门,果然目的不纯。”
“没错。”袁崇宝应道,“他们一早便知镖车是空的,却假装不知情,将空镖送还回来,以便找寻机会与我们接近。公子,属下有些担心,以唐门在巴州的势力,若出手抢夺镖物,咱们怕是难以应付。”
他的话,虽然有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所说却是实情。南宫武明白,凭自己这帮人的实力,别说整个唐门,就连唐飞絮、唐飞镰这两个人,都应付不来。
袁崇宝见南宫武沉默不语,便道:“公子,属下有一计。那唐门二人此刻应已睡熟,不如我们趁夜偷闯进去,将这二人斩杀,以绝后患!”
南宫武望了他一眼,诧异于这个客栈掌柜,竟能如此心狠手辣。
“我们杀不了。”南宫武摇了摇头,“即使杀得了,也不能杀。”
袁崇宝一阵默然。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有些偏激了,这绝对不是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比自己更为冷静。
“要不然,属下继续以稗草车押运镖物,即刻启程前往巴州分会,神不知鬼不觉,将唐门二人甩掉。公子以为如何?”
南宫武又摇了摇头,道:“此计太过冒险,你要知道,除了唐门,还有其他势力在盯着我们。财源客栈的一举一动,怕是都在贼人的注视之下,你赶着稗草车离开,无异于自投罗网。”
袁崇宝叹息道:“公子,那该如何是好?”
南宫武道:“袁叔,您方才说,以唐门在巴州的势力,若出手强抢镖物,我们将万难应付。可事实上,唐门并未这样做,而是颇费周章地接近我们,您觉得,这是为何?”
袁崇宝想了想,道:“公子布下九舆疑阵,他们并不确定公子所率领的这支队伍,一定是押运真镖的队伍。所以,他们接近我们,目的是套出真镖的所在,一旦确定真镖在我们手中,定会出手抢夺。”
“是的。”南宫武道,“作为豪族大派,唐门自然要顾忌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其行事作风亦绝非一般草寇可比。在确定真镖之前,他们不会盲目出手,以防到头来空忙一场,还白白得罪了锱铢门。以此看来,我们暂时并无危险。相反,我还觉得,有唐门一路同行,并不是一件完完全全的坏事。巴州一带多有悍匪,唐门与我们结伴而行,对沿途匪众倒是个震慑,可为我们减去一些麻烦。”
袁崇宝听着南宫武的分析,心中越发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且不论年轻人所说的正确与否,单看他这份临危时的胆识和气魄,便已非常人能及。
“与唐门二人同行,怕是他们难免会弄出些幺蛾子!”袁崇宝道。
南宫武一笑,道:“那便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这自信豁达的一笑,令袁崇宝益发觉得此人捉摸不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