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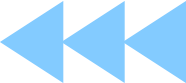
人们经常试图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当一个推销员夸你长得漂亮时,他是真心这样认为,还是只是在奉承你?你精心准备后去赴一个约会,但对方似乎对你不感兴趣,这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位父亲在责骂他的女儿,这是因为他脾气粗暴,还是因为女儿做了错事?人们经常思考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尤其是当一些预料之外的事件或消极事件发生时(Weiner,1985)。正如开篇案例所示,在惊人的惨剧发生之后,人们对凶手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猜测和讨论。社会心理学家构建归因理论,描述人们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起因的方式。
海德(Heider,1958)被公认为“归因理论之父”,他对归因的讨论在现今的研究中仍占据一定的位置。海德认为,人们如同业余的科学家,以“朴素心理学”或“通俗心理学”的方式解释日常生活事件。他认为人们在尝试解释他人行为时,有可能做内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即认为该个体的行为原因与其人格、态度或个性有关,也叫性格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也有可能做外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即认为该个体的行为原因与其所处的情境有关,也叫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例如,当我们分析责骂女儿的父亲行为的原因时,如果认为这是由于父亲本人脾气粗暴或不善于管教孩子,就是在做内部归因;如果认为这是由于女儿与行为不端的男性交往,就是在做外部归因。这种简单的内部和外部归因二分法是海德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并且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研究发现,已婚夫妻经常分析伴侣的行为,特别是对方的消极行为(Hewstone & Fincham,1996)。婚姻美满的夫妻倾向于对伴侣的消极行为做外部归因(“他之所以说话刻薄是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太大”),而婚姻不幸的夫妻则对伴侣的消极行为做内部归因(“他说话刻薄是因为他是个自私的混蛋”或“他说话刻薄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类似地,当伴侣表现出积极行为时,婚姻美满的夫妻倾向于做内部归因(“他送花给我是因为他真心爱我”),婚姻不幸的夫妻倾向于做外部归因(“他送花给我是因为碰巧有人给了他一束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模式对婚姻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将好事做内部归因、坏事做外部归因有助于促进关系,而相反的归因模式则会产生痛苦,破坏婚姻关系。
海德还认为,尽管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都有可能,但比较而言人们更偏好做内部归因。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人身上,往往容易忽略情境,倾向于认为行为起因是个体的性格。海德提出的二分法和人们对内部归因的偏好影响重大,后续研究将对这两个问题不断进行探讨,下文还会进一步地讨论。
琼斯和戴维斯(Jones & Davis,1965)提出对应推论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描述了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从他人的行为推断其特质。他们指出,人们在对他人行为进行推理时,会考虑是否满足一些条件,如果满足则做性格归因,如果不满足则不认为行为代表这个人的性格。第一个条件是社会赞许性,社会赞许的行为往往不能清楚表明个体的性格,而低社会赞许的行为则可以揭示真正的个性。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工作面试中表现得友好和外向,我们很难确定他究竟是性格如此,还是为了获得工作而有意这样表现;但如果他在面试中表现得内向、害羞和退缩,我们可以更肯定地推测他确实性格内向。第二个条件是行为是否是自由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在特点,但如果是个体被迫做出的行动,我们很难知道个体真实的性格和态度。第三个条件是非共同效果(noncommon effects),即由某种特殊的原因而不是其他任何明显的原因所引起的效果。琼斯和戴维斯认为,我们应该关注他人产生非共同效果的行为,因为根据这些行为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例如,假设一个你不太熟悉的朋友刚刚订婚,她的未婚夫长得很帅,性格很好,很富有,并且很爱你的朋友。通过她与这个人订婚这件事,你能够了解她什么呢?但如果她的未婚夫没有稳定的收入,性格特别讨厌,对你朋友也不太好,唯一好处就是长得帅。那么她与这个人订婚能告诉你什么?你可以肯定,她选择丈夫时更注重外表吸引力而不是性格和财富等其他因素。因此,根据琼斯和戴维斯的理论,在他人的行为是社会赞许性低的、自由选择的,以及产生非共同效果时,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关于他人性格特点的推断。需要指出,琼斯和戴维斯的理论阐述了在何种条件下,更适合根据他人行为推论其特质,或者说提出了有助于理性归因的建议。而人们实际的归因不一定满足琼斯和戴维斯所提出的条件,因而可能会出现偏差和错误,下文将会提及。
凯利(Kelley,1967,1973)认为人们在进行归因时,会注意并思考多种信息,他的归因理论被称为共变模型(covariation model)。凯利指出,为了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归因,人们对可能原因的存在与否和该行为的发生与否两者之间的模式,进行系统化的观察。在归因时,应该收集和检查三种重要的共变信息,分别是一致性(consensus)信息、独特性(distinctiveness)信息和一贯性(consistency)信息(Kelley,1967)。一致性信息是指对于相同的刺激,其他人做出与行为者相同行为的程度。独特性信息指的是,某个行为者对不同刺激做出相同反应的程度。一贯性信息是指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某项行为出现于同一行为者和同一刺激之间的频率。例如,假设你在一堂课上看到一名学生在睡觉,你会把他的行为归因为什么?根据凯利的理论,你应该思考三个问题:其他学生是否也在这堂课上睡觉(一致性信息)?这名学生在其他课程的课堂上是否也睡觉(独特性信息)?这名学生是否总在这门课程的课堂上睡觉(一贯性信息)?
凯利认为,结合这三种信息,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归因。当行为的一致性和独特性都低,但一贯性高时,我们很可能会做内部归因。例如,如果其他学生在这堂课上不睡觉,这名学生在其他课程的课堂上也睡觉,并且这名学生总在这门课的课堂上睡觉,我们就会认为这名睡觉的学生是个懒惰、不认真听课的人。当行为的一致性、独特性和一贯性都很高时,我们很可能会做外部归因。例如,如果其他学生也在这堂课上睡觉,这名学生在其他课程的课堂上不睡觉,并且这名学生总在这门课的课堂上睡觉,我们就会认为原因出在这门课程上,有可能是课程比较乏味。当行为的一贯性低时,我们无法清楚地做内部或外部归因,我们会采取某种特殊的外部或情境归因,认为由于环境中的某种特殊因素导致了这一行为。例如,如果这是这名学生第一次在这门课的课堂上睡觉,我们会认为也许他昨晚有事没有睡好,导致今天上课时睡觉。结合这三种信息做出的归因见表2.1。
表2.1 共变模型:为什么这名学生在上课时睡觉?

共变模型假定人们以理性、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因果归因。凯利的理论引发了大量研究来检验这一看法是否正确。结果证实,人们确实经常以共变模型所预测的方式进行归因(例如:Fösterling,1989;White,2002)。但是,存在两种例外情况。首先,人们并不总能拥有所有三类信息。第二,研究表明,独特性信息和一贯性信息对人们的因果归因影响较大,而一致性信息经常被忽略。在一个实验中,被试阅读了关于两个研究报告的信息,这两个研究报告的结果令人惊讶(Nisbett & Borgida,1975)。例如,在一个研究中,15名被试中有11名被试没有帮助一名明显疾病发作的病人,直到这名病人窒息。在被试阅读这些信息后,研究者要求被试评价救助病人研究中一名始终没有提供帮助的个体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该人的个性因素决定的。结果发现,尽管被试得知研究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反应是类似的,这种一致性信息却没有起作用,没有使得他们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情境归因(Nisbett & Borgida,1975)。另外一些研究也证实,人们在进行归因时更多依赖于独特性信息和一贯性信息(Wright,Luus,& Christie,1990),独特性信息和一贯性信息对因果归因的影响是一致性信息的几倍(McArthur,1972)。另外,凯利还探讨了一条影响因果归因的原则,叫做折扣原则(discounting principle)(Kelley,1972)。折扣意味着,当其他潜在原因同时存在时,某个行为原因的重要性将降低。例如,一天早上你的老板表扬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你认为老板真心满意你的工作,心里非常高兴。吃过午饭后,老板把你叫去问你是否愿意承担一项额外的、非常困难的任务。现在你不再那么重视第一个可能的原因(老板真心满意你的工作),因为存在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即老板想让你同意承担额外的工作才表扬你。研究表明,折扣原则确实影响人们的归因(Morris & Larrick,1995),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十分普遍(McClure,1998)。
总之,凯利理论的假定是人们理性地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系统地、逻辑地进行因果归因。尽管人们的归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凯利的假设,但在很多时候人们的实际归因会偏离归因理论的预测,忽视一致性信息,以及出现错误和偏差,例如基本归因错误。
除了内部和外部原因之外,人们在归因时还会考虑其他维度:影响行为的因素是跨时间稳定的,还是随时间而变的?这些因素是否是可控的,如果想改变或影响它们,是否可以做到(Weiner,1993,1995)?这两个维度独立于之前讨论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行为的某些内部原因,例如人格特质和能力,是非常稳定的(Miles & Carey,1997)。而某些内部原因则通常是易变的,例如动机、健康和疲劳。类似地,一些外部原因是可控的,例如如果愿意,就能够增加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一些外部原因则是不可控的,例如残疾和慢性疾病。证据表明,在试图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原因时,人们会关注这三个维度:内部/外部、稳定/不稳定、可控/不可控(Weiner,1985,1995)。这些考虑也影响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结论,例如某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Graham,Weiner,& Zucker,1997)。
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多数人都持有一种假定,即认为人们的所作所为根源在于他们的内在性格和特质,也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们所处的情境。这种推论人们的行为与他们的性格相一致的倾向叫做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 bias)(Jones,1979)。而社会心理学家一再证实,社会情境对行为的影响非常巨大。人们在对他人行为进行归因时,高估内在性格因素、低估外部情境因素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被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Ross,1977;Ross & Nisbett,1991)。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琼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1967)让大学生阅读一篇短文,内容是支持或反对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研究者告诉一半学生,作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告诉另一半学生,作者对于自己的立场无法选择,他被指定写支持或反对的文章。在前一种条件下,大学生可以确定地推测短文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态度。而在后一种条件下,由于作者是按照指派的立场进行写作,因此文章内容不能反映作者的态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还是倾向于认为,文章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态度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卡斯特罗。被试只是做了一些小的调整,而对作者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卡斯特罗仍是根据其写作内容来进行评估,认为这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想法(见图2.1)。

图2.1 基本归因错误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进行了一项模拟测验游戏(Ross,Amabile,& Steinmetz,1977)。研究者随机指定一些大学生扮演考官,另一些大学生扮演考生,还有一些大学生充当旁观者。研究要求扮演考官的被试编制一些证明自己知识面丰富的难题,于是这些被试想尽办法出一些自己知道答案但别人很可能不了解的问题。结果很容易预料,那些扮演考生的被试难以回答出这些问题。最后,研究者要求所有被试对扮演考官和考生的被试的学识打分。在这样的情境中,提问一方显然是有利的。但是,扮演考生和旁观者的被试却给扮演考官的被试很高的分数,认为他们确实懂得很多(见图2.2)。

图2.2 对考官和考生一般知识的评价
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个性因素为什么会被称作基本归因错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内部归因都是错误的,因为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确实反映了其个性。然而基本归因错误的重点是,人们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倾向于低估或忽视情境的作用。有很多证据表明,社会情境对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主题。但是,当将这样的证据呈现给人们时,例如告知被试,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时间匆忙时不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被试仍然将一名个体的不帮助行为归因于个性(Pietromonaco & Nisbett,1982)。这与前文所述人们忽视一致性信息的倾向是一致的。后续研究不断证实,即使行为很明显地受到环境的限制,人们还是坚持做内部归因(例如:Lord,Scott,Pugh,& Desforges,1997;Newman,1996)。归因的重要之处是它会影响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政治立场。例如,那些认为贫穷和失业是由个人原因造成(例如懒惰和不努力)的人们,通常不支持帮助这些人的政策;相反,那些将贫穷归因于社会原因(例如缺少机会、受歧视)的人们,则更支持给予穷人帮助的政策(Weiner,Osborne,& Rudolph,2011)。
为什么人们会出现基本归因错误?原因之一是,当我们尝试解释他人行为时,我们注意的焦点往往是人,而不是周围的情境(Baron & Misovich,1993),并且影响他人行为的情境因素通常是我们看不到的(Gilbert & Malone,1995)。因此,情境信息难以获得,而人却有很高的知觉显著性(perceptual salience),容易成为注意焦点且貌似很重要,从而我们倾向于认为人是引起行为的唯一合理和符合逻辑的原因(Heider,1958)。在一项研究中,2名男学生假装进行一段对话,实际上他们是实验者的同谋,对话完全是预先规定好的(Taylor & Fiske,1975)。在每轮实验中,有6名真实的被试参加,他们坐在围绕对话两人的指定的位置上(见图2.3)。其中2名被试分别坐在2名对话者的两侧,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名对话者;另外4名被试分别坐在2名对话者后方,他们可以看到一名对话者的背面和另一名对话者的正面。通过这种安排,研究者操纵了被试可以看得最清楚的对话者,也就是视觉上最显著的人。坐在对话者两侧的被试(观察者1和2)能够清楚地看到对话者A和B,坐在对话者A后方的被试(观察者3和4)能够清楚地看到对话者B,坐在对话者B后方的被试(观察者5和6)能够清楚地看到对话者A。在2名实验同谋的对话结束之后,被试回答有关2名对话者的问题。例如,谁主导对话的进行以及谁选择谈论的主题?对话的结果如何?从被试的回答可见,他们看得最清楚的人,被他们认为对对话最有影响(见图2.4)。虽然实际上所有被试听到的对话是完全相同的,但只看到A正面的人(观察者5和6),认为是A主导对话并选择谈话主题;只看到B正面的人(观察者3和4),认为是B主导对话并选择谈话主题;而能够清楚地看到A和B的被试(观察者1和2),认为两人共同主导对话。

图2.3 操纵知觉显著性的实验


图2.4 知觉显著性的影响
由于人们的注意焦点更多地放在人身上,而不是周围环境,并且环境很难看到或了解,所以人们普遍会低估或忽视环境的影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本归因错误如此普遍。那么,为什么我们把注意焦点放到人身上,就会使得我们高估人对自身行为的决定作用?原因涉及在“社会认知”一章将会详细讨论的心理捷径之一,即所谓的锚定和调整启发式(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锚定和调整意味着人们在做判断时,从一个参考点开始,然后从这个参考点做出调整之后做判断(Tversky & Kahneman,1974)。问题在于有时参考点是武断和没有意义的,而人们的调整往往不够充分,过度地“锚定”在最初的参考点上。基本归因错误很可能是这一启发式的一项副产品。人们在进行归因时,经常会以自己注意的焦点作为起始点。例如,当我们看到某人文章中的观点强烈支持卡斯特罗的统治时,我们最初的倾向就是从个体的性格方面来解释,认为该人强烈支持卡斯特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立场是被指定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因此我们考虑到情境的作用,对我们的归因进行调整。然而,锚定和调整启发式的固有问题是调整不够充分。因而,在琼斯和哈里斯的实验中,即使被试知道作者无法自由选择文章主题,也仍然认为作者所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自身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从短文主题代表作者观点这一起始点开始,进行了不充分的调整(Quattrone,1982)。
有研究者根据已有证据认为,人们在归因时经历的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Gilbert,1989,1991,1993)。在第一阶段,我们首先做内部归因,即假定他人行为的起因是个性因素。在第二阶段,我们再试着考虑他人所处的情境,对这个内部归因进行调整,但是这一阶段的调整往往不够充分。通常第一个阶段的内部归因迅速且自发地进行,而第二个阶段根据情境进行的调整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有意识注意的参与。因此,如果我们在解释他人行为时先入为主,或者忙于其他事情而无法集中注意力,或者不愿意想得太多,或者很疲倦等,就很有可能跳过第二个调整的阶段,直接做出极端的内部归因(Gilbert & Hixon,1991)。而如果我们在做出最终的归因之前有意识地减慢速度并谨慎地思考,或者希望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归因,或者怀疑目标对象的行为时,我们就会进入归因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对最初的内部归因进行一定的调整(Burger,1991)。
需要注意,将行为归因于个体的内在因素并不见得一定是错误的。有些时候,将行为归因于内部因素是有效率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准确性(Gilbert & Malone,1995)。但问题在于,即使在情境的作用非常清楚时,人们也会表现出这种偏差。例如,尽管我们知道被指定的立场不能代表作者或演讲者的真实观点,在测验游戏中担任考官是有优势的,我们仍然会犯基本归因错误,并且往往认识不到这种偏差的存在。另外,人们的归因随时间过去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听到某人以某一指定立场辩论时,如果要求听众立即做出归因,人们会认为辩论立场代表了辩论者自己的观点,但在一周之后进行归因时,人们会更关注情境的作用(Burger,1991)。另一项研究考察了投票者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归因(Burger & Pavelich,1994)。研究者发现,在选举结束后第二天,大部分人认为选举结果说明获胜者很有个人魅力或者其地位和身份比较特殊,而在一年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将结果归因于获胜者的人格特质,大部分人更重视当时的情境因素。对六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相关评论的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重视情境的影响(Burger & Pavelich,1994)。
人们的基本归因错误出现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而对自己的行为,人们则倾向于用情境因素来进行解释。这种在观察他人的行为时偏好做性格归因,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更重视情境因素的倾向,叫做行动者-观察者差异(actor/observer difference)(Jones & Nisbett,1971)。例如,如果你看到一位母亲正在大声责骂她的孩子,你可能会觉得她教育孩子的方式有问题,不是个好母亲。但是,这位母亲自己却可能会觉得,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太大造成自己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男性大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自己和自己最好朋友的行为做出解释(Nisbett et al.,1973)。例如一个问题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为什么喜欢最常约会的女孩?”和“在过去的一年中,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喜欢他最常约会的女孩?”研究者对被试的回答进行编码,从而确定他们的归因类型。例如,如果回答“她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人”,这被认为是情境归因;而如果回答“我需要一个能够轻松相处的人”,这被认为是个性归因。这项研究发现,被试在解释喜欢自己女朋友的原因时,他们给出情境原因的数量是个性原因的两倍;而当解释最好朋友喜欢女朋友的原因时,他们给出的情境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数量大致相当。当被试回答选择自己专业和朋友选择专业的原因时,归因模式也类似:解释自己时,做出情境归因和个性归因的数量大致相等;而当解释朋友时,做出个性归因的数量是情境归因的4倍。综合这一研究的结果可见,个体用个性因素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数量大致相同,但用情境因素解释自己行为的数量是解释他人的两倍。一篇综述性文章总结了行动者-观察者差异的研究结果,发现在绝大多数研究中,行动者和观察者都倾向于更多地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而在进行情境归因时,与解释他人行为相比,人们更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境归因(Watson,1982)。人们在预测自己对未来事件(例如得知成绩或总统选举的结果)的情绪反应时,很容易忽略自身人格特质(例如幸福感、神经质和乐观)的作用(Quoidbach & Dunn,2010)。
造成这种行动者-观察者差异的原因之一仍是知觉显著性(Jones & Nisbett,1971)。当我们观察他人时,人是注意的中心,情境被忽视;而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注意是向外的,指向周围的其他人、物体和事件等,而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因此,行动者和观察者在解释行为原因时,分别受到对各自而言最显著和突出的信息的影响:对观察者而言,显著的是人,因而做内部归因;而对行动者而言,显著的是情境,因而做外部归因(Malle & Knobe,1997;Ross & Nisbett,1991)。如果行动者-观察者差异的原因是对二者而言显著的信息的不同,那么,让二者交换位置可能会影响归因。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录制了一段录像,其中有两个被试完成一段初次见面的对话,同时有两台摄像机完成录像工作(Storms,1973)。这一研究发现,随后没有观看谈话录像和观看的录像与自己原来的角度相同的被试,出现行动者-观察者差异;但是,有一组被试在谈话后观看自己对面的摄像机拍摄的录像,结果这组被试的归因刚好反了过来,他们当中的行动者对自己的行为做性格归因,而当中的观察者对行动者的行为做情境归因。可见,视角的不同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归因(Storms,1973)。
行动者-观察者差异的第二个原因是,行动者比观察者掌握更多关于自己本身的信息。行动者知道自己因为什么事情而做出某种行为,也清楚自己的行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下的变化(Baxter & Goldberg,1987;Malle & Knobe,1997)。例如,你作为一名老师在课堂上非常健谈和活跃,那么你的学生很可能会对你做出个性归因,认为你很外向。但实际你知道自己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上课或与朋友在一起时表现很外向,而与陌生人在一起时则会很害羞。因而,你作为行动者认为自己是随情境变化的,而学生作为观察者则认为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并且,我们越是缺乏在不同情境下观察他人行为的机会,就越容易将其行为归因于个性(Gilovich,1987)。当要求被试看某个人的录像带,并让被试向别人描述录像带中人的行为时,二手的印象更极端(Gilovich,1987)。部分原因是由于重述使得个体将注意集中在人而不是环境身上(Baron et al.,1997)。类似地,人们从朋友那里听说后形成的对某人的印象,通常比朋友对该人的第一手印象更极端(Prager & Cutler,1990)。如果对某些人直接观察,最好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他们进行观察,可以使我们对他们所处的情境更加敏感(Idson & Mischel,2001)。而对那种我们不了解或间接听说的陌生人,我们更容易进行特质归因。
有些时候,行动者-观察者差异会减弱。例如,当他人的行为使我们产生移情时,我们有可能会根据情境因素解释他人行为(Regan & Totten,1975)。不过,移情并不总是会发生。
假设你拿到期中考试的考卷之后,发现自己的成绩是95分。你会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好成绩?你很可能会拿内部原因来解释:你很聪明,你付出了很多精力来学习,等等。而如果你发现自己得了65分呢?你很可能会关注外部因素:考试太难,老师评分不公平,等等。这种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性格因素,将失败归因于外部、情境因素的倾向,叫做自利性归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s)(Miller & Ross,1975)。在职业体育比赛这一领域中,经常可以看到自利性归因。在比赛取胜之后,运动员和教练将其归因于内部因素,例如运动员能力高,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例如运气差,裁判不公平,对手发挥太好,等等(Lau & Russell,1980;Lalonde,1992)。哪些人更有可能做自利性归因?研究者考察了运动员的技巧、经验、运动种类(个体运动还是团体运动)等因素对归因类型的影响(Roesch & Amirkhan,1997)。他们发现,经验较少的运动员比经验丰富的运动员更多地做自利性归因,技艺高超的运动员比能力较差的运动员更多地做自利性归因,个体运动的运动员比团体运动的运动员更多地做自利性归因。
在婚姻关系中,存在一种性质类似的归因偏差。1979年,心理学家罗斯和西科里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37对夫妇完成一份关于双方关系的调查问卷(Ross & Sicoly,1979)。问卷的内容是要求双方评估,他们在20项活动中所承担的责任,这些活动包括做饭、洗碗、清理房间、照顾孩子、沟通情感等。结果发现,在其中的16项活动中,如果将夫妻双方认为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比例相加,所得数值超过了百分之百,研究者将其称为归因中的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指的是对于与他人共同完成的结果,个体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其他研究也不断证实,司机、政治家、公司主管、企业员工、学生、教师等都表现出自利性归因(Kingdon,1967;Davis & Stephan,1980)。例如,公司主管将利润上升归因于自己的管理能力,将利润下滑归因为经济不景气;政治家将选举胜利归因于自己的声誉和策略,将选举失利归因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等等。自利性归因在很多时候会造成人际冲突,例如夫妻关系不和谐,员工间彼此抱怨,谈判时互不相让等(Kruger & Gilovich,1999)。不过在有的时候,自利性归因具有适应意义。例如,将被解雇归因于外部因素的工人会更努力地寻找工作,并且更容易找到新工作,而把失业归因于内部原因的工人则正好相反(Schaufeli,1988);将成功归因于自身的稳定特点,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在未来尝试类似的任务(Taylor & Brown,1988)。
人们进行自利性归因有多种原因,多数研究者认为,动机因素和认知因素的结合导致了这一归因偏差。例如,错误的期望,对成功的渴望,对自尊的保护等。从动机的角度看,通过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因果关系,可以保持或提高自尊(Snyder & Higgins,1988)。另外,由于人们非常关注如何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通过将失败的结果归因为外部因素,可以为自己保持脸面(Weary & Arkin,1981)。最后,由于人们期望成功,因此造成了信息加工的某种倾向,导致自利性归因(Ross,1977)。
在我们拥有的各种自我认识当中,有关我们自己难免一死以及灾难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认识,是最难以接受的(Greening & Chandler,1997)。当悲剧事件例如强奸、绝症、致命意外等发生时,即使是发生在陌生人身上,它们也会让我们惊慌。这些悲剧提醒我们,既然它们会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么它们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人们会采取各种办法否认这些事实,方法之一是进行防御性归因(defensive attributions),也就是使我们不受脆弱以及难免一死等感受困扰的解释。
防御性归因的一种形式是不切实际的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即认为好事比较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比较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坏事则比较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比较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Regan,Snyder,& Kassin,1995)。早期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正性结果发生的概率比负性结果要高(Irwin,1953)。而当涉及自身生活中的正性和负性事件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一项研究要求大学生回答,与同性别的其他同校学生相比,一些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Weinstein,1980)。这些事件包括拥有自己的房子,喜欢毕业后的工作,活过80岁,有酗酒问题,离婚,无法生育,患心脏病,遭遇枪击等。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历正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5%,而经历负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低20%。人们在许多领域中都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例如女性对患乳腺癌的态度和男性对患前列腺癌的态度(Clarke et al.,2000),毒品使用者对自己过度使用药物的危险的态度(McGregor et al.,1998),赌徒对自己赢得彩票的态度(Rogers,1998),以及摩托车驾驶员对自己发生严重事故的态度(Rutter,Quine,& Albery,1998),青春期后期的年轻人对自己被艾滋病感染的态度(Abrams,1991),人们对自己遭遇地震的态度(Burger & Palmer,1991),成为犯罪中的受害者的态度(Perloff & Fetzer,1986),等等。另外,人们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的未来的看法也很乐观。例如,当要求大学生评价自己、好朋友以及一个偶然相识者,在未来经历大量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可能性时,他们非常乐观地看待自己和好朋友的未来,而对一个偶然相识者未来的看法则要悲观得多(Regan,Snyder,& Kassin,1995)。不过,近年有研究者指出,不切实际的乐观的现有研究存在一些方法学上的问题,需谨慎解读(Harris & Hahn,2011)。
研究发现,乐观与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Armor & Taylor,1996)。例如,当要求学生评价自己和同校的其他学生将来经历各种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可能性时,非抑郁被试认为自己的未来比一般人的未来更美好,但抑郁被试则刚好相反(Pyszczynski,Holt,& Greenberg,1987)。但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由于相信自己总能免于不幸,人们往往不去采取应有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糟糕的结果。例如,过分乐观的学生倾向于在考试前不做充分的准备(Goodhart,1986),相信自己与他人相比不太可能怀孕的女大学生不愿意采用避孕措施(Burger & Burns,1988),被殴打过的女性对重回虐待过她们的男性身边所冒的风险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Martin et al.,2000),那些结婚时相信自己将来离婚的可能性是零的伴侣,有一半以离婚告终(Baker & Emery,1993)。
防御性归因的另一种形式是公平世界的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Lerner,1980)。人们不断地从媒体中看到各种不幸,这意味着这些不幸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处理这些信息的一种方法是,相信坏事只发生在坏人身上,或者至少只会发生在那些做出愚蠢行为或决定的人身上。我们是好人,我们不会那样愚蠢和不小心,因此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一项研究中,以抽签的方式选择一名被试参与记忆任务,其余被试作为观察者(Lerner & Simmons,1966)。当这名抽中者的记忆出现错误时,就要接受电击。当观看受害者接受十分痛苦的电击之后,研究者让观察者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当观察者无力改变受害者的命运时,他们经常会否定和贬低受害者。公平世界的信念也来自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认为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这也导致对不幸者的贬低。
很多研究都发现,犯罪或意外的受害者常被认为是咎由自取,这称作“责怪受害人”(blaming the victim)现象(Walster et al.,1966)。一项研究让被试阅读有关一位男性和女性交往的详细描述,例如一位女性与上司约好共进晚餐,她来到上司的家,每人喝了一杯红酒。一半被试阅读的故事有一个好的结局:“他把我带到沙发旁,握着我的手向我求婚。”这些被试不认为这个结局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并且十分赞赏男女主人公的表现。另外一半被试阅读的故事结局则完全不同:“他随后变得十分粗暴,把我推倒在沙发上,强奸了我。”当看到这种结局时,被试认为它在所难免,并且指责那位女性在故事前段的行为非常不妥(Carli & Leonard,1989;Carli,1999)。因此,那些相信公平世界的人,认为被强奸的受害者一定行为轻佻(Abrams et al.,2003),遭受虐待的配偶一定是因为犯错才挨打(Summers & Feldman,1984),穷人注定过不上好日子(Furnham & Gunter,1984),生病的人应该为他们的疾病负责(Gruman & Sloan,1983),失败者能力较差(Baron & Hershey,1988)。通过使用这样的归因方式,人们相信不幸和失败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不必为自己的安全忧虑。
研究者曾经认为,基本归因错误、自利性归因以及防御性归因等归因偏差具有普遍性,任何地区的人在归因时都会使用这些认知捷径(Norenzayan,Choi,& Nisbett,1999)。但是,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社会行为的作用。由于情境对个体行为影响很大,文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情境力量。北美和西欧的很多国家强调个人自主,个体被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行为反映了其内在特点、动机和价值观(Markus & Kitayama,1991)。而东亚、非洲和中南美的很多国家则强调群体,个体从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中获得自我感。因此,两种文化下人们的归因方式很可能存在差异。
如前所述,使用西方被试进行的研究不断证实基本归因错误的存在,即人们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为个性因素。一种可能是,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的个人主义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使得其成员学会从性格而不是情境中寻找原因(Dix,1993)。相反,在强调群体成员身份、相互依赖以及服从群体规范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化过程可能教导成员用情境而不是个体原因来解释行为(Triandis,2001;Markus & Kitayama,1991)。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比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表现出较少的基本归因错误。很多研究者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
在琼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1967)的经典实验之后,很多研究利用这一实验的变式进行了文化间比较。在这一实验设计中,被试阅读一篇文章,文章作者的立场是被事先指定的,随后要求被试对作者的真实立场进行评定。结果在美国被试中发现了基本归因错误,他们认为作者所表达的态度就是其真实的态度;而韩国、日本和中国被试也认为作者的文章表明了其真实的偏向(Choi & Nisbett,1998;Krull et al.,1999)。但是,当情境因素更加突出时,两种文化的差异出现。研究者让被试经历与他们将要对其做出判断的目标人物相同的过程,以此来使情境信息更加突出。与目标人物一样,被试在写文章时也被指定了一个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立场。最后,让被试对目标人物的态度做出判断,这时他们应该认识到目标人物与他们自己经历过的一样,被情境所限制,因此所写的文章不代表其真实的态度。结果发现,在对目标人物做判断时,美国被试仍然犯基本归因错误,仍旧认为文章揭示了一些关于目标人物真实立场的信息;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被试将情境信息考虑在内,对目标人物做出的内部归因大大减少(Choi & Nisbett,1998;Choi,Nisbett,& Norenzayan,1999)。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两则刊登在报纸上的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谋杀事件,一个案件的凶手是一位中国研究生,另一个案件的凶手是一名白人邮政工人(见开篇案例)。结果发现,英文报纸比中文报纸更多地将两名凶手的行为归因于性格因素(Morris & Peng,1994)。还有研究者比较了印度和美国人对常见事件的解释,发现印度人更关注外部背景,美国人则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Miller,1984)。例如,一位美国人对邻居的逃税行为的解释是:“她就是那种人,总想压过别人。”而一位印度人对一名欠债者的解释是:“他失业了,他没有办法还钱。”这项研究的被试包括8岁、11岁、15岁的未成年人和成年美国人及印度人,要求被试解释一个认识的人的行为,有些行为带来好结果,有些行为带来坏结果(Miller,1984)。他们发现,印度人所做的情境解释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人所做的性格归因是印度人的两倍;归因负面行为比归因正面行为的差异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人们认为正面行为或亲社会行为对性格的诊断性较差。并且,文化差异随着社会化逐渐增加:美国和印度儿童之间的相似性高于两国的成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美国人的性格归因增多,而印度人的性格归因数量不变。
在描述相识者时,印度人的描述包含情境,提到角色、社会身份和职业;美国人的描述通常缺乏情境,只包含抽象的人格特质(Shweder & Bourne,1982)。在要求被试用以“我是……”开头的20条陈述描述自己时,美国被试使用抽象的人格特质(例如“我是好奇的”、“我是真诚的”)的数量是日本被试的3倍;日本被试对自己的描述更多反映了社会身份(例如“我是一名京叶学生”),或者提到特定的情境(例如“我是一个在周五晚上玩麻将的人”)(Cousins,1989)。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描述是情境化而不是抽象的,是特定的而不是一般性的;在韩国、中国等东亚国家也有类似发现。另外,美国人无意地从行为推断人格特质,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自己在这样做,这叫做自发特质推理(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Newman,1993)。而在与东亚文化类似的西班牙文化中,没有发现自发特质推理。甚至在对动物行为和物理运动的解释上,也存在东西方差异。当要求解释一条鱼游离鱼群的行为时,中国被试倾向于提到外部因素,美国被试倾向于提到内部因素;当看到物体因水力、磁力或空气动力而运动时,美国被试更多地认为该物体的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Morris & Peng,1994)。
总结已有研究可以认为,基本归因错误在所有研究过的文化中都存在(Krull et al.,1999)。但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由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经验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抑制这种性格归因的倾向,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相比,他们在归因时更有可能考虑到情境信息,特别是在情境信息非常突出以及备受关注时。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并非不进行性格归因,而是更有可能注意到情境对行为的影响(Choi,Nisbett,& Norenzayan,1999)。从前面讨论的归因两阶段过程来看,各种文化下的人们可能都从同一个起始点出发,自动地对他人做出性格归因,表现出对应偏差。而在第二个阶段,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会查看情境,他们将情境考虑在内,从而对自己最初的归因进行修改,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则倾向于跳过第二个阶段,从而保持了最初的性格归因(Choi et al.,2003;Knowles et al.,2001)。
在对行动者-观察者差异的考察中,研究者发现,在对作为行动者的自己进行归因时,美国和韩国被试没有太大差异,他们对自己都做出了情境归因;差异出现在作为观察者对他人进行归因时,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是由其性格引起的,而韩国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的行为是由情境引起的(Choi & Nisbett,1998)。其他研究考察了自利性归因,发现这一偏差的强度随文化的不同有所差异,与强调个人自主的文化相比,它在那些强调群体和谐的文化中表现较弱(Oettingen,1995)。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谦虚和人际和谐,并不鼓励将成功归因于自己,而是归因于他人例如老师或父母,或者学校的教育质量等情境因素(Bond,1996)。而西方国家则强调个人成就,鼓励对成功的内部归因。研究表明,美国学生更多地将成功归功于自己,而中国学生和美籍华人则更多将成功归因于情境因素(Lee & Seligman,1997)。对失败的归因则相反,美国人从情境中寻找原因来解释失败,而中国人则将失败归结为内部原因(Anderson,1999)。并且,日本学生与加拿大学生相比,较少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Heine & Lehman,1995)。公平世界的信念也存在文化差异。有研究者认为,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相信公平世界的社会中,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会被看成是“公平”的(Furnham,1993)。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相信穷人和弱势群体之所以所得较少,是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就少。因此,公平世界的信念可以被用来为不公平进行辩护。研究表明,与贫富分化不那么明显的文化相比,在贫富分化极端严重的文化中,公平世界归因更常见(Dalbert & Yamauchi,1994;Furnham,1993)。例如,印度和南非的被试在公平信念量表上的得分比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津巴布韦被试要高,而得分最低即最不相信公平世界的是英国人和以色列人(Furnham,1993)。
从上述讨论可见,因果归因的文化差异相当明显,在采用不同物体和事件的多种研究范式中都得到证实。这种差异的焦点在哪里?根据两阶段的归因理论,人们首先进行不费力的(effortless)性格推断,然后进行费力的(effortful)情境纠正(Gilbert,1993)。那么,文化差异可能来自:东亚被试先情境推理然后性格纠正,美国被试先性格推理然后情境纠正;或者,东亚被试与美国被试的性格归因类似,而东亚被试所做的情境纠正多于美国被试;或者,最初的性格归因就是东亚被试比美国被试弱(Choi,Nisbett,& Norenzayan,1999)。总结已有跨文化研究证据可见,更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情形:东亚被试所做的情境归因较强,而性格归因方面东亚被试与美国被试类似。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根据一个人过去行为的信息,预测这个人未来的行为。而人格特质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行为。研究发现,美国被试根据(即便是少量的)他人过去行为的信息对未来行为做出自信的预测,并且高估人格特质的预测效力(Kunda & Nisbett,1986)。在一个研究中,给被试提供一名行动者在一个过去情境中的行为的信息,要求美国被试和中国被试对这个人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Norenzayan,Choi,& Nisbett,1999)。在一种条件下,被试阅读两名目标个体在一个具体行为上的个体差异信息,该差异暗示一种人格特质但没有提到特质词,然后要求被试预测他们相信这一个体差异也会反映在另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同一特质)上的程度。在另一种条件下,被试阅读类似的基于个体差异信息的行为描述,但描述中提到明确的特质(例如“乐于助人”),然后预测他们相信这一个体差异在未来会保持稳定的程度。结果表明,东亚被试与美国被试一样使用人格特质来预测未来行为,根据具体行为信息来推测跨情境的行为稳定性,他们也会进行自发特质推理(Norenzayan,Choi,& Nisbett,1999)。
尽管有些时候东亚被试和美国被试都犯基本归因错误,未考虑情境因素的作用,但是,当突出情境信息时,文化差异很明显,东亚被试比美国被试更能认识到情境因素的影响,美国被试依然忽略非常突出的情境信息(Choi & Nisbett,1998)。这个研究在前文已经介绍过。在另外的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了解一名目标个体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主张一种或另一种立场(Masuda & Kitayama,1996;Gilbert & Jones,1986)。在标准的无选择条件下,研究者告诉被试,由于实验需要两种态度立场之一的录像,目标个体被要求在录像机前读支持一种立场的短文。在这种条件下,美国被试和日本被试都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在另一种条件下,两名被试一起参加实验,其中一名随机选择的被试从两个相同的信封中做出选择,信封里包含将由目标个体读的短文。然后,目标个体在一个录像机面前读被试选择的短文,另一名被试观看了整个过程。在这种条件下,美国被试依然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而日本被试的基本归因错误完全消失。可见,当情境特征突出时,日本被试与美国被试表现出显著差异,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考虑情境限制的作用。
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差异与不同文化下人们持有的关于人类行为原因的通俗理论(folk theory)相一致。研究者询问被试,他们同意描述人类行为的三种不同哲学的程度(Norenzayan,Choi,& Nisbett,1999)。一种是强烈的性格主义哲学,认为“人们如何行为主要由他们的人格决定”;第二种是强烈的情境主义哲学,认为行为“主要由情境决定”;第三种是相互作用主义(interactionist)哲学,认为行为“总是由人格和情境共同决定”。结果发现,韩国和美国被试赞同第一种哲学的程度类似;但是,韩国被试赞同情境主义哲学和相互作用主义哲学的程度强于美国被试。因果归因上的文化差异也与不同文化中人们对人格的看法相一致。研究者给被试施测一份量表,它测量人们对两种不同人格理论的同意程度(Norenzayan,Choi,& Nisbett,1999)。一种理论是实体(entity)理论,相信行为是由相对固定的内部倾向例如人格、智力、道德品质决定的;另一种是增长(incremental)理论,认为行为依赖于情境,任何内部倾向都有可能发生变化。韩国被试在很大程度上否认实体理论,而美国被试赞同实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程度相同。
为什么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能认识到情境的影响?人种学、历史学、哲学等许多领域的学者认为,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受中国影响较大的文化)的知识传统就很不一样。古希腊人持分析(analytic)思想,焦点是根据客体的属性对其分类,利用与它的类别成员身份有关的规则来解释它的行为。而古代中国人持整体(holistic)思想,他们对客体存在的场(field)很感兴趣,倾向于根据客体与场的关系来解释它的行为(Norenzayan & Nisbett,2000)。相应地,古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和数学分别的强项和弱项差别很大:古希腊科学寻找解释事件的普遍规律,关注根据客体的本质来分类;中国科学更实用和具体,不关心基础或普遍法则。现代的东亚人与古代中国人类似,关注场和情境在决定事件上的作用。西方文明则受古希腊影响,主要关注客体。不同文化对场和客体的差异性关注得到了研究证据支持。与这种区别有关的一个概念是场依存(field dependence),即难以将客体与它所处的场或环境区分开来。测量场依存通常采用棒框测验(rod-and-frame test),被试需要把一个矩形框架中的小棒调整为竖直的,且周围没有其他参照物。如果框架的朝向影响被试对小棒的竖直判断和调整,说明被试是场依存的,如果不影响,说明被试是场独立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东亚被试比美国被试场依存的程度高(Ji,Peng,& Nisbett,2000)。
那么,为什么西方人发展出分析式认知,东方人发展出整体式认知?也许原因主要在于生态和经济因素(Nisbett et al.,2001)。在中国,人们比欧洲人早几百年从事密集的农业活动。农民需要彼此合作,并且农业限制了人们的迁移,人们需要维持和谐关系和大量合作,社会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在中国,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注意可能推广到对世界的整体式理解。在古希腊,山脉延伸到海洋,地理条件造成大规模农业不太可能存在。人们通过养殖动物、捕鱼和贸易为生。这些职业不那么需要密切合作,因此希腊人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鼓励只注意客体和与客体有关的目标,社会环境可以被忽略。因此,整体认知和分析认知分别源自历史上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这一观点得到了研究支持:当前的农民比猎人和工业化人群更加场依存;在紧密的社会约束下生活的美国种族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加场依存;重视社会关系协调的个体比不关注社会关系的个体更加场依存(Witkin et al.,1974)。
尽管跨文化研究发现了动机、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是静态和一成不变的。通过一些启动任务,可以让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转向或者更为个人主义,或者更为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Oyserman & Lee,2008)。研究显示,当处于中性条件下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为整体,与西方文化下的分析思维方式有所区别(Zhou et al.,2012)。但是,在经受短时的控制感剥夺之后,中国被试转向分析式思维,并且这有助于恢复控制感。
多种因素与抑郁有关,其中之一是人们对生活事件的归因,这些归因影响抑郁的产生、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大多数人表现的自利性归因偏差不同,抑郁的人倾向于采用相反的归因模式。他们将消极的结果归因于持久的内部原因,例如性格或能力的欠缺,将积极的结果归因于暂时的外部原因,例如运气好或他人对自己的特别帮助。因此,这些人感觉难以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抑郁的归因模型来源于一项动物研究,研究中一些狗反复遭受无法逃避的电击(Overmier & Seligman,1967)。随后,这些狗即使处在可以逃脱电击的情况下,也不会采取行动帮助自己,而是被动地忍受电击,表现出动机缺失。这些狗似乎认为没有什么能让自己减轻痛苦,这种错误的知觉被称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Maier,Seligman,& Solomon,1969)。塞利格曼将习得性无助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研究中,他认为,当人们感觉自己无法控制重要的生活事件时,抑郁就产生了(Seligman,1975)。根据塞利格曼的看法,抑郁症患者患病的部分原因可能与他们生活中有过重大的失去控制力的经历有关。但是,并非每个人在失去了一次重大的控制力之后都会变得抑郁。因此,塞利格曼等人在1978年修正了习得性无助理论,加入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归因(Abramson,Seligman,& Teasdale,1978)。他们认为,当人们感到无法控制重要的生活事件,以及将这些事件归因为内部的(是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稳定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和涵盖一切的(这会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原因时,抑郁就产生了。一些人具有消极的归因风格,即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原因。这种消极的归因风格造成这些人在消极事件发生时容易产生抑郁(Abramson,Seligman,& Teasdale,1978;Peterson & Seligman,1984)。
针对抑郁的归因模型,有足够证据表明抑郁者比不抑郁者更倾向于对消极结果做出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归因(Brewin,1985;Peterson & Seligman,1984)。这些证据来自:实验室研究,被试对实验条件下诱发的挫折进行归因(Kuiper,1978);现场研究,人们对自然发生的消极生活事件做出归因(Zautra,Guenther,& Chartier,1985);档案数据,从日记、其他书面或口头材料中收集对消极事件的归因(Peterson,Luborsky,& Seligman,1983);以及问卷调查研究,对一般性归因风格的评估(Peterson & Seligman,1984)。塞利格曼等人编制了一套归因风格问卷,其中包括6个假设的积极事件和6个假设的消极事件(Seligman et al.,1979)。研究者总结被试对这些事件的归因,并比较抑郁被试和非抑郁被试的回答。结果显示,与抑郁被试相比,非抑郁被试对积极事件更倾向于做出内部的、稳定的、涵盖一切的归因,对消极事件的归因则刚好相反(Seligman et al.,1988)。研究者还考察了在与成就有关的事件上归因风格不同的大学生,对糟糕的考试成绩如何做出反应(Metalsky,Halberstadt,& Abramson,1987)。结果发现,刚得知成绩时,所有大学生的情绪反应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成绩,但是在两天后,那些考得差且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学生,更有可能继续保持抑郁情绪。
因此,消极的归因风格是可能会引起抑郁的一种高危因素。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着重改变抑郁者的归因,让他们对成功的结果自信,并停止为消极结果尤其是不可避免的消极结果自责,转而把某些失败看作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结果。这些治疗方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Bruder et al.,1997;Robinson,Berman,& Neimeyer,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