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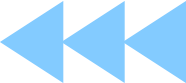
人们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沟通信息,一种是言语沟通,即言谈的内容;另一种是非言语沟通,即不包括口头言语的个体间的交流,包括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身体语言等;第三种是泛言语沟通,即将言谈内容去掉之后剩下的言语信号,例如音调、语速等(Richmond et al.,1991)。研究者经常将后两类统称为非言语沟通(Knapp & Hall,1997)。非言语线索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感受的信息。与言语线索相比,这些表现相对难以控制,甚至在人们试图隐藏其内部感受时,非言语线索仍然会泄漏真实的感受(DePaulo,1992)。有些非言语线索可以重复言语信息,或者辅助其完整的表达;有些非言语线索则与言语线索相矛盾;有些时候非言语线索还可以代替言语线索来表达一定的含义(Ekman,1965)。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非言语沟通,就可以对他人的情感状况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并且,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并没有有意地关注他人发出的非言语线索和试图发现他人的感受,这些线索仍然会影响我们。例如,当聆听他人阅读一篇演讲稿时,虽然听者试图注意演讲的内容,而没有注意阅读者的情绪状态,但阅读者声音中流露出的情绪仍会影响听众的心情(Neumann & Stack,2000),这叫做情绪感染(mood contagion),即情绪感受自动地由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
人们在体验不同情绪时倾向于表现为不同的行为。研究表明,关于人们内在情绪状态的信息通常由几种基本渠道来传递: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身体语言、个人空间、触摸以及副语言。研究者通常分别地对非言语沟通的各种渠道进行研究,但在日常生活中,多种非言语线索往往同时出现(Archer & Akert,1980)。
当你想到愉快或悲伤的事情时,你的面部表情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特定的面部表情是与特定的情绪相对应的。而且,很多时候人们能够通过某人的面部表情识别其当时的情感。达尔文(1872)的进化理论认为,情绪具有适应功能和生存价值,所有人类成员都有相似的情绪反应模式。心理学家艾科曼(Ekman)等人力图证明,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在各种文化中都是一样的。他们给阿根廷、巴西、智利、日本和美国被试呈现人脸照片,结果发现所有国家的被试都能成功地识别对应某种情绪的面部表情。并且,即使是在从未接触过现代文化、与世隔绝的一些土著文化中,被试也能正确识别出他们从未见过的西方人的表情(Ekman & Friesen,1971)。很多研究证据证实,有7种情绪表情在全世界以相同的方式表达,并且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表情推测他人正在体验的情绪,这7种情绪是,高兴、惊奇、生气、厌恶、害怕、悲伤和轻蔑(Ekman & Friesen,1986)。
需要注意,上述研究考察的只是几种基本的情绪,而实际上人们的情绪往往以混合的方式发生,例如又悲又喜、又惊又怒等。并且,每种情绪反应在强度上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能够表达非常丰富的情绪。另外,尽管面部表情能够揭示他人的情绪,但表情发生的情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当情境线索和面部表情不一致时,人们有可能会根据情境线索判断他人的情绪。例如,当看到表现恐惧的脸的照片,但同时阅读一个暗示照片上的人很愤怒的故事时,很多人会把照片上的脸描述为愤怒而不是恐惧(Carroll & Russell,1996)。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当情境与面部表情不一致时,面部表情为潜在情绪提供了准确指引(Rosenberg & Ekman,1995)。有些时候,人们会努力掩盖自己的情绪,使得别人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情感。例如,当别人说了伤害你的话时,你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尽量不在脸上表现出来,目的是不让对方的伤害目的得逞。有研究让被试观看一些遭受身体损害的人的幻灯片,一些被试被要求压抑自己的情感表达(Richards & Gross,1999)。结果发现,那些被要求压抑情绪的被试做得很好。但是,情绪压抑会导致血压升高,以及更多的负面情绪体验(Butler et al.,2003)。
另外,每种文化下的情绪表达规则有所不同,这些规则规定了人们应该表达出哪一种情绪(Matsumoto & Ekman,1989)。例如,美国文化抑制男性表达悲伤等情绪;日本的传统文化则约束女性不得表现爽朗的笑容,西方女性则不受这种规范限制(Ramsey,1981;La France,Hecht,& Paluck,2003)。日本人还常以笑容和笑声来掩饰负面的情绪表情,他们与西方人相比面部表情较少(Aune & Aune,1996)。在美国,面带微笑的人被看作是和善、友好和值得信赖的;但在日本和韩国,微笑有时会被认为对重要的事情态度轻佻(Dresser,1994)。尽管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把微笑的脸看作代表友好,但是,中国人还认为这些人缺乏自制力和镇静(Albright et al.,1997)。因此,由于情绪混合、情境与表情的矛盾、人们压抑情绪表达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人们对面部表情的解读有可能会出错。
在社会交往中,目光接触可以传递信息。例如,人们把来自他人的注视看作是喜欢和友好的表示(Kleinke,1986);而如果对方避免目光接触或转移目光,我们会认为他/她不友好、不喜欢自己,或是害羞(Zimbardo,1977)。虽然注视通常被理解为表达喜欢和积极情绪,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顾对方的反应持续注视他人,就会被认为是在瞪视(staring)。瞪视经常被理解为愤怒和敌意,被瞪视的人容易表现出攻击性(Ellsworth & Carlsmith,1973),人们对瞪视的反应可能是迅速中止交往甚至离开现场(Greenbaum & Rosenfield,1978)。为此,有学者建议,当发生道路冲突时,驾驶员应该避免与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员的目光接触,否则可能会导致对方的攻击行为,因为对方已经处于高唤起状态(Bushman,1998)。因此,目光接触可以表达相反的含义,情绪的正负取决于当时的情境。此外,关于目光接触的社会规范存在文化差异,一些文化(例如尼日利亚、波多黎各和泰国)认为直接的目光接触是不礼貌的,尤其是在面对地位较高者时,更是提倡避免直接目光接触(Aronson,Wilson,& Akert,2004)。
由身体或身体某部分的姿势、位置或动作所提供的知觉线索叫做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身体语言经常暴露人们的情绪状态,大量的动作尤其是身体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所做的触摸、摩擦、抓弄等动作,往往表明情绪的唤起。这些动作的频率越大,唤起或紧张水平越高(Baron & Byrne,2002)。较大幅度的动作,包括整个身体的移动,也能提供关于他人情绪状态甚至是表面特质的重要信息(Baron & Byrne,2002)。例如,有研究表明,在芭蕾舞中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角色更多表现出对角线状或直角的姿势,而热心的、富有同情心的角色则展示更多圆滑的姿势(Aronoff,Woike,& Hyman,1992);与收缩、封闭的姿势相比,扩张、展开的姿势代表更高的权力(Carney,Cuddy,& Yap,2010)。另外,手势也可以传达丰富的信息,一些手势在特定文化中具有清楚、易懂的含义。但需要注意,手势并不具有普遍性,每种文化下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含义的手势,这些手势不一定能被其他文化下的人们理解,甚至可能被误解(Archer,1997)。例如,在美国,拇指与食指接触,其他手指竖起来的手势表示“好”或“没问题”;在法国代表“零”;在中东一些国家是猥亵的手势,类似于美国人竖起中指的意思。
非言语沟通还可以通过运用个人空间来进行。通常,朋友比陌生人站的距离要近,希望使自己显得友好的人会缩短与他人的距离,彼此感到性吸引的人距离也比较近。人们能够意识到他人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自己是否有兴趣(Aiello & Cooper,1972;Patterson & Sechrest,1970;Allgeier & Byrne,1973)。使用个人空间的规则具有文化差异(Hall,1969)。例如,西方人感觉舒适的距离通常比东方人要远一些。
人们对触摸的反应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触摸自己的人是谁,触摸的性质,触摸发生的情境,等等(Baron & Byrne,2002)。根据这些因素,触摸可以表示爱情、性兴趣、控制、关心甚至攻击。研究表明,如果触摸是适当的,被触摸者会做出积极反应(Smith,Gier,& Willis,1982)。握手是很多文化都接受的触摸陌生人的方式。研究表明,紧紧地握手可以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并且,握手还可以揭示人们的人格,由持续时间、紧握度、力量和活力构成的握手指数与人格的几个方面显著相关,例如开放性和外倾性(Chaplin et al.,2000)。不同文化中人们彼此碰触的频率有所不同,频率较高的文化例如中东、南美和南欧的国家,频率较低的文化例如北美、北欧、巴基斯坦等地区和国家。另外,同性之间亲密接触例如拉手、勾肩搭背,在美国等文化中很少见,而在韩国和埃及却是常见现象(Aronson,Wilson,& Akert,2004)。
言语形式的变化被称作副语言(paralanguage),是指话语之外说话人声音中的所有变化,包括音调变化、音量大小、节奏、言语中的停顿等(Taylor,Peplau,& Sears,2006)。副语言当中包含很多含义,尤其是情感意义(Banse & Scherer,1996)。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通常同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有研究者考察了人们利用多种非言语线索的准确性(例如:Archer & Akert,1980)。他们构建了一种非言语沟通解码任务,称作社会解释任务(social interpretation task,SIT)。社会解释任务由20幕自然发生的行为录像构成,被试观察并倾听真实人物的实际对话及其非言语行为。每一幕录像长度约一分钟,被试在看完这段真实的互动场景之后,回答关于其中人物或人物彼此间关系的问题。结果发现,非言语线索对于人们准确理解录像内容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使用几种不同的非言语渠道来帮助自己选择正确答案。例如,他们注意录像中人物的声调、身体位置和姿势、目光接触、触摸等方面的不同(Archer & Akert,1980)。另外,一些人在解读非言语线索方面的能力较强,例如外向的人表现更好(Lieberman & Rosenthal,2001);并且,女性比男性更善于解读和表达非言语行为(Rosenthal & DePaulo,1979)。
当人们说谎时,他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动作以及副语言等方面都会有所变化。研究者认为,当人们试图欺骗别人时,他们可能非常平静地说谎,但是非言语线索可能会暴露他们在说谎这一事实,这被叫做非言语泄露(nonverbal leakage)(例如:Ekman & Friesen,1974)。当我们留意这些非言语线索时,就有可能成功地识别谎言。
第一种有效的线索是微表情,即瞬间闪现的面部表情。在一个情绪唤起事件之后,微表情迅速出现并且很难抑制(Ekman,1985)。因此,密切关注微表情可以发现人们的真实感受。例如,当你询问某个人是否喜欢某本书时,你发现一个表情之后紧跟着另一个表情,例如瞬间的皱眉之后表现微笑,这就是说谎的信号。第二种线索是副语言线索。音调提高,比正常情况简短的回答,反应前的犹豫,更多的言语错误等,都是说谎的特征(Zuckerman,DePaulo,& Rosenthal,1981;Stiff et al.,1989)。第三种线索是目光接触,说谎的人比说实话的人更经常眨眼、瞳孔更大;他们与人的目光接触水平较低或者较高,因为他们企图通过直视别人的眼睛来造成诚实的假象(Kleinke,1986)。第四类线索是,说谎的人有时会表现出夸张的面部表情。例如笑得更多、更夸张,或者表现出超常的、过分的悲伤。第五类线索是不同的渠道之间表达不一致,这是因为说谎的人很难同时控制所有通道。例如,一个想要表现热情友好的人可能会微笑并与他人目光接触,但身体却远离而不是贴近别人(DePaulo,Stone,& Lassiter,1985)。另外,当人们试图隐瞒或说谎时,他们可能可以控制言语内容和面部表情,但身体动作和副语言线索可能会泄露他们的意图。例如,与改变声调相比,说谎者能更成功地改变面部表情(Zuckerman et al.,1981)。
尽管有如此多的非言语线索可供利用,但一般而言,觉察谎言并不如觉察真实信息的准确性那么高(DePaulo,1992)。如果预先知道某人可能要说谎,是否能对觉察谎言有所帮助?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当得知别人试图欺骗我们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关注他们的言语,或者只能关注他们的非言语线索,很难同时关注二者。并且,我们识别谎言的动机越高,就越可能仔细关注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没有留意能更好地揭示谎言的非言语线索。一项研究要求被试判断录像中的人是否在说谎,为了操纵动机,一半被试被告知回答情况代表其智力和社会技能水平,另一半被试则没有接受这样的指示语。结果发现,低动机组比高动机组被试判断的准确性更高(Forrest & Feldman,2000)。可见,识别谎言的动机越强,效果反而越差。另外,从说谎者的角度看,当人们说谎的动机很强时,他们实际上更容易被觉察,原因是他们努力控制非言语行为而表现得不自然(DePaulo,Lemay,& Epstein,1991)。
尽管我们识别相同文化的人们的谎言比识别其他文化的人们的谎言更为准确,但即使是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谎言,我们识别的准确性也高于随机猜测(Bond & Atoum,2000)。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发现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在说谎,非言语线索似乎不需要翻译。在别人说实话时,女性比男性更善于解读非言语线索,但是男性对谎言的觉察能力比女性强。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比男性更礼貌,尽管她们有能力觉察谎言的非言语线索,但是在面对欺骗时,她们出于礼貌会关闭这项功能(Rosenthal & DePaulo,1979)。有研究显示,在理解口头语言上存在严重缺陷的失语症患者,与正常控制组被试相比,在识别谎言方面准确率更高,其原因可能是前者能更好地识别面部表情线索(Etcoff et al.,2000)。
有研究者指出,无意识过程有助于谎言识别(Reinhard et al.,2013)。一系列实验显示,与被鼓励进行审慎的意识加工的被试相比,被阻止意识加工的被试探测说谎的准确率更高。这是由于无意识思维过程允许人们整合用于准确探测谎言的丰富信息(Reinhard et al.,2013;综述见:Street & Vadillo,2016;ten Brinke,Vohs,& Carney,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