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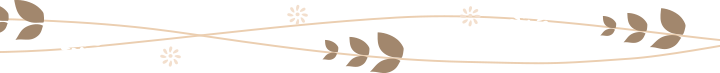
六只骰子六点儿,赛了千千并万万的苏东坡,谈起创作经验来真个是欢天喜地:“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可步步算计的福楼拜,一说到写作就老是愁眉苦脸。有一回,他六个星期只写了二十五页:
这二十五页写得真辛苦呀。我写得太精细,抄了又抄,变了又变,东改西改,眼睛都发花了,所以暂时看不出问题。不过我相信这些页都能站住脚。——你还跟我谈你的气馁呢!你要是看看我怎样气馁就好了!有时我真不明白我的双臂怎么没有疲劳得从我身上脱落下来,我的脑袋怎么不像开锅的粥一般跑掉。我活得很艰难,与外界的一切快乐隔绝;在生活里,我没有别的,只有一种持久的狂热支撑自己,这种狂热有时会因无能为力而哭泣,但它仍持续不断。我爱我的工作爱到迷恋的、邪乎的程度,犹如苦行僧穿的粗毛衬衣老搔他的肚子。(致路易丝·科莱,1852年4月24日)
对照川端康成的《名人》。经过一小时零九分长考,名人终于走了一手,见只见:
名人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左顾右盼,时而又强忍恶心似的耷拉下头,痛苦万状。他一反常态,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也许这是在逆光下看名人的缘故吧,他的脸部轮廓朦胧松弛,仿佛是一个鬼魂。
人类精神的创造过程,远不像终端产品那样美妙。蓬头垢面,失魂落魄,这才叫“意匠惨淡经营中”。但这样的苦行和鬼相,不为人知,人亦不乐知。世人欣赏的是捷才,喜欢的是快钱。赌徒的胜利来得容易,棋手的成功取得辛苦,人情好逸恶劳,所以大家都愿意做那个买彩票中巨奖的幸运赌徒,你胼手胝足节衣缩食挣下一大份家业,头上是没光环的。所以李白容易被神化,什么御手调羹、力士脱靴、水中捉月等等。杜甫就没有人神化他,连后人捏造的饭颗山头的诗人形象,也是一脸苦相。不知为什么,苦吟者总给人智短力绌的印象。因此,有人明明勤奋出成果,偏要说自己没怎么花力气。比如殚精竭虑写《失乐园》的弥尔顿,就喜欢把夜里辛辛苦苦攒成的诗句,说成是不请自来的缪斯的赏光。俗话说“贪天功为己有”,他情愿倒过来,“贪己功为天有”。
可一般读者面对的只是现成的文本,只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照韩愈的说法是“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就像到了龙门石窟,被卢舍那大佛一下子震慑了,整个儿是圆融光辉的巨大存在,当年千锤万凿的劳动已经被抹去了痕迹。所以瓦雷里才会说,灵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在几分钟之内,读者所受到的冲击却是诗人在长达几个月的寻找、期待、耐心和烦躁中积聚起来的发现、对照以及捕捉到的表达方式的结果。他归功于灵感之处远远多于灵感可以带给诗人的东西。(《诗与抽象思维》)
所谓灵感,不过是相对渐悟而言的顿悟,是旬日艰难之后的刹那轻松。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文心雕龙·神思》)“应机立断”的“断”来得快,当然是灵感;“研虑方定”的“定”来得慢,但也不能说不是灵感。人分两种人,诗有两种诗,赌博和下棋确实可以解释两种基本的写作机制,但两者绝非水火不容。除了发语天然的民歌手,世上没有只凭一时兴会写诗的人,他必须历练很久,才能获得诗神的垂青。你看他像是掷骰子豪赌了,其实只不过熟能生巧,运算速度快过常人而已。天才如李白,也曾前后三拟《文选》,“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可见铁杵磨成针的传说加在他头上,只是要告诉我们赌徒是怎样炼成的。
毕竟诗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所以没有哪位诗人赌运亨通,却对下棋一窍不通。但如果诗光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磨出来,而不曾噼噼啪啪伴随着一串灵感的小火花,让人频频开出好彩来,他的努力便是无望的,不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说:
我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出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过去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才是诗人的高回报。像福楼拜那样苦大仇深的文字的“囚徒”,也常有“翻墙越狱”的狂喜:“我也有很难抑制快乐的时刻。那时,某种由衷的、极富快感的东西从我的身上突然喷发出来,有如灵魂出窍。我感到心荡神驰,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思绪里,仿佛一股温热的馨香通过室内的通风窗扑面而来。”你看,这不就是骰子一掷十卢九雉的高峰体验么?所以,哪怕可怜如福楼拜,也是集囚徒与赌徒于一身的:
从文学的角度谈,在我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酷爱大叫大嚷,酷爱激情,酷爱鹰的展翅翱翔,句子的铿锵和臻于巅峰的思想;另一个竭尽全力挖掘搜索真实,既喜爱准确揭示细微的事实,也喜爱准确揭示重大事件;他愿意大家几乎在“实质上”感受到他再现的东西;后者喜欢嘲笑,并在人的兽性里找到乐趣。(致路易丝·科莱,1852年1月16日)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前者热,大叫大嚷,是赌博型的;后者冷,谨小慎微,是下棋型的。可见,福楼拜在写作过程中不断经历着下棋和赌博。有时举棋不定了,忽然谜一样出现了一个触媒,便有了神来之笔。所以他有一见道之言:“上帝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人只知道中间。”瓦雷里也说:“上帝无偿地赠给我们第一句,而我们必须自己来写第二句,而第二句必须跟首句首尾同韵,而且无愧于它神赐的兄长。”这就是赌博和下棋交替使用。上帝是“前驱有功”,由他开始的第一行是博,掷骰子,靠天收。从第二句起,由自己“继”以“后援”,是弈,精算师,手艺活。所以灵感问题还涉及作品的大小。上帝送上的,或自己碰上的,可能是一首绝句或俳句;而对于一首具有延展性的长诗来说,瞬间的灵感就靠不住了,就好比百米冲刺要靠爆发力,跑马拉松却要凭耐力。
不同的诗如此,不同的诗人身上这博和弈的比例也不一样。有的人思路缜密,律法精严,下笔不苟,比如老杜,但也不能说老杜的诗全都是改出来的。他难道就没有博塞的欢娱,最适当的字词一下子都凑巧妥妥帖帖在最适当的地方排好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老杜这首“生平第一快诗”,写来一定也很快。又比如莎士比亚,好像是用赌徒的方式完成了高明的棋手才能有的最稳定的发挥,几乎每一行都熠熠生辉,但是说穿了,他也就是一台每秒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罢了,算得快也还是算。
所以,说写作分两种机制,恐怕还是强生分别,因为细究下去,所有的写作都是在众多的偶然中寻求那个唯一的必然。博中有弈,因为靠灵感也不是一味的“弃术任心”。完全的“弃术”,“任心”也任不来。而弈中又有博,不断的量变最后产生质变,临界点一下子突破了,于是茅塞顿开,冰山忽化。老杜《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中有两句特别能说明问题:“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前一句是弈棋,是滴水穿石;后一句是赌博,是电光火石。
相比博塞之文,刘勰更推崇善弈之文,但顾随问得好:你说善弈者还要“以待情会,因时顺机”,所谓“机”“会”,难道不仍然类似于博徒邀遇的那个“遇”么?再说,善弈之文的理想境界也是要自然浑成,要把制作的痕迹尽量抹去,虽出诸人工,却宛若天成。也就是说,诗人要能用弈棋型的手法来制造赌博型的效果,不可无匠心,不可有匠气。
马基雅维利说过:“我们所做的事,有一半受到命运主宰,另一半可由自己控制。”换句话说,人生就是一场博弈,一半可控,一半不可控。从前中国民间说科举考进士靠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那可控的更是只有五分之一了。诗的写作应该反过来吧?《庄子》中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本来你走慢我也走慢,你走快我也走快,但你若是一溜烟跑掉,我就目瞪口呆,赶不上了。“亦步亦趋”可以形容下棋,但是“奔逸绝尘”就一定是赌博。下棋可以学,赌博学不来,所以从古到今的创作理论,什么小说教程、诗法大全等等,都只能对下棋的人有用,对赌博的人无效。这恰恰是因为,写作这件事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既可以谈论,又不可以谈论,既说得清楚,又有一些最关键的东西说不清楚。陆机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刘勰说:“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他俩到最后都“未识”“不能言”“不能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