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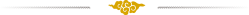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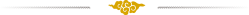
劳动的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初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物属于劳动者。没有地主和雇主要求同他分享。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因分工改进劳动生产力,劳动工资也随之而提高。一切东西都会变得更加便宜。用更少量的劳动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在这种状态下,由于等量劳动生产的商品自然会相互交换,所以,更少的劳动的产物就可以买到各种商品。

雇用童工的早期工厂

但是,虽然所有的东西在实际上会变得更加便宜,许多东西在表面上比以前却会更贵一些,或者说会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例如,假设在大多数的行业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10倍,或者说一天的劳动能生产出相当于最初10倍的产量;但在个别行业中劳动生产力只提高了一倍,或者说一天的劳动只能生产出最初两倍的产量。用大多数行业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去交换该个别行业中一天劳动的产物,10倍于原生产量的前者只能购买到两倍于原生产量的后者。因此,后者的任何数量,例如一磅,似乎比以前要贵5倍。可是实际上,它要便宜一半。虽然要用其他货物5倍的数量去购买它,却只需有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生产它。因此,获取它会比以前容易一半。
但是一引入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这种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的原初状态,便宣告终结。所以,早在劳动生产力取得最大的改进以前,那种状态便已终止,它对劳动报酬或工资的影响如何,就不必进一步去探索了。
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会要求从劳动者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集的几乎全部的产物中得到一份。地主的地租构成了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产物的第一项扣除。
种田者很少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以维持生计到庄稼收割。他的生活费用一般由雇主,即雇用他的农场主的资本预付;除非能分享劳动的产物,除非自己的资本能带来回报,否则农场主是没有兴趣雇用农业工人的。这种利润是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所得产物的第二项扣除。
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物,也同样要扣除利润。在所有的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部分的工人在完工之前都需要有一个雇主,为他们提供原料,预付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分享劳动在所提供的原料上增添的价值,这一份就是他的利润。
确实,有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工人,其资本足以购买工作所需的原料,并在完工以前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既是雇主,又是工人,能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或劳动在所使用的原料上所增加的全部价值。这包含了通常归两个不同的人所有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
不过这些情形并不常见,在欧洲各地为雇主工作的工人和独立工人的比例大概是20:1。各地一般将劳动工资理解为:当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人是另一个人的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的工资。
一般所说的各地劳动者的工资,都取决于利益迥然不同的双方通常所订立的合同。劳动者盼望尽可能多得,雇主盼望尽可能少给。前者倾向于联合起来提高劳动工资,后者倾向于联合起来降低劳动工资。

英国博尔顿的家庭工厂

然而不难预料,通常两方中的哪一方能在争执中居于有利地位,能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少,联合容易得多,另外,法律允许或至少不禁止他们联合,但法律却禁止工人联合。我们没有任何议会法令,反对联合降低劳动价格;但却有许多法令反对联合提高劳动价格。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坚持得更久。地主、农场主、制造业者或商人,即便一个工人都不雇,靠已有的资本也往往能生活一两年。而失业的工人,很多都不能撑一星期,能撑一个月的更少,能撑一年的简直没有。长期来看,像工人不能没有雇主一样,雇主也不能没有工人,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
据说,我们虽然常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很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但如果有人因此认为雇主很少联合,那他就是昧于世事,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随时随地地联合,秘而不宣,但又始终如一地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实际工资率。破坏这种联合在任何地方都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行为,都会遭到近邻和同行们的谴责。我们确实很少听到这种联合,因为这是一种平常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有时也加入某些联合,甚至把劳动工资压到实际工资率之下。这些联合总是不声不响地偷偷进行,直到付诸实施那一刻,那时工人们会像平常一样毫无抵抗地屈服。工人们虽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联合,别人却闻所未闻。不过,这种联合常常遭到工人们相反的防御联合的抵制;有时没有这种挑衅,工人们也自动联合起来,以提高劳动的价格。他们常用的借口,有时是食物价格贵,有时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然而不管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些联合总是广为人知。为了迅速解决问题,他们总是狂呼呐喊,有时使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绝望,像绝望者那样荒唐放纵地行动——要么饿死,要么威胁雇主们立即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些场合,雇主们这一边也同样狂呼呐喊,不停地向地方官高声呼救,要求严格执行那些已经通过的严厉反对仆人、工人和工匠联合的法律。因此,工人们很少从这种喧嚣联合的暴行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些暴行,部分由于地方官的干预,部分由于雇主们的超乎寻常的坚定,部分由于大多数工人为了眼前的生存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被惩罚或处死而告终。
但是,尽管雇主们在同其工人的争议中通常占有优势,劳动工资却有一定的比率,即使是最低下的那种劳动的普通工资,也似乎不可能在长时期内降到这个比率以下。
人总得靠工作来生活,他的工资至少要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情况下,工资甚至还必须多一些,否则他就不可能养家糊口,而且这类工人的家族就不可能维持到下一代。因此,坎梯隆先生似乎认为,最低贱的那种普通劳工所赚得的,无论何处至少必须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以便其能抚养两个孩子;妻子由于必须照顾孩子,认为其劳动只要足以维持她的生存即可。但是,据统计,半数孩子在成年以前就夭折了。因此按这种说法,最穷的劳动者也必须努力至少养育四个孩子,以便其中两个能有机会活到成年。但是四个孩子的必要生活费用几乎等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用。该作者又提到,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值他的生活费用的两倍;他认为,一个最低级劳动者的劳动,所值不可能比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更少。至此,看来至少可以肯定:为了养家糊口,即使是最低级的那种普通劳动,夫妻总共的劳动所得,也必须多于恰恰维持两人生活的费用,但是多多少,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比例还是其他比例,我不去加以确定。
可是,某些情况下工人占优势,使他们能将工资提到大大超出上述比率;该比率显然是符合普通人道主义的最低工资。
在任何国家,当对靠工资生活的人,即对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当每年供应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更多时,工人就没有必要去联合起来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人手缺乏使雇主们彼此竞争,他们为雇到工人而竞相抬价,这样就自行打破了阻止增加工资的自然联合。
很显然,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增长,必须同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增长成比例。这些基金可分为两种:第一,超过维持生活必需的费用的收入;第二,超过雇主们自己使用必需的费用的资本。
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有钱人的收入超过他认为足以维持自己家庭的需要时,他就把全部或一部分剩余,用来维持一个或更多的家仆。如果增加这个剩余,他自然就会增加家仆的人数。

等待救济的工人阶层

当一个独立工人,如织工或鞋匠,拥有的资本,除购买自己工作的原料,以及维持自己出售货物以前的生活以外,还有剩余时,他自然会用这种剩余去雇用一个或更多的工匠,以便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利。如果增加这种剩余,自然就会增加他的工匠人数。
因此,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自然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
引起劳动工资上升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因此,劳动工资最高的,不是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任何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在纽约州,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币3先令6便士,合英币2先令;造船木工,美币10先令6便士,外加值英币6便士的1品脱朗姆酒,总计英币6先令6便士;建房木工和泥瓦匠,美币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美币5先令,约合英币2先令10便士。这些价格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据说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资也和在纽约一样高。在北美各处,食物的价格比在英格兰低得多,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说发生过饥荒。在最坏的季节,虽然出口较少,但他们总是足够维持自己。因此,如果劳动的货币价格比在母国各处都高,其真实价格,即它给予劳动者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支配能力,比例一定高得更多。
北美虽然还没有英格兰那么富有,但比英格兰更繁荣,而且在获得财富的道路上前进得更快。任何一国繁荣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长。在大不列颠,以及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在近500年中居民人数未能翻倍。而在不列颠的北美各殖民地,已经发现居民人数每20或25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现在,这种增加主要不是由于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由于人口的大量繁衍。据说,耄耋之人常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后代有50个到100个,有时更多。劳动的报酬在那里是如此丰厚,以至于子女众多的家庭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是父母富裕和富足的源泉。根据统计,在自立门户以前,每个孩子的劳动会给父母带来100镑的净收入。一个中下阶层的年轻寡妇,带着四五个子女,要在欧洲再嫁是几乎不可能的,而在北美却像一种财富一样经常被追求。孩子的价值,对婚姻是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对北美人一般早婚就不觉奇怪了。尽管这样的早婚使人口大量增长,在北美抱怨人手不足之声却仍不绝于耳。对劳动者的需求和用来维持他们的基金,似乎比能雇到的劳动者人数增长得更快。

更高工资的驱使

虽然一个国家可能非常富有,但它如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便不能期望那里的劳动工资会很高。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即居民的收入和资本,数目可能极大,但是如果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雇用的劳工人数就能很容易地供给次年所需的劳工人数,甚至还能超过。这样人手就不可能稀缺,雇主们也不可能为雇到工人而竞相抬价。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人手会自然地增加,超过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持续不足,工人为获得工作不得不竞相降价。如果在这种国家,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本人的生活费,并使他能养活家庭,那么,劳工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不久就会使它降到与一般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比率。中国长期是最富的国家之一,即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者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中国或许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许久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特性所容许达到的充分富裕程度。旅行家们的记载在许多其他方面虽有不同,但在如下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中国的劳动工资很低,工人发现难以养活一家人。如果一整天在地里干活的所得在晚上能换得少量大米,那他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状况可能更糟。他们不像在欧洲那样,懒散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而是背着本行业的工具,在街上不停地奔走,提供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一样。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穷的国民。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成百上千的人家在陆地上没有栖息之地,而是长期生活在河流、运河之上的小渔船中。他们能找到的生活资料是如此贫乏,以至于渴望捞到从任一欧洲船只抛下的最脏的废弃物。任何腐尸,例如狗或猫的死尸,即便腐烂过半并发臭,他们也喜欢,就像其他国家的人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婚姻在中国受到鼓励,不是由于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利,而是由于有杀掉他们的自由。在所有的大城市,每晚都有几个儿童被抛弃在街头,或是像小狗一样被溺死在水中。做这种可怕的事情甚至据说是许多人赖以谋生的公开的职业。
可是,中国虽然或许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未走向倒退。没有一个城市被居民遗弃。土地一旦开垦就不会被荒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劳动必然继续维持着,而维持这种劳动的基金也因而必然不会明显减少。所以最底层的劳动者,尽管生活资料匮乏,一定能想方设法勉强维持自己的种族,使惯有的人数保持不变。
但在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明显下降的国家,情况就会不同。在各类不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仆役和工人的需求会比前一年少。许多在上层阶级成长的人由于在他们自己的行业中找不到工作,会乐于在最低级的行业中找工作。最低级的行业中不仅本身有过剩劳动力,还有所有其他阶层的劳动者流入,因此就业竞争会十分激烈,以至于劳动工资降低到使劳动者的生存变得极为可怜和贫乏的程度。即便按这种苛刻条件,许多人也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就被迫靠乞讨或干穷凶极恶的勾当,才能觅得一口饭吃。匮乏、饥荒、死亡会马上在那个阶级中蔓延,并扩展到整个上层,直到该国的居民人数减少到被苛政和灾难摧毁后剩下的收入和资本可以容易维持生存的程度。这或许差不多是孟加拉以及东印度某些其他英格兰殖民地的现状。在一个土地肥沃而之前人口大量减少,因此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的国家,如果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饿死,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那里用于维持贫穷劳动者的基金一定在迅速减少。保护和治理北美的不列颠宪法与压迫和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的本质区别,用这两地的不同情况来说明,也许是再好不过的。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不足,是国家停滞的自然征兆,而他们的饥饿状态则是迅速衰退的自然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