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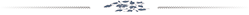
“先儒”、“后儒”之辨,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合儒”策略之一,也是他们诠释程朱理学的重要手段。清代前期,耶稣会士继承了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hoeus Ricci,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人)的传教路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用“先儒”、“后儒”的划分方式,以孔孟等早期儒家为“先儒”、“正儒”,以汉代以后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为“后儒”、“俗儒”,推崇先秦典籍,贬抑后人注疏。他们认为,“先儒”存有疏漏,“后儒”遭受蒙蔽,提出以天主教“补儒之未逮”,辟“俗儒”以复“正儒”,从而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比如,他们以先秦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对应“天主”(Deus为拉丁文,音译为“陡斯”,“天主”为当时专门创造的词),以“仁”对应“爱”(Agape),强调原始儒学与天主教的一致性;以“太极”、“理”为依赖“上帝”即天主者,认为宋明理学以此为本体是“误认天主”。
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大都受到利玛窦的影响,认为“五经”等儒家早期经籍含有天主教的记载,并以孔子为哲学家,以祭孔为后人表达追思的仪式而非宗教信仰。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比利时人)等在上书请求清廷重新审理四年前的“历狱”时,为论证天主教的合法性,引《诗经》为据说:“惟是天主一教,即《诗经》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为万物之宗主。”
 二十二年,他在向康熙帝介绍“理推之学”(西方逻辑学——笔者注)时,称赞“孔孟之学,不世不磨”。
二十二年,他在向康熙帝介绍“理推之学”(西方逻辑学——笔者注)时,称赞“孔孟之学,不世不磨”。

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字再可,意大利人)为“历法之争”中南怀仁的有力支持者,他在《不得已辩》中指出,“先儒”学说中存有“天主”之义:“‘天主’二字,亦中华有之,吾西国称‘陡斯’也。其义则曰‘生天生地生万物之大主宰’,简其文曰‘天主’。‘六经’、‘四书’中言上帝者,庶几近之。”
 他认为儒家所说之天含义有二,一为有形象之天,一为无形象之天。无形象之天,“指天主,即华言上帝也,乃生我养我之大本大原也”。
他认为儒家所说之天含义有二,一为有形象之天,一为无形象之天。无形象之天,“指天主,即华言上帝也,乃生我养我之大本大原也”。
 他还说,天主教的天堂地狱之说也见于儒家典籍:
他还说,天主教的天堂地狱之说也见于儒家典籍:
《诗》曰“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曰“三后在天”;《书》曰“乃命于帝庭”,曰“兹殷先多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非天堂乎?有天堂,必有地狱,二者不能缺一。若谓盗跖、颜回、伯夷、桀、纣同归一域,则圣贤徒自苦耳。天堂地狱之说,载之经史,见之事迹,班班可考。

他在《不得已辩》中,针对“后儒”程朱理学宗奉者所说的“无极而太极”、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等观点逐一予以驳斥。利类思认为,汉代以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歪曲和泯灭了先秦儒家“事天”的真意,需要天主教来纠正和恢复。而孔孟等先儒所说道理虽然正确,但并不完备,需要天主教来补充。
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1678~1735,捷克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来华,擅长数学、天文学、音乐。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像敬神一样供奉孔子,孔子是作为一个智慧超群的大哲学家受人尊敬的。”
 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字信未,比利时人)于康熙年间来华。从其刊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的序言看,他继承了利玛窦的思路,以孔子为尊,对程朱理学作了批评。他指出,孔子是敬天的,孔子以前更是崇拜上帝的,而理学家背离了孔子的传统,以“太极”、“理”为本体,为万物之根,为原初的物体(prime matter),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
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字信未,比利时人)于康熙年间来华。从其刊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的序言看,他继承了利玛窦的思路,以孔子为尊,对程朱理学作了批评。他指出,孔子是敬天的,孔子以前更是崇拜上帝的,而理学家背离了孔子的传统,以“太极”、“理”为本体,为万物之根,为原初的物体(prime matter),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字复初)、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字明远)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国王数学家”身份来华。在儒学问题上,他们同样采用了“先儒”、“后儒”的划分方式,视程朱理学家为“后儒”。
李明用儒家早期经典来论证中国古代存有天主神迹。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他从天主教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先人也是诺亚的后裔:“迹象表明,诺亚的子孙的足迹曾踏上亚洲的土地,并最终进入中国的最西部,即现在称之为陕西和山西的这块地方。”其时间早于《圣经》中的编年史记载,三皇五帝就是诺亚的后人。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同样起源于天主,而儒家早期的典籍中可能就含有前基督时期的各种启示。他进而指出,中国上古时期存在宗教信仰,而这种宗教就是天主教。他在致法国红衣主教布荣的信中说:“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中国在三皇五帝时都有祭祀上帝的宗教仪式。“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此后三百年的周幽王时期——即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

对于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李明在写给法国第一重臣、大主教兰斯公爵的书信中对其生平事迹作了专门介绍:“孔子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光辉所在”,是“他们理论最清纯的源泉,他们的哲学,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权威人物”。
 他在给红衣主教布荣的信中说:“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
他在给红衣主教布荣的信中说:“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

而对于宋明理学,李明称之为“儒教”、“文人的宗教”,认为“它在文人学士中具有宗教、政治和哲学色彩”。他声称,宋明理学家“满脑子装的都是流传中国的偶像崇拜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没有遵循先圣思想的精髓,他们的所有注释都堕入了谬误之中”。他还说:
他们所谈的神灵好像就是自然,也就是说这种力量,或者说这种自然的法则将产生、组织和维系整个宇宙。他们说,这是一个纯净的、完美的、永恒的原则,是万物之源、万物之灵,这才是真正的区别所在。他们利用一些精美绝伦的字眼,表面上好像并没有抛弃古人的东西,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教义。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麻木不仁的家伙那儿听来的教导,认为这种道散布在物质里面,制造了各种变化。公正无私、无所不能、一统阴界、审判苍生的上天不复存在了,其著作里面只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与任何宗教信仰都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口口声声、连篇累牍地说要热爱上帝,要遵从天命,实际上他们口是心非,说话的时候就带有亵渎的意味,也压制了所有宗教情绪。
在李明看来,中国的“先圣”、“先儒”是遵从天主的,而“后儒”即理学家及其宗奉者仅是承袭了儒者之名,而无其实,是一群古代偶像的崇拜者,一群无神论者。

白晋是“索隐派”(Figurists)的核心人物。索隐派认为,人类同源,天主的真理启示具有一定隐蔽性,在犹太——天主教文本之外的“教外圣贤”身上同样隐藏有天主的真理启示。由于中国人不知道天主教,故对很多先秦典籍只认识其表层文字含义,而不理解其深层意义,只有信奉天主、熟悉《圣经》的人,才能发现和理解潜藏于其中的隐秘真理。因此,他们力图通过特定的诠释,在先秦典籍中发现天主的启示。在方法论上,他们存有一种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的倾向。
白晋著有《中国语言中之天与上帝》、《古今敬天鉴》、《天主三一论》以及系列研究《易经》的著作。在礼仪之争中,白晋与众多耶稣会士一样,认为天主教义与儒家学说兼容互补。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思想不仅与天主教义完全吻合,而且是天主教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这些经典的记载中,人们不但可以悟出天主教义,还可以找到后来记载在《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圣言降生成人的奥秘,救主之降世与死亡,圣职之功能,均以一种先知预言方式蕴藏于中国古代宝贵的巨著中。”为此,在康熙的关照下,白晋还对《易经》进行了数年研究,试图从中寻找有关天主教和《圣经》的记载,以论证“合儒”策略的合法性。他断定,《易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古代典籍之一,天主教的一切奥秘、教义和箴言,都可从《易经》等儒家典籍中找到。《易经》的作者伏羲实际上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克。
 白晋编撰的《古今敬天鉴》(又名《天学本义》)同样站在天主教立场上,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与天主教义加以交互阐释,选择儒学文献资料证明天主教义,依据《圣经》发明先秦儒家经典的天学本义:
白晋编撰的《古今敬天鉴》(又名《天学本义》)同样站在天主教立场上,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与天主教义加以交互阐释,选择儒学文献资料证明天主教义,依据《圣经》发明先秦儒家经典的天学本义:
南北东西四方之人,同为上天一大父母君师所生养,治教皆原属一家,惟一天学之人。中华经书所载,本天学之旨,奈失其传之真。西土诸国存天学本义,天主《圣经》之真传,今据之以解中华之经书,深足发明天学之微旨。

经此诠释,儒家上古典籍便含有了天主教的真理启示。白晋对于“后儒”的评价前后有较大变化。前期坚持利玛窦规矩,以排斥为主;后期为推进“合儒”策略,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如“理”、“太极”等,并不一概否定,而是采用索隐派的方法,有选择地加以利用、附会。
法国耶稣会士马约瑟(Joseph-Henrg-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字龙周),著有《儒教实义》、《经传议论》、《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等。作为索隐派成员,他虽继承了白晋牵强文义的诠释策略,但不太重视“前儒”、“后儒”的划分,对“后儒”有较多附会、肯定。
马约瑟对中国典籍的疏证受到索隐派方法影响,以天主教义为普适性准则,相当随意地剪裁儒家典籍。他坦然声称:“作此种疏证及其他一切撰述之目的,即在使全世界人咸知,基督教与世界同样古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已早知有天主”,他本人入华30年之努力也尽在于此。他在疏解过程中,“凡有不明之段落,历代意见纷纭之解释,《诗经》中之譬喻,《易经》中之卦爻,咸加利用,以备传教之引证”。
 马约瑟视儒家经典中的“圣人”、“大人”等文字与“天主”等同,然后以《易经》为中枢,把《诗》、《书》、《礼》等其他典籍统摄起来。与白晋相比,马约瑟更为大胆。白晋坚持“先儒”、“后儒”的区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后儒”对先秦儒学的疏解视为对真义的遮蔽与曲解。马约瑟则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区分,主张天主教义不仅体现在“天”、“上帝”之中,而且体现在“道”、“太极”、“性”、“理”等基本范畴之中,不仅伏羲等三皇五帝深得天主教义,而且二程、朱熹也知晓上帝学说。例如,其《儒教实义》采用白晋《古今敬天鉴》的模式,以诠释儒家经典的名义来传播天主教义理。他认为,宋代以降,儒者心中依然保留了“上帝之实义”,只要是“醇儒”,便必定会“信古经大训”、“事皇天上帝”;反言之,判断“正儒”、“醇儒”、“真儒”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信奉“天学”。
马约瑟视儒家经典中的“圣人”、“大人”等文字与“天主”等同,然后以《易经》为中枢,把《诗》、《书》、《礼》等其他典籍统摄起来。与白晋相比,马约瑟更为大胆。白晋坚持“先儒”、“后儒”的区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后儒”对先秦儒学的疏解视为对真义的遮蔽与曲解。马约瑟则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区分,主张天主教义不仅体现在“天”、“上帝”之中,而且体现在“道”、“太极”、“性”、“理”等基本范畴之中,不仅伏羲等三皇五帝深得天主教义,而且二程、朱熹也知晓上帝学说。例如,其《儒教实义》采用白晋《古今敬天鉴》的模式,以诠释儒家经典的名义来传播天主教义理。他认为,宋代以降,儒者心中依然保留了“上帝之实义”,只要是“醇儒”,便必定会“信古经大训”、“事皇天上帝”;反言之,判断“正儒”、“醇儒”、“真儒”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信奉“天学”。
 他在该书中判断“圣道”真伪时说:先秦“真道”随着孔、孟没而式微,秦、汉以来,异端蜂起,佛、老篡诬,直至宋代诸子出,才得以存续。
他在该书中判断“圣道”真伪时说:先秦“真道”随着孔、孟没而式微,秦、汉以来,异端蜂起,佛、老篡诬,直至宋代诸子出,才得以存续。
濂、洛、关、闽之徒,卓然自尊,而黜汉、唐之学。横渠自成一家,康节又是一门。至朱子则无所不容,然虽善言其理气,亦照诗书之明文未尝不尊称皇天上帝,以超出庶类,而为万物之主宰也。后之学者,若论理不论文,则明儒视宋儒,与宋儒视汉儒无异,而是非无尽云。

马约瑟之所以肯定后儒朱熹之功,是因为朱熹传继圣人道统,但这里的圣人已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天主教的“圣人”,道统也不再是程朱理学的“道统”,而是尊称皇天上帝的天主教之“道”。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er de Charne,1695~1767,字玉峰)于雍正六年(1728)进京,在华长达39年,所著《性理真诠》则是肯定“先儒”,排斥“后儒”,攻击宋明理学抹杀了造物主的存在。他说:“先儒”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近儒不然,矜谈性理,两端至理,一笔勾倒。惟认理气为天地之本、人物之原,而于上古经书所称皇矣上主,及降衷之恒性,竟不细加详察矣。噫!今之学者,虽自矜名儒,谈理切实,而其实较拜佛邪神之异端尤甚”。
 他在该书中赞同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字思极,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us Lingobardi,1559~1654,字精华,意大利人)等人的观点,认为“太极”是一种“元质”,而非造肇万物之主宰。
他在该书中赞同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字思极,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us Lingobardi,1559~1654,字精华,意大利人)等人的观点,认为“太极”是一种“元质”,而非造肇万物之主宰。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e,1602~1699,字克敦,西班牙人)于顺康年间来华传教。他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与利玛窦等人有明显不同,认为祀孔、祭祖是宗教仪式,主张禁行中国礼仪。但在儒学问题上,他则采取利玛窦式的思路,肯定“先儒”,排斥“后儒”。他无视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解释完全从《圣经》出发。
利安当的《天儒印》接续了《天主实义》的做法,更加全面地借用儒家早期典籍来阐发天主教义。《天儒印》于康熙三年(1664)问世,体现了利安当对“先儒”的看法。他虽不是索隐派成员,也不是耶稣会士,其观点却与后者有着相似之处。《天儒印》不仅以中国上古时期为信仰上帝的时代,而且认为“四书”在在皆隐含着天主教的启示和教义,只要借助《圣经》,就可以获得这种认识。该书截取“四书”中的某些关键字句,直接用天主教义加以阐发、印证,而很少做实证性研究,因此,其牵强附会程度往往超过耶稣会士。
利安当认为,先秦经典“四书”中关于“天主”及其属性的记载随处可见。在早期传教士的著作中,对“陡斯”一词的汉语对应词无统一固定用法,汉语称呼较为混乱。崇祯元年(1628)嘉定会议对此做出明文规定,此后只准使用“天主”一词,而禁用“天”、“上帝”等词汇来指称“陡斯”。利安当虽反对实行中国礼仪,但又认为儒家经典中对应于“陡斯”的词汇并不少见。在《天儒印》一书中,凡是“四书”中含有本体、本原、终极之意的词汇,他均采取强行就我的做法,将其认定为是对“天主”的另一种表达。依此原则,他认为“四书”的“天”、“道”、“本”、“至诚”、“至善”等均为“天主”。且看他对《大学》“至善”、《中庸》“立天下之大本”中“本”字的解释:
《大学》云:“在止于至善。”超性学论,惟天主可云至善,则至善即天主也。其曰“止于至善”者,谓得见天主之至善而息止安所也。夫止者,吾人之向终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盖既知吾人究竟,即当止向天主,则定而静而安而虑矣。虑而后能得者谓于目前而能豫筹身后之图,则有备无患,自得所止也。凡失天主为永祸,得天主为永福。得即得至善永福之天主也。

本者,所以然之谓也。凡物有三所以然,曰私所以然,曰公所以然,曰至公所以然。如父母为人之私所以然,主宰一家者也;如君王为人之公所以然,主宰一国者也。二者名曰小本。天主为万有之至公所以然,名曰大本,是人类之大父,乾坤之共君,主宰天地万物者也。

这种解释先立天主教宗旨,然后以“四书”注之,明显不合经典原意,实质是以天主教义为中心的普遍论。
他关于天主之属性的介绍也采取此种附会方式。如他引用《中庸》解释天主的“全知”、“全能”、“全在”、“创生元祖”说:
《中庸》云:“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盖言惟天主则无所不知也。
“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盖言惟天主则无所不能也。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上下察者,非以明天主无所不在之义乎?
《中庸》云:“造端乎夫妇。”天主创生人类,其始惟一男一女。结为夫妇配偶,令其传生,是为万世人类之元祖。所为造端也,此人生之所自来也。

以上所引《中庸》的内容,原是用以阐述日用伦常的“君子之道”,利安当则无视儒家学说的宗旨,完全把儒家典籍视为可凭其胸臆(天主教义)而加以解读的文本。
在对“后儒”以及“理”、“太极”等的看法上,他与利玛窦较为接近。利玛窦反对以“理”、“太极”对应“天主”,是因为他们在属性上是没有灵性、不能自立的物类“依赖者”。利安当在《传教论文》(
Mission Treatise
)中明确反对以“理”、“太极”来对应“天主”。他认为,这些概念在本质上是属于“物质性”的,而非精神性实体,不能脱离气而存在;它们先于气而存在,是逻辑上的或本原上的,而非时间上的。同时,这些概念所指也不具有生机、生命、意志、理智等上帝属性。

需要指出的是,利安当与利玛窦等虽然都是立足于在华传教,但由于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不同,他们的传教思想、策略也自然有所不同。利玛窦、白晋等耶稣会士推重“先儒”,排斥“后儒”,目的是为“合儒”“补儒”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利安当对“先儒”、“后儒”的态度则相当强硬,完全以天主教为绝对真理,而漠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它对“先儒”的肯定,目的是使“先儒”屈从于天主教义,而不是认同“先儒”的价值,这与对“后儒”的排斥,在实质上并没有差别。
来华传教士的“先儒”、“后儒”之辨,最终并没有得到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认可。以白晋为例,教廷所派传教士认为,按照白晋的说法,中国人的祖先成了最早的基督徒,中国人“认识”基督教更在耶稣降生之前,这是对圣教的亵渎和曲解。康熙帝认为,白晋“只是自以为是,零星援引群书而已,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其“援引皆中国书,反称系西洋教”,胡编可笑,是对儒家学说的歪曲和附会。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学说在中西方均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在西方,他们对“先儒”的肯定,被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拿来作为批判天主教普适性理论、揭露宗教神学专制的论据。在中国,他们对“后儒”的否定以及对西学的传播,一方面为理学宗奉者所攻击,另一方面又被当时的反理学思想家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