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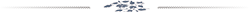
乾隆中叶,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是清代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清代汉学历经长期积累,至此达到鼎盛。四库馆聚集了戴震、纪昀、朱筠、周永年、邵晋涵、任大椿、金榜、王念孙等一批著名学者,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由于获得了官方支持,汉学得以与宋学分庭抗礼。清代学术分裂为宋学、汉学两大阵营。
宋学仍居“正学”之位,但不复成军。所谓的理学名臣,仅有陈宏谋、朱珪、尹会一等寥寥几人。有人称,“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
 理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陈陈相因,沦为官样文章和晋身之资。陈宏谋不由发出感慨:“每见著述家多以理学自负,而无裨于实用,理学竟为天地间无用之人,学术不明,为世诟病,可为浩叹。”
理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陈陈相因,沦为官样文章和晋身之资。陈宏谋不由发出感慨:“每见著述家多以理学自负,而无裨于实用,理学竟为天地间无用之人,学术不明,为世诟病,可为浩叹。”
 朱珪在庙堂大讲理学,晚年却嗜仙理佛。颓势难挽,翁方纲等较为开明的学者,转向汉宋兼采,取长补短。理学不能维系社会信仰,难以满足统治者需要。在此状况下,乾隆帝调整文治政策,主张兼采汉、宋,以汉学辅助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朱珪在庙堂大讲理学,晚年却嗜仙理佛。颓势难挽,翁方纲等较为开明的学者,转向汉宋兼采,取长补短。理学不能维系社会信仰,难以满足统治者需要。在此状况下,乾隆帝调整文治政策,主张兼采汉、宋,以汉学辅助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汉学家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官方的态度。“铲除畛域”,“一本至公”,为清廷所用。
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汉学家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官方的态度。“铲除畛域”,“一本至公”,为清廷所用。
汉学则跃居清代学术主流,几乎占据学界全部势力。故后世学者每每以汉学考证来界定清代学术,称之为“正统派”。汉学一家独大,但并非整齐划一。章太炎、梁启超等在前人基础上明确提出吴、皖两派说。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把汉学划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派。此外,又有浙东学派、扬州学派等提法。以人物言,无疑以惠栋学派和戴震学派最具代表性。
汉学的风格,与宋学比较而易见。清代之宋学,是顺着宋元明而来。清代宗理学者恪守宋儒程朱之道,在治学、修身、治国方面是统一的,至少形式上如此。换言之,他们是沿着宋元明之道路继续前行,守成而非独辟,历史与现实一以贯之。汉学则不然。汉学之所以为汉学,从名义和动机上说,是要改换轨辙,改宗汉儒,走汉儒之道。就儒家的理想而言,道、学、政一体,此道至少涵括治国之道、修身之道和为学之道。走汉儒之道,意味着在治国、修身和为学等方面以汉为法。以惠栋为代表的清儒标举汉学,即以此为逻辑起点。惠栋认为两汉经学在佛学兴起之前,去圣贤最近,纯粹当尊。他弃宋尊汉,于宋元以下学说一概排斥。确如梁启超所说,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唯问“汉不汉”,以“古今”为“是非”标准。
 惠栋一派不仅自居于汉学正宗,而且要把汉学立为儒学正宗。他的再传弟子江藩编《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排斥宋学,且几将顾炎武、黄宗羲等汉学前驱摈而不录,明确表露出该派自居正统的“初衷”。
惠栋一派不仅自居于汉学正宗,而且要把汉学立为儒学正宗。他的再传弟子江藩编《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排斥宋学,且几将顾炎武、黄宗羲等汉学前驱摈而不录,明确表露出该派自居正统的“初衷”。
 钱穆说吴学是由反宋学起家,“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
钱穆说吴学是由反宋学起家,“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
 可谓至论。该派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已明确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
可谓至论。该派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已明确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
 惠栋一派博古而不通今,他们所主张的“汉儒之道”在社会中难以落实。例如,他们的治学便与自身的修行相悖。他们一边否定宋儒的性理之学,一边运用宋儒的修身之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惠氏家族的这副名联,可以说是当时众多汉学家的写照。
惠栋一派博古而不通今,他们所主张的“汉儒之道”在社会中难以落实。例如,他们的治学便与自身的修行相悖。他们一边否定宋儒的性理之学,一边运用宋儒的修身之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惠氏家族的这副名联,可以说是当时众多汉学家的写照。
青出于蓝,后胜于前。戴震一派尤其是戴震本人,在清代汉学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梁启超甚至认为,“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有别于惠栋一派“弃宋宗汉”,“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
有别于惠栋一派“弃宋宗汉”,“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称:“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称:“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
 戴震受学江永,江永治汉学兼综朱子,故戴震对程朱理学理解较为深刻,而不像惠栋一派轻易予以否定。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戴震受学江永,江永治汉学兼综朱子,故戴震对程朱理学理解较为深刻,而不像惠栋一派轻易予以否定。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职是,他的学术思想始终带有和会汉、宋,兼取二者之长的特点。一方面,他继承惠栋的治学门径,重视故训和实证,从而避免了宋学空疏之弊。他明确提炼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职是,他的学术思想始终带有和会汉、宋,兼取二者之长的特点。一方面,他继承惠栋的治学门径,重视故训和实证,从而避免了宋学空疏之弊。他明确提炼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但他又不像惠栋一派佞汉、泥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的考证方法类于近代历史科学的归纳法,较为客观平易,与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极相似,而异于含有宗教意味的注经解经。另一方面,较之惠栋一派偏嗜考据,他重视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结合,尤其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他反对为考据而考据,曾以轿夫喻考据,以轿中人喻义理,指出不要把轿夫误作轿中人。戴震不以考据为目的地,故能比一般汉学家走得更远。他所著《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都是以义理为归宿的代表作。由考据而明义理,戴震走的是不同于宋儒的寻求义理之路,得出的也是不同于宋儒的答案。因为是用近乎史学的方法治经学,故他得出的义理带有世俗化或者说祛魅倾向。例如,他对核心范畴“道”、“理”的理解明显不同于宋儒。朱熹从形上本体来理解“道”、“理”,谓“道即理之谓也”,理者性道之统挈。戴震则以“气化流行”来解释“道”,以“密察条析”来解释“理”,以“气在理先”来解释宇宙之本原;又从人伦日用来界定“理”、“欲”关系,主张“天理”、“人欲”的统一,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圣人之道”。
但他又不像惠栋一派佞汉、泥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的考证方法类于近代历史科学的归纳法,较为客观平易,与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极相似,而异于含有宗教意味的注经解经。另一方面,较之惠栋一派偏嗜考据,他重视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结合,尤其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他反对为考据而考据,曾以轿夫喻考据,以轿中人喻义理,指出不要把轿夫误作轿中人。戴震不以考据为目的地,故能比一般汉学家走得更远。他所著《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都是以义理为归宿的代表作。由考据而明义理,戴震走的是不同于宋儒的寻求义理之路,得出的也是不同于宋儒的答案。因为是用近乎史学的方法治经学,故他得出的义理带有世俗化或者说祛魅倾向。例如,他对核心范畴“道”、“理”的理解明显不同于宋儒。朱熹从形上本体来理解“道”、“理”,谓“道即理之谓也”,理者性道之统挈。戴震则以“气化流行”来解释“道”,以“密察条析”来解释“理”,以“气在理先”来解释宇宙之本原;又从人伦日用来界定“理”、“欲”关系,主张“天理”、“人欲”的统一,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圣人之道”。
 所以,钱穆尽管不以戴震立异程朱为然,却欣然承认,戴震治学“极平恕,还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
所以,钱穆尽管不以戴震立异程朱为然,却欣然承认,戴震治学“极平恕,还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
 联系现实世界,戴震敏感地觉察到“天理”与“人欲”之冲突,当道者无不奉理学的“存理去欲”说作为戕害人性的正当工具,从而提出了宋学家“以理杀人”的惊世之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联系现实世界,戴震敏感地觉察到“天理”与“人欲”之冲突,当道者无不奉理学的“存理去欲”说作为戕害人性的正当工具,从而提出了宋学家“以理杀人”的惊世之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无论理论还是现实,戴震所主张的都是一条既异于宋学,又别于“专门汉学”的道路。梁启超说“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无论理论还是现实,戴震所主张的都是一条既异于宋学,又别于“专门汉学”的道路。梁启超说“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于斯可征。简言之,戴震所探索的是一条非汉非宋的新路。
于斯可征。简言之,戴震所探索的是一条非汉非宋的新路。
不过,戴震的义理学说在当时仅得到洪榜、焦循、凌廷堪和阮元等极少数学者的支持或继承。戴震之所以被奉为汉学大师和皖派核心人物,凭借的是其经史考据成就。章学诚洞察到:“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汉学考据风气下,戴震的义理新路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当然,其理论方法本身也有局限。戴震强调“圣贤之道”存乎古经,经非故训不明,故训是获得“圣贤之道”的唯一途径。这就夸大了考据学的作用,限制了自身获取义理的其他途径。正如方东树所指出:“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
汉学考据风气下,戴震的义理新路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当然,其理论方法本身也有局限。戴震强调“圣贤之道”存乎古经,经非故训不明,故训是获得“圣贤之道”的唯一途径。这就夸大了考据学的作用,限制了自身获取义理的其他途径。正如方东树所指出:“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
 由于强调义理尽出于考据,意味着一以古圣贤是从,不敢“以自为创而通其变”,
由于强调义理尽出于考据,意味着一以古圣贤是从,不敢“以自为创而通其变”,
 束缚了创新活力,结果是历史禁锢了现实。钱穆论乾嘉学术时指出:“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
束缚了创新活力,结果是历史禁锢了现实。钱穆论乾嘉学术时指出:“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
 乾嘉学术之偏陷,作为主帜的戴震在所难免。与其他汉学家一样,他过于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社会实践,研寻历史上的“圣贤之道”胜过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关切。这些都决定了戴震及乾嘉汉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道路。
乾嘉学术之偏陷,作为主帜的戴震在所难免。与其他汉学家一样,他过于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社会实践,研寻历史上的“圣贤之道”胜过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关切。这些都决定了戴震及乾嘉汉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