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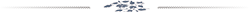
清代前中期,汉学家曾一再批评理学空疏无用,一些人甚至把明朝灭亡归因于此。时过境迁,嘉道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少理学家反唇相讥,认为是汉学的支离破碎,无实无用,导致了清朝国运衰落。
其一,指责汉学脱离现实,空疏无用。
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评,以从汉学阵营倒戈而来的夏炯言论最为激烈。他的《说学》、《乾嘉以后诸君学术论》、《学术有用无用辨》对乾嘉汉学几乎做了全盘否定。他认为“学术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以此衡量,“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名物、制度、音韵、训诂最下。“乾嘉以后近百年来讲学之士专为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丝毫不适于用,且破坏碎裂,转为贼经”。他将清代中期著名汉学家从江永、戴震到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的著述一一点评后归纳说:“此数家者,皆近百年来名稍显著之人,试一一取其书平心而察之,何编足以发明义理,何帙足以有裨经济,即以经史而论,较之国初诸老,真有霄壤之判,徒觉其鄙芜琐碎,坐井观天而已。”

徐桐是晚清时期顽固派的代表,在学术上崇尚程朱理学,他指摘汉学有蹈空之弊。针对汉学家指责宋学为空疏的说法,徐桐反驳说:“汉学家讲训诂者斥义理为空疏,今之言汉学者靡然从之,是大惑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理、义二字,由孟子发之,宋儒推阐其蕴,直至体用同原,显微无间。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皆理义之发挥。本诸身,征诸民,实实落落,真真切切,停停当当,何蹈空之有?讲训诂而不求诸日用行习之故,得非蹈空乎?讲训诂而专骛于标榜名利之场,得非蹈空乎?弃义理以言学,吾不知其所学何事。昔人谓王氏之学如洪水猛兽,今之言汉学者殆又过矣。”
 他认为理学家注重心性修养,强调实体力行,何有空疏之弊?相反,汉学家既不注重内在修养,又乏外在事功建树,才是蹈空不实。
他认为理学家注重心性修养,强调实体力行,何有空疏之弊?相反,汉学家既不注重内在修养,又乏外在事功建树,才是蹈空不实。
其二,攻击汉学考据偏离圣人之道,有害无益。
宗宋学者认为,汉学之害,从其小者言之,不能躬行实践,有害身心。夏炯偏激地说:“训诂考据之学百余年来遍于天下,所称一二好学之士,无非孜孜矻矻数典证文,其于治心检身、由己及物之道微论,躬行实践、能见诸实行者无一人。”
 徐桐说:“今之言汉学者,叩以躬行则未能无愧,叩以求仁则悍然不知。”
徐桐说:“今之言汉学者,叩以躬行则未能无愧,叩以求仁则悍然不知。”
 刘蓉指出,汉学家既不能知,又不能行,猖狂恣肆,甚于阳明“良知”之说:“世之为宋学者,病在隘陋无识,拘滞而不达于理,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舍,必致严于礼义之辨,兢兢不敢少过,则犹庶几君子之操焉。道虽未宏,学与行尚出于一也。至为汉学者乃歧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
刘蓉指出,汉学家既不能知,又不能行,猖狂恣肆,甚于阳明“良知”之说:“世之为宋学者,病在隘陋无识,拘滞而不达于理,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舍,必致严于礼义之辨,兢兢不敢少过,则犹庶几君子之操焉。道虽未宏,学与行尚出于一也。至为汉学者乃歧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以反汉学著名,晚年所作《辨道论》继续攻击汉学,指责汉学“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方东树《汉学商兑》以反汉学著名,晚年所作《辨道论》继续攻击汉学,指责汉学“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光绪年间,笃守理学的豫师认为,方东树《汉学商兑》对汉学在“实力行习”上对圣贤道理的危害还缺乏剖析,于是作《〈汉学商兑〉赘言》以作补充。他在自序中说,汉学毁学术、堕士行,为害世道人心:“其著书立说倡议附会,后生小子乐其引而又便于私也,翕从日众,以为学术人心之害。”
光绪年间,笃守理学的豫师认为,方东树《汉学商兑》对汉学在“实力行习”上对圣贤道理的危害还缺乏剖析,于是作《〈汉学商兑〉赘言》以作补充。他在自序中说,汉学毁学术、堕士行,为害世道人心:“其著书立说倡议附会,后生小子乐其引而又便于私也,翕从日众,以为学术人心之害。”

汉学之害从其大者言之,贼经害道,为祸家国。在宗宋学者看来,汉学家脱离现实,不事身心修养,更遑论经邦济国。夏炯说:“其徒事训诂词章者,日钻月研,咬文嚼字,不复知身心为读书之本,阨而未用,于检身、齐家、治生、接物之道一切不讲,一旦侥幸入官,则农桑、水利、学校以及事上官、接僚属、御书吏等事,更觉茫然无措,一毫无异于俗吏之为也。”
 贺熙龄在归结嘉道之际社会衰落的原因时指出,汉学家“身心未治而欲心治天下国家,无怪其颠倒迷惑而不能自主,眩摇于祸福利害而无能自克也”。
贺熙龄在归结嘉道之际社会衰落的原因时指出,汉学家“身心未治而欲心治天下国家,无怪其颠倒迷惑而不能自主,眩摇于祸福利害而无能自克也”。
 他认为,社会衰落与汉学家专事考据、不关心现实有关。姚莹则称,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从汉学家排斥理学上找到原因:“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入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
他认为,社会衰落与汉学家专事考据、不关心现实有关。姚莹则称,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从汉学家排斥理学上找到原因:“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入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
 孙鼎臣更为极端,他把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归咎到汉学家头上,认为“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羌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
孙鼎臣更为极端,他把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归咎到汉学家头上,认为“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羌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
 晚清宗宋学者对汉学家的这些批评,过分夸大了学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对于学术功用的评价,是从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的:“学之有用无用,在能讲明义理否耳。”
晚清宗宋学者对汉学家的这些批评,过分夸大了学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对于学术功用的评价,是从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的:“学之有用无用,在能讲明义理否耳。”
 运用这一标准,他们不可能对汉学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
运用这一标准,他们不可能对汉学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
平实而论,经世致用是儒家各派的共同主张,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均以此相标榜,但具体表现及实践程度存有差异。相对说来,宋学侧重于“尊德性”,汉学稍偏于“道问学”。晚清时期,社会危机加剧,经世思潮兴起,学术的功用性成为士大夫广为关注的问题,宗宋学者的批评虽有偏失,但对于纠正汉学末流的考据之风,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最后要指出,晚清时期的宗宋学者反对的是清代汉学,而非汉代经学。唐鉴、罗泽南等程朱理学正统人士,以宋儒为宗,但不讳言汉儒有传经之功,他们直接批评汉儒的言辞较为少见。夏炯30岁以后转而激切诋毁汉学,却坦然声称:“夫许、郑之学,皆确然不可易之学也。程、朱虽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主于发明义理,其于汉儒之名物制度未尝不深许焉,而萃精力于其中。”
 再者,晚清宗理学者反汉学,并不是全盘否定清代汉学。他们在一定限度上对汉学的考据成就予以承认,他们论争的手段、方法也或多或少带有汉学印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汉学的影响力仍旧较为强大,他们受到了环境的濡染;另一方面,为增强说服力,他们在论争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一些汉学的方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时期,汉宋之争是相对的,汉宋兼采才是大趋势。
再者,晚清宗理学者反汉学,并不是全盘否定清代汉学。他们在一定限度上对汉学的考据成就予以承认,他们论争的手段、方法也或多或少带有汉学印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汉学的影响力仍旧较为强大,他们受到了环境的濡染;另一方面,为增强说服力,他们在论争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一些汉学的方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时期,汉宋之争是相对的,汉宋兼采才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