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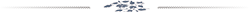
清代学者在“五经”等古文献整理、校勘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他们对《古文尚书》、古本《大学》、《易经》图说等的考订却直接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宗宋学者要想守住门户,就需要对汉学家所提出的这些棘手问题做出解释。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对这些问题没有回避,为维护理学道统,据理力争。兹举伪《古文尚书》为例。伪《古文尚书》对于程朱理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被程朱理学奉为道统心传的十六字经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于该书《大禹谟》篇。而经清儒阎若璩、惠栋、孙星衍等考证,此书为东晋伪书。有人进而就题发挥,对理学权威提出质疑。孙星衍说:“尧、舜、禹、汤、文、武之言,可任其以伪乱真乎?……且圣人之学具在‘九经’,何言不足垂教?而藉伪晋人之言以为木铎,则盗亦有道,释典亦有劝善之言,岂儒者所宜择善服膺哉?若知其伪而不疑,反附于阙疑之义,是见义不为,非慎言其余也。”

宗宋学者明确表示,《古文尚书》事关道统,汉学家排斥伪古文的做法不足取。方宗诚指出:“后儒以《古文尚书》为伪,而《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皆于道体、治本、学术之要极有关系,人生所不可一日昧者,去之则皆泯没矣。”
 他认为,十六字经文含有恒常之道,关系世道人心,万不可因其是伪书而否定其学说的价值。
他认为,十六字经文含有恒常之道,关系世道人心,万不可因其是伪书而否定其学说的价值。
夏炯也从维护圣学道统出发,批评阎若璩的做法失当。他说:阎若璩“攻诘《大禹谟》‘人心惟危’一十六字,以为无一字不从剿袭而来,则肆妄未免太甚。夫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逮有宋濂、洛、关、闽诸儒复生,道统相继,不能外‘危微精一执中’数句。穷而在下,守此数言则为天德;达而在上,守此数言则为王道。其著为成效,昭然可睹……谓《古文尚书》未可尽信则可,谓《古文尚书》无一字可信则断不可。古文之真伪未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辞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深赖以不坠,历代以来朝廷颁置学宫,儒者奉为圭臬,阎氏试自问所学能窥见此中之万一乎?”
 在他看来,《尚书》版本的真伪与义理的是非并无必然联系,读经贵通大义,不能因噎废食。
在他看来,《尚书》版本的真伪与义理的是非并无必然联系,读经贵通大义,不能因噎废食。
夏炘专作《〈古文尚书〉不可废说》陈述不可废的理由,并贬斥汉学家阎若璩等胶柱鼓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过是拾朱子余唾而已。他说:
疑古文者自朱子始。黄勉斋作行状特载疑古文之词,其意盖亦深以古文为不然也。然朱子《中庸章句叙》发明《大禹谟》十六字为历圣传心之要,而文集杂著中《大禹谟》一篇字笺句释,虽于“曰若稽古”三句颇致其疑,而其余阐明精训无余蕴,以为能备二典之所未备……然则古文虽伪,而其言之足以垂世立教。其见取于朱子如此。继朱子而攻古文者,自宋、元迄明,代不乏人。至我朝阎百诗、惠定宇诸先生出,穿穴抵衅,搜瑕索瘢,耳食之徒,众喙一词,莫不唾而弃之矣。然古文之伪在乎来历之暗昧,筋脉之缓迟,文气之散漫,而非谓古昔之格言正论不藉是以存之也……彼阎、惠诸君子其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未免胶柱而鼓瑟矣。

他还指出,汉学家攻击《尚书》为伪,不过是炫耀淹博之资而已,古籍之重于世者,首在其“名言至理”,而不在成书早晚:“今人攻梅赜伪古文,莫不以壁中十六篇为真古文,而深惜其书之不存。窃以为逸十六篇即全在,其书亦无足轻重也。凡古籍之重于世者,为其名言至理足以垂世立教耳。苟言之,不足以垂世立教,则虽上古之书亦不过供学人之记诵,夸奥古竞该博而已。”
 他认为,十六字心传为“名言至理”,《古文尚书》有利于“垂世立教”,理学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他认为,十六字心传为“名言至理”,《古文尚书》有利于“垂世立教”,理学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山阳潘德舆以诗文名世,思想上以理学为宗,他通过分析经文含义来说明这十六字符合圣人原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诋《古文尚书》者谓其出于道书,而以心岐[歧]为二为有流弊,然此二语不可驳也。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前一性字即人心也,后一性字即道心也。孟子剖性为二,而后儒不能驳也,故一心也而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一性也而有义理焉有气质焉,一身也而有大体焉有小体焉,皆《中庸》明辨之义。明辨居致知之终,学矣问矣思矣,复加以明辨者,知不厌其详也。”
 这里,他从理学基本范畴入手,论证“人心”、“道心”与《孟子》、《中庸》切合,以证明《古文尚书》可据。
这里,他从理学基本范畴入手,论证“人心”、“道心”与《孟子》、《中庸》切合,以证明《古文尚书》可据。
宗宋学者对汉学家经学辨伪的反驳,实际上仍旧没离开对训诂与义理二者关系的辨析。汉学家遵循“训诂明则义理明”的原则,由字通经,由经通道,他们首先看重“五经”,而以文字为“五经”之基石;而理学家讲究穷理,重大义,首在“四书”(实际上是《四书章句集注》),“五经”以“四书”为权舆,经文真伪尚属其次。宗宋学者则反之,认为“解经者,解其义也。义苟寻矣,则言语文字之有舛讹,可姑置也”。
 双方的辩论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们对待知识与道德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在诠释方法和思维模式方面的差异。
双方的辩论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们对待知识与道德的不同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在诠释方法和思维模式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