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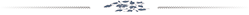
清代前期,一些理学人士主张将西方宗教与科技区分开来,排斥西教,节取西法。理学名儒陆陇其、陆世仪、李光地、张伯行等都具有这种倾向,尽管每个人各有所侧重,具体态度亦稍有差异。
张伯行重在排斥西教。张伯行(1652~1752),字孝先,号敬庵、恕斋,河南仪封人,人称仪封先生。著有《道学源流》、《道统录》、《续近思录》、《正谊堂文集》等。与同时期的理学名家相比,张伯行理学思想较为保守。他曾立志“大为整顿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归一道同风之上理”。
 凡不同于程、朱者,诸如佛老之学、陆王心学、颜李学说等,均加以挞伐。对于来自西洋的天主教,自无例外。
凡不同于程、朱者,诸如佛老之学、陆王心学、颜李学说等,均加以挞伐。对于来自西洋的天主教,自无例外。
张伯行对天主教的看法,集中见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所写的《拟请废天主教堂疏》。此疏篇幅不足四百字,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一名封疆重臣对于天主教的态度。
奏疏开宗明义,“为请废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维俗事”。也就是说,排斥天主教意在维护纲常名教、世道人心。理由如下:
第一,天主教与“崇儒重道”政策不合。朝廷以“崇儒重道”为治,海内向风,天下兴隆。“切见西洋之人历法固属精妙,朝廷资以治历,设馆京师,待以优礼,于理允宜。不谓各省建立天主堂甚盛,边海地方如浙江、广东、福建尤多。”“每教堂俱系西洋人分主,焚香开讲,收徒聚众,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诚恐其意有不可测。”“固属精妙”,表明他并不反对西历;“其意有不可测”,则说明他对西洋传教士的疑忌。
第二,天主教与儒家伦常名教不合。张伯行站在理学立场上,指责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禁行祭祖,“悖天而灭伦也”;禁止祀孔,“悖天而慢圣也”;男女无别,有伤风化。他说:
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于天。未闻舍父母、祖宗而别求所为天者,亦未闻天之外别有所谓主者。今一入其教,则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灭伦也。尧、舜、禹、汤、文、武列圣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师以至于郡县,立庙奉祀,数千年来,备极尊荣之典。今一入其教,则灭视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圣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释奠之礼,而天主教不敬先圣先师。恃其金钱之多,煽惑招诱,每入其教者,绅士、平民分银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为,渐不可长。且入教之人,男女无别,混然杂处,有伤风化。

张伯行主要从祭祖、祀孔、男女有别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儒学与天主教的不同,其中触及了宇宙本体问题。张伯行以天理为本体,认为“人自形生神发以来,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
 反对凌驾于天之上的“天主”的存在。
反对凌驾于天之上的“天主”的存在。
最后,他请求康熙帝特降明诏,“凡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肄业之所,以厚风俗,以防意外。傥其不时朝贡往来,则令沿途地方官设馆供亿足矣”。

张伯行的观点在当时士大夫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如雍正元年(1723),礼科给事中法敏、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等都曾以正人心、敦教化为由,主张严禁天主教。
陆世仪、陆陇其则对西法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
陆世仪对西学的兴趣,与其治学特点有一定关系。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儒宗理要》、《思辨录》等四十余种。他学宗程、朱,但表现出较为开放的品格,门户之见较轻,对于陆九渊、陈献章、王阳明的学说“未尝力排深拒”。
 他对西洋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也没有因华夷之别而加以排斥。陆世仪治学注重经世致用,认为理学并不局限于天理性命之学:“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
他对西洋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也没有因华夷之别而加以排斥。陆世仪治学注重经世致用,认为理学并不局限于天理性命之学:“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
 他关注西洋科技,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其经世致用的需要。
他关注西洋科技,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其经世致用的需要。
陆世仪关于西学的阐述主要见于《思辨录辑要》。《辑要》虽是一部儒学书籍,却以西学丰富了儒学中“切于世用”的内容。
在数学方面,陆世仪主张吸收西方几何学之精。陆世仪受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数学思想的影响,强调数学为其他应用科学的基础。他说:“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不知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
 他认为西方几何学精当:“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
他认为西方几何学精当:“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
 《崇祯历书》由徐光启主持,是中国首部参用西学的历法。他明确认识到其中的“泰西几何”比中国《九章算术》中的勾股法精确、高明,这说明他研读过这方面的著作。
《崇祯历书》由徐光启主持,是中国首部参用西学的历法。他明确认识到其中的“泰西几何”比中国《九章算术》中的勾股法精确、高明,这说明他研读过这方面的著作。
在天文学方面,陆世仪不抱华夷成见,认为西洋学说有可取之处。他在比较中西天文图时指出:“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同时,他虽持中国旧说,认为儒者谈天道,必合星历与占验而会通之,但对于西方天文学不讲“占验”、“气运”表示理解:“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殊近理。”他认为,西学不言占验,是“有所慎而不言”。

陆世仪较重视西洋历法,力主把历算之学纳入儒学教育当中:“至于历数,则儒者所必当究心。”
 他不仅钻研过“会通中西”的《崇祯历书》,而且公开赞扬西洋历法。他在谈论中西所测岁差时指出:中国古历“不若近时西学,岁约一分五十秒不等,约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者之为密也。盖讴罗巴人,君臣尽心于天,终岁测验,故其精如此。”
他不仅钻研过“会通中西”的《崇祯历书》,而且公开赞扬西洋历法。他在谈论中西所测岁差时指出:中国古历“不若近时西学,岁约一分五十秒不等,约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者之为密也。盖讴罗巴人,君臣尽心于天,终岁测验,故其精如此。”
 他认为,西历以“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更切实际。
他认为,西历以“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更切实际。
从总体上说,陆世仪虽对西学表现出一定兴趣,但受中国当时科技水平及其理学思维方式的限制,他对西学的接受还较为肤浅。比如,他一方面承认“西学言日月蚀为地影所障,似亦有理”;另一方面又受程朱理学宇宙生成论影响,认为西洋的日月蚀理论不合理学的阴阳二气交感说,西方的“地球间隔之说,犹有可议也”。

陆陇其(1630~1693),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著有《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等十余种。他治学恪守程、朱道统,排斥阳明学说不遗余力。他的学术风格、社会地位均与陆世仪有异,但同样关注西学。
陆陇其接触西学的记载,主要见于《三鱼堂日记》及吴光酉编《陆清献公年谱》。其中,康熙十四年(1675)、十七年,陆陇其对西学接触较多,他对西学的了解,基本是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利类思等人的交往得来的。
陆陇其接触西学,主要是为探究西洋历法之详。他游天主教堂拜访利类思,与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往来、借书,以及拜访中国历算专家梅文鼎、邵武峰等人,都是为讲求历法。
据日记所载,陆陇其利用进京赴部谒选之际,于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十九日,“游天主堂,见西人利类思,看自鸣钟。利送书三种,曰《主教要旨》,曰《御览西方要记》,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性学要》示余”。三月二十一日,“南怀仁来答帖言去年所制浑天仪在司天台,其木者则留天主堂”。三月二十三日,“同屠尹和至天主堂观浑天球……”三月二十八日,“南敦仁(即南怀仁——引者注)遣人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四月初五日,“至天主堂晤利类思,以《中星简平规图》归。因前南敦仁送星图有‘时盘’,未知用法,故以问利”。四月初八日,“西人利类思以南怀仁《不得已辨》来送。因前初五日,愚曾以岁差及太阳过宫之疑叩之,故以此书相赠。”四月十三日,因对南怀仁《不得已辨》所谈西洋历法存有疑问,会利类思。五月初二日,见开州人王嗣虞,王著有《历体略》数卷,通中西历法。五月二十五日,“至报国寺买《日躔表》二本,乃西洋历书中之一种也。读之始知郭守敬消长之法,西洋法未尝不用”。闰五月初六,“会曲阜朱年翁,朱馆于侍御黄敬玑家,为余借得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其书凡十六卷……读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针”。
 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7)正月二十九日,“会王天巿,携南怀仁所送《坤舆图说》、《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历》以归。”
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7)正月二十九日,“会王天巿,携南怀仁所送《坤舆图说》、《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历》以归。”

陆陇其与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说明,他对西学并不一味排斥。他在参观浑天球后,称赞“西人最巧算”;阅读南怀仁的历法著作《不得已辨》后,自称“读之豁然,西法曾未易吹毛”。
 他还明确反对杨光先等人排斥西学的做法。他在日记中说:“午未间,杨光先之说方行,士子为《历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实行之说,尽属尘羹;考引数、根数之谈,俱为海枣。’何轻易诋呵如此?”
他还明确反对杨光先等人排斥西学的做法。他在日记中说:“午未间,杨光先之说方行,士子为《历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实行之说,尽属尘羹;考引数、根数之谈,俱为海枣。’何轻易诋呵如此?”
 康熙十七年五月,陆陇其“见杨光先《不得已》书”。针对杨氏书中对西法的驳斥,陆陇其引汤若望的上疏、著作中的观点为据,指出杨说不能成立。
康熙十七年五月,陆陇其“见杨光先《不得已》书”。针对杨氏书中对西法的驳斥,陆陇其引汤若望的上疏、著作中的观点为据,指出杨说不能成立。

与陆世仪一样,陆陇其关注西学与尊奉理学并不矛盾,他是把历算之学作为儒家经世之学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的。尽管其间利类思、南怀仁曾不失时机地多次向陆陇其赠送宗教书籍,宣传天主教义,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十分明确:“西人之不可信,特亚当、厄袜及耶稣降生之说耳。”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著作集《榕村全书》41种凡197卷。他的西学志趣与陆世仪、陆陇其有所不同。他研习西学,主要是为迎合康熙帝的需要,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
从时间上看,李光地在康熙朝前期对西学了解较少。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李光地扈从康熙帝南巡期间,君臣二人在南京观星台上的对答显示出其西学知识贫乏,以至用陈腐的天人感应学说来附会、搪塞。据《康熙起居注》记载: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
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知今历不谬矣。”……
上又历指三垣星座问光地,不能尽举其名……
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

康熙帝对李光地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耐人寻味的是,回京后数月,李光地即遭降职处分。此后,为迎合康熙帝的旨趣,李光地的学术宗尚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从游移于朱、王之间变为独尊朱学;另一方面,开始着意探求西学,并先后两次把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署所,讲授天文历算。

在梅文鼎的指教下,李光地的西方天文历算学知识大有长进。历学方面,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光地自称对历法已能“识梗概”,
 并完成了历学著作《历象本要》。天文学方面,他对西方的地圆说、九重天说、宗动天说等宇宙理论已有所领会。
并完成了历学著作《历象本要》。天文学方面,他对西方的地圆说、九重天说、宗动天说等宇宙理论已有所领会。
 数学方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梅文鼎的指导下,研读了康熙帝赠送的《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等著作。其中,《几何原本》被徐光启称为“度数之宗”,是一部富有影响的西方数学名著。李光地所著《算法》一文,即体现了他对《几何原本》和西方数学的见解。在该文中,他比较中西数学的差异后指出,西法密而中法疏,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更助于实际应用。
数学方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梅文鼎的指导下,研读了康熙帝赠送的《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等著作。其中,《几何原本》被徐光启称为“度数之宗”,是一部富有影响的西方数学名著。李光地所著《算法》一文,即体现了他对《几何原本》和西方数学的见解。在该文中,他比较中西数学的差异后指出,西法密而中法疏,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更助于实际应用。

通过学习,李光地已经注意到西方历算之学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担任顺天学政、直隶巡抚期间,聘请梅文鼎讲授历算之学,并倡导和组织士子研习。当时,他的署所集中了一批既尊奉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所造诣的人才,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等,以及光地之子李锺伦、文鼎之孙梅瑴成。这批算学人才后来成为清代前期重要科技著作《律历渊源》、《历象考成》的编撰主力。梅文鼎本人更是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李光地不仅为梅文鼎刊刻了《历学疑问》、《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多种科学著作,并为其书作序,而且将他举荐给康熙帝。
值得注意的是,西学直接影响了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其一,他以西学诠释程朱理学的命题,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以《榕村语录》为例,李光地把西学纳入视野,作为天文历算等经世实学的重要参照,进而用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来解释理学命题。在《理气》篇中,李光地在说明宇宙生成、宇宙本体问题时,多次援引西学知识。如他以西方地理学来论说“天理”的绝对性:“看天似无心,然从事事物物体贴来,觉得处处都似算计过一番。如黄道、赤道不同极,常疑何不同极,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细想,若同一极,必有百年只见半日、半月之处,惟略一差互,便隐见盈亏都均齐矣。”

其二,他借助于“西学中源”说,用西学来论说和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康熙帝、梅文鼎的影响,李光地大肆鼓吹“西学中源”说。
 如李光地《西历》一文称,西方地圆说与《周髀》吻合,九重天说源自《楚辞·天问》所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如李光地《西历》一文称,西方地圆说与《周髀》吻合,九重天说源自《楚辞·天问》所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不过,从李光地鼓吹“西学中源”说的用意看,讲求西学与尊奉理学结合在一起,“述圣尊王”的色彩十分浓厚。
不过,从李光地鼓吹“西学中源”说的用意看,讲求西学与尊奉理学结合在一起,“述圣尊王”的色彩十分浓厚。
 他以西学源自中学,重要目的之一是论证尊儒重道的合理性,说明“圣人无所不通”。他还多次径直将程、朱学说与西学硬相比附,赞颂程、朱有先见之明,借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
他以西学源自中学,重要目的之一是论证尊儒重道的合理性,说明“圣人无所不通”。他还多次径直将程、朱学说与西学硬相比附,赞颂程、朱有先见之明,借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
程子谓:“日无时而不为精,地无处而不为中。”妙极。此分明是说地圆,而不指明其故,阙于所不见也。
朱子言:“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一吻合。
《朱子语类》中论历,不过六七条,而已尽理法之微妙。今西历最侈为独解处,不能加也。

在李光地的认知世界里,讲求西学必须以尊奉理学为前提。由此也就不难想见,当西学与他所尊奉的程朱理学产生严重矛盾时,出于卫道之需,他会排斥乃至于放弃已经接受的西洋学说。他在晚年,一方面承认西方地圆说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天圆地方”、“动静体性”之说来解释宇宙的变化。
 甚至为维护理学的纲常学说,他竟据天人感应学说来诋斥西洋历算之学。
甚至为维护理学的纲常学说,他竟据天人感应学说来诋斥西洋历算之学。

李光地对西学的了解,较陆世仪、陆陇其并不见得有多少进步,但所触及的问题却有所深入。二陆基本上是把西学与儒家“六艺”之学等同视之,西学在本质上没有超出经世实学的范围。李光地则不同,从上述看,他已经着手处理西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
清代前期,从技艺层面接受西方历算之学者并不止上述诸人。吕留良虽怀有华夷大防观念,但对西学并未表现出排斥心态。他在《答谷宗师论历志》中曾建议利用明朝《崇祯历书》会通中西历法:“至烈皇帝时,始有西历一书,然未经会通中历,确有定论,颁布海宇,则此书在先朝尚为未定之书,但可资其议论,以究天学异同。”
 他主张用西历来会通中历,没有“用夷变夏”的顾虑。戴名世论及天文之学时赞同梅文鼎的观点:“有西法所有而中国之所无者,有中国之所有而西法之所无者,要当博采而兼收之,其说不可尽废。”
他主张用西历来会通中历,没有“用夷变夏”的顾虑。戴名世论及天文之学时赞同梅文鼎的观点:“有西法所有而中国之所无者,有中国之所有而西法之所无者,要当博采而兼收之,其说不可尽废。”
 王锡阐兼通中西,学宗程、朱,晚年经常与张履祥、吕留良研习理学,所著《历策》、《历说》、《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圜解》等,多是在吸收了西方历算之学的基础上写成的。
王锡阐兼通中西,学宗程、朱,晚年经常与张履祥、吕留良研习理学,所著《历策》、《历说》、《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圜解》等,多是在吸收了西方历算之学的基础上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