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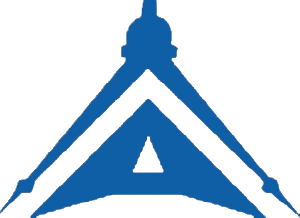
《诗经》里这种悠长的情感,不仅是当时的人可以体会的,也可以变成今天的某种美学,所以我建议大家要从不同角度去阅读《诗经》。我之前提到台湾现在有一些学者试图恢复歌唱《诗经》的方式,他们为此动用了宋元以后的很多资料,但你会感觉到乐器的形式、歌唱的形式太繁复,反而不能接近《诗经》。
当初唱《氓》的时候如果有乐器伴奏,会是什么乐器?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琵琶,很可能是一种很简单的乐器——埙,或者是笛,甚至是打猎射箭用的弓(可以摩擦产生声音)。动作也非常简单,如果是《天鹅湖》里那样王子把公主举起来,这样的动作就很不像《诗经》。日本受唐代雅乐的影响,舞蹈动作也非常简单,就是把脚抬起来,手再移动一下。这种舞姿其实是仪式性或典礼性的东西,我想用它来提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诗经》恢复成乐舞的形式,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荷马史诗》里有一系列的古代英雄,还有美女海伦,可是《诗经》里的主角是谁?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氓”,是一个在中老年时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点感伤的农家采桑女子。《诗经》的主角一直活在土地上。为什么我看陈凯歌的《黄土地》会想到《诗经》?因为这些人活在黄土地上,与农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只有在农业社会,人才能谦卑得像土地一样,在土地里生长,最后又回到土地中去,感情特别朴素、平实。如果大家想感受《诗经》的情感,不仅要阅读《诗经》,还要把《诗经》当成一种在当代延续的美学来看。
我建议大家去看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他有一部电影叫《生生长流》,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我过去不知道伊朗是个这样的地方,想到伊朗就想到霍梅尼那类政治符号。可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呈现了伊朗农村的一所学校,完全像我小时候读书的学校一样,学生很少有穿鞋子的,需要翻山越岭去上学。整部电影几乎没有故事,就是在讲一个小男孩有一天不小心把同学的作业本放到自己的书包里了,老师恐吓他说如果下一次作业再不做,就不要来上课了。小孩子听到老师的话非常紧张,一天都忐忑不安,可是又不敢对妈妈讲。他想办法偷偷溜出去,把作业本还给自己的同学。整部电影带出了伊朗的风景——安静的田地,辽阔的山野。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朋友具体住在哪里,只知道住在哪一个村,还有他的朋友的名字叫阿里,他就跑去一家家地问。伊朗有很多人名字都叫阿里,他一问,人家说我们这个村子有好多叫阿里的。整部电影节奏非常缓慢,在谈人与人之间非常简单的情感。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里,情感就是这么单纯、朴素。
我觉得阿巴斯电影里的东西非常符合《诗经》美学。《诗经》里的人都不是英雄,没有“木马屠城”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大部分都是走过一块玉米地时心里那种哀伤,或者在河边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却不知道如何去追求的惆怅,全是淡淡的东西,这就是农业社会的诗。农业社会里具有与大自然同期性的循环,农业本身会变成一种美学。游牧民族的情感则比较强烈,内蒙古或新疆的民歌情感都比较热烈、泼辣。农业民族学会了把种子埋在土里,等待它发芽、开花、结果,天生有一种长久的耐心,所以《诗经》是典型的农业美学产生的作品。
印度也有一位大导演雷伊,已经过世了,他拍过一部讲印度农民生活的电影叫《大河之歌》。他和阿巴斯的电影至今还在被全世界讨论,是因为农业文明还没有完全消失。
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诗经》的情感就会慢慢淡下去。今天的高雄不晓得有多少“氓”,大概每个便利店里都有,但没有那种感伤,也不会变成民歌的形式。我们在《雨夜花》、《月夜愁》里听到的情感是非常像《诗经》的,因为里面有农业背景。到了繁忙的工商业社会,连那种月夜里走在三岔路的情感也会消失。
还有一个像阿巴斯和雷伊一样被全世界讨论的导演,是台湾的侯孝贤。他的电影表达的是真正的农业社会里的情感,大家可以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体会到非常明显的《诗经》情感。
在他的电影《悲情城市》里,女主角辛树芬走向九份的山路,两边是秋天里刚刚发白的芒草,画外音叙述了她的幸福感。那大概是侯孝贤电影里最美的片断,完全像《诗经》。侯孝贤电影中的人物都不是英雄,全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比如小毕,比如《冬冬的假期》中的角色,又比如《风柜来的人》里那个早年打棒球,后来头被棒球打到,从此就坐在澎湖海边看晚霞的中年男子。这类小人物是属于农业社会的,具有悠远、朴素的情感。一直到他后期的电影《南国再见,南国》里面,半黑道的小混混儿骑着摩托车在阿里山的山路上行走,也非常像《诗经》。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诗经》的情感扩大。我之前谈过,大学中文系讲《诗经》的方法和我非常不同,我不是要注解它,只希望《诗经》在今天仍然是被珍惜的人类情感,虽然农业社会已渐渐远去。如今,侯孝贤的日本粉丝团甚至会专门来台湾看九份小镇。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来临,人在土地里那种深厚的经验,那种悠远、朴素的情感,正在慢慢丧失,但农业社会的文明却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学,在艺术领域里弥足珍贵。
还有一位非常能代表《诗经》情感的导演——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大家去看他的《早安》、《晚春》和《东京物语》,可以看到东方农业美学所产生的那种诗一般的情感,非常稳定。这就是《诗经》所代表的审美,在整个亚洲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发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化是偏向于游牧和商业的(比如腓尼基人),它的农业没有亚洲这么稳定,亚洲很多民歌具有的共性,即《诗经》的这种审美,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有一年暑假,我在法国看到电影院里在放侯孝贤的电影。这不是说侯孝贤的电影多么重要,而是侯孝贤电影背后隐藏的农业时代的审美是今天的法国人非常怀念的,那里面也有他们的乡愁。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简单的、回到自然的、在土地里生存的情感已经慢慢消失了,对此,他们非常怀恋。
今天的台湾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摇摆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也有很多乡愁,因为那刚好是要进入工业革命的关口。歌里有阿伯说“繁华的都市路怎么走?”,其实是象征了一个社会的转型。在那样的歌曲中能感觉到农业社会里的人进入都市,成为工业社会的人的哀伤。《孤女的愿望》里所流露的状态,正是从《诗经》里延续到这个剧变的时代的,民歌运动中的许多歌曲都和这种情感有关。
如今,这样的情感好像已经完全消失,要进入另外一个快节奏的、所有情感都要被切断的社会,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流行歌几乎都是用嘶叫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寂寞和孤独,没有了那份悠远、深长的爱。可是我们在《氓》里,至少可以看到这个“氓”和这个女子的情感是绵长的,诗中讲桑树叶子青翠肥硕,讲桑叶黄了以后的掉落,它是有季节的。
我从《诗经》里选的这几首诗其实有很强的代表性,每个人物在处理情感时,都与大自然中的某一种植物有关。女孩子常常用桑叶来形容自己的情感,因为她在农业社会里能体会到桑叶从青绿,到变黄,再到掉落,这就是季节。人的悲秋之情其实是农业社会里隐藏着的对青春逝去的忧伤,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兴手法。
女子在讲“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时,是在用桑叶形容自己,曾经青春过,鲜丽过,也曾引得那个“氓”蚩蚩地笑。可是下面一段就是“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说桑树发黄了,枯萎了,凋零了,其中有非常明显的农业社会中的情感。
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里几乎没有自然,因为香港已经是一个没有自然的都市。电影《重庆森林》里的男主角爱上一个人,他会到超级市场去买一个凤梨罐头,罐头上写着二十八号到期,因为二十八号那天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也是比兴,可是王家卫的比兴与《诗经》的比兴完全不同,他是在一个商品里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号码。
我曾有个同学喜欢坐某号的车,因为那个号码是他女朋友的生日。在工业社会或者商业社会来临以后,人们会在商品里寄托情感,可是《诗经》里的情感寄托非常悠远,因为大自然是长久不变的。雷伊的《大河之歌》和阿巴斯的《生生长流》,讲的都是永恒的情感。当然,这种永恒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农业社会在人类的大历史中不一定是永恒的。但是,人类迄今为止至少已经有一万年的农业经验了,因此,它变成了我们的巨大乡愁。我们在唱《雨夜花》或者吕泉生的歌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用土地及很多自然界的东西来做比兴,因为这些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接下来不一样了,有些联系被切断了。
《诗经》是彻底的农业审美,站在土地上的人相信有稳定的自然周期,他的情感周期与自然周期会合在一起。所以说《诗经》“哀而不伤”,无论多么悲哀,最后都不会绝望。因为农业社会里的人们相信循环,冬天万物都会枯萎、死去,可是大家知道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定会来。当孔子讲“哀而不伤”的时候,其实是知道大自然有平衡,有节奏,人们的希望可以投注在里面。
在读这几首诗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其中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和节奏。但是有些翻译会把一首很好的诗窄化,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读原诗。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有读原诗的能力,总是要去找各种注解本,可是注解会使你离诗越来越远。其实,原诗里的文字我们都能读懂,我们不必去注解它们,而是在若即若离中去感觉它们。
《诗经》里常用到叠韵、叠字,比如“蚩蚩”、“离离”、“迷迷”——你想要形容某种感受,但是没有找到最恰当的逻辑和解释,这些表达可以使你进入相应的感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一个民间小伙子居无定所,抱着一些布来换我的丝,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要来做生意(换丝),而是来打我的主意的。这是一切恋爱故事的开始。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对自己的漂亮很有自信,也知道这个男孩子有什么样的心机,她很高兴被追求,所以“送子涉淇”——已经谈了恋爱,男孩子要走了,因为要过河去做生意。
这就是农业社会里的情感,记忆都是自然的。女孩子送男孩子渡过淇水,这本身就是一个画面。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阿巴斯的电影,他的电影要么是过河,要么是经过一片草原。他有一部非常精彩的谈恋爱的电影叫《橄榄树下的情人》,男孩和女孩从头到尾总共没有讲过十句话。每次两个人都离得很远,因为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朗的民风还是非常保守的,虽然心里很喜欢,可是却离得好远。短镜头无法拍下那样的场景,所以阿巴斯一直都用长镜头,这几个喜欢拍农业社会背景的导演都喜欢用长镜头。
侯孝贤也喜欢用长镜头,现在西方都在讨论他的长镜头。在《恋恋风尘》里,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一起长大,坐同一列火车去上课,从来没有谈过爱情,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家庭作业,这就是早期的中学生的恋爱。两人是邻居,男孩比女孩大一岁,他觉得她是妹妹,关心她,常常教育她。女孩也很听话,永远穿着白制服,永远坐九份的小火车出来,过隧道,两人之间从来没有调皮过。后来,男孩去金门当兵,两人也通过一段时间信,但慢慢地就没有了。女孩子却因为通信认识了一个邮差,后来和邮差发展出一份感情。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那个男孩子是她的爱人,而是觉得他更像一个哥哥。那个男孩哀伤了好一阵子,在军队营房的床上哭。在电影的结尾,男孩回到兰阳平原的家里,看到阿公在整理番薯田,就叫了一声“阿公”。阿公见他退伍回来,只是回应了一个招呼,也不会去拥抱亲吻——因为农业社会里没有这种东西,便继续整理番薯田。男孩子蹲在一边看阿公整理,问他:“今年番薯怎么样?”阿公有些抱怨:“今年因为台风,番薯收成不怎么好。”然后两人开始聊些无关紧要的事。这个时候,侯孝贤的镜头开始往上拉,越拉越远。个人再大的哀伤,都会被大自然担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过去的。
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的镜头都是长时间固定不动的,没有蒙太奇,这是因为农业社会里有一种对土地的信仰,或者是对长久岁月的信仰,这种信仰最后会变成一种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