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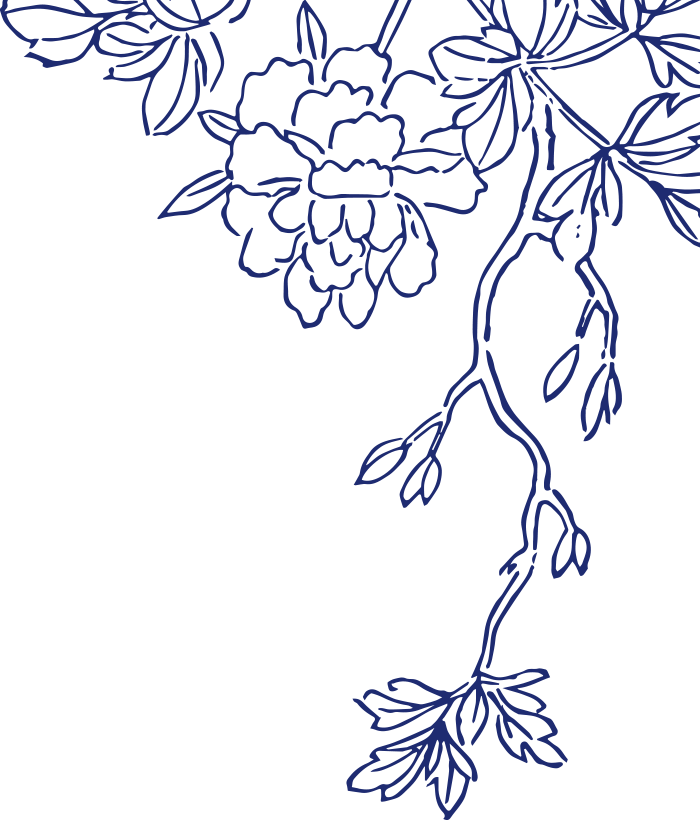
下面这个柳家的就开始骂他了,一方面有一点急,因为急着赶快要进去开饭做菜;另外一方面,做主厨的常常脾气也很爆,而且她会觉得这个小孩子好像在整她。柳氏就“呸”了一声,骂这个小警卫说:“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注意“抓破了脸”,因为财产一旦私有以后,人们就会有“我的”概念,“这是我的东西,你不能碰”的观念就会出来。
还记得吗?探春曾经施行了一个新的制度,是说把大观园所有的树分给不同的老妈妈来管,所以每一年新鲜水果摘下来以后,她们可以拿出去私自卖,卖了以后赚的钱,来跟主人分。以前果子掉在地上烂掉都没有人理会,多摘几个也没有人管。可是现在因为有人照管,就表示说这是我的水果,如果是我的,那等于是从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一旦变成私有财产以后,每个人的眼睛都会盯着看。
我们注意一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群结构,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我去台东的兰屿时,忽然知道原来人类有一些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度。兰屿的达悟族(也称雅美族)实行的是一种原始的公社制度,他们四月一起去捕鲱鱼,捕完鲱鱼以后,吊在那边晒干,这个是公众财产。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吃,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大概应该吃多少。就像我们假设有一个便利店里面的东西是共有财产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拿。
比如说我童年时最早记得的那个社区,不是每一家都有自来水,所以社区中间有一口打的井,每一家都可以到那边去洗菜。你也会觉得那个水是一种公有资源,因为公有,它一定有一种公有的道德会出现。所以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就会骂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用水;或者骂说,洗米跟洗马桶应该在不同的位置,你怎么可以把马桶拿到洗米的位置。我们小时候就会被这些老人家指责,然后就开始学规矩。
柳家的这段话,透露出大观园的水果从公有变成私有以后的情况。她继续说:“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似那黧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黧鸡”是一种斗鸡,柳家的形容那些果子的“看护人”就像斗鸡一样,眼睛睁得圆圆地盯着你,好像说你是不是要偷我的水果了?因为只要你经过水果树底下,你就有嫌疑。

下面她就开始举例了:“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郝舅母就看见了。”这个小警卫有一个舅妈姓郝,她就是管那个果子树的。有没有发现,如果在法律上,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个柳家的经过李子树,把手抬起来了。这个“手抬起来”到底是要偷李子,还是要赶蜜蜂,其实我们不知道。她跟别人说,我要赶蜜蜂;可是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认为她是要偷果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了不起的文学就是说,其实你对那个事件的真相永远不知道。我也可以猜疑说,这个柳家的是不是真的想过,如果管果子的人看不清楚,我就摘两个李子。可是她跟别人讲的时候说,我不是要摘李子,我只是要赶蜜蜂。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可能也有这种东西,有时候跟别人转述事件的时候,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比较正面、比较中立的人物。
这里面的逻辑就生出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比如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最有名的一部小说——《罗生门》。你会发现有一个事件发生,然后四个人都在叙述这个事件,可四个人叙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表示,我没有偷那把刀。所以我们今天把“罗生门”变成了一个典故,如果说这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就意味着每个人都隐藏了一部分没有讲,所以你搞不清楚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柳家的打蜜蜂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有趣,它可能是一个罗生门。
我们现在有一个成语叫“瓜田李下”。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就是经过西瓜田的时候不要提鞋,鞋带松了也不要去绑,因为蹲下去绑鞋带,别人就觉得你在偷西瓜;在李子树下,不要去整理你的帽子,因为一整理帽子,别人就觉得你在偷李子。意思都是要避嫌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过番薯田的时候,那个老妈妈就眼睛盯着看,有时候我们故意蹲下来去逗她,她就拿一根竹竿飞奔出来。
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幽默,它会让你感觉出这个柳家的潜台词:我们哪里敢去碰那个水果,走过李子树底下两个手根本动都不敢动。因为只要动一下,赶一赶蜜蜂,已经被怀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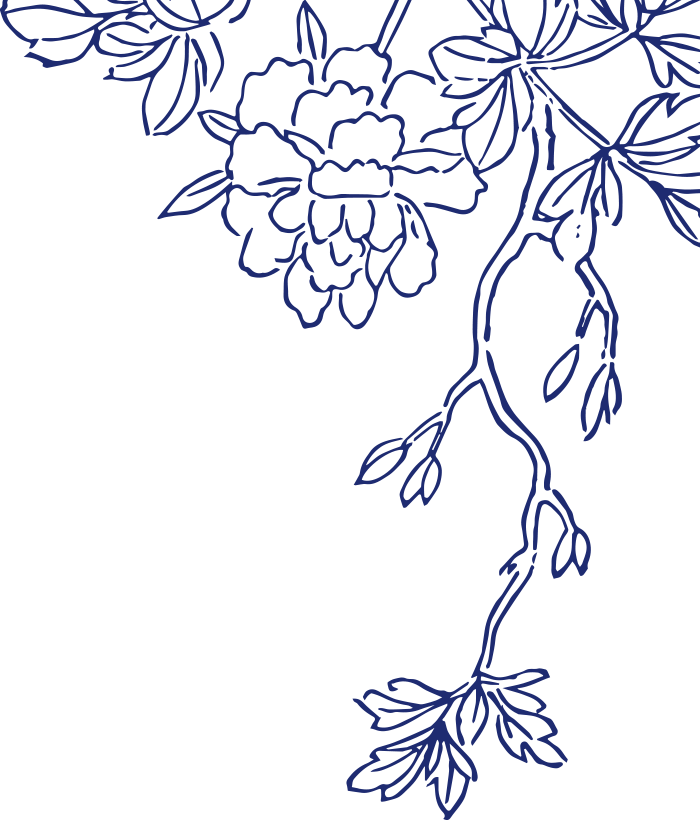
她接着说这个故事:“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泼声浪嗓喊叫起来,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倒像谁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抢白了他一顿。”注意“泼声浪嗓”,曹雪芹的民间语言出来了。这个“浪”字绝对是很难听的,就是女人叫春一样的声音。她其实有一点在骂说,她好像A片里面那种人在乱叫一样。大概林黛玉听到这种语言,连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女人,她有一种泼辣,一个比她年纪小很多的小男孩,她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所以就把性的粗俗的语言拿出来。
这些管理的人就假借着佛,假借着贾母,假借着王夫人,表示说你们不要乱动这些东西,等到进了上头,以后都会分给你们,所以先不要急。那这个柳家的就很生气说:“好像我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馋痨”就是想吃东西想得生了重病。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注意一下曹雪芹的了不起。就是这里除了语言的活泼之外,还有一个是这种身份的人,她所描述出来的事件的活泼。这样的事件,在林黛玉的口中永远听不到,因为林黛玉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摘李子,她不需要跟别人在口边去抢东西吃。
因为这个管李子的人是小警卫的舅妈,柳家的也有一点气这个小警卫,她就说:“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鸦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这又是民间语言,今天在整个正规的学校教育里,你可能永远学不到这个东西。比如我们在法国读书学法语,因为一直在大学里,法语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永远碰不到。有一天你如果去巴黎的pub里面待一待,会发现一半的话听不懂,因为那个语言是在学校里面听不到的。如果有一天你接触到那种跳街舞的小男孩,会发现那个语言有大概四分之三听不懂了,他们又有他们语言的特征。所以语言其实是跟一个文化的阶层有关系的。《红楼梦》的了不起在于包容了各个不同层次的语言。
我觉得语言本身本来就应该包容很多不同的东西进来。这几年我很喜欢夏曼·蓝波安的文学,因为他把达悟族很多的东西变成了汉语,我觉得他在丰富汉语。比如,他会描述他的爸爸年纪很大了,就是用达悟族的语言说:“我很老了。”可他不是直接说“我很老”,而是说:“我是那个很低的夕阳了。”我听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达悟族住在兰屿,是在海边,他们看到太阳越来越低的时候,就是生命快要结束了。夏曼·蓝波安用汉字写出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达悟族语言的魅力出来了。我觉得像这样的作家,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他自己族群语言的魅力,他可能会丰富我们的语言。
我跟很多朋友提到,我有很长的时间在大学里,最不喜欢的语言是大学的语言。因为它就是很正经八百,没有活力、没有魅力,比起六合夜市的语言,比起我在桃园的文昌公园听到的那个客家老人家的语言,比起达悟族的语言,它都没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