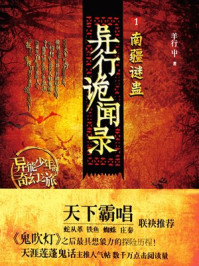是寒冷把她冻醒的。还有挫伤的疼痛,因为路程很远。她被绑了起来,没有办法不让自己的身子滚来滚去,撞上隔板。车子终于停下,男人打开车门,用一块塑料篷布把她裹起来。他把她一把扛在肩上。想象自己已经沦落为货物是可怕的,同样可怕的是想象自己已经落入一个把自己当货物扛在肩上的男人手里,任之摆布。这让人不由猜想,他究竟会做什么。
他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做,不管是把她放到地上,还是就地拖袋子,又甚至是把她滚下楼梯。楼梯的边缘敲打着她的每一根肋骨,她也没有办法保护头部,阿历克斯大声号叫,但男人不为所动地拽着她前行。当再一次撞到后脑勺后,她昏厥了过去。
不知道昏迷了多少时间。
现在,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刺骨的寒意侵占了她的双肩,钻到了她的怀里。双脚冰冷。胶布绑得太紧,她感觉浑身血液都停止了循环。她睁开眼睛。至少,她试图睁开眼睛,因为她的左眼皮还是黏合着。嘴也张不开,被一张大大的透明胶带贴着。她自己都不记得,是昏迷时贴上的。
阿历克斯躺在地上,侧卧着蜷曲着,双臂被绑在背后,双脚也被捆绑着。她的髋部承受着全部的重量,隐隐作痛。她表现出一种昏迷后的迟钝,浑身疼痛,像是经历了一场车祸。她试图弄明白自己置身何处。她扭动胯部,终于背部着地,她的肩膀太疼了。左眼终于睁开了,但什么都看不见。“我瞎了!”阿历克斯对自己说,惊恐万分。几秒钟后,她半睁着的眼睛终于向她传送来一幅模糊的画面,看起来像是来自几光年之外的星球。
她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再把它吐出,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是一个车库或是一个仓库。一个大而空旷的地方,光线从顶上射入,弥散开来。地面坚实而潮湿,肮脏的雨水散发出臭气,凝滞的积水,这就是为什么她会觉得这么冷:这个地方阴气逼人。
她首先回想起来的,是一个男人把她贴着自己紧紧箍住。他身上发出酸涩、强烈的气味,那是一种动物般的汗味。在那些悲剧性的时刻里,人总会回想起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他扯我头发——这是她首先想到的。她想象着自己脑袋上一大片区域光秃秃的,被拔去了一大把头发,开始哭泣。其实,与其说是这个画面使她哭泣,不如说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疲惫、痛苦,还有恐惧。她哭泣,这样哭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胶带封着嘴唇,她喘不过气来,她开始咳嗽,但不那么容易,她呼吸困难,眼中噙满泪水。一阵恶心从胃里翻腾起来,却又无法呕吐。她的嘴里充满了苦涩,不得不重新吞下。这让她发疯,让她恶心。
阿历克斯努力呼吸,努力理解,努力分析。尽管对于当下的情况充满绝望,她还是试着重新找回一些冷静。虽然冷静有时候没什么用,但没有它,就一定玩完了。阿历克斯试着平静下来,试着降低心跳频率。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做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她回想着。她饱受折磨,但此刻让她感到尴尬的是她的膀胱,肿胀着,受着压迫。她在憋尿这方面从来不擅长。不到二十秒,她就做了决定,她放弃抵抗,直接尿在了身下,尿了很久。这个自我放任的动作不算是个失败,因为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她不这么做,她将受更久的折磨,或许扭来扭去几个小时,最终还是难免尿在身上。何况在这样的情形下,她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担忧,撒尿的欲望,实在是个阻碍。只是几分钟之后,她感觉更冷了,这是她之前没想到的。阿历克斯开始发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寒冷,或者因为害怕。她又回想起两个画面:男人站在地铁里,在车厢的末端,对着她微笑;还有他的脸,在他死死抱住她塞进货车之前。着地时她重重地摔在地上。
突然远处的金属门砰砰作响,响声刺穿空气。阿历克斯立刻停止哭泣,窥伺着,浑身紧绷,好像随时都要炸裂。然后她腰部一用力,又重新回到侧睡的姿势,闭上双眼,准备忍受一顿暴打,她知道他要揍她,这就是他绑架她的原因。阿历克斯屏住呼吸。她听见男人远远走来的声音,脚步坚定而沉重。终于,他站在她的面前。透过睫毛,她看到男人的鞋子,一双大号的、擦得锃亮的鞋子。他没有说话。他俯视着她,一言不发,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监视她睡觉。她终于还是决定对他完全睁开眼睛。他双手背在身后,脸倾斜着,看不出一丝意图,他俯视着她,就像俯视着……一个东西。从下面看,他的脑袋硕大无比,眉毛黝黑茂密,构成了一片阴影,笼罩了他眼睛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他的前额,比他的脸还要宽,感觉像是满溢了出来。这让他看起来有种智力发展迟缓的、原始的感觉,冥顽不灵。她想找到合适的词,却只是徒劳。
阿历克斯想说些什么,胶带阻止了她。不管怎么样,她能说的也不过就是:“求求你……”她绞尽脑汁想自己能和他说些什么,如果他把她松绑的话。她想找到除了哀求之外的话,但是她想不出,什么都想不出,一个问题都没有,一个要求都没有,只有这个哀求。她想不出任何话语,阿历克斯的大脑像是凝滞了。只有模模糊糊的这些印象:他把她绑架了,捆扎起来,扔在这里,他会对她做什么?
阿历克斯哭了,她不能自已。男人一声不吭地走开。他走到房间的角落。他大手一挥,掀开一块篷布,她看不清盖着什么。她只有这一个神志不清的祈祷:让他不要杀我吧。
男人背对着她,弓着背,边后退边双手拉着什么重物,一个箱子?它贴着混凝土地面发出吱吱的声响。他穿着一条深灰色布裤子,一件宽大、变形的条纹套头衫,感觉像是穿了好多年。
就这样退了几米,他不再拉,抬头看向天花板,像是在瞄准什么,然后他就这样站在那里,双手叉着腰,像是在盘算要如何开始。最终,他转过身来,看向她。他走过来,俯身,一只膝盖靠近她的脸,伸出手臂,突然一下,切断了绑住她脚踝的胶带。然后他的大手抓住黏住她嘴唇的透明胶带的一端,用力一拉。阿历克斯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他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把阿历克斯提起来。当然,阿历克斯也不是很重,但是不管怎么说,是一只手!她整个人感到一阵晕眩,站立使她的血液向上涌,她再一次开始摇摇晃晃。她的额头差不多到男人的胸口。他死死抓住她的肩,把她转了个向。还不等她说一个字,他动作麻利地割断了她手腕处的绳子。
阿历克斯鼓起全部的勇气,完全没有思考,她说出了脑海中盘旋的字眼儿:“求求你……”
她简直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她开始口吃,就像她小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面对面,这是无限接近真相的一刻。阿历克斯想着他可能对自己做什么,她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她想去死,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她想他现在就杀死她。她最害怕的,是在这种等待中。她的想象不断冲击着她,她想着他可能对自己做的事,闭上眼,她看到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她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它躺在那里,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带着伤,不停地流血,它受着煎熬,好像它不是她,但它就是她。她看着自己死去。
有点儿冷。小便的气味,让她觉得羞辱,她又感到害怕,他会做什么,只要他不杀了我,老天保佑他不要杀我。
“脱衣服。”男人说。
声音严肃而坚定。他的命令也一样严肃而坚定。阿历克斯张开嘴,但还不等她说一个字,他已经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她一个踉跄倒向一边,她走了一步,摇摇晃晃,又走了一步,她跌倒在地,脑袋撞到地面。男人慢慢朝她走去,抓住她的头发。一阵剧痛。他把她提起来,阿历克斯感觉她所有的头发都要被他从头皮上拔下来了一般,她死死抓住男人的手,试图阻止他,她的双腿已自发地重新有了力量,阿历克斯站了起来。他又给了她一巴掌,由于他依然抓住她的头发,她的身体只是轻微动了一下,脑袋只是稍稍偏了一下。但这巴掌打得很响亮,她痛得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脱衣服。”男人重复道。一字不差。
他放开她。阿历克斯走了一步,摇摇晃晃,她努力保持平衡,却一下跪了下来,她忍住痛没有叫出声。他走过来,俯身。在她上方,他的大脸、沉重的大脑袋、灰色眼睛……
“听得懂吗?”
他等着她回答,举起一只大大的张开的手,阿历克斯猛然一跳,她不断说着:“是。是,是,是。”立马起身,她只想不再挨打。为了让他理解自己已准备好完全地、彻底地服从他,阿历克斯飞快地脱去T恤,扯掉胸罩,匆忙地摸索着牛仔裤的扣子,好像她的衣服突然着了火似的,她想立刻全部脱掉,好让他不再揍自己。阿历克斯扭动着身子,脱光了身上所有衣服,所有的,飞快地。于是她就这么站着,两条手臂贴着身子,就在这一刻,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刚刚失去了什么,并且再也找不回来。她的失败很彻底,这么快地脱掉全部的衣服,这意味着她已全盘接受,不再有丝毫反抗。某种程度来说,阿历克斯刚刚已经死了。她的感觉似乎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好像她的灵魂已经飘浮在身躯之外。或许正因为这样,她突然有了提问的勇气:“你想……想要什么?”
他的嘴唇薄得像几乎没有一样。甚至当他微笑起来,也看不出是在微笑。现在,他的表情,是一个问号。
“你能给我什么,贱货?”
他努力表现出一种贪婪,好像他真的是在诱惑她。对于阿历克斯来说,这些字眼儿有着深意。对于所有女人来说,这些字眼儿都是有深意的。她吞了一口口水,心里想着:他不会杀我了。她的脑袋围绕着这个念头打转,死死不让任何别的念头来打破这种信心。但她的内心总有什么东西在告诉她,他还是会杀了她的,她的大脑似乎被一根绳子捆了起来,越捆越紧,越捆越紧,越捆越紧……
“你可以操……操我。”她说。
不,不是这么回事,她感觉到,不是以这种方式……
“你可以……强奸我,”她又加了一句,“你怎样……都可以……”
男人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他退后了一步,隔着一些距离看着她,从头到脚。阿历克斯张开双臂,她想表现出一种自我献身,放弃抵抗,她想表现出她已经放弃了所有自由意志,完全受他支配,臣服于他,她只想争取时间,只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
男人安静地打量着她,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上下游走,最后停在她的下体,久久没有移开。她没有动,他微微倾斜了一下脑袋,一脸疑惑。阿历克斯为自己在男人面前裸露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他不喜欢她,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他,她还有什么能给他,他又会怎么做呢?他摇了摇头,似乎非常沮丧,失望,不,这不行。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伸出手,用拇指和食指抓住阿历克斯的右乳头,使劲一转,他转得太快太狠了,以至于阿历克斯痛得佝偻起身子,立刻发出一声惨叫。
他放开了她。阿历克斯抱着胸口,瞪大了双眼,凝神屏息,她左右脚轮换着跳来跳去,疼痛使她失去理智。她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她问道:“你想要……做什么?”
男人笑了,像是在提醒她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好吧……我想看着你死,贱货。”
于是他走到一边,像是个演员。
终于她看见了。在他身后,在地上,一个电钻,一个木箱子,不是太大。刚好能装下一个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