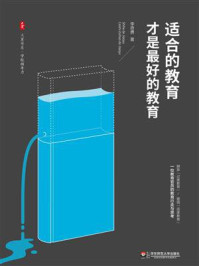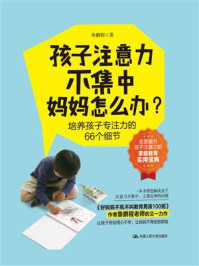亚历克斯·厄舍(Alex Usher)

一、引言
过去十五年来,“世界一流大学”一词已经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全球话语。本质上,这一术语指的是高水平的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大部分能够获取大量经费,从而能够聘用顶尖人才,或购买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然而,过去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普遍性的公共支出缩减,至少在理论上,使高校的经费状况处于风险之中。本章的目的是考察多个领先工业化国家中世界一流大学财政状况的变化,以确定哪些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将会蓬勃发展,而哪些不会。针对各个国家,本文不仅会考察入榜“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高校,也会考察没有入榜的大学,这使我们能够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将资源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学。本文的最后还将探讨政府在高等教育拨款方面的政策考量。
二、世界一流大学:历史简述
“世界一流大学”一词是中国在制定“985工程”相关政策时所提出的,捕捉了高等教育历史和全球化历程中的乐观阶段。从柏林墙倒塌到20世纪90年代科技热潮,从全球经济增长的较长时期,到之后经济增长的沉寂,一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形成了极其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共识。这一共识有三个要点:首先,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其次,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特定行业的企业的区域聚集;最后,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那些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研究型大学,可以作为这些集群的枢纽。
中国实施“985工程”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国内产业的“价值链”。作为一个低成本制造业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大学来促进技术前沿工业领域的发展。这是中国大学曾发挥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初,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将经济的发展投注在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一些精英大学上(Andreas 2009),希望这些大学能够帮助国家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但“价值链”一词在中国以外也产生了共鸣。在美国,由硅谷(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所创造的地区繁荣和全球影响使全美的政策制定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大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欧洲,同样的观点也在2000年得到响应,当时欧盟各国通过了“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致力于使欧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这也使欧洲高校成为这个雄心勃勃的区域增长战略的核心。与此同时,亚洲的领先经济体(如韩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也积极拥抱“前沿经济的竞争需要加大科研投资”这一主张。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政策选择。该排名的出现使各国终于有了一个透明的工具,去评估它们最好的大学与美国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差距,而后者的成功是前者所渴望效仿的。整体上,没有多少国家会对本国高校的排名名次感到满意。因而拥有一所(或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很快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在欧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为了实现“里斯本议程”以及赶超美国。在亚洲,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一国成为主要创新经济体的象征,与此同时也为了推动国家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中竞争所必需的爆炸式增长。
2004年,阿特巴赫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述:“谁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觉得不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没人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也没人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Altbach 2004)。几年之后,时任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的贾米尔·萨尔米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魔法公式”总结为“时间、人才、良好的治理和经费”(Salmi 2009)。一时间,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将资源投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项目上。政府或通过个体研究项目,或通过重点建设计划(OECD 2014),或通过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向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经费。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规模增加了一倍。总之,21世纪初的十年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大学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时期。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高等教育无法再指望大幅增加年度经费。除德国和瑞士以外,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开始实质性地削减开支。在美国,政府生均经费拨款在2008~2012年期间下滑了28%(尽管招生人数的增长和经费削减的原因各占一半)。在英国,大学的公共财政削减了40%以上(这一点通过学生学费的大幅上涨得以补偿)。在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国家,政府经费拨款也大幅削减;芬兰尽管在一段时期内克服了这一趋势,但近期宣布将在5年内实质性削减近15%的经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外,情况有所不同。在印度、海湾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支出增长显著。尽管有些国家的教育预算一直比较有限,但是即使在2014年、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或者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支出仍然在增长。
倘若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时代吻合并依赖世界各地公共拨款的增长时期,那么值得一问的是:失去了经费增长的世界一流大学会如何?在这个经费短缺的新时期,我们能期望什么?我们或许能够从美国历史中获得一些启示。美国从1968~1970年代末的这一段时期,有时被称为“停滞的十年”或“失落的十年”。在这一时期内,越南战争造成了持续的联邦预算赤字,加上长期的经济缓慢增长,导致美国高等教育预算的紧缺。与此同时,大学被要求扩招,意味着它们除了预算缩减外还面临着一个新的成本挑战。美国高校通过减少开设的学位项目,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学位项目,来应对这一困难(Graham & Diamond 1997;Geiger 2009)。事实上,高校常常不得不在教学功能和科研功能之间进行选择,而后者并非总能胜出。
许多国家发现自己现在处在相同的境况中,不仅预算紧缺,还要面临着教学和科研优先性的艰难选择。除此之外,全球经济似乎已经进入了一段缓慢增长的长期阶段。在21世纪初的十年,全球GDP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但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保持在2%~3%的范围内。这一经济前景与之前的增长时期形成鲜明对比,随之而来的人口变化和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也将在未来多年制约高等教育的支出。本文的目的则是为了考察这一时期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在操作层面上,本文将世界一流大学定义为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名的高校(以下称为ARWU百强高校)。10个国家的高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法国、荷兰、德国和瑞典占据了ARWU百强高校前50名中的49个席位,前100名中的91个席位。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顶尖高校所发生的事情从定义上而言便是世界一流大学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这10个国家。
本文从国家层面的数据库中收集了有关这10个国家高校支出的数据。相比于收入,支出能够更好地衡量财政能力,因为它们更趋连贯,更不容易突然波动,因此是代表高校真实财政能力的更好指标。财务数据以当地货币的实际价值呈现,基准是数据可用的最后一年。由于不同国家对“支出”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本文使用现有数据中对“支出”涵盖最广的定义,以减少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支出定义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当国家层面的财务数据库不可用时,我们采用高校自身的财务报告。
本文不仅旨在考察高校的总体支出,还会考察生均支出,这是因为通过扩大学生人数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部分都用在了培养这些新生上,而非用于提升科研能力方面。因此,也有必要考察招生人数。同样,我们还非常注意这些信息的数据质量。本文还会使用国家层面数据库的学生人数,以考察生均学生的实际支出。学生人数通常(但不总是)按人数来统计。同样,当国家层面的数据库无法提供充分的数据时,我们会采用高校自身的数据进行补充。
各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有所差别。其中有5个国家的国家层面数据和高校数据都很完善,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瑞士政府当局公布全国性数据而不公布高校层面的数据,但高校自身的数据很透明公开,几乎可以收集到所有高校的数据。在日本、荷兰和德国,既有全国性的数据,也有一些不太完整的高校层面的数据(日本高校对其数据相对透明,但并没有在机构网站上妥善存档,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年份数据都可获得;在德国和荷兰的高校中,只有少数高校会公布对当年入学率和财务的简要描述)。在法国,只有国家层面的数据可用,因为高校个体(至少是ARWU百强高校)在年度报告中不公布财务状况。总体而言,在本研究所感兴趣的91所大学中,能够获得81所高校的全部或部分数据。
(一)美国
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将始于目前为止产生这类大学最多的国家:美国。美国高等教育的财务危机已被广泛报道且为世界各地所知晓。然而,若只看高等教育整体层面的支出,危机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图3.1呈现了美国四年制大学(公立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从2000~2001学年至2011~2012学年期间总支出的变化,以2011年的美元币值为基准计算。通货膨胀以后,高校支出实际增加了39%(私立大学增加了43%,而公立大学提升了37%),或每年增加大约3%。
高校维持支出增长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学生学费获得收入(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以入学人数为基准的奖学金拨款)。但由于学生既是成本的去向也是收入的来源,因此同时考察美国高校生均支出的变化情况非常重要。如图3.2所示,生均支出的情况与总支出有所不同。

图3.1 美国四年制大学的实际支出(以201 1年的美元币值为基础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教育统计年鉴(NCES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图3.2显示,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实际生均支出(也是收入)的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就私立大学而言,2000~2001至2007~2008学年期间,每年生均支出的增长率大约为2%,之后实际收入保持稳定。公立大学在过去十年的早期落后于私立大学(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导致公共经费下降),但随后赶上私立高校,直到2007~2008年,来自公共资源的收入大幅下降,迫使大学削减开支。截至2011~2012学年,生均支出仍然低于2007~2008年的4%左右。

图3.2 美国4年制大学的生均实际支出(2000~2001至201 1~2012)
资料来源:美国教育统计年鉴(NCES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当同样的分析应用到ARWU百强高校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美国拥有51所ARWU百强高校,包括23所私立大学和28所公立大学,这些大学整体的实际支出趋势如图3.3所示。参考这些数据很难发现“危机”的所在:如图3.3所示,通货膨胀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支出均以每年约4%的速度稳定增长。这比4年制大学整体的支出增长略高,后者每年的增长率为3%。

图3.3 美国ARWU百强高校的总实际支出(2000~2001年至2012~2013年,以2012年的美元币值为基础计算)
资料来源:综合大学教育数据系统。
如前文所述,在没有考虑学生人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主要的进步作出谨慎推断。对生均支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ARWU百强高校的增长实际大于美国高等教育整体。正如图3.4所示,在美国高等教育整体层面,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生均支出仅增长了大约6%,而ARWU百强高校的增长幅度超过其6倍,在同一时期接近40%。在整个时期内,私立研究型大学的表现略好,但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泡沫时期的不同表现。而从2008年以来,公立大学的表现更胜一筹。

图3.4 美国百强大学的实际生均支出(2000~2013)
资料来源:综合大学教育数据系统。
(二)英国
英国共有9所大学进入了ARWU排名的前100名: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of London)、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布里斯托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以及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对于一个高等教育公共投入极少的国家而言(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英国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也保持着持续而活跃的对话。通过新闻,人们会认为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之中。事实上,英国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拨款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最高学费从每年的3 000英镑增长至9 000英镑,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将学费提升至最高(或接近最高)。而与此同时,从公共渠道所获得的经费显著下降,下降幅度近50%。
然而,学费变化和拨款减少的程度不同。如图3.5所示,英国高校在过去几年来表现良好,在2006~2007年至2013~2014年期间的收入实际增长了15%,而9所ARWU百强高校则增长得更多——7年期间增长了25%。这与美国百强高校自2006年以来的增长情况极为相似,后者每年增长3.5%左右。

图3.5 英国高校支出的实际变化
资料来源: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UK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也就是说,如果高校大量扩大招生,支出的净增长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到2013~2014年期间,学生人数并没有多大的增加,事实上,学费在2012年甚至还有小幅下降(Orr,Wespel & Usher 2014)。然而,学生人数的下降主要发生在ARWU百强高校之外的大学。因而,非ARWU百强高校的生均支出比整体支出的表现更好,而ARWU百强高校亦是如此。英国高校生均支出实际变化如图3.6所示。

图3.6 英国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2006~2007至2013~2014)
资料来源: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有4所ARWU百强高校,即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以及西澳大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遗憾的是,只能获得这些高校2008年以后的财务数据
 。澳大利亚的基本数据显示,ARWU百强高校的支出增长反而不及其他高校(如图3.7所示)。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澳洲政府奇怪的财政支出统计方式有关。ARWU百强高校的一次性经费下降主要是因为莫纳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onash)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2008年的时候资产减值转销(也被统计为支出)所致,导致当年支出虚高,从而造成了一个异常高的基准。但即便抛开这些,在减值转销后的4年里,4所ARWU百强高校也仅仅勉强恢复到了2008年基准的水平,它们整体收入的增长也不如其他大学那么快,即便将最高点考虑进去。
。澳大利亚的基本数据显示,ARWU百强高校的支出增长反而不及其他高校(如图3.7所示)。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澳洲政府奇怪的财政支出统计方式有关。ARWU百强高校的一次性经费下降主要是因为莫纳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onash)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2008年的时候资产减值转销(也被统计为支出)所致,导致当年支出虚高,从而造成了一个异常高的基准。但即便抛开这些,在减值转销后的4年里,4所ARWU百强高校也仅仅勉强恢复到了2008年基准的水平,它们整体收入的增长也不如其他大学那么快,即便将最高点考虑进去。

图3.7 澳大利亚高校支出的实际变化(从2008年开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如果将过去几年内大量学生入学高等教育系统的情况考虑进去,澳大利亚ARWU百强高校的数据看起来更糟。自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0%。从生均情况来看,ARWU百强高校的生均支出在2008~2013年期间增长了15%。同样,这一数据可能因为2008年的高基准而有所夸大,但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趋势与大多数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ARWU百强高校的生均支出甚至还不断下降。澳大利亚高校生均支出实际变化如图3.8所示。

图3.8 澳大利亚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从2008年开始)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
(四)加拿大
加拿大有4所高校进入ARWU百强。其中2所,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都是规模较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大约有8万名学生,是ARWU百强高校中规模最大的大学,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人数落后不多,约6万名学生)。另外2所大学,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和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与其他百强高校中的多数大学一样,学生人数分别约为4万名和3万名。这4所大学的经费合计占加拿大高等教育总支出的四分之一。
2008年以前,加拿大高校经费支出的实际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快,每年接近6%,ARWU百强高校则达到了7%。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收入增长的大幅减缓,从而也导致支出增长的下降。起初,高校支出的下降源于投资组合的重大损失,而随着财务流程的改善,高校又面临着省政府大量削减高校的运行经费。

图3.9 加拿大高校支出的实际变化(2000~2001至2012~2013)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加拿大大学管理人员协会大学财务信息调查(CAUBO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Survey)。
倘若以生均为基础来考察数据,可以客观清楚地发现支出的增加主要与扩招有关。如果考虑招生增长,则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支出自2000~2001学年以来的实际增长只有8%,而非68%。或许更重要的是,自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加拿大高等教育整体的生均支出不断下降。ARWU百强高校的表现稍好些,从2008年以来的支出或多或少保持稳定。

图3.10 加拿大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自2000~2001年以来)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大学管理人员协会大学财务信息调查以及中学后教育学生信息系统。
(五)瑞典
瑞典在很多方面都与世界趋势相反。最为显著的是,瑞典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便持续提高高等教育的支出。而在2007年之前的几年里,高等教育拨款的增长维持在一般水平,金融危机之后反而不断增加。2007~2008至2013~2014年期间,高等教育整体的支出增加了23%(也即每年大约提升3.5%)。

图3.11 瑞典高校支出的实际变化(2003~2004至2013~2014)
资料来源:瑞典高校以及瑞典高校的年度报告(2005~2014)。
然而,如果从生均的层面考察经费拨款则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状况。在瑞典的3所ARWU百强高校中,即卡罗琳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和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招生人数在2007~2008至2013~2014年期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其他瑞典高校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学生人数自2007~2008年以来保持不变,事实上从2010至2011年的高峰以来还减少了10%。由于学生人数的这些变化,ARWU百强高校自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生均支出一直不如非ARWU百强高校。瑞典高校生均支出实际变化如图3.12所示。
(六)瑞士
瑞士有3所大学进入了ARWU百强,即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苏黎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Zurich)和巴塞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sel)。有关高校招生和财务方面的数据均无法通过国家层面的数据库获得,而总支出数据也仅覆盖了2007~2012年。然而,高校自身一般通过年度报告能够提供非常完善的数据,因而至少可以获得3所ARWU百强高校的数据,并对它们自2005年以来的活动形成非常清晰的了解。

图3.12 瑞典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2003~2004至2013~2014)
资料来源:瑞典高校&高校年度报告(2005~2014)。
要在可比较的时间范围内获得可比较的数据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也使得图3.13不太一样:数据开始于2007年,是可获得数据的第一年。该图显示,就支出的瑞士法郎而言,ARWU百强高校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不断增加经费拨款(从2008年以来增长了25%),但并不比非ARWU百强高校更多。

图3.13 瑞士高校支出的实际变化(2005~2013年,从2007年开始)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统计局(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苏黎世联邦理工、苏黎世大学以及巴塞尔大学年度报告。
当考虑学生人数时,情况有所不同。自2008年以来,3所ARWU百强高校的招生人数增长了11%,也就意味着自金融危机以来,生均支出仅增加了7%。然而,从整体层面来看,入学人数增长近25%。因此,如果考察生均支出,ARWU百强高校比瑞士的其他同行做得更好。瑞士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如图3.14所示。

图3.14 瑞士高校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2005~2013年,数据从2007年开始)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统计局(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苏黎世联邦理工、苏黎世大学以及巴塞尔大学年度报告。
(七)荷兰
荷兰仅有14所大学,但有4所进入了ARWU百强,即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阿姆斯特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格罗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和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遗憾的是,难以获得荷兰具体高校的数据,不仅中央统计局不提供高校层面的数据,4所高校中也只有格罗宁大学提供充足的公开数据可供考察财务和学生方面的时间序列变化。然而,由于4所大学的支出占全国高等教育支出的45%,4所大学的支出变化趋势不太可能异于全国趋势(如图3.15所示)。

图3.15 荷兰高校的总支出(2004~2013年,以2013年欧元的币值为基准计算,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荷兰教育、文化与科技部(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 and Science)。
从本质上说,图3.15显示,除了2008年、2009年两年期间的一次大幅增长以外,荷兰高校的开支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学生人数不断扩大:2004~2013年期间,高等教育机构(仅包括大学,不包括高等专科学院)的招生人数大约增长了30%,而增长主要集中在2010年之前。其结果是,当考察生均情况时,荷兰高校的支出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内下降(由于学生人数上升,但支出保持不变),而后上升(学生人数继续上升,但支出增长得更快),之后又再次下降(学生人数上升但支出并没有增长)。到2013年,生均支出的水平再次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2004~2013年荷兰高校实际生均支出变化如图3.16所示。

图3.16 荷兰高校的实际生均支出(2004~2013)
资料来源:荷兰教育、文化与科技部。
我们无法确定ARWU百强高校的情况,但图3.17呈现了格罗宁根大学生均支出的变化。该图显示了有所不同的模式,收入在2008年以前持续下降,之后有小幅上涨。整体上,罗宁根大学在过去十年来的表现似乎不及荷兰高校的平均水平。

图3.17 格罗宁大学的生均支出(2005~2012)
资料来源:格罗宁大学年度报告。
(八)德国
德国有4所大学进入了ARWU百强,即弗莱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海德堡大学(Heidleberg University)、慕尼黑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unich)和慕尼黑工业大学(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在这些高校中,只有2所大学在网站上公布了有关学生和财务方面的历史数据,其中仅有1所提供了2010年之前的系列数据。因此,图3.18只展示了德国高校整体的数据。很明显,德国高校在过去十年来的收入增长非常显著,截至2013年提升了88%。支出数据所显示的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一些明显的波动,似乎受2009年德国联邦和各州共同拟定的高校公约的影响(Garnder 2009)。该公约的一些经费似乎被提前开支了,因此导致了2010年拨款的下降,但之后经费有所恢复。

图3.18 德国高校总支出(2000~2013年,以2013年的欧元币值为基准计算,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Statistiches Besamt)。
对于可以获得若干年数据的2所ARWU百强高校而言,如图3.19所示,尽管经费拨款有所提升,但不如其他高校那么显著。在2006~2010年期间,这些高校的总支出增长了30%,而德国高校整体支出的增长为39%。自2010年以来,高校整体的经费提升了8%,而2所百强高校的增幅为7%。
然而,值得回顾的是,2009年公约的颁布主要是为了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因此,学生人数近年来大幅增加,使生均支出的增长看起来不那么令人眼前一亮。从2009年开始,所有高校的生均经费都在持续下降,但这与经费提前分配也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生均支出回归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的水平。如图3.20所示,在这段时期内,学生人数的增长消耗了公约的全部经费。

图3.19 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总支出(2006~2014年的若干年份,以2014年的欧元币值为基准计算,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海德堡大学年报;慕尼黑工业大学“事实与数据”。

图3.20 德国高校的实际生均支出(2004~2013)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而2所ARWU百强高校,很难达到一致的模式。两所学校均获得了大量的经费,但海德堡大学在扩大招生方面远不及慕尼黑工业大学。其结果是,两所大学的生均支出朝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2006年之后,海德堡大学的经费提升了26%,而慕尼黑工业大学则下降了15%。然而,如图3.21所示,两所大学的生均支出在2010~2014年期间均有所下降,海德堡大学的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慕尼黑工业大学则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3.21 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实际生均支出(2010~2014年,以2014年的欧元币值为基础计算)
资料来源:海德堡大学年报;慕尼黑工业大学“事实与数据”。
(九)日本
日本也有4所ARWU百强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和大阪大学)。国家层面关于高校招生和公共拨款的数据可以通过日本教育、文化、体育与科技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获得。总经费(而非支出)可以通过经合组织关于教育机构公共/私人支出的公开数据推算得出。
日本对高校的政策近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如图3.22所示,日本对高校的经费拨款也在相对较窄的范围内波动。2011~2012年度的拨款比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时仅高出大约4%。

图3.22 日本高校的总收入(2005~2006至201 1~2012学年,以201 1年的日元币值为基础计算)
资料来源:日本教育、文化、体育与科技部;经合组织教育概况。
由于日本年轻人口的规模略有下降,即便高等教育参与率增长也意味着学生人数的停滞不前。因此,如图3.23所示,生均经费支出的变化模式与图3.22所示的高校整体收入的模式几乎一致。

图3.23 日本高校的实际生均支出(2005~2006至201 1~2012)
资料来源:日本教育、文化、体育与科技部;经合组织教育概况。
日本高校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国家层面没有关于具体高校收入或支出的数据(至少没有用英语呈现的数据)。然而,一些高校的部分数据可用。京都大学2005年以来财务和招生方面的信息都很完整,而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只能获得部分年份的部分数据(大阪大学没有任何数据可用)。这3所大学公布了2006年的学生人数以及2005年的财务数据,据此可以作出一些关于学生生均支出的大致推断(见表3.1)。
表3.1 日本ARWU百强高校的财务和入学率数据

资料来源: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名古屋大学的年度报告。
(十)法国
法国高校的财务数据很难获得。法国4所ARWU百强高校,即巴黎第六大学(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巴黎第十一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ris-Sud)、巴黎高等师范学院(L'Ecole Normale Superieur)以及斯特拉斯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仅公布当年的年度财务报告或学生人数。因而,我们只能考察法国国家层面的数据。由于法国采取绩效拨款的方式,因此顶尖高校很可能比高校平均水平更好,只是无法依据公开数据说明具体情况。
图3.23呈现了法国在2005~2006至2013~2014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公共支出。根据法国政府提交给经合组织的数据,公共经费占法国高等教育整体收入的80%~85%左右,因此,实际支出可能比这里所呈现的数据更高。尽管如此,由于通过第三方渠道所获得的经费近年来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图3.24作为高校预算变化的一般模式。如图所示,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法国高校支出增长了10%以上,而金融危机之后则下降了8%左右。

图3.24 法国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2005~2006年至2013~2014年,以2013年的欧元币值为基准计算,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法国教育部统计(Reperes et references statistiques)(2008~2015)。
法国高校入学率的增长就算不是缓慢,也只能算是稳定。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入学率仅上升了3%。因此,当呈现生均支出数据时,经费拨款下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图3.25所示。

图3.25 法国高等的生均支出(2005~2006年至201 1~2012年,以2013年的欧元币值为基础计算,单位: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法国教育部统计(2008~2015)。
四、数据总结
我们可以通过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对以上数据进行总结:
首先,当前的高等教育支出是普遍高于还是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根据本文所考察的10个国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大部分国家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即便是在通货膨胀之后。但这些国家的高校所招收的学生人数也相应增加。如果同时考虑通货膨胀和学生人数,只有英国、瑞典和德国的情况比6年前更好。在日本、荷兰和瑞士,重新计算过币值的生均支出均比较稳定;在加拿大、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整体的支出自2008年以后均有下降。
其次,ARWU百强高校是否与其他高校享有同样的待遇?在多个国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我们无法得出结论。在日本和英国,ARWU百强高校和非百强高校所得到的待遇似乎相同。但在瑞典和澳大利亚,非ARWU百强高校的生均收入比ARWU百强高校更好。而在瑞士、加拿大和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私立大学,ARWU百强高校似乎比其他大学的表现要好得多。
最后,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ARWU百强高校的经费是否有所改善?我们所见的ARWU百强高校生均支出增长显著的3个国家分别是美国——生均经费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10%~12%;英国——生均经费提升8%~10%;以及瑞士——生均经费提升约7%。在加拿大、瑞典和日本,证据表明ARWU百强高校的生均支出相对稳定,增长率在3%左右浮动。在荷兰和法国,我们认为ARWU百强高校遵循国内的一般模式。在德国,结果似乎是混合的:有些高校遵循一般模式,有些则不是,取决于招生规模的大小。只有在澳大利亚,ARWU百强高校的支出明显更低,生均经费下降了15%左右。
图3.26呈现了自2008年以来,各国高等教育生均支出的实际变化,包括ARWU百强高校和非ARWU百强高校。

图3.26 各国生均经费拨款的实际变化(2008年至今)
五、结论
谈及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命运,可以得出几点结论。政策条件(特别是有关学生人数的增长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而言,在学生人数大幅增长的国家,高校最多能够保持收支平衡。因此,政策选择非常重要。当然,美国和英国的高校为应对政府经费削减而采取的提高学费的举措也使得它们能够维持财务增长的轨迹。
这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大学的成功并不完全依赖于此。无疑,资金似乎并不会对ARWU排名产生实际的短期影响:如果会的话,澳大利亚高校的表现会比现在糟糕得多。显而易见的是,机构战略、招聘实践以及管理水平同样至关重要。不过,我们目前还很难评估高校这些方面的特征。
同样明显的是,充裕的经费会使高校更容易应对很多挑战。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的私立大学更可能保持它们在国际排名上的领先地位,甚至可能还会扩大它们的优势。美国的顶尖公立大学,以及英国和瑞士的高校也会比其他国家的高校更容易应对目前的形势。
在其他国家,经费的增加似乎往往伴随着招收新的学生。也就意味着,高校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经费以加强科研首先必须招收更多的学生,并且主要是本科生。政府可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为高校提供了很好的筹码,但坦率地说,这一方式并不总有效用。因为通过扩大招生所得的大部分资金往往都花在了学生培养上,很少有“结余”能够用于追求科研卓越。因此,政府如果想要在高校中发展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找到其他增收的办法,并要减少通过扩大招生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可能的途径包括加强对学费的管控、增加竞争性卓越项目,或采用其他的一些措施。
筹集更多经费以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另一办法是提升高校的效率,并将经费重新投入在科研活动上。澳大利亚的ARWU百强高校在过去几年里一直采用该举措,世界各国政府也可能希望了解这些高校获得成功的方法。鉴于目前许多政府依然面临整体性财政困难,这可能是高校追求世界一流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非继续等待公共经费的投入。
正如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曾说过的名言:“先生们,我们已经花光了钱。现在是应该开始思考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 Altbach P.(2004 January-February).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Academe.
[2] Andreas J.(2009).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Palo Alto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Garnder M.(2009 September 20).Germany:Record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World News,(81).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090618200051988
[4] Geiger R.(2009).Research & relevant knowledge.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5] Graham H.D. & Diamond N.(1997).Rise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Elites and challengers.
[6] Baltimore C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7] OECD.(2014).Promoting research excellence:New approached to funding.Paris:OECD.
[8] Orr D.Wespel J. & Usher A.(2014).Do changes in cost-sharing have an impact on the behaviour of stud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9] Salmi J.(2009).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ashington DC: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