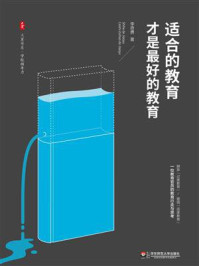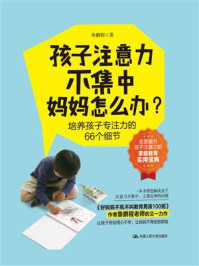贾米尔·萨尔米(Jamil Salmi)

一、引言
“石油时代之后,知识是未来的关键。”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伯格(Erna Solberg)
“生产力不是一切,但长期而言,它几乎等于一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知识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生产、选择、更新、商业化以及使用知识的能力,对于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言至关重要(World Bank 1999)。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在构建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促进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培养有技术、有效率且灵活的劳动力,以及应用和传播新的理念和技术来帮助其所在国家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体。
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系统涵盖各种类型的组织模式,不仅包括研究型大学,也包括应用技术学院、文理学院、短期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这些机构共同培养着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各类技术工人和员工(World Bank 2002)。每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发挥着自身的重要作用,许多政府所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不同成员之间的平衡发展。
在高等教育系统当中,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培养专业人才、高水平专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关键角色,而这些人才是经济发展和为支持国家创新型体系进行知识创造所需要的重点人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他们的顶尖高校处在知识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随着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首次发布国际性的大学排名以及之后其他国际大学排名的竞相出现(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台湾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比中心基金会、QS等陆续发表全球排名),有更多的系统性方法可被用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确定和分类(Salmi 2009)。为了国家的声誉,越来越多的政府想要找到能够促使本国顶尖大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有效的方法。尽管有少数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创建了新的大学,但大部分感兴趣的国家采取的战略是高校合并以及升级现有大学。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一些政府纷纷推出了所谓的“重点建设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s),投入大量的额外经费用于提升大学的绩效。
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目标是评估重点建设计划对相关大学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下文首先分析了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特征,随后则考察了它们的成就和局限。
二、重点建设计划的特征
以德国为代表,高等教育的“重点建设计划”可被描述为是政府为了加快提升现有大学而大量投入额外经费的计划
 。
。
“卓越计划”旨在促进尖端研究和提升德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质量,从而使德国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研究基地,使其更具国际竞争力,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高校和科学共同体的杰出成就上。

表1.1呈现了这些重点建设计划的总数量和大致的地区分布,可将这些重点建设计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9~2004年的十五年间,当时还没有“重点建设计划”这样的表述;第二个时期则是2014年之前的十年。通过对这两个时期的比较可以发现,自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THE全球性大学排名相继在2003年、2004年发布以来,世界各地的重点建设计划数量急剧增加,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趣日益加大。本文附录1列出了各国项目的完整名单,这些项目在本文中统称为“重点建设计划”
 。
。
表1.1 不同地区和时期“重点建设计划”的数量

资料来源:由作者整理。
表1.2则详细列出了两个时期内实施过某种重点建设计划的国家地区名单。
表1.2 重点建设计划的国家/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由作者整理。
注:有些国家/地区实施了多个重点建设计划或一个重点建设计划跨越了两个阶段,这里每个国家和地区只列出一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表1.1重点建设计划的数量比表1.2的国家/地区数量多。
以上表格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包括北欧国家、加拿大、中国、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少数几个国家较早地预见了提升大学作为创新型经济支柱的重要性。而近期的重点建设计划主要实施于东亚和西欧,这符合它们经济现代化的议程。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拉丁美洲人口规模庞大且经济实力雄厚,却缺席了这场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教育领导者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远见。尽管如此,近年来,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还是推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奖学金计划以资助学生出国留学。
美国和英国的高校一直处于国际大学排名的领先地位,加之其获得的科研经费水平本身已经很高,因此没有考虑额外的经费资助计划。瑞士也符合这一情况,该国的两所联邦理工大学,即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TH Lausanne),在现有充裕资源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改进。
在以上所有的案例中,通过重点建设计划所获得的额外经费都完全来自公共财政,只有少数国家的资助方式比较新颖。例如在德国,“卓越计划”是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L ä nder)合作的形式实施的。同样,在中国的项目中(“211工程”和“985工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投入50%。现已停止的西班牙重点建设计划则是通过优惠贷款的形式将资源划拨给入选大学。或许最新颖的资助方式是法国最新启动的重点建设计划,其经费主要来自一大笔捐赠(95亿美元)所产生的年度收益,成为划拨给入选高校的经费来源。这样的经费资助形式可以维持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这也是所有其他的重点建设计划所缺失的。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专项项目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入选大学的数量有限,且主要聚焦于科研。此外,这些项目倾向于资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而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
除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都有资格竞争这些额外经费以外,大部分重点建设计划都只针对公立高校。
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实施的重点建设计划数量和周期不同。表1.3呈现了各国/地区重点建设计划的持续情况:是实施了一项计划还是多项计划,以及每项计划延续了一个周期还是多个周期(通常为两个周期)。重点建设计划的时间跨度通常是中期至长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计划(或周期)的持续时间从3年到7年不等。
表1.3 重点建设计划的重复性

资料来源:由作者整理。
绝大多数的重点建设计划几乎都完全集中于提升高校的科研能力,主要的例外是中国台湾地区,该地区在实施以科研为主的项目同时,还启动了一个追求卓越教学的专项计划。台湾地区于2005年推出“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The Teaching Excellence Development Program),共投入大约6.5亿美元的预算来促进台湾公立和私立大学课程与教学实践的现代化,入选的31所大学在为期5年的时间内获得了总计2 150万美元的资助。德国在实施一个大型科研发展项目的同时,也启动了一个小型的项目以推动卓越的教学。其他几个国家的重点建设计划在着重提升科研的同时,也纳入了改善教学实践的经费,例如芬兰、西班牙和韩国等。
在促进卓越科研方面,不同重点建设计划的重点和落脚点存在很大的区别。在有些情况下,资助单位是整个大学,它们获得用以资助整体发展计划的一揽子拨款。而在其他情况下,政府重点强调建立新的卓越研究中心或增强现有的研究中心。德国的“卓越计划”结合了这两种形式,并提供三类资助,一类针对入选高校的发展计划,一类针对新的跨学科研究集群,还有一类则是针对新设立的研究生院。参与高校首先需要同时入选一个新研究生院和一个新研究集群才有资格参选学校“卓越计划”。在韩国,“21世纪智慧韩国工程”第一期资助的是高校整体,第二期则直接为单个学系提供支持。
无一例外,几乎所有的重点建设计划均由各国的教育部或高等教育部所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部和主要的国家研究机构合作,共同负责项目的实施过程。由于涉及很具体的专业技术评估工作,这种合作在竞争性的遴选过程中尤为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机构主要依赖专家小组来评估不同学科提案的有效性。例如,在德国第二期“卓越计划”的评估阶段,由457名专家所组成的37个专家小组负责对127份新研究生院和研究集群的申请进行评估。这一方式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减少政治干预,并且可以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更为灵活的管理框架。
重点建设计划的经费数量反映了资助水平的显著差异(如表1.4所示)。其中,中国大陆地区、法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脱颖而出,成为对高校整体资助最为大方的国家或地区。以色列和日本则对单位卓越研究中心的资助水平最高。北欧国家的资助最少,主要因为它们高校的基础经费已经显著高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本文附录2列出了各国重点建设计划的具体经费数量。
受资助高校或卓越中心的遴选过程或许是重点建设计划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条件的高校会同时参与资助名额的竞争,政府采用同行评议程序选择最好的提案,国际经验显示竞争性经费拨款能够大大改进高等教育机构的绩效,并成为促进高校转型和创新的有力工具(World Bank 2002)。同行评议过程一般由评估专家团队进行,这些团队有些可能仅包括国内专家,有些则由国内和国际专家共同组成。而在有些情况下,国际专家代表了大多数,如在法国重点建设计划中,甚至连国际评审团负责人都由外国专家担任(一所知名瑞士大学的前校长)。
表1.4 最新重点建设计划对每所大学/卓越中心的资助范围

资料来源:由作者整理。
国际专家参与遴选过程会增加评审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例如,在德国最新一轮的“卓越计划”中,提案的评估专家中有87%来自德国以外的地区。
在重点建设计划实施的最初阶段,遴选基本上对所有高校或卓越中心开放,因而获选高校事先并不知情,少数情况下政府会倾向于“择优选择”重点建设计划的受资助高校。例如,泰国便是采用“择优录取”的办法,政府指定了9所高校作为额外经费的获得者。中国的经验则介于两者中间,教育部在“985工程”中将高校分成三类,并根据不同的分类分配资助经费。在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计划”(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ies Program)遵循的是公开竞争的方式,但在“联邦大学计划”(Federal Universities Program)中,政府则根据地区发展情况决定合并哪些大学、资助哪些大学等。最新的“5—100计划”取决于一群少数有资格的大学之间的竞争。
总结对重点建设计划主要特征的概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早期的重点建设计划更多是内生性的长期方针,也即主要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最新的重点建设计划则似乎主要由外部环境诱导,旨在提升高校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能比国外大学的表现更出色,这可以通过国际大学排名进行评估。例如,俄罗斯2013年的重点建设计划明确提出其目标是到2020年要有5所高校进入世界百强。
其次,许多重点建设计划标志着参与国资助政策理念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在西欧很明显。如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所有公立大学传统上被认为同等出色,而重点建设计划使这些国家从统一预算转向了竞争性的绩效经费拨款模式。
考虑到这些特点,那么这些重点建设计划究竟有多成功呢?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这些计划的变革性影响?
三、重点建设计划的影响
要评估重点建设计划对受益大学的效力和影响并非易事,主要因为两方面的原因:时间和归因。首先,升级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需要8~10年(Salmi 2009 & 2012)。由于很多重点建设计划实施的时间很短,试图评估它们的成效在大多情况下时机尚不成熟。事实上,受资助大学的科研产出不太可能会在重点建设计划实施的前几年便大幅增加。因此,一个全面的分析需要对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的大量样本高校进行长期比较。
第二个挑战则来自归因。即便基于大量的高校样本可以确定相关性,但要确立因果关系还需要通过案例研究进行深入的分析,正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大学案例研究》(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这本书所呈现的案例分析那样(Altbach & Salmi 2011)。
考虑到以上限制,本文尝试从重点建设计划对促进受资助大学的科研能力和产出等方面的初步成果中总结出一些基本结论。本文还将考察科研和教学、卓越与公平以及卓越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
在对近期重点建设计划的影响缺乏分析的情况下,比较过去十年内(2004~201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0强高校的表现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组数据(见表1.5)根据各国排名最好大学的名次进行了国家排名。从这一层面来看,过去十年内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排名靠前的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名次显著提升(至少提升8名),包括丹麦(+20)、澳大利亚(+9)和瑞士(+8)。而在排名靠后的国家中,中国大陆的大学提升得最快,从201~300位区间提升到101~150区间。中国香港、爱尔兰和中国台湾等三个国家或地区在2004年没有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0名,但2014年进入了该排名的全球200强。奥地利、以色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排名则显著下降。然而,该表只是呈现了各国排名最好的大学的名次变化,很难据此推断重点建设计划与这些名次的变化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或许北京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例外,因为这两所大学的名次有显著的飞跃。
。第一组数据(见表1.5)根据各国排名最好大学的名次进行了国家排名。从这一层面来看,过去十年内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排名靠前的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名次显著提升(至少提升8名),包括丹麦(+20)、澳大利亚(+9)和瑞士(+8)。而在排名靠后的国家中,中国大陆的大学提升得最快,从201~300位区间提升到101~150区间。中国香港、爱尔兰和中国台湾等三个国家或地区在2004年没有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0名,但2014年进入了该排名的全球200强。奥地利、以色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排名则显著下降。然而,该表只是呈现了各国排名最好的大学的名次变化,很难据此推断重点建设计划与这些名次的变化之间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或许北京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例外,因为这两所大学的名次有显著的飞跃。
表1.5 基于ARWU排名世界200强高校的国家/地区排名(2004年和2014年)

资料来源: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boutarwu.html)。
注:粗体字标注的国家或地区实施了重点建设计划。
表1.6呈现了2004~2015年期间各国/地区上榜大学的数量变化,该数据更有说服力。6个取得显著进步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28所新增上榜大学)、澳大利亚(6所新增上榜大学)、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韩国和西班牙(各有4所新增上榜大学),除了西班牙以外,其他国家的进步无疑可以归功于重点建设计划的持续投入。然而,在没有开展深入案例研究的情况下,很难将西班牙高校的进步归功于重点建设计划,因为该国近年来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重点建设计划的经费投入遇到障碍。
表1.6 各国/地区上榜大学的数量变化(2004年和2015年世界500强)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boutarwu.html)。
注:粗体字标注的国家/地区实施了重点建设计划。
位于名单末尾的最大“输家”是日本和美国,与十年前相比,两国2015年的世界500强高校数量分别减少了16所和24所,德国和英国则分别减少了4所和5所。需要注意的是,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些国家高校排名名次的进步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下降,但这4个国家的变化还是值得一说。就美国而言,有趣的是相比于私立大学,更多的公立大学跌出了排行榜,这似乎也证实了自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公共财政资助的大幅下降对美国公立大学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公立高校占整体高校的比例从2004年的64.5%下降到2014年的63.7%。虽然下降的幅度较小,但趋势是很显著的。
日本入榜500强高校数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金融危机有关,日本的大学很难从重点建设计划中获取额外经费。观察者们注意到,日本高校在大力提升国际化方面也遇到困难(Kakuchi 201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04~2015年期间有两所高校跌出了全球百强(从5所下降到3所)。
在德国,入榜高校数量的下降是因为两所知名大学被排除在500强之外:柏林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和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事实上,这两所高校的出局并非由于它们实际表现的下滑,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就如何分配二战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属单位达成一致,而这两所大学原本都属于柏林大学。在两难之际,“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决定将这两所大学都排除在排名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所高校都在德国“卓越计划”的11所重点资助大学之列。
英国高校竞争力的下降更难以解释,英国不仅有5所大学跌出500强榜单,百强大学的数量也从11所下降到9所。
另一种考察各国高校在2004~2015年期间名次变化的方法,是在人口规模的基础上计算各国世界百强高校的数量。表1.7呈现了分析结果,并且注明了各国实施重点建设计划的情况。
表1.7 每百万常住人口世界百强高校的数量变化(2004~2015)

资料来源: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boutarwu.html)和世界地图集(http://www.worldatlas.com/aatlas/populations/ctypopls.htm#.UkjUH3brz9c)。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几点发现:首先,表现最好的国家全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包括瑞士(得分最高)、北欧国家、荷兰和以色列。其次,进步最快的国家是瑞士、丹麦、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其中澳大利亚、丹麦和以色列等三个国家都实施了重点建设计划;最后,表现显著下降的是日本、英国、瑞典和奥地利。
尽管这些结果并不能充分说明重点建设计划的效果——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计划最近才实施,还无法呈现显著的进步,比例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但它们证实了持续高水平经费投入的重要性(如瑞典和荷兰)。
对2004~2014年期间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名次显著提升(超过25名)的所有高校进行的考察更能说明问题(见表1.8)。
表1.8 2004~2014年进步最快的高校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boutarwu.html)。
*“排名变化”一栏中前面出现的名次是指学校2004年的排名,若学校在2004年未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100强,则以第一次进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名次替代。
尽管表1.8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但似乎进步最快的大学中大多数都是重点建设计划的受资助高校。表格中,中国大陆、爱尔兰、以色列、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高校的进步尤为明显。法国和葡萄牙高校名次的提升主要是2013年合并的结果,而不太可能是因为合并后高校质量的立即改善。该表也证实了前面表格中,关于瑞士和荷兰高校在不需要任何专项重点建设计划的情况下依然有杰出表现的发现。
四、绩效的驱动力组合
为了评估各类重点建设计划在排名方面以外的相对优势,本文的分析使用作者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一书中所提出的分析框架(Salmi 2009)。该框架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成就——受雇主青睐的毕业生、尖端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有活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本上可以归因于顶尖大学的三组互补的要素:①人才汇聚(教师和学生);②资源丰富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并能开展顶尖研究;③高水平的管理,鼓励战略愿景、创新性、灵活性,使高校能够自主决策以及管理资源,不受官僚体制的束缚。(见图1.1)
高校要实现卓越,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是拥有大量的优秀学生和杰出教师。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能从本国也能从国际上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吸引最高水平的教授和研究人员。

图1.1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主要因素组合
资源充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二个特征,主要因为一个复杂的研究型大学的运行需要耗费巨资。这类大学有4种主要的经费来源:政府就运行经费和科研的预算拨款、来自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合同经费、捐赠带来的财政收益以及学生学费。
第三个维度则是高校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和管理自治的程度。世界一流大学所运行的环境鼓励竞争、自由探索、批判性思维、创新和创造力。拥有完全自主性的高校也更灵活,因为它们不受外部烦琐而官僚化的规则和标准制约,即便是合法的问责机制也无法约束它们。这样一来,它们能够灵活管理自己的资源,并迅速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的需求。自主性对于建设和维持世界一流大学而言虽然不是唯一的要素,但确是必要的要素。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管理要素,如善于激励下属且执着的领导者,有关高校未来发展方向的强有力的战略愿景,成功与卓越的理念,不断反思、学习和变革的组织文化。
为了完善此分析框架,最新的政策研究总结了在高校追求卓越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促进因素”(Altbach & Salmi 2011)。在建立一所新大学时,首要因素便是广泛依赖移民。韩国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表明,大力延揽海外学者回国是快速建立高校学术优势的有效途径。
第二个因素是使用英语作为大学的主要工作语言,可以极大增强高校吸引高水平海外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能力,可参见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成就。出于同样的原因,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也有意使用英语作为其工作语言。
聚焦优势领域是高校实现更快发展的第三个合适的路径,正如亚洲的香港科技大学和浦项科技大学,俄罗斯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等案例。
第四个因素是使用标杆工具引导大学的不断提升。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在战略规划中先与国内其他顶尖大学相比较,后又与国外同行高校作比较。
第五个因素是进行课程与教学创新。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首个采用美国模式的大学,这一特点使其与香港其他按照英国模式运行的高校相区别。莫斯科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则是第一个在课程中融合了教学和科研,并设立数字图书馆的俄罗斯大学。这些创新特征,部分源于“后发优势”,对于新大学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它们需要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以便能够与现有大学争夺生源,使这些学生愿意冒险进入“未知”的新学位项目。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已经成功的高校还需时刻保持警惕,并始终保持一种紧迫感,以免自鸣得意、不思进取。这就需要这些大学不断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一旦发现有异常、矛盾或威胁的情况,需迅速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断探索其他需要改进的地方。
评估近期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优势和劣势,可以考察它们在以下方面的贡献程度:①加强人才汇聚;②改善资源基础;③提高管理水平。
(一)人才汇聚
除了促进高校整体水平的提升,许多重点建设计划还提供经费以资助高校设立大量新的卓越中心或加强现有的卓越中心,这些卓越中心往往侧重于跨学科研究。
在科学界,就职于好的大学非常重要——在这些大学里,最顶尖的科学家在设备最先进的实验室里开展最前沿的研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将其描述为一个滚雪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杰出的科学家获得资助开展令人兴奋的研究,并吸引着其他教师和优秀学生的加盟,最后形成群聚效应,这对该领域的年轻人都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9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重点建设计划的一项最近评估发现,重点建设计划最大的益处之一是能够为高影响/高风险的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合作研究提供经费(OECD 2014)。
重点建设计划……主要通过推动卓越中心和高校不断证明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展示建立跨学科合作的能力,与私营部门和海外机构建立联系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科研能力,从而能够促使科研体系结构发生巨大变革(OECD 2014年,第18页)。
此外,部分国家/地区的重点建设计划,如中国大陆和新加坡,明确将对高校科研的资助领域与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经济优先事项或特定的议题,如气候变化,相关联。
为了促进人才培养和人才汇聚,一些重点建设计划投入经费为刚刚开始博士后科研生涯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以及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业前景。例如,德国的“卓越计划”提供专项经费用于设立研究生院,为来自本国和国外的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新的、更有吸引力的职业路径。
此外,国际化已成为多个重点建设计划的一项核心特征。许多重点建设计划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深化高校的国际化维度,如选送博士生出国、招募外国学生和学者、设立合作学位项目、与外国伙伴开展科研合作项目等。西班牙甚至将其重点建设计划明确地命名为“国际卓越校园计划”(International Campuses of Excellence)。除了能够加快形成群聚效应以外,加强国际化也是抑制“近亲繁殖”的有效途径,而“亲近繁殖”一直被认为是多个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缺陷(Salmi 2009)。
相比之下,日本由于没能够充分拥抱国际化而严重限制了本国高校的全球影响力。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国外机构合作受限是导致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与英国科研产出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Kakuchi 2015)。日本学者所发表的科技论文中仅有25%是国际合著论文,而英国的这一比例高达52%。此外,日本高校外籍学者的比例仅为4%,而国际顶尖高校如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外籍教师比例分别高达30%和40%。日本教育部于2014年10月所实施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便旨在提升本国高校的国际地位。
高校规模是重点建设计划想要实现人才发展目标所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一些国际排名主要比较高校的论文发表量和教师获奖数,但并不考虑招生规模,因而包括中国、丹麦、法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便一直积极鼓励本国的大学合并,以作为快速实现科研群聚效应和提升科研产出的途径(Harman & Harman 2008)。在丹麦,政府设立了一个创新基金,该基金除了资助其他事项以外,还奖励同类高校的合并。在中国,大学之间的合并也非常普遍。例如,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同样,上海的复旦大学也合并了一个医学院,而浙江大学则是由5所高校合并而成。
在俄罗斯,高校合并也成为历次重点建设计划的重点。2007年,俄罗斯通过合并现有大学的方式成立了两所旗舰联邦大学,分别位于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Rostow-on-Don)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Siberian city of Krasnovarsk)。这两所新大学均获得了大量额外经费用以招聘顶尖的科研人员和匹配最先进的实验室(Holdsworth 2008)。在随后的几年中,俄罗斯政府继续鼓励高校通过合并的方式建立更多的联邦大学。
最近一项对芬兰高等教育系统表现的研究表明,芬兰高校相对较小的规模和分散的资源是一个制约因素:
对芬兰的研究成果喜忧参半。科研产出与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密切相关的,但根据2014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芬兰只有赫尔辛基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一所大学进入了世界百强。其他四所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学要么在301~400区间[奥卢大学(Oulu University)和图尔库大学(Turku University)],要么位于401~500位区间[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和东芬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这可能表明芬兰缺乏大量处于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科研团队,从而无法形成群聚效应(Salmi 2015 p.37)。
继2010年通过合并创建了阿尔托大学之后,芬兰可能还需要合并其他的高校,并进一步削减大学和理工学院的数量,从而避免专业项目的重复设置,这样一来才可能在许多现在规模还相对较小的大学和院系中形成群聚效应。
总体而言,由于高校文化的差异,有些也因为缺乏共同目标,合并形成的新大学所产生的效果好坏参半。在这个层面而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故事或许能够提供有益启示。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th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和曼彻斯特理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合并,组成了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其目标是“到2015年进入世界前25名”
 。合并后的最初几年,曼彻斯特大学所面临的挑战重重(Qureshi 2007),主要的问题包括教职员工和课程设置的重复性、难以实现为获得合并的支持而做出的一些许诺以及对劳动合同和机构负债的处理等。此外,新成立的高校为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以聘用“超级明星”学者,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一流设施,这进一步加重了新大学的人事负担,而该校本就面临着将两个不同的教师群体,包括各自的文化、制度和劳动合同都融合到一所大学的挑战。尽管新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名次的跃升令人印象深刻——从2004年的78名上升到2008年的40名,但自此之后,学校的名次再也没有显著的变化。此外,合并所产生的财务、文化和人际交往的障碍是否已经得以解决还有待观察。
。合并后的最初几年,曼彻斯特大学所面临的挑战重重(Qureshi 2007),主要的问题包括教职员工和课程设置的重复性、难以实现为获得合并的支持而做出的一些许诺以及对劳动合同和机构负债的处理等。此外,新成立的高校为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以聘用“超级明星”学者,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一流设施,这进一步加重了新大学的人事负担,而该校本就面临着将两个不同的教师群体,包括各自的文化、制度和劳动合同都融合到一所大学的挑战。尽管新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名次的跃升令人印象深刻——从2004年的78名上升到2008年的40名,但自此之后,学校的名次再也没有显著的变化。此外,合并所产生的财务、文化和人际交往的障碍是否已经得以解决还有待观察。
与之类似的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最近对4所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大学的“认同形成”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这4所高校在合并之前区域性质不同,而合并的目标是希望新高校能够以国际化为重点,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障碍(Chirikov 2013)。研究发现,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最显著的困难并不出现在合并的开始阶段,而是合并之后的阶段。这些困难反映了来自学者的各种抵制,抵制的原因包括担心会失去本学科的认同以及不得不在陌生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竞争、怕学生不熟悉新的大学品牌、认为政府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容模棱两可、担心大学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按照一所创业型大学那样运行以及管理合并高校的行政结构会更加复杂化等。当两所高校都致力于合并并且优势互补时,合并似乎更容易成功,丹麦奥胡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arhus)便是这样的例子(Salmi 2009)。
合并所带来的风险还包括将学校变成一个难以有效管理和显著提升的巨型大学。例如,在法国,最近在马赛和艾克斯省地区由4所大学合并而成的大学招生规模达到了12万人。在拉丁美洲,巨型大学如墨西哥的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相对较差的表现,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Salmi 2009)。
为了探究重点建设计划如何帮助受资助高校汇聚人才,确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竞赛中的三个严峻风险和挑战非常重要。首先,过于强调科研会传递教学质量不那么重要的错误讯息。事实上,国际大学排名的指标普遍偏向研究型大学,其代价是排除了以招收本科生为主的一流高校。例如在美国,很多文理学院或科学院,如卡尔顿学院(Carleton)、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y)、奥林学院(Olin)、波尔纳学院(Pomona)、卫斯理学院(Wellesley)和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s)被公认为非常杰出的本科教学机构,然而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进入国际大学排名,因为它们不是科研重地。在最近一次的大学演讲中,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British Minister for University and Science)公开抨击高校由于过度强调科研发展而导致教学质量低下的状况。
“由于许多大学认为其声誉、在国家排名上的名次以及边际资金主要由学术产出决定,教学在我们的体系中已经令人遗憾地沦为了科研的穷亲戚”(O'Malley 2015)。
其次,聚焦于世界一流大学很可能会进一步助长精英主义,导致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恶化。为了促进学术卓越,顶尖大学在招生方面往往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其风险是会将来自低收入或弱“文化资本”家庭的优秀学生排除在外。拥有1 000: 1的录取率,印度理工学院成为世界上最挑剔的高校。同样,常青藤盟校是美国选择性最高的大学。研究表明,美国顶尖大学所录取的学生的平均SAT成绩近几年持续上升,而SAT成绩与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Gladwell 2011)。
第三,一些大学过于受排名引导,为了增加科研产出,它们可能被诱使走捷径而不是真正提升科研实力。有些大学不断接洽其他高校的学者,以便在一些国际排名的声誉调查中给予本校积极评价。大量澳大利亚高校都聘请了“排名专家”,用以指导如何提升排名(MacGregor 2013)。观察者们指责沙特的高校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增加学校的科研产出,途径是聘请兼职的高被引科学家,这些学者同意在发表文章时署名沙特阿拉伯的高校(Bhattacharjee 2011)。
(二)经费拨款
重点建设计划的资助水平和经费来源构成了第二个需要考察的关键维度,因为它们会极大地影响这些重点建设计划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在这方面可以得出三点观察结论。首先,这些计划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假设对一所大学进行一次性投资就足以使其转型,而没有明确解决经费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重点建设计划的安排都是一次性加大投资来提升受资助高校,或者最多持续两个周期。如果受资助大学不设法使其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充分扩大资源基础来维持变革所需要的经费水平和运营成本,重点建设计划的投入便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事实上,随着受资助大学不断通过招募年轻且富有经验的学术人员来补充它们的人才库以及提升科研实力,它们需要担心的是重点建设计划结束以后,自己是否有能力继续留住这些人才。
尽管这在通过一般性税收而获得丰富资源的高等教育系统可能并不构成大问题,如北欧5国和瑞士,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公共资源的投入不持续的话,受资助大学可能无法维持自身的发展,这一情况极易发生在许多正面临经济困难的国家。引用澳大利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莱恩·保罗·施密特(Brian Schmidt 2012)的话来说:“科研能力是通过对项目和人才的长期投资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波动是一种浪费,效果适得其反。”
法国所采取的资助方式是为重点建设计划入选的高校设立国家捐赠基金,这一做法是少数考虑了可续性结构要素的案例之一。然而,考虑到法国当前所面临的财政挑战,目前还不清楚该计划会如何运行。加拿大则提供了另一个相关案例:199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使“卓越研究中心网络计划”(Network of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成为政府对高校预算拨款的长期项目。
德国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进展也颇值得关注。德国宪法法院近期通过了来自联邦政府修改宪法的请求。这将允许联邦政府更多地介入到德国高校的经费拨款当中,而以往高校的经费拨款一直是由州政府负责。这一变化部分是受到“卓越计划”的直接影响,反映了政府对“卓越计划”可能缺乏可持续性投入的担忧,此外也因为联邦政府一直无权对教学进行拨款。
其次,在一些情况下,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已危及政府履行其实现重点建设计划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极端的案例是西班牙的惨痛经历。西班牙的重点建设计划不仅没有考虑可持续性要素——经费被作为一种无偿贷款发放给资助大学,整个重点建设计划也因金融危机而在实施两年后被迫中止,从而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整体上,西班牙高校在2008~2014年期间的核心预算损失了15%,共计23亿美元,而重点建设计划仅提供了8.29亿美元的额外经费(Mitchell 2015)。
同样,印度也没能实现政府在2012年宣布第一个重点建设计划时所作出的会提供额外经费的承诺。而当下,囊中羞涩的印度政府将进一步削减经费,这也可能会对为数不多入榜国际大学排名的精英大学造成威胁,如印度理工学院及其分校(Behal 2015)。俄罗斯最近宣布将全面削减10%的经费,这也很有可能会对新的“5—100”重点建设计划的受资助大学产生不利影响(Vorotnikov 2015)。
启动了重点建设计划的富裕国家当前也感受到了持续经费的短缺,在维持顶尖高校所需科研经费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澳大利亚的情况便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澳大利亚高校的财政状况最近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该国首相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2015年极力推动大规模削减大学预算,这与他在竞选之前的承诺正好相反,当时他作为反对派领袖,强烈批评当届政府没有给予国内顶尖大学充足的经费。
显然,极少有国家能匹及中国的经验,该国以长远的眼光和连贯的政策对顶尖大学的发展予以资助,其重点建设计划已经跨越了近20年之久。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观察,与财政资源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分配有关。在多个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通过重点建设计划的形式引入竞争性经费也就标志着这些国家与传统的经费拨款方式彻底分道扬镳——在传统的模式中,所有的大学,无论绩效好坏,获得的经费水平基本相同。这是重点建设计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其所产生的一个积极效果是额外经费被证明能够为高校制定变革性愿景、确定优先发展事项和通过具体项目实现愿景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
与此同时,随着顶尖大学不断从高等教育公共预算总额中寻求更多的份额,观察者们担心重点建设计划会造成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扭曲。例如,在澳大利亚,由国内顶尖研究型大学所组织成的8校联盟(Group of Eigh,简称G8)主席在2008年解释说:“澳大利亚不能过于分散其相对较少的资源,它必须投资于优势领域。这意味着部分高校和专业领域应该得到特殊优待。如果澳大利亚没有一些大学处在世界顶尖位置,澳大利亚就会落后于他国”(Gallagher 2008)。与之相似,泰国教育部长在2009年宣布“入榜世界500强的大学……有资格获得财政支持”
 。
。
这种观点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是,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顶尖大学的高校才有资格获得经费优先权,而这种优先权是其他声誉略差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不应该也无法期望获得的。这种偏向研究型大学的拨款方式会给同样重要的其他类型的高校带来经费不足的风险,而后者也属于平衡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三)大学治理
最新的政策研究表明,一个恰当的管理框架、一位强有力且善于激励人心的领导以及富有成效的管理会显著促进研究型大学的成功(Altbach & Salmi 2011)。在这方面,几个重点建设计划的一个主要共同缺陷在于缺乏能够促进这些额外经费项目实施所需或相关的治理改革。例如,在德国,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需要在各州的高等教育治理框架内遵守“文官规则”(civil service rules),而“卓越计划”的一些受资助高校在创建和管理新博士学位项目和跨学科研究集群的过程中引入了创新型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由于德国高校大都继续遵守着公共部门刻板的规章制度,在这种以传统方式运行的高校中建立卓越的孤岛会使同一机构有两套并行的管理结构,容易引发风险。因此,德国高校这种不利的管理框架使其很难充分利用“卓越计划”所提供的额外经费。此外,制度化创新需要将新的研究中心融合到已有的管理结构当中,但这取决于现有的教师和系所是否愿意将定期预算的“蛋糕”分配给通过“卓越计划”招聘的顶尖学者,这些学者受资助的年限仅为五年。在缺乏恰当的治理改革的情况下,这些大学可能会发现要扩大和维持已有的积极变化非常具有挑战性。
在西班牙,由政府于2011年所成立的用于评估“国际卓越校园计划”实施情况的国际委员会总结认为,过时的管理是西班牙高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大学应该被给予成功和失败的自由。政府用皮带拴住大学使其难以实现卓越…需要找到规章、监督和大学自主权之间的适当平衡……(Tarrach et al. 2011 p.4)
类似地,在中国台湾地区,对近期重点建设计划的评估研究发现,公立高校必须遵循的严格的薪酬计划致使其无法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吸引和保留顶尖的国外研究人员(Hou & Chiang 2012)。在俄罗斯,尽管有重点建设计划所提供的额外经费,但大学和科学院之间持续的分割被认为是阻碍高校提升科研产出的严重障碍。
在法国,即便高校在2009年实施了管理改革以加强高校的自主权,但目前来看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因为高校依然遭遇着明显僵化的体制,使它们无法轻易自主地设置新的教师岗位,也不能为顶尖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正在进行的高校合并效果的担忧。尽管合并必然会汇聚大量的科研人员,并可能会促使高校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名次的提升,但合并不太可能解决法国高校所面临的根本性缺陷,包括开放式的录取政策、疲软的财政基础、僵化的管理制度以及过时的管理策略等(Salmi 2009)。
同样,对主要侧重国际化的日本重点建设计划的批评者认为,这些经费计划没有解决影响该国顶尖大学的核心治理和管理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公立高校的薪酬结构问题,高校因此很难防止顶尖的科研人员流失到私营企业(Kakuchi 2014)。
相比之下,丹麦似乎是少数将综合治理改革融入重点建设计划的国家之一,旨在将高校变革为更灵活、更有活力的机构。额外财政资源和治理框架之间的高度结合,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丹麦高校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的快速崛起。2004年至2014年期间,哥本哈根大学的名次增加了20名,从79名提升至59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斯胡大学(Aarhus University),也是该国排名第二的顶尖高校,从2004年的101~150区间攀升至2014年的74名。
同样,在中国,由C9项目所支持的顶尖大学最近也被允许对治理和管理结构进行改革,以便提高高校的自主权和灵活性(Ruish 2014)。这种治理改革是对前文所介绍的大量额外经费资源的补充。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案例很有意思,该校由一位强有力且富有远见的校长掌舵,通过加强科研取得了显著进步(见前表1.8)。这种进步发生在大家对校长的“管理主义”的担忧下,该校长努力将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融合在一个战略中,以提升都柏林大学的科研产出和国际声誉
 。
。
追求卓越与缺乏充分的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面临的第二个严重的管理问题。顶尖大学是否能在学术自由可能受限的情况下产出杰出的成果还有待观察。
五、结论
“追求卓越,和追求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一样,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丹尼尔·林肯(Daniel Lincoln)
位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最新排名前十名的大学都是1900年以前成立的,其中有两所高校的历史甚至长达800年之久。事实上,世界顶尖大学都是历史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点并不足为怪,因为这些大学享有所谓“越陈越香”的优势:声誉效应使这些大学不断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从而能够自我延续卓越标准和杰出成果。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意识到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国际大学排名的推动,政府对大学角色和重要性的考量发生了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政府认为,通过适当的领导管理和重点投资,目前还未进入全球高校金字塔上层的大学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转变成世界一流大学。
政府对提升本国顶尖大学绩效和声誉的决心转变成了世界各地的重点建设计划。本章分析了这些重点建设计划的主要特征,并试图鉴定初步成效。正如前文所解释的那样,考虑到大多重点建设计划实施的时间尚短,高校的有效转型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要对重点建设计划的有效性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现有数据清楚地表明,最成功的高校是那些组合了三类主要卓越要素的大学,也即人才汇聚、资源充裕以及高效管理,而第三者对于快速变革可能是最为关键的。
本文的另一个发现是重点建设计划可能会产生消极行为并带来不良后果。政策制定者和高校领导者必须谨防重点建设计划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如对教学质量产生有害影响、降低弱势群体学生平等求学的机会以及减少机构多样化等。
事实上,“重点建设计划”这一概念可能并不恰当。这些项目似乎更专注于打造“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国际大学排名衡量,而不是追求高校整体的卓越。这些计划充其量促进了高校对科研卓越的追求。但科研只是大学的功能之一,同等重要的还有教学质量以及高校为所在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生产部门和社区所带来的价值。
一个重点建设计划不能替代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有益改革。从定义上来看,重点建设计划的目标是支持和变革那些有可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大学。但这一做法并不能排除同时实施全系统的改革,特别是在质量保障、经费拨款和高校管理等方面。系统的改革不仅能加强重点建设计划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能确保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总之,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并不是那些能吹嘘拥有最多排名靠前的大学的体系。政府应该少操心世界一流大学数量的提升,而是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构建世界一流大学体系,这样的体系不仅涵盖不同使命、定位明确的各类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能够满足各类个体、社区和国家的整体需求,而这种需求也反映着经济体的活力和社会的健康状况。
附录1:每年启动的重点建设计划列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录2:各国/地区实施的重点建设计划及每所大学获得的经费

(续表)

(续表)

(续表)

参考文献
[1] Altbach P. & Salmi J.(2011).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2] Bhattacharjee Y.(2011).Saudi universities offer cash in exchange for academic prestige. Science 334(6061)9 December 2011.
[3] Behal S.(2015).Sweeping funding cuts will hit elite institutes. University World News 351 23 January 2015.
[4] Chirikov I.(2013).University mergers need to confront identity issues. University World News 265 30 March 2013.
[5] Csikszentmihalyi M.(1997). Creativity: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6] Gladwell Malcolm.(2011).The order of things:What college rankings really tell us.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14.
[7] Harman G. & Harman K.(2008).Strategic mergers of strong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1(1):99-121.
[8] Holdsworth N.(2008).Russia:Super league of “federal”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World News October26.Retrieved December3 2008 from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081024094454199.
[9] Hou A.Ince M. & Chiang C.L.(2012).A reassessment of Asian pacific excellence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n:the Taiwan experience. Scientometrics 92(1)April 2012.
[10] Kakuchi S.(2015).Restrictions on collaboration are hinder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World News 349 9 January 2015.
[11] Kakuchi S.(2014).Not just international but“Super Global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World News 344 21 November 2014.
[12] Kehm B.(2006).The German“Initiative for Excellence”and the Issue of Ranking.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44 Summer 2006.
[13] Li J.(2015).Communist Party orders Marxism course for universit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January 2015.
[14] MacGregor K.(2013).Concerns growing over“gaming”in university rankings. University World News 227 23 June 2013.
[15] Mitchell N.(2015).Excellence schemes“should be risking-taking”:EUA. University World News 349 9 January 2015.
[16] OECD(2014). Promoting Research Excellence:New Approaches to Funding .Paris:OECD.
[17] O'Malley B.(2015).Minister blasts patchy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University World News 381 9 September 2015.
[18] Qureshi Y.(2007).400 university jobs could go.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March 9.Retrieved May 20 2007 from http://www.manchestereveningnews.co.uk/news/education/s/1001/1001469_400_university_jobs_could_go.html.
[19] Ruish Q.(2014).Universities get more autonomy. Global Times 10 October 2014.
[20] Salmi J.(2015).Tertiary Education in Finland: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Retrieved Mat 20 2007 from http://www.minedu.fi/export/sites/default/OPM/Tapahtumakalenteri/2014/12/Kk_johdon_seminaari_liitteet/Jamil_Salmi_Report_Tertiary_Education_in_Finland.pdf.
[21] Salmi J.(2012).The vintage handicap:Can a young university achieve world-class statu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London:May 2012.
[22] Salmi J.(2009).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23] Salmi J. & Saroyan A.(2007).League tables as policy instruments:Uses and misuses.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19(2).OECD Paris.
[24] Schmidt B.(2012).Don't just throw more money at education to boost productivity. The Australian 18 September 2012.
[25] Tarrach R.Egron-Polack E.de Maret P.Rapp J-M. & Salmi J.(2011).Daring to reach high:stronguniversitiesfortomorrow's Spai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Experts EU2015 .Madrid:September 2011.
[26] Vorotnikov E.(2015).Government plans to cut 10%off university funding. University World News 355 20 February 2015.
[27] World Bank(2002). Constructing Knowledge Societies:New Challeng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28] World Bank(1999). The 1998 / 9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29] Yeung L.(2015).Fear of erosion of academic freedom. University World News 357 6 March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