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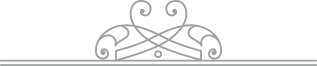
林达
1995年年底,我带着“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稿《历史深处的忧虑》回国,其实当时连书名都还没有。
书稿内容基于我作为平民在美国的体验,讲述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向中国朋友介绍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权利”概念,更强调美国民众为此在不同时代怎样支付不同代价。我还记得,作为一个普通新移民,写作有很放松的一面,同时,在国内的经历又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背景,致使写作中也常常出现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用轻松笔调让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许已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会有如此心情。今天回头去看,这不是“个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国一段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我们成长的年代,适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一度完全挤压了个人空间,这类话题也就长期成为禁区。1976年“文革”结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府权力的合理退让和个人对自由开放的急切要求还不同步,形成了社会的焦点之一。虽然这本书不是对个人自由的盲目呼唤,而是在介绍个人权利理念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些命题中蕴含的社会两难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同时,社会和民众也被迫在“安全”与“自由”的冲突中不断权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难题。这一点,在今天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期之后,又有了新的含义。可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国社会还在一个门槛上,这样的话题虽不再是绝对禁区,却仍然敏感。对于作者来说,历史甚至现实的负担也都还在。所以,当时的写作心情,其实也在无形中预示寻求出版的困难。
那年回到上海,先把稿子寄给了在北京的朋友郭大平,他把稿子转给他的朋友郑也夫,还记得他说,“也夫的眼睛比较毒”。接下来,郑也夫热心表示愿意帮助推荐出版。于是,1996年年初我带着书稿来到北京。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郑也夫帮助推荐了路数不同的各家出版社,也包括私营书商的先驱者。几乎所有出版社对书稿本身的反应都是正面的,却也都明确表示,因书的主题敏感,不能出。记得有一个总编刚开始看,就立即否定了出版的可能,却不肯马上归还书稿,说是自己喜欢,一定要看完了再还。出现的最大可能,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已经接下稿子,提出出版条件,一是要删改,二是给样书不给稿费。我们都答应了。接下来,编辑小心翼翼做了大量工作,删去他估计可能触电的字句,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内容。返回来的稿子五花六花,看得出编辑的全部苦心和好意。可是,删节稿还是被总编无奈地否决了。期间,周孝正说,我替你向也夫求个序吧。记得是一起吃着小饭铺,孝正开了口,也夫只是回了一句:“我觉着这本书要出事儿。”结果,临出版前应出版社要求,我自己匆匆忙忙补了个序,也因为这句话,当时帮过忙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敢在书中表示感谢。那是后话了。
郭大平、郎可华夫妇,周孝正,郑也夫,梁平,史铁生、陈希米夫妇,都帮了很多忙。当时没有找三联书店,也夫的意见是,这样敏感的稿子怕“显眼”,找个“不惹眼”的出版社,还可能“塞出去”。结果,铜墙铁壁,怎么也塞不出去。我不能无休止地在北京待下去,临走,留下一份稿子给周孝正,托他有机会再给别家试试。然后我就回了上海。临行,郑也夫给了一个朱学勤的地址和电话。说这是他的朋友,可以试试请他帮忙。
说实话我不知道谁是朱学勤。我先打电话约了时间,把郑也夫的名字推在前面。朱学勤家当时还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一个简陋的宿舍楼。为有事相求而敲开一个陌生人的门,本身就是件尴尬事情,好在朱学勤受朋友之托很是热情,不问三七二十一抓起电话就打给上海的一家文学出版社。我急着拦住他,请他先了解一下书稿内容再说。事后他说,当时他估计一定又是一本“闯荡曼哈顿”的故事。我简单介绍之后,朱学勤的脸色才从客气的热情转到真正的兴趣:他看重“形而中”,而这本书稿正是介绍制度层面的东西。书稿在讲些浅显好听的故事,也就面对大众。这种方式其实是跟美国人学来的。这次,朱学勤认真了,要先留下书稿读一读。
几天后,收到朱学勤电话,说是他把稿子推荐给了三联书店。绕了这么一大圈,才提到主题,是想说,三联书店确有它和别家不同、十分特别的地方。朱学勤是认真的,他先给编辑吴彬打了电话,又把稿子直接寄了过去,吴彬对书稿持肯定意见,又转给了总经理董秀玉。总经理还是拍板的关键,为最后落实,朱学勤又直接打电话给董秀玉,催问对书稿究竟如何定夺。朱学勤告诉我说,总经理董秀玉在电话中问他,你对书的判断怎么样?听完朱学勤的介绍和推荐,她马上回答,三联愿意出这本书。我听了想,这种行事风格,好像有点“旧社会”。
我回美后不久,适逢朱学勤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家玩。那是1996年5月,问他三联那里怎么样了。他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我老住宅破破的小房间里,立即给三联编辑吴彬打了个电话。回答是:通过了。朱学勤这才松口气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原来在打电话前,他其实并没有把握,原因是不久前,三联又来了一位新领导,谁也不了解他,谁也不敢保证能通过。现在编辑说:他签字了。唯一的要求是,这本书不要宣传。朱学勤加了一句,也是好人啊。
出书前还有一个周折:这本书的第一个书名是《自由与代价》,希望能够一目了然地点出书的内容。
在个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对自由的呼唤往往是文学性的,充满了浪漫抒情甚至热血膨胀的激情表达,自由仅仅呈现它感性的一面,如裴多菲笔下生命、爱情的理想续篇。这也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中国时,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及社会大众诠释自由的基本层面。若要再往前回顾,这条线索可以一直牵到中国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开端处。而我在这本书里,想介绍的自由概念是冷静的,可以陈述和理性讨论、可以现实规范的。个人自由不仅是具体的,也是仰仗他人和社会支付代价而得以维护的,这些代价同样是具体的。因此,美国的自由是由无数案例作为支撑的,是对个人行为、政府行为的司法界定。而所谓案例,又是触及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鲜活故事。同样的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可能引出对司法规范新的挑战和突破。每当遭遇新的历史条件,而社会可能一时无力支付新的代价时,某些个人权利就难以得到历史上同样程度的维护,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痛苦挣扎的困境。美国正是由于对历史标杆性案例的判定和由此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才使得社会从困境中逐步成熟。没有“代价”的同时引入,仅仅引入浪漫概念的自由是极为脆弱和不完整的。
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书名出现“自由”二字是出版社需要再三斟酌的事情。考虑再三,编辑还是决定不采用《自由与代价》的书名,结果书名就改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后来不少读者反映说书名有点不知所云,这不是有意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书名的“自由”不存,“代价”也只好随之而去。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7年,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介绍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儿童画作的书,此刻编辑吴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为书起名为《像自由一样美丽》——中国的社会进步真是非常具体。只是,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自由呼吁仍然非常容易流于感性表层,而能够对“自由和代价”作透彻的社会思考、扎扎实实在司法层面落实,还是相当欠缺的一块。前路漫漫,需要努力的道路依然漫长。
通过审批后又等了一年。1997年5月,这本书悄悄地出版。编辑吴彬保持了稿子的原貌,基本没有什么删改。我们后来长久合作,吴彬习惯并不多说什么,然而专业、自有定力,假如提出意见,总在点子上。
大家都看到了,那本书出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个坎儿迈过,大家松了一口气。下一本《总统是靠不住的》已经出得非常轻松。出版界在这一言论层次上的困扰也在无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联书店。
这书“要出事儿”,几乎是1996年初所有退回书稿的出版社总编的判断,话说得更悬的都有。这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环境。回头想想,这种紧张形成的心理压力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有话憋着不让说,就憋得血压高,憋出一口高压锅来。到一定程度,就算想开盖也不敢开了。其实,让一个原本紧张的社会逐渐松弛下来,是可能做到的。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共同的智慧和勇气。现在的新一代无法想象我讲述的当年故事,其实也就是刚过了十来年。
迄今为止,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好多本书了,现在这些书放到哪里也都可以出,不会有问题。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在1996年的那个门槛上,三联书店显得如此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