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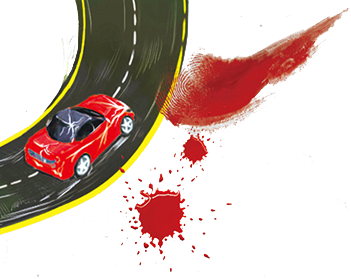
简将一块打了补丁的白布铺在埃利斯那张小桌上,然后摆了两组略有磨损的餐具。她在洗碗池下方的橱柜里找到一瓶弗勒利葡萄酒,本想马上尝尝,然而还是决定等埃利斯回来再说。她摆出酒杯、餐桌盐、胡椒粉、芥末和餐巾纸,想着要不要做饭。不,还是等埃利斯回来做吧。
她并不喜欢埃利斯房间的陈设。屋里空荡荡的,又窄又没个性。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简吓了一跳。一直以来,她跟这个温柔活泼的成熟男人约会,还以为他住在一个能彰显他个性的地方——一间美观、舒适的公寓,有着各式讲述他丰富阅历的纪念品。然而你不会想到,住在这儿的男人居然结过婚、打过仗、吸过毒,还当过学校的橄榄球队队长。冰冷的白色墙面胡乱贴了几张海报。瓷器是旧货店淘的,炊具也是便宜洋铁铺买的。书架上的平装本诗集里没有题字,牛仔裤和汗衫就放在吱嘎作响的床下一个塑料箱里。他的成绩单在哪儿?侄男外女的相片在哪儿?他珍藏的那本《伤心旅馆》又在哪儿?还有从布隆或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带回的纪念小刀,像所有人一样迟早会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柚木色拉碗,这些东西都在哪里?这里看不到几件别具意义的物品,也没有一件东西是因其意义而非其功用而存在,整个房间看不到他的灵魂。
房间的主人显然孤僻而神秘,从不与他人分享内心的想法。一股强烈的伤感涌上心头,简渐渐意识到,埃利斯就是这样的人,跟他的房间一样,冷漠而神秘。
真是不可思议。他是那么自信,走路的时候昂首挺胸,仿佛从未惧怕过任何人。在床上他狂放不羁,能够自如地将欲望宣泄。他毫无顾忌,说话办事不会有丝毫紧张、犹豫或羞怯。简从没见过这样的人。然而,已经有太多次——在床上、在餐馆,或是走在街上,当自己与他一同欢笑,倾听他讲话,观察他沉思时眼角泛起的皱纹,或者是拥抱他温暖的身体时,却发现埃利斯已温存不再。此时的他变得不再充满怜爱、不再风趣,既不体贴也没有风度,更没有同情心。他让简感觉被排除在外,像一个陌路人,一个闯入他内心世界的入侵者。那种心情真如乌云遮日一般。
简非常清楚,自己不得不离开埃利斯。她疯狂地爱着这个男人,而对方却似乎无法给自己相同的回应。他已经三十三岁了,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如何与人亲密交往,那他可能永远都学不会了。她坐在沙发上开始读《观察家报》,那是在来这里的路上从拉斯帕伊大道的一处国际报刊亭购买的。头版是一条来自阿富汗的报道。去那里忘掉埃利斯,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她立刻喜欢上了这个主意。虽然她热爱巴黎,她的工作也很多姿多彩,但她想要的还很多:阅历,冒险,以及为自由奋力一搏的机会。她并不畏惧。让-皮埃尔说医生被认为太宝贵,不应该送到战区去。在那里,得冒着被散弹击中或是陷入交火区的危险,不过这与在巴黎被一辆摩托撞倒的概率也差不了多少。她对阿富汗反抗军的生活充满好奇。“他们吃什么?”她问让-皮埃尔,“他们穿什么?住帐篷吗?有冲水马桶吗?”
“没有马桶。”他答道,“那里没有电源,没有公路,没有红酒、轿车、中央供暖、牙医、邮差、电话、餐馆、广告、可口可乐、天气预报、股市行情、室内装潢师、社工、口红、卫生棉条、时尚、晚宴派对、出租车,全都没有,更没有公交排队……”
“行了!”简打断他:他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几个钟头。“公交和出租车总是有的吧。”
“农村没有。我要去的地区叫作‘五狮谷’,位于喜马拉雅的丘陵地带,是反抗军占领的一处要塞。即使是被苏联人轰炸前,那里也十分落后。”
简十分确定,没有抽水马桶、口红或者天气预报,她也可以过得很好。她怀疑即使是在战区之外,让-皮埃尔也低估了阿富汗的危险;然而这并未使她却步。她妈妈当然会气得发疯;而她父亲——如果他还活着,则一定会说:“祝你好运,杰妮
 。”他懂得在有生之年做些有意义的事是何等重要。虽然他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却没赚过多少钱,因为无论他们在何处生活——拿索、开罗、新加坡,最长是在罗德岛——他总是免费为穷人诊治,大家纷纷来找他,花得起钱看病的反而被吓跑了。
。”他懂得在有生之年做些有意义的事是何等重要。虽然他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却没赚过多少钱,因为无论他们在何处生活——拿索、开罗、新加坡,最长是在罗德岛——他总是免费为穷人诊治,大家纷纷来找他,花得起钱看病的反而被吓跑了。
阶前的一个足球打断了她的遐思。她发现自己根本没读进几行字。她支棱起脑袋仔细倾听着。似乎不是埃利斯的脚步声。不过确实有人敲门。
简放下报纸把门打开。门口站着让-皮埃尔。他跟她一样意外。沉默中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简问:“你一脸内疚。我也是吗?”
“没错。”他说着咧嘴笑笑。
“刚才还想到你呢。请进。”
他走进屋里,四下张望着:“埃利斯不在?”
“我在等他,应该快回来了。坐吧。”
让-皮埃尔修长的身体坐在沙发上。简不止一次在想,让-皮埃尔也许是她见过最美的男子。他脸形匀称,堪称完美,高高的前额,鼻子坚挺,凸显出高贵,一双水汪汪的棕色眼睛,丰满的嘴唇隐约藏在茂盛的深棕泛褐色的胡须之下。他的衣服算不得高档,但都经过精心挑选,而且都在不经意间被他诠释得十分优雅,这一点让简十分羡慕。
简很喜欢他。他最大的缺点是自恃过高。不过在这方面他倒也十分天真,像个喜欢夸耀的孩子,让人生不起气来。她欣赏让-皮埃尔的理想主义,以及他为医学事业的奉献。他魅力四射,而且有着疯狂的想象力,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滑稽:受到什么荒唐事的启发——也许仅仅是说漏了嘴,他也会有滋有味地自问自答,有时甚至可以持续十几分钟。若是有人引述萨特对足球的看法,让-皮埃尔便会立刻化身存在主义哲学评论员,现场解说一场足球比赛,逗得简直不起腰。人们说,在绝望之时,让-皮埃尔也会倒向另一个极端,然而简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一面。
“来尝尝埃利斯的酒。”简说着拿起桌上的酒瓶。
“不了,谢谢。”
“怎么,你已经开始预习如何在伊斯兰国家生活了?”
“那倒不是。”
他看上去神色凝重。“怎么了?”简问。
“我得跟你好好谈谈。”他说道。
“三天前已经谈过了,还记得吗?”简说得毫不客气,“你让我离开男朋友,跟你一起去阿富汗——恐怕很少会有女孩子能够拒绝。”
“我说正经的呢。”
“好吧,我还没想好。”
“简,我发现了埃利斯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简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要说什么?要编个故事,说个谎话,好说服自己跟他走吗?应该不是。
“好吧,是什么?”
“你看到的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他看起来完全是在危言耸听。“别搞得像个殡仪执事一样,你到底什么意思?”
“他不是个身无分文的诗人。他为美国政府卖命。”
简皱起眉头。“为美国政府卖命?”她的第一反应是让-皮埃尔颠倒了始末,“他教一些法国人说英文,那些学生中有人在为美国政府工作。”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一直在监视激进团体。埃利斯是个特工,为中情局工作。”
简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也太离谱了!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离开他吗?”
“是真的,简。”
“不可能。埃利斯不可能是间谍。难道我会不知道吗?我们两个基本上一起生活,已经一年了!”
“但并不是真正一起生活,对吧?”
“那也没什么分别。我了解他。”话一出口,简不禁想:这样一来,很多事就说得通了。她并非真正了解埃利斯,但至少可以确定,他不是个卑鄙下流的坏蛋。
“全城都传开了。”让-皮埃尔道,“拉赫米·乔斯贡今早被捕,大家都说这是埃利斯的错。”
“拉赫米为什么会被抓?”
让-皮埃尔耸耸肩:“肯定是因为颠覆政权。总之,拉乌尔·克莱蒙特满城找他,有人要找他报仇。”
“哦,让-皮埃尔,这太可笑了。”简说。她忽然觉得浑身发热,说着走过去将窗子打开。朝街上一看,埃利斯的一头金发刚刚闪进前门。“喏,”她对让-皮埃尔说,“他回来了。你得把刚刚讲过的荒唐事再给他重复一遍。”说着,她听到楼梯上响起了埃利斯的脚步声。
大门打开,埃利斯走了进去。
他看起来兴高采烈,仿佛带回来的尽是好消息。看着那张圆润的笑脸,还有那受了伤的鼻子和摄人心魄的蓝眼睛,简的心中立即泛起一阵内疚——之前她还在跟让-皮埃尔调情。
埃利斯在门口停住脚步,看到让-皮埃尔也在这里,多少有些意外。他的笑容有所收敛:“你们好。”他说着将身后的门锁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简一直觉得这么做很古怪,但现在看来完全像是间谍的作风。她努力不去想那些。
让-皮埃尔率先开口:“他们盯上你了,埃利斯。你已经暴露,他们在追杀你。”
简看看他们两个。让-皮埃尔比埃利斯高,但埃利斯肩膀宽阔,胸前也很结实。两人盯着彼此,活像两只彼此打量的猫。
简伸出双臂抱住埃利斯,内疚地吻了吻他,说道:“让-皮埃尔讲了个极其荒谬的故事,说你是中情局的间谍。”
让-皮埃尔将身子探出窗外,扫视楼下的街面,然后转回身面对埃利斯:“告诉她吧。”
“你哪来的这种想法?”埃利斯问他。
“全城都传开了。”
“那你究竟是从谁那听来的?”埃利斯生硬地道。
“拉乌尔·克莱蒙特。”
埃利斯点点头,用英语说道:“简,坐下来好吗?”
“我不想坐下。”她生气地说。
“我有话对你说。”他道。
这不会是真的,不可能。简心中一阵恐慌,直逼咽喉。“那就说吧,”她说,“别总是让我坐下!”
埃利斯瞟了一眼让-皮埃尔,用法语问道:“可否回避一下?”
简开始感到生气:“你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说让-皮埃尔是错的?告诉我,埃利斯,说你不是间谍,我快要疯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埃利斯说。
“简单得很!”她再也无法抑制声音里的情绪,“他说你是个间谍,说你为美国政府卖命;还说自我们认识起,你便一直无耻地对我说谎,背叛我。是真的吗?说啊!”
埃利斯叹了口气:“我想是真的。”
简感到自己就快要炸开了。“你这个浑蛋!”她叫道,“你这个该死的浑蛋!”
埃利斯的表情凝固着,如同石头一般。“我本想今天告诉你的。”
敲门声响起,两人都没有理会。“你一直监视着我,还有我的朋友们!”简大喊道,“我真是惭愧!”
“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埃利斯说,“再也不用对你撒谎了。”
“你也没机会撒谎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敲门声再次响起,让-皮埃尔用法语道:“门外有人。”
埃利斯说:“不想见我,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还是不明白吗?你的所作所为,对我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她道。
让-皮埃尔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把那该死的门打开!”
简喃喃道:“上帝啊。”说着朝门口走去,将门打开。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男人,身着一件绿色灯芯绒夹克,袖子上还有一道口子。简从未见过他。她问道:“你究竟有什么事?”紧接着她看到,对方手里有支枪。
接下来的几秒钟似乎过得异常之慢。
一瞬间简意识到,如果真被让-皮埃尔说中,埃利斯是个间谍的话,那很可能正如他所说,有人想找埃利斯报仇。而在埃利斯那个不为人知的间谍世界中,“报仇”很可能意味着带枪的杀手来砸门。
她张开嘴巴,仿佛要尖叫出声。
陌生男人迟疑了片刻。他看起来有些意外,似乎没预料到开门的是个女人。他看看简,再看看让-皮埃尔,目光又回到简身上:他清楚,让-皮埃尔不是他的目标。但他还是有些疑惑,因为埃利斯不在场。而此时,埃利斯正躲在半开半掩的门边。
简没有尖叫,她用力想将门关上。
就在她将门用力甩向持枪男人之时,对方也看出了她的用意,并伸出一只脚把门缝卡住。门打在他的鞋上,弹了回去。然而在向前迈步时,他不得已伸展双臂以保持平衡。现在,他的枪指着天花板的一角。
他想杀埃利斯,简意识到。他想杀埃利斯。
她一下子扑到枪手身上,举起拳头猛击对方面部。猛然间,即使她恨埃利斯,也不希望他没命。
不到一秒的时间,杀手便回过神来。他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把简甩在一旁。她重重地坐在地上,脊椎的下端一片淤青。
她清楚地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那只将她甩开的胳膊再次来袭,将门大大地甩开。他挥舞着持枪的那条手臂,埃利斯高高地擎着一只酒瓶冲向他。瓶子落下的一瞬间,子弹射出。瓶子的碎裂声与枪声同时响起。
简满脸惊恐地盯着两个男人。
枪手倒地,埃利斯依然站着。她这才意识到,子弹打偏了。
埃利斯弯下腰,从陌生男子手里把枪拿走。
简吃力地站起身。
“你没事吧?”埃利斯问。
“还没死。”她说。
他转头问让-皮埃尔:“街上还有几个?”
让-皮埃尔朝窗外扫了一眼:“街上没人。”
埃利斯一脸诧异:“他们肯定藏起来了。”他把枪装进口袋,走向书架,“退后。”说着他把书架扳倒在地。
书架后是一扇暗门。
他许久看着简,仿佛有话要说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紧接着,他跨入门中,不见了踪影。
过了一会儿,简徐徐来到暗门前,朝里看了看。里面还有另一个套间,没什么家具,而且落满灰尘,仿佛已经一年没有人住过。一扇门大敞着,门外是一段楼梯。
她回头看看埃利斯的房间。枪手倒在地上,身下是一摊红酒。就在这间屋里,他想杀埃利斯:一切都变得如此不真实。一切都是那样不真实:埃利斯是间谍,而让-皮埃尔也知道;拉赫米被捕;埃利斯家有一条逃生通道……
他走了。就在几秒钟前,她还对他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看来愿望实现了。
她听到楼梯上响起脚步声。
她将目光从枪手身上移开,看了看让-皮埃尔。他也是一脸震惊。过了一会儿,他穿过房间向她走来,伸出双臂将她抱住。她倒在他的肩膀上,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