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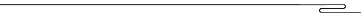
旅行时你会察觉到,世界各地的人的问题虽然看似不同,实则无太大的差异。四处都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与否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一些,这样人们才能活得安宁、有修养,不至于经常和自己或邻人产生冲突。除此之外,整个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贫穷、饥饿以及彻底的绝望。美国与西欧面临的却是经济繁荣带来的问题,经济繁荣但缺乏素朴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目前西方社会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奢华享受,已经到达彻底腐败和不道德的程度了。
此外还有组织化的宗教——世界各地的人多多少少都在排斥它——所造成的问题,以及什么是宗教精神、什么是冥想等等——这些都不是亚洲独有的问题。然而讲者本身并不代表任何思想体系——印度的或其他区域的,因为讲者并不是专家学者,只要我们能共同探索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不过切记语言并非事物本身,无论我们阐述得多么仔细,多么错综复杂,多么合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
由印度教、回教、基督教等所造成的思想分裂,已经为世界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而且制造了这么多的仇恨与对立。一切宗教或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都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观念罢了,但不幸却造成了人类的分裂。
这些意识形态带来了诸多的战争,虽然人们在宗教信仰上还算是有某种程度的宽容性,可是一旦超越了某个界线,接下来的就是毁灭、偏狭、残忍与暴力——宗教战争。意识形态也同样带来了国家、民族的分裂,譬如黑人的国家主义以及各部落之间的战役。
我们人类真有可能和平地、自由地、正直地共处于世上吗?自由绝对是必要的,但不是为所欲为式的自由,因为个人永远是受到制约的,不论他住在印度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他永远都受到他的社会、文化以及他整个思想结构的制约。那么,人有没有可能从这些制约中彻底解脱出来,不只是意识形态或观念上的解脱,也包括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否则我根本看不到民主的可能性,也看不到展现正确行为的可能性。甚至连“正确行为”这样的说法都遭到了藐视,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能运用这些词汇而不至于造成讥讽的效果。
自由不是一种概念,有关自由的哲学并不是自由本身。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自由了,就是依旧不自由。身处牢狱中的人,不论这牢狱点缀得多美,仍然是不自由的。自由并不是一种陷入思维中的状态。思想不可能是自由的。思想乃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而且不可能带来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在活生生的当下、在日常生活里才会出现。自由不是从某个东西之中解脱出来。从某个东西之中解脱出来,只不过是一种反应罢了。
人类为什么会赋予思想这么高的重要性?思想往往会形成概念,然后人就按照这些概念而活。形成一些意识形态,臣服于这些意识形态,乃是世上显而易见的事。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便是其中一例。再如宗教组织,包括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的新教等等,两千年来都在通过宣传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不断地经由威胁及承诺驱使人臣服其下。你可以在世界各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你会发现人类一向赋予思想过高的意义及重要性。愈是学有专精,智力愈是高超,就越重视思想。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思想真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吗?
世界各地都有暴力问题,不单是巴黎、罗马、伦敦、哥伦比亚,此地以及其他各地也都出现了学生抗争,而且黑人与白人、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也越来越彼此仇视。人心之中不知怀着多少的残忍与暴力,虽然外表上看来很有学养,反应有节制,口里不时祈求着和平的降临。这份暴力,就是宗教派别、政治及种族界分造成的结果。
这份深埋于人心深处的暴力,可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及转化,好让人们活在和平的氛围里?人心深处的暴力显然是从动物性及社会承继而来的。人类已经把战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了,虽然各地偶尔有一些反战论者持着标语反对战争,但总有一些人是爱好打仗的!或许有人不赞成打越战,不过他们还可能为了别的议题而抗争,引起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因此,人类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争战,也就是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
人类的显意识及潜意识里的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接着我们又要问了:人类有没有可能在适应教育、接受社会规范及文化熏陶之下,同时产生心理上的真实革命?
心理上的革命有可能立即出现吗?不是在未来,也不是渐进式的,因为房子已经失火了,你不可能慢条斯理地谈论着如何救火的问题:你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时间本来只是一种幻觉罢了。因此,什么能真的令人类改变?什么东西能够让身为人类的你我真的改变?难道必须依赖奖赏与惩罚吗?这些方法早就试过了。地狱的惩罚、进天堂的承诺等等,这些方法都用过了,但人类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仍然善妒、贪婪、暴戾、迷信、充满着恐惧。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透过理性分析来了解人为什么会如此暴戾、恐惧、贪婪、好斗、野心勃勃——分析是一种很容易的方式——难道就能带来改变吗?很显然不能。那么到底什么方式才能带来立即而非渐进式的心理革命?对我而言,这似乎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
分析——专家学者的分析或反省式的分析——并不能带来解答。分析一向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大量的洞见,你的分析一旦出了错,接下来的分析就会跟着出错。如果你的分析得到了某种结论,而你立即从这个结论往下推演,那么你也受到了阻碍。此外,在分析之中还有“分析者”与“被分析之物”的对立问题。
若是不透过动机分析或对肇因的探究,我们要如何才能带来心理上的彻底革命呢?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自己愤怒的原因,但这并不能制止你的愤怒。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战争的起因,包括经济上的、国家的、民族的、宗教上的议题,或是政治人物的颜面问题、意识形态等等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在互相残杀。五千年来已经出现过一万五千场重大的战争——我们到现在仍然没有爱,没有慈悲。
一旦洞察到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分析者与被分析之物”、“观者与被观之物”、“思想者与其思想”之间的界分是否真实的问题。不是理论上而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吗?这个“观者”——这个让你产生“看与听”的存在中心——是否只是一个把自己与被观之物分开来的概念性存有而已?如果你说你在生气,那么这股怒气与那个知道自己正在生气的存有,是不是真的有区别?那股暴力不就是观者的一部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试着去了解它。我们若是关心当下立即产生心理上的革命——不是未来才产生一些变化——这个议题,就必须试着去了解问题的核心:这个所谓的“观者”、“我”、“自我”、“思想者”或“经验者”,与被观之物、经验或思想真的有差别吗?当你在看着一棵树,观察一只飞鸟,欣赏水面上的月光时,那个“经验者”真的有别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吗?当我们在看一棵树时,我们是真的在看它吗?请再随着我探究一下。我们可曾直接地看过一棵树,还是只透过知识组成的意象或过去的经验在看它?你可能会说“是的,我知道它的颜色有多美,形状有多么好看”,但你只是在通过记忆、通过以往对它的感觉,再次享受起那份快感罢了。你可曾观察过那“观者”与“被观之物”的差异?除非你曾深入于这个议题,否则接下来要谈的事很可能被你疏忽掉。其实只要“观者”与“被观之物”是分开来的,冲突就一定会出现。只要心中一产生对去年秋色的回忆、认知及意象,“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界分及冲突就出现了。制造出这种界分的正是思想本身,假如你看着你的邻居、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男友或女友,不论眼前是谁,这时你能不能不带任何意象或过往的记忆,直接看着这个人?因为如果带着某种意象去看此人,你们的关系就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两组意象所形成的间接关系,只有概念性的关系,而没有真实的关系。
我们都住在概念世界里,住在一个由思想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总试图借着思想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从最机械化的到最深层的心理问题。
如果“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确有区别,那么这种区别就是人类冲突的源头。当你说你爱某人时,那种感觉真的是爱吗?其中必定有“观者”与“被观的对象”之间的界分?这种“爱”本是思想的产物,一定会造成界分的概念,因此并不是真正的爱。
思想是不是我们用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唯一手段?或许是的,我们正在质疑这件事,我们并没有立刻下结论。也许除了机械性的、技术性的或科学性的问题之外,思想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当“观者”即是“被观之物”时,冲突就停止了。这种情境很容易发生,而且很平常;每当重大危机出现时,“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界分就不见了,这时行动会立即产生。假如一个人的生活里出现了重大危机——我们总是在逃避危机——他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之下,脑子里虽然还有许多老旧的记忆,故而无法立即做反应,但行动已经产生了。这时心理上已经出现了立即的革命,也就是“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界分不见了。换句话说,我们一向活在过往的历史里,所有的知识都属于过去的历史,人终其一生都活在过去,活在已经发生过的事物里面——从其中再产生出“过去的我是什么”,以及“我将来应该怎么样”等等的想法。人生基本上就是奠基于昨日的种种,而“昨日的种种”只会使我们变得无感,剥夺掉我们本有的天真与易感性。因此,“昨日的种种”便是那“观者”本身,“观者”的心中充斥着一层又一层显意识及无意识的记忆。
全人类都存在于我们的显意识及深层的无意识里。每个人都是数千年的演化成果。这些记录,人类所有的历史、所有的知识及过往的一切,全都深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你能深入地探究,就会发现它们,因此自我认识才会变得那么重要。“自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手货,我们不断地重复别人的话语,不论是弗洛伊德或任何一个专家的见解。如果你真想认识自己,绝不能借着专家的眼睛来看自己,你必须直截了当地观察自己。
你如何能在不成为“观者”的情况下来认识自己呢?你所谓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并不是在说双关语。我是在质疑我们所谓的“认识”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的在认识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说我“认识”梵文,我“认识”拉丁文,我“了解”我的妻子或丈夫。我们可以学着去认识一种语言,但我真的了解我的妻子或丈夫吗?当我说我了解我的妻子时,我会不会立即产生一个有关她的意象:这个意象永远属于过往的历史,这个意象会阻碍我对她的观察——她目前可能已经有所改变了。因此我真能说我“了解”吗?当你问道“我能不能在不形成观者的情况下来认识自己”,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这是十分复杂的一件事:我学着认识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累积了许多有关自己的知识,亦即过往的一切,然后我又继续累积对自己的认识。我经由这些累积的知识来观察自己,并试图对自己产生一些认识。这个做法行得通吗?显然是行不通的。
观察自己与认识自己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观察是一种不间断或不累积的过程,“自我”则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东西,它总是有新的想法、新的感觉、新的变动、新的暗示、新的迹象。观察并不是与未来或过去相关的一种状态,我不能说我已经观察到了,或是我将要观察。因为心永远处在一种不断观察的状态里,它永远活在当下,永远是新鲜的,它不被累积下来的知识败坏。如果你深深地探索下去,就会发现存在的只有不间断的观察而非知识的累积,然后心就会变得异常警醒、敏锐,因此我永远无法说我“认识”自己,任何一个人如果说“我认识”,显然就还不认识什么。观察乃是一种活跃而不间断的过程,它跟已经有所认识是无关的。我“认识”为的是在已经学会的东西上再添加一些东西,但若想观察自己,就必须拥有观察的自由,可是如果经由过去的知识来进行观察,自由就被否定了。
提问者(以下简称“问”):为什么“观者”与“被观之物”的界分会导致冲突?
克里希那穆提(以下简称“克”):是谁在付出努力?只要有努力,只要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因此,在“观者”与“被观之物”之间,难道没有对立性吗?这并不是一种意见上的狡辩,你自己去观察一下就知道了。假如我说“这是我的”,那么不论那是财物、性、权力或工作,都会出现因界分而造成的抗拒,如此一来就起了冲突。当我说“我是印度教徒”、“我是婆罗门”或这个那个时,我已经在自己的周围建构了一个世界,一个我认同的世界,于是界分就产生了。很显然,当一个人说他是天主教徒时,他已经把自己和非天主教徒做了区分。所有的区分,不论是内心的或外在的,都是在助长敌意。现在问题又出现了,我能不能既拥有一些东西,又不会制造敌对、矛盾或冲突?还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次元,可以完全消弭掉“所有权”这个东西,达到真正的自由之境?
问:我们有可能不带着任何概念而行动吗?你有可能进到这间房子里,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而不带有任何对这把椅子的概念吗?你似乎在暗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概念?
克:也许我没有解释得很仔细。人当然得有概念,譬如我问你住在哪里,你一定会回答我,除非你有健忘症。“告诉我”这件事,就是源自于概念或记忆,而人必须有记忆和概念。不过概念也会助长意识形态,带来灾害——你是美国人、我是印度人等等。你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我信奉一种意识形态,这都只是一些概念罢了,但我们竟然会因此而相互残杀。即便是在同一间实验室里研究科学的伙伴,也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在人类的关系之中,概念到底有没有任何地位?这又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所有的反应皆是概念,所有的反应也就是:我有一种想法,然后我依照这个想法去行动。首先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一个公式或基准,然后就按照它来采取行动。因此,在概念、想法与行动之间,一定存有界分。处在概念这一边的是“观者”,行动则是在观者之外的另一种东西,于是界分与冲突就因此而形成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受限的、从社会背景里产生的心智,是否能摆脱掉概念思考,以不机械化的方式行动?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我说有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这就是冥想:探索心智有没有可能完全安静下来,从所有的概念思考中解脱出来,只有在需要用它的时候才产生思想。我现在是在用英文说话,这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但是你能不能彻底安静地听我说话,心中没有任何念头?你一旦“试图”去达到这种状态,思想就出现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看着一棵大树或麦克风时,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念头指的就是思想或概念。看着一棵大树而没有任何思想,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可是看着一个朋友,一个伤害过你、奉承过你的人,而不带着任何成见,就很难做到了,这意味着你的脑子是安静的。虽然它也会有反应,迅捷的反应,不过仍然可以安静到完整而彻底地看着跟前这个人。只有处在这种状态,你才会对他产生真正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完善的行动。
问:是的,我想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
克:很好,不过你真的必须实践才行。人必须认识自己,但接着又会产生“观者”与“被观之物”、“分析者”与“被分析的对象”之间的界分问题。有一种观察的方式可以免除这些问题,那就是立即的了解。
问:你现在正试图用语言来解释一个语言无法传达的状态。
克:因为你我都懂得英文,所以我们才用语言来沟通,若想正确地进行沟通,你我必须同时具备热切而又专注的品质才行,否则我们是无法真的产生交流的。假如你我正在说话而你却朝着窗外观望,或者你很认真而我一点也不认真,那么这类情况都会让沟通停止。因此,传达一个你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是极为困难的事。不过有一种沟通的形式并不需要借助语言,但只有当你我都很认真、专注与直接,而且双方的心智都处在同样的层次、同样的节拍,它才会出现。那时就会形成一种非语言性的“神交”;那时我们就可以安静地对坐,但不是你的寂静或我的寂静,而是我们共同的静谧;那时或许就会出现真正的神交了。不过这种要求也许太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