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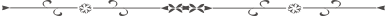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从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方面的启蒙教育。儿童入学,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也是宋以后道学(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认为最重要的文献。孩子刚学认字,通常所用的课本《三字经》,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事实上,这本书乃是中国儿童的识字课本。《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也没有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不同。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就是这样兴起的。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也都是反思的产物。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我们对宇宙进行思索或与人谈论它,都是在其中进行反思。但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和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宇宙”,内涵有所不同。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
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器官,来对思索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这是我对宗教的认识。
如果从这个意义——也就是人们通常的认识——来看待宗教,就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许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今天,许多西方人看到: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例如,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话一点不错。但是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如果追求彼岸世界不是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为什么对世界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成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如果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何以中国人成为例外呢?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在道德伦理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呢?
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可以称之为超伦理道德的价值。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有的人或许喜欢称之为宗教价值。但是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这个价值不仅限于宗教,除非宗教在这里的含义和我在上面所说的不同。举例来说,基督徒看爱神是一个宗教价值;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里,神的含义就是宇宙。严格说来,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也并不是超越道德伦理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具有位格的,因此,基督徒爱神可以比拟为儿子爱父亲,而儿子爱父亲便是一个伦理价值。因此,基督教所讲的爱神是否超越道德,便成了问题。它只是类似超道德,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爱神”才是真正超越道德的价值。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里不谈“损”和“益”的区别,我对老子这句话也并不完全同意。援引这句话是为了借此表明: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其功能不是要增长正面知识,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已有维也纳学派加以阐述。但是,维也纳学派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了另一个目的。我不同意这一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了澄清概念,把形而上学的性质看成只是概念的抒情诗;但是,从他们的论辩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宗教倒是提供有关实际的正面信息,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提供的不同。因此,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如果除宗教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则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的确应当为之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而且,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因为通过哲学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掺杂想象和迷信。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 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上面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作了一般性的论述,下面将具体地谈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主流,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了解它,我们需要首先看一下,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人是各式各样的。每一种人,都可以取得最高的成就。例如,有的人从政,在这个领域里,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样,在艺术领域里,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人可能被分为不同等级,但他们都是人。就做人来说,最高成就是什么呢?按中国哲学说,就是成圣,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问题在于,如果人追求天人合一,是否需要抛弃社会,甚至否定人生呢?
有的哲学家认为,必须如此。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有的道家认为,生命是个赘疣,是个瘤,死亡是除掉那个瘤。所有这些看法都主张人应该从被物质败坏了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的成就,必须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出世”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站在入世哲学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从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也因而过于肤浅;它诚然积极,但是像一个走错了路的人,走得越快,在歧途上就走得越远。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样的看法完全对或完全错。从表面看,这种看法不能认为就是错的,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他的来生。《论语》第十一章十一节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敢问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曾说:“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 》)这无异于说,圣人是道德完美的人。就表面看,中国哲学所说的圣人是现世中的人,这和佛家所描述的释迦牟尼或基督教所讲的圣徒,迥然异趣,特别是儒家所说的圣人,更是如此。这便是引起中国古代道家嘲笑孔子和儒家的原因。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用这种过分简单的办法是无从了解中国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有一位哲学家在谈到宋朝道学时说它:“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
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这是否要取消这种对立?但它们依然在那里,只是两极被综合起来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正是中国哲学力图解决的问题。
按中国哲学的看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他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圣人的这个成就相当于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里的圣徒。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这不是说他必须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从实际看,圣人往往不可能成为政治首脑。“内圣外王”是说,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至于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是否就成为政治领袖,那无关紧要。
按照中国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或基本原理。
听起来,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一个人怎样能成为哲学家呢?柏拉图认为,这个人必须先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长成的头脑得以转到永恒理念的世界中去。由此看来,柏拉图和中国哲学家持有同样的主张,认为哲学的使命是使人树立起内圣外王的品格。但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一种自我牺牲。中国古代的道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吕氏春秋·贵生》篇里载有一个故事讲,古代一个圣人被国人拥戴为君,圣人逃上山去,藏在一个山洞里,国人跟踪而去,用烟把圣人从山洞里熏出来,强迫他当国君。这是柏拉图思想和中国古代道家相近的一点,从中也可看出道家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到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根据中国主流哲学的传统,修改了道家思想中的这一点。
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使人培养自己以求得圣人的品格。他把处世为人看作不仅是国民的职责,而且如孟子所说,把它看为是“天民”的职责。人而成为“天民”,必须是自觉的,否则,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能具有超越道德的价值。如果他因缘际会,成为国君,他会诚意正心去做,因为这不仅是事人,也是事天。
既然哲学所探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它自然难以脱离政治。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中国各派哲学里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或逻辑,而是说,它们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了柏拉图的全部哲学,又同时就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所辩论的“白马非马”,似乎与政治毫不相干,但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公孙龙子·迹府 》)。在今日世界,政治家们个个都标榜他的国家一心追求和平,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有的一面侈谈和平,一面就在准备战争。这就是名实不符。按公孙龙的意见,这种名实不符应当纠正。的确,要改变世界,这就是需要加以改变的第一步。
既然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为主题,研究哲学就不是仅仅为了寻求哲学的知识,还要培养这样的品德。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它不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十分严肃的事情。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说:“中国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苏格拉底,因为他把伦理、哲学、反思和知识都融合在一起了。就哲学家来说,知识和品德是不可分的,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个哲学,哲学家只是载道的人而已,按照所信奉的哲学信念去生活,乃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家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生活在哲学体验之中,超越了自私和自我中心,以求与天合一。十分清楚,这种心灵的操练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将丧失。因此,从认识角度说,哲学家永远处于追求之中;从实践角度说,他永远在行动或将要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在哲学家身上就体现着‘哲学家’这个字本来含有的智慧和爱的综合。他像苏格拉底一样,不是按上下班时间来考虑哲学问题的;他也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坐在椅中,而置身于人生的边缘。对他来说,哲学不是仅供人们去认识的一套思想模式,而是哲学家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规范,甚至可以说,一个哲学家的生平,只要看他的哲学思想便可以了然了。”
●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一个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障碍,其次是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这里,先从后一个问题说起。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打开《论语》,每一小段只包含几个字,各段之间往往也没有联系。打开《老子》,全书只有约五千字,只相当于一般杂志上一篇文章的篇幅,但是老子的全部哲学都在其中了。习惯于长篇大论地进行理性论辩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些中国哲学家在说什么,由此不免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连贯。假若果真是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存在了。不相连贯的思想,怎能称得上是哲学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不一,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也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相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所述可以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内容不相连贯,但还没有说明,何以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十分简短。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如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它们仍然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即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多。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一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中国艺术的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庄子》第二十六章《外物》篇最后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这时两人不是用语言来交谈,《庄子》书中说到的两位圣人,相遇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 庄子·田子方 》)。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语言的作用不在于它的固定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去领悟道。一旦语言已经完成它的暗示的作用,就应把它忘掉,为什么还要让自己被并非必要的语言所拖累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绘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在公元三、四世纪期间,玄学(在西方称之为“新道家”)是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当时有一部书,名为《世说新语》,其中记载当时名士们的隽语韵事,所记载的名士言论,往往十分简短,有的甚至只有几个字。这部书的《文学》篇里记载,一位高官(本人也是一个哲学家)问一位哲学家,老、庄和孔子思想上的异同何在。哲学家回答道:“将无同?”这位高官对哲学家的回答很满意,立即委派他做自己的秘书。这位哲学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因此他被称为“三字掾”(“掾”是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他回答高官的问题,既无法说老、庄与孔子毫无共同之处,又无法说他们之间毫无区别。于是,他用回问的方式作为答复,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回答。
《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的简短词句,并不是本来根据某种讨论前提作出的结论,现在由于前半遗失而使它们显得无头无脑。它们是充满提示的箴言。正由于富于提示,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如果把《老子》书中提到的概念列举出来,重述一遍,可能用上五万字或五十万字,它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老子》一书的含义,但它本身将成为另一本书,而永不可能代替《老子》的原著。
在前面,我曾经提到过的郭象是《庄子》一书的著名注释家。他的注释本身就是道家的一本重要古典文献。他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论辩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书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他的论述比《庄子》一书清晰得多。但是,《庄子》原书富于提示,郭象的注释则明晰具体。人们会问,两者之中,哪个更好呢?后来一位禅宗僧人曾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 》 卷二十二 )
● 语言障碍
任何人如果不能用原文阅读某种哲学著作,要想完全理解原著,的确会有困难,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哲学著作由于它们的提示性质,语言的困难就更大。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中的种种提示,很难翻译。当它被翻译成外文时,它由提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
任何翻译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解释。当我们把《老子》书中的一句话译成英文时,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述它的含义。译文通常只能表达一种含义,而原文却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原文中的丰富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大部分丢失了。
《老子》和《论语》都有许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不免认为其他译本不够满意。但是,无论一个译本如何力求完美,它总不及原著。只有把《老子》和《论语》的所有译本,加上将来的各种新译本,才可能显示《老子》和《论语》原书的风貌。
五世纪时的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是把佛教经典译成中文的一位翻译大家。他曾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吃饭,要吃别人的唾余,所吃到嘴里的当然没有原来那饭的香味和鲜味。